午后之爱
鬼金
午后之爱
鬼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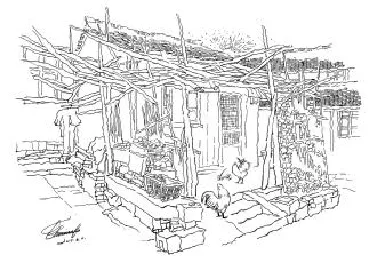
我看见窗户上的雨滴滑落,还有雨滴敲打玻璃的声音。先是缓慢的,之后变得急促起来。我躺在沙发上,扭头观看,那密密麻麻的雨滴,变成水流,在玻璃上蔓延着,像一张巨大的脸,哭泣的脸。但我想象不出五官的位置,尤其是眼睛的位置。也许,一个雨滴打在玻璃上的那一瞬间,一个痕迹就是一只眼睛。我这么想。
做完爱后,我自己冲了个澡。她没有给我洗。以前,都是她给我洗的。即使我赖皮在床上,她也会拉我起来。今天,没有。她从我的怀里挣脱后,就睡着了。可能因为剧烈的运动,让她累了。三次。一次是她在我上面。一次是我在她上面。另一次是回归动物的姿势。完事之后,她说,我动不了了。她躺在床上,侧脸对着我。眼神里还荡漾着高潮过后的喜悦。抿嘴笑着,说,我是不是老了,要受不了你了。我说,怎么会?是我老了。她笑。那笑,在脸上溢开来。那么美。我凑过去,在她光滑的脸上亲了一口。她贪婪地迎上来,用她的舌头。也许因为身体的快感还没有退去,彼此的舌头是甜的,像被蜂蜜浸过。直到舌头发麻,嘴唇肿胀。她还眼神迷离地看着我,脸上翻着潮红。我吸了支烟,在等她哀求我,给我清洗。但她转过身,睡着了。我很快听到甜蜜的鼾声。她的背影让我感觉到她的孤独。她脖颈后面的蝴蝶文身,蓝色的,还在那里。我们相识的时候,那蝴蝶文身就存在。我伸出手,想去抚摸一下,但怕惊醒她,我放弃了。我羡慕她的睡眠。近段时间,我老是失眠。尝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解决问题。安眠药。我厌恶这个“眠”字,就像我厌恶“死”。我拒绝去吃。我要醒着,是的,醒着。我倒要看看我的身体能熬到什么时候。
之前,妻子劝我去看看心理医生。我说,心理医生还不如我呢?也许我去了,心理医生到变成了我的病人。妻子就笑说,瞧你能耐的。我说,不相信吗?妻子说,相信。这么多年,我对人的洞悉是透彻的。只要被我看上一眼,我几乎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这么说,绝不危言耸听。绝不。如果说失眠是一种病的话,我喜欢这样病着。但妻子咨询了心理医生说,你可能是抑郁症。我笑说,怎么会呢?现在,像我这样的穷人,怎么会。那可是那些官员的专利,每一个自杀的官员最后都被确定为抑郁症。我,怎么可能?像我这样,随时都可能因为工厂破产而失业的穷家伙,抑郁症怎么会找上我呢?妻子说,是医生说的。我说,医生不是上帝。即使是上帝说的,也没用。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我的失眠可能更是肉身的一种需要。妻子是高中的语文老师,但她有时也不能理解我。不能。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另类的工人。一个喜欢阅读和写作的人。
妻子见我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摇了摇头,去厨房做饭了。我拿起看了一半的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继续看。吃过午饭,妻子回学校继续给学生上课。妻子建议我去望溪公园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毕竟春暖花开了。而我因为工厂放假在家里沤了一个冬天。妻子说,就是冬眠,也该苏醒了。我笑说,说到冬眠,你希望我是哪种动物?熊还是蛇?妻子拿着拖把在擦地,看了我一眼说,当然是熊了。你希望我搂着一条冬眠的蛇睡觉吗?我手里拿着那本《自由》笑。妻子拖完地,说,我们一起走,坐50路汽车在木樽站,你下车,就是望溪公园,我回学校。我说,好的。找了个书签,夹在书页里。那书签是《世界文学》杂志夹在书里面配送的。上面有奥克塔维奥·帕斯的几句诗:
鸟儿在啼鸣,歌唱
却不知歌唱的内容:
全部的理解就是自己的喉咙。
我穿上衣服跟着妻子出门。在公共汽车上,我看到有一个人的手里拎着个笼子,笼子里面是一只黑白花纹的荷兰鼠,在飞快地蹬着笼子的铁丝,笼子跟着转动起来。车里的很多人都在看。
到了木樽站,我下车。
妻子说,晚饭回来做。
我说,我从公园回去时去菜市场看看,买些菜。
妻子说,好的。
我问,吃什么菜?
妻子说,买些青菜吧,冰箱里还有肉。
好的。我说。
车门开,我就下车了。我回身看了眼那只荷兰鼠,还在那里不知疲倦地蹬着,笼子几乎变成风车了,遮挡住它身形。前面的乘客可能是踩到对方脚了。骂骂咧咧的。我能感觉到那股子火药味。近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到人群里的戾气。经济的下滑。生存的压力。望城政府的不作为。我厌恶这股子戾气,绕过去,向望溪公园走去。我犹豫要从哪个门进去。最后决定,从三号门进去,顺着台阶可到达纪念碑。以前我数过,有563级台阶。我刚进去,走了不到一百级台阶,看到在一片空地上,围了很多的人。条幅上显示这是某公司的一个主题活动。我瞄了一眼,看到有人喊,马上就要放蝴蝶了。我好奇地停下来。没等几分钟,只见工作人员搬来很多纸盒,打开盒盖,无数的蝴蝶从里面飞出来,翩翩起舞,有的还落在了人的耳朵上,像一朵花。也许因为在盒子里呆久了,很多蝴蝶倒出来,就死了。五颜六色的蝴蝶招人喜爱。人们疯抢着。踩死了很多在地上的奄奄一息的蝴蝶。一只蝴蝶向我扑过来,我伸手要抓,旁边的一只手伸过来,抓在手中。他看了看我说,我先抓到的。我退到一边,在一个石椅坐下来,点了支烟。旁观者。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的姿态。等人群渐渐散了,环卫工人过来打扫,我看到,还有一些蝴蝶地上,残缺着翅膀在挣扎。但都被环卫工人扫起来,倒进旁边的垃圾箱。我看到有一只蝴蝶,慢慢从垃圾箱里爬出来。它只剩下一侧的翅膀,看上去有些失重,身子向一边倾斜着。对于蝴蝶,我没有研究,但我知道有一个叫纳博科夫的作家对蝴蝶很有研究。还有庄周梦蝶。至于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我不感兴趣。我看着那只蝴蝶蘧然地在垃圾箱那儿,我站起来,把它引渡到我的手上。翅膀上的眼睛是那么好看。我引渡它到旁边的花丛中,我希望它能活下来。我沿着台阶继续朝纪念碑走去。这囚禁在家里一个冬天,我还真有些喘了。歇了一会儿,继续爬台阶。两侧的常青柏树,让人产生一种肃穆。
我和妻子青梅竹马。我们都是工人子弟。她父亲跟我父亲还是一个班组的。她父亲工伤掉了条腿。楚河巷里的人都喊他,瘸子。中学的时候,我没考上高中,只好去了技校。而她上了高中,还考上了大学。但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只是没上过床。亲亲。摸摸。还是有的。那时候,我有手淫,但我不敢去想她,我觉得那是亵渎。直到,她大学毕业。我因为自卑和她分手了。分手半年,她就找了一个中学老师,结婚了。而我一直耍单。其间,也经历过几个女人,但都不是可以过日子的人。几年后,她找的男人睾丸癌,走了。我们再一次走到一起。好像老天爷就是这么安排的。人与人也是需要在对的时间遇见。我必须承认,是她调教着我,让我成熟,像个男人了。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那个了。但,就是这么回事。
我来到纪念碑下,坐在那里喘气,点了支烟。从这里俯瞰到整个望城城区。那条流淌在城市中间的河。厂区那边还是烟雾缭绕的,给人窒息感。在纪念碑下,我是矮的,渺小的。纪念碑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伸向天空的巨人。我绕纪念碑转了一圈,竟然无意识看到下面的草丛里,有一个老人在大便。我鼻子灵敏的仿佛闻到了臭味。为了不让老人尴尬,我很快转到另一面。阳光很暖地照在身上,我坐下来,打开手机上的便笺,看我昨天晚上写的几段话:
而后,虚脱。你被镶嵌,被挤压,被隐藏在墙里。你呼喊,细雨,轻寒。你的面孔模糊。阴天,皈依空寂的人,灵魂在奔跑。在人类的头顶,在接近星空的高度,归于阗静。你滑脱出那个子宫,你被呼喊招魂。这黑暗的荒凉的世界。叹息。一声。可你转身想回去的时候,那门已然关闭。婴儿。嚎啕。溺死在大地的镜子里。
这雨中,总有它缺席的部分。分开那些雨滴,在身体的左面。在雨中,灵魂出离。那些伞下的人,我隐藏在他们之中。寻找缺席的你,在身体的右面。
我们谈论到来自春天的恐惧,来自可能的暗杀,来自内心深处的忧患,春天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谈论而加速来临。还没有绿,没有花朵举手发言,更多的是沉默和喑哑。那些即将弹出枝头的舌头会被阉割。蝴蝶和蜜蜂,在哀悼一个季节的葬礼。那水泥建筑里的人被囚禁着,和灰尘一起生长。唯一的窗是夜晚,孤寂的月亮。那些环形山看上去也同样的暗淡,看不清晰。那些谈论的人,低头吸烟。他们看到焚烧,看到枪杀,看到别离,看到血,看到鲸鱼集体死亡。看到……他们在烟雾里看到逃离的灵魂,看到灵魂出窍的人,他们的肉身已被掩埋。是的,他们听到了泥土砸在身体上的声音。他们停止吸烟,停止谈论,他们被隔壁偷听的人告密,并逮捕,甚至可能被处死。
我喜欢这样的片段书写。记录着我某一刻的所思所想。它们也许是无意义的,但对于我是重要的。我坐在纪念碑下,想再写点什么。这时候,来了一个电话。是陈曲胜。被电话打断思路,我有些气恼。
我问,干吗?
陈曲胜是我师兄,在工厂里,我们一个师傅。他实习完就辞职了。他是工亡名额进的我们厂。他父亲在一次爆炸中,连尸体都没找到。他在我们技校的一个专给工亡家属培训班上课。但在技校我们几乎没说过一句话。他总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独来独往。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辞职。突然一天就不来了。后来,在街上遇见过一次,他领着几个小弟,在砍人。他们一身黑色的西装,像电影《黑客帝国》里的某个镜头。他们围着那个中年人挥舞着砍刀。几乎可以听到砍到骨头的声音。他看到我,冲我摆了摆手。我因为恐惧,马上要离开。他向我走过来,手上的砍刀还滴着血,血珠像砍刀红色的乳头。我承认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说,曲胜,你咋就辞了工作呢?
陈曲胜说,怎么干下去啊?我老是能看到我父亲的鬼魂在那车间里游荡……
我说,哦。那现在……
陈曲胜举起手中的砍刀,上面的乳头变得肥硕了,滴在地上。他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在虎山的铁矿,给老袁当保镖。只要阻碍我们铁矿的人,一律干掉……
我不懂。对于这个世界,我是封闭的。
有人喊,陈哥,警察来了,快跑。
陈曲胜说,你的电话号码,没变吧?哪天我找你和师傅喝酒。
陈曲胜身体矫捷地奔跑着,跳上了一辆汽车。
那个被砍的人,在地上,在血泊之中,趴着,俨然血湖上的一具浮尸。
那一幕,我至今想想还胆战心惊。他给我来电话干什么?之前他却是打过电话说出去喝酒,洗澡,但我都拒绝了。
可是,电话响个不停。我只好接了。还没等我说话,他就命令似的说,我听说师傅出事了,我在外面跑路,不方便回望城。你去处理一下,所有费用,等我回来,给你报销。
我问,师傅怎么了?我咋不知道。
陈曲胜说,你一天只知道看书什么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师傅因为嫖娼被抓起来了。是我一个警察哥们跟我说的。
我说,怎么可能?前一阵扫黄,不是把小姐都清理了吗?
陈曲胜说,我也不知道。那警察哥们说,在审讯的时候,师傅提到了我。他才秘密给我打了电话。我也不好找别人,只好找你……
我说,以前不是交完罚款就可以出来了吗?
陈曲胜说,这次够呛,说还要刑拘五天。这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师傅的工作,你在厂里想办法给他请假,去医院开病假。我怕师傅没有工作,更受不了。毕竟干了一辈子,快退休了,被工厂给除名……
我说,我尽力想办法,现在病假也不好开,厂里老去医院查。
陈曲胜说,好的。
没想到,在我从纪念碑下来,想去医院找人,刚走到放飞蝴蝶的那个地方,我听到闲逛的老人收音机里,播放了师傅嫖娼的新闻。师傅成了望城的名人了。收音机里的主持人还在辩论着。我给陈曲胜发了条短信,说了情况。陈曲胜回短信说,没想到这样,看来世道真是变了。我没回陈曲胜的短信。坐在那里吸烟。仍有几只蝴蝶的尸骸没有被环卫工人清理干净,但已经被人踩得流淌着汁液了。翅膀破碎。我不忍看下去,转移目光,看着那些树木上的芽孢,疮疖般,突出在枝条上,随时都可能涨破,从里面流出脓液似的。我哑然地坐在那里,就仿佛那疮疖长在我身上,从里面往外鼓,是的,往外鼓……
从下面上来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和女孩。他们坐在草坪上。其中的一个女孩尖叫着,发现了一只受伤的蝴蝶。他们捧着蝴蝶感叹着。丁香花的气味里,我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是我的鼻子出现问题了吗?我看着那正在发育的女孩的身体,心里面肿胀起来,像一个老色鬼。眯着眼睛,窥看着。他们坐在草坪上,朗读着什么。我换了石椅坐下,这里距离他们近些。我竖起耳朵。有一个男孩满脸的青春痘,很像上技校时候的我。我多看了他几眼。他站起来,朗诵着,我听着,哦,是艾略特的《荒原》。太熟悉了,我。他的朗诵让我感到亲切。“《荒原》,一,《死者葬仪》,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拨动着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
那声音令我感动。那《荒原》令我感动。我上技校的时候,第一本从图书馆借的书就是《四个四重奏》,如今,也只剩下这《荒原》的开头还记忆犹新。我很想上去加入他们的朗读,但我放弃了。对于他们的青春的身体,我是感伤的。我的中年是破败的。这么多年的夜班生活已完全戕害了我的身体。我这个轧钢厂的囚徒,幻想着成为斩首黑夜的刽子手。我常常在夜班幻想着,这样的夜晚。没有人声,没有喧嚣。只有宁静、美和死的庄严。一只黑色夜蝴蝶飞进我工作的驾驶室里,将油灯扑灭。
那男孩的朗诵被打断了。他有些沮丧。有人说,太灰色了。我来一首积极的正能量的《我爱你祖国》。我同情地看着男孩,自我关闭了我的耳朵。男孩孤单地站起来,向纪念碑走去。一个老头在我的身边坐下来,收音机里还在讨论着师傅嫖娼的事,连师傅的父亲是当年参加辽沈战役的事都挖掘出来。主持人在用这样的事羞辱着师傅。应该是现场采访。我听到师傅的呼吸声。主持人谴责的问话,令我气愤。我起身离开。也许是午饭吃的剩菜坏了,肚子有些疼。我四处寻找着厕所。但我肚子疼得厉害,即使找到厕所,也来不及了。我钻进旁边的灌木丛中……我他妈的窜稀了……等结束后,肚子好受很多。可是更尴尬的事情是,我兜里没纸。我蹲在那里,折了根树枝,掰去上面的弱枝,看上去光滑了很多,这样,不至于伤害到我的……但毕竟没有手纸那么柔软和舒服。那柔软的部位还是受到伤害,丝丝疼。我仍旧蹲着,等待疼痛的褪去。树丛中,我看到一小坨黑色的……我知道,这个地方之前也有人排便过……只是,他(她)的干硬,风干后,像一块黑色的化石。而我的,漫溢到草木根部……是养料,是的,养料……这么想,我独自笑了。
从灌木丛出来,因为灌木丛的阴冷,屁股有些凉飕飕的。
这时候,妻子来电话。
妻子问,还在公园吗?
我说,是的。什么事?
妻子说,你师傅出名了,你知道吗?
刚才从遛弯的人的收音机里听到了。我说。
妻子说,我觉得媒体有些过了。那些贪官们多少女人……你又受刺激了吧?
我说,没。我刚刚窜稀了,拉出来,舒服多了。靠,我竟然没带手纸。
妻子说,我们出去散散心吧?
我说,去哪儿?
妻子说,半个月前,我们高中不是有一个同学跳楼了吗?上面要来调查,校长安排我们教师集体去卡尔里海旅游。可以带家属的,你跟我去吧。人数都统计上去了,我给你报了名,没跟你商量。
我说,还用跟我商量吗?你就是我的独裁者,你就是我的领导。
妻子在电话里笑。
关于独裁者这句话,是我们在床上的玩笑。妻子是喜欢上位的人。我就开玩笑说,她是独裁者。
妻子说,那晚上,要不要我再独裁你一次。
我说,可以啊,你想就可以,我没有反驳的权利……
妻子说,怎么?学得这么乖。还是饶了你,等我们去卡尔里海海边的旅馆里,我再独裁你……
哦,哦,哦。我笑说,欢迎独裁。不过,你怎么独裁我,我都是向你开枪射击的人。
妻子近来的性欲很强烈,几乎可以说,贪婪了,令我有些吃不消。有一天,她竟然要和我69,被我拒绝了,她有些不高兴。这是我对独裁者唯一的反抗。
从望溪公园出来,我去了菜场,买了些蔬菜。路过广场的大屏幕时,我看到了师傅。他苍老了很多,低着头,警察在审问他。他说,我没,那个女孩是我远房的侄女从农村来,要我到宾馆里去,她给我带了一些土特产。她在洗澡的时候,你们就闯进来了……就这么回事,我没嫖娼,我没……师傅老泪纵横。广场上的很多人在观看,议论纷纷。他们已经被舆论导向一个道德的方向。警察说,你这是说我们在污蔑你陷害你吗?师傅说,我没那么说。警察说,可我们在她的皮包里发现了避孕套,这怎么解释?师傅说,我怎么知道。警察说,你还狡辩。师傅说,我没狡辩。
听着那些围观的人义愤填膺的,我愤怒了。真想大喊一句,你们都是傻逼。但我还是克制了。我想到了陈曲胜,那个砍人的人。我在意识里挥舞着砍刀,对这些围观的人进行杀戮。是的,杀戮。我的骨子里总是隐藏着让我恐惧的暴力因子。屏幕上,一个网站的记者手拿着带着网站标识的话筒,对着师傅的嘴,像是要师傅给他口交似的,问,你不忏悔吗?师傅说,我忏悔什么?记者说,你嫖娼,你已经扰乱了社会秩序。师傅说,我说过了,我没嫖娼。记者说,可是那个女孩已经招了,做过小姐。你还能抵抗多久?师傅说,那是她的事情,再说了,她是我侄女,我嫖她,就是乱伦,你懂不懂。就像你能嫖你妹和你妈吗?记者的脸色气得铁青。我奇怪了,这样的采访也能播放,也许我们这个国家的媒体进步了。后来,师傅就被他们押着,回了牢房。他橘黄色的囚衣上写着他的代号:2015331。我在心里给师傅点赞。
回到家,我拿起那本《自由》继续阅读。
妻子回来的时候,从超市买了很多吃的,为了明天的出行。吃过晚饭后,她开始收拾行李箱。我的内衣内裤,她的内衣内裤。我还在看书。妻子曾嘲笑我说我装逼,看的书都是国外的。我没有反驳。她收拾完行李问我还带什么吗?我举了举手里的《自由》说,咖啡和小罐的蜂蜜,别忘了。妻子说,不会的,也不知道你从哪个女人那儿学来的。我笑,继续看书。
临睡前,我在手机便笺上写下这几个字:明日,卡尔里海。海。一个每天都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快乐、痛苦、新生、死亡……
第二天,中午飞机降落在卡尔里海机场。飞机上妻子的同事们说着各种不同的八卦。有人还说,要是没有那学生的跳楼,这样的旅游机会是没有的,而且还坐飞机。我把手机耳机掏出来,塞进耳朵里。我的《自由》被妻子放到行李箱里,对于我,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妻子的男同事我也不喜欢,有些娘。从他们自诩的知识分子的眼光里,我同时也看到了对我这个工人阶级的鄙视。我希望飞机快点儿降落。这群傻逼。误人子弟的,道貌岸然的家伙。我甚至跑到卫生间坐在马桶上呆了半个小时。不停地拉动马桶。后来,工作人员用钥匙打开门,看到我坐在那里,问我,没事吧?我说,没。从卫生间出来,飞机就播报即将降落的消息了。这是一个不大的飞机场,只有五六架飞机。我下了飞机就掏出烟,才想起来,在安检的时候,我的打火机上交了。我只好把烟叼在嘴里。从出口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有人在吸烟,跑上去,借火。狠狠吸了一口,浑身都舒坦了很多。几口结束一支,又来一支,用自己的烟头对上火。他们是团购,有旅游公司的人在接。这让我很不舒服。妻子白了我一眼,在警告我不要这样,既然来了,就要高兴。我要求打开行李箱,把我的《自由》拿出来,放在我的背包里。妻子脸色阴沉地看了我一眼,帮我取出来,推给我。沉甸甸的一本书,让我有了重量感。在旅游公司的大巴里,导游简单介绍了几天来的安排,还要去距离卡尔里海的A市参观一个古尸博物馆,并在A市留宿一宿,之后,返回卡尔里海,再玩一天,从卡尔里海登机回望城。我,是的,我只是一个局外人。这些对于我没必要关心。倒是女导游看上去年轻漂亮,声音好听。妻子的男同事们,目光贪婪。到达海边还要近一个小时,导游发动大家唱歌。他们唱得鬼哭狼嚎的。我看着都觉得可怜。一个男同事还提出要跟女导游对唱一个情歌。女导游蹙着眉头,但还是答应了。唱到动情处的时候,男同事的手搭在了女导游的肩膀上。女导游躲开。妻子倒是没唱,但可以看出来,她已经融入到他们的情绪之中了。我再一次掏出耳机,塞进耳朵里,找出我在手机里下载的灵魂乐,独自听着。有人怂恿我和妻子也来一首,我拒绝了。倒是妻子去独唱了一首《绿岛小夜曲》。到了宾馆,妻子责备着我,说,如果知道这样就不带你来了。我不吭声。分房间的时候,我们竟然分了一个两张床的房间。这是妻子要求的。我无所谓。妻子的女同事开玩笑说,禁欲啊?多好的机会,就当度蜜月了。妻子没回答她。脸色很不好看。我故意逗她说,我的独裁者生气了。妻子说,懒得理你。我差点儿就发火了。但我克制了。午饭的时候,妻子竟然没有叫我。还是她的同事把电话打到房间里叫我,我才下去的。我后悔我参加他们的午餐了。他们是一群饕餮之徒。我吃了很少的东西,就回房间看书了。他们吃完下午去海边玩。我拒绝了。

那天晚餐,我没有去吃。妻子很晚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简单冲了澡,她就睡到自己的床上了。我无聊地看着电视。电视剧什么的,我根本不喜欢,最后停在一个讲宇宙的节目,听着讲解员在说,宇宙是万物的总称,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是物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并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在时间上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在空间上没有边界没有尽头。宇宙是多样又统一的;多样在物质表现状态的多样性;统一在于其物质性。宇宙是由空间、时间、物质和能量,所构成的统一体。
也许是喝酒的原因。妻子的呼噜声很大。我关了电视,下楼,在海边漫步。遇到一个穿荧光雨衣跑步的男人,我们搭讪着,在他跑完步,我们去海边的酒馆里喝酒。他竟然是一个韩国人,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我们聊了很多韩国电影。酒馆只有一个女老板。看上去年轻美丽,在赠送我们小菜的时候,他邀请她喝一杯。她顿了一下,听出他是韩国人。她坐下来,陪我们喝酒。更多是陪他。后来,他们牵着手去了酒馆的后台……
我独自喝酒,透过落地玻璃看着海边绚丽的灯光。
这时候,她走进来。是她。真的是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怀疑我是不是喝多了。但,不是。她看上去还是那么美,身材保持得还像当年一样。那是一个练过舞蹈的身体。她也认出我了。但她的眼神里没有丝毫惊讶,就像是平时的一次约会。
我说,你好。
你一个人吗?她问。
我说,刚才在海边遇上了一个韩国人,就来喝一杯,现在他……
我指了指后台。女人的呻吟声。
她笑了笑。
我说,坐下来,喝一杯吧。你一点儿没变。
她说,是吗?老了。
我给她倒了杯酒,我说,庆祝无意义。
她笑了,说,来,庆祝无意义。
我们闲聊着,但好像都不去触及过去。我还记得,她最后给我一次大的短信是这样的:“等你快死的时候,一定要来找我,你必须只能死在我的阴道里,而现在,你去操几百个比我丑的女人都可以。”
我给她打电话不接,给她工作的图书室打电话,人说她不在那儿工作了。差不多有五年没见了。也没有她的消息。现在,她却出现在面前。我不敢相信,但是,这是真的。我感受着她的呼吸。她是我在一次钢铁系统的笔会上认识的。她在矿山的一个图书室上班。偶尔写诗。我是在和妻子结婚后的认识她的。我们彼此通信,交流着彼此的阅读感受。那时我几乎放弃了诗歌写作,开始写小说。有一天,我想找福克纳的《村子》,但找遍望城的图书馆都没有,我想到了她。给她打电话问,她的图书室是否有这本书。她说有。
那个韩国人身体真好,快一个小时了,还没有回来。女人高潮迭起的声音。剧烈。
我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说,我们走吧。
我把属于我的那部分花销,近五十元。我放了一张一百元的,在桌子上,用酒杯压住。我们沿着海边的栈桥散步。她说起她离开后去了北京,打过几份工,遇到了几个男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再加上北京严重的雾霾,她辞职回来了。她工厂的厂长是她父亲的老战友。她又回到了图书室。她轻描淡写地说,我轻描淡写地听。我没有打断她。她说完了,我说。我说了我近来的情况,和这次意外的旅行。但我没有说我还在写字。是她问我,还在写吗?我说,嗯。她问,我还可以看吗?我说,嗯。海边有风,凉。我们往回走。她说,她住在灯塔船旅馆,2666房间。如果你明天午后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我说,好。
我们分手,我回到房间。妻子的呼噜声还是那么响亮,足以让这黑夜颤抖。
早上,导游的电话打到房间里。我还在睡觉。妻子对着镜子化妆,转头问我,你去吗?
我问,去哪儿?
妻子说,古尸博物馆。
我说,不去。
妻子说,就知道你不会去。
我说,一些古代的尸体有什么看的。
妻子继续在那里,化妆。她突然问,你昨晚上出去了吗?
我说,去海边走了走。
哦。妻子说。
妻子说,我们要在A市留宿一宿,你要照顾好自己。宾馆的饭菜不好吃,你就去外面吃。
我说,好的。
女导游已经在敲门了。妻子拎着她的东西出去了,回身对我说,有事打电话。别下海游泳,几天前,这里有人被鲨鱼袭击了。
我说,我不会游泳,不会去的。
窗外的天,有些阴。海面上灰蒙蒙的。我站在窗前点了支烟。想到她。想到她说起过,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是姑妈养大的。那天,我歇班,坐一列绿皮火车去的,到了已经是午后。在小镇的一个饭馆里,我们还喝了酒。那个午后,她说了很多。她工作的地方在一个小镇的山凹里。三层楼,都是书。关于矿山的各种各样的工具书。文学的部分也很大。木质的地板,被她擦得干干净净。坐在图书室里,不时可以听到远处爆破的声音。隆隆的。整个栋房子都跟着颤抖起来,像地震。我看到那些书上的蒙尘被震落下来,在光线中飞舞。她已经把我要的《村子》找出来,递给我。我翻看着。我说,谢谢。我们闲聊。她说到姑妈的时候,眼泪涟涟的。她姑妈去山上放羊的时候,被飞起来的一块石头砸中了头部。我也许是出于本能,搂住她的肩膀安慰着她。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文学的东西,生与死,爱与欲。她确实是我遇到的最有见识的女人。我们的很多观点都是相通的,是灵犀的。我亲吻了她。火烧起来。彼此点燃。她在脱去衣服的时候,光着脚,在地板上做了一个舞蹈的动作。她说,她小时候学过舞蹈。光线密实地从窗户照射进来,她的肌肤上像流淌着蜂蜜。我们做爱,彼此换着体位。我甚至感谢妻子对我的调教。在光线的照射下,她仿佛透明的,骑在我的身上,耸动着。伴着远处的炮声。和整栋房子的震颤。我们镶嵌在一起。更深入地融入对方的身体,仿佛对方的身体里有一个光明的隧道。地板上汪着我们的汗水。她的脐窝也盈满了。清澈的汗水。我贪婪地吮吸到嘴里,用舌尖舔着她的脐窝,向她的丛林深处移动我的舌头。而她含住我的身体,啯,吸,舔。我们69了。我们不清楚做了几次,直到瘫软在地板上。她扯过一条毛巾给我擦着身上的汗水。光线中,那些汗珠是金色的。躺了很长时间,她爬起来,端了盆温水,瘸着走过来。我问,你怎么瘸了?她嗔怪着说,还问。她给我擦拭着下面,和身体上的她的和我的融合到一起的体液。她给我清洗完,端着盆,走着一字步,扭动的屁股是那么完美。我被她的搞怪逗笑了。她洗完自己,回来,我说,再给我来一段裸体芭蕾。她哀求着我说,腿软,站不住了。时间是残酷的,一晃就傍晚了。我必须赶傍晚最后一趟回望城的火车。她送我到站台,火车来了,我在车厢里看着她。她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她在站台上为我舞蹈……我感动得头伸出窗外,呜呜地哭着。
之后,我又去过几次,直到有一天她给我发了那最后的一个短信。
我冲了澡,看了看时间。外面已经开始下起小雨。我带着我的《自由》,找到灯塔船旅馆,敲开她的门。她赤裸着身体,给我开门。等我进屋后,她树獭般挂在我的身上。缠了我一会儿,她开始给我跳舞。她的舞蹈充满了生命中经历的疼痛,这是没有想到的。我疼爱地上前抱住她。她这时已经泪水潸然,直到我们开始做爱……融为一体……
她还在酣睡,她的脸上挂着甜蜜的微笑。
我没有打扰她,把那本《自由》放到她的枕边,轻声关门离开。
雨是那么大,仿佛整个世界都要被湮没了。
我在海边走着,有一种想冲进大海的冲动。妻子来电话说,你没来,真是个损失,各个年代的古尸都在这博物馆里。我说,是吗?但我没有遗憾。妻子说,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给你看。我说,好的。雨越下越大,我在雨中奔跑着,边跑边脱光衣服,我在裸奔……是的,我在裸奔……开始涨潮了,冲上来的浪花支离破碎……我在裸奔……
也许是做爱后在雨中裸奔,回到宾馆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酸软,骨头都是疼的。我躺在床上,像病了似的。昏昏沉沉的,我睡着了。
那些古尸恢复了人形,身穿各个朝代的衣服,列队,一个一个,向我走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