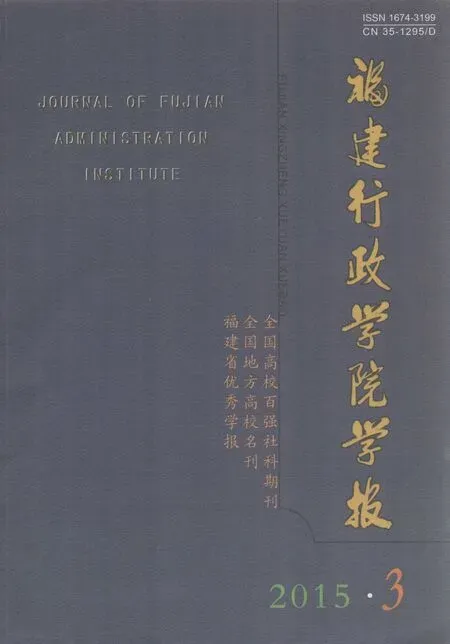伦纳德·怀特行政思想的演变:基于四版《行政学导论》的考察
李玉耘
(潍坊学院 法学院,山东 潍坊261061)
伦纳德·怀特在《行政学导论》中提出的四个行政学研究的假设,被认为是对行政学基本原则的最简洁的表述[1]38-51,这也是怀特行政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在第一版书的序言中写道,本书建立在至少四个假设之上:第一,行政是一种通用的程序,无论在何处其基本特征大体相同,这样可以避免市行政、州行政和联邦行政的分类研究;第二,行政学研究应该开始以管理为基础,而不是法律,因此,要更多关注美国管理协会的事务,而不是法院的判决;第三,行政现在基本上仍然是一种技艺,但要特别注意它转变为一门科学的重要趋势;第四,行政已经成为并且将来一直是现代政府问题的核心。[2]vii-viii本文将详细阐述这四个假设的内容及其在四版《行政学导论》中的演变。
一、行政是一种通用的程序
怀特在撰写《行政学导论》时,发现了研究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即分析行政问题要从所有的公务都指向的具体的行政活动入手,就会看到在所有的具体行政活动中,必然存在一个共同的程序,或者所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执行。因此,在他的眼里,公共行政就是公共法律的详细而有系统的执行,每一次普通法律的具体应用都是一个行政活动。这样,公共行政研究的范围就非常大,这就要求公共行政研究既要分析政府、军队和司法部门的行政问题,也要分析现代国家支持的各种活动,比如警察、教育、医疗、公共设施建设、交通管制、环境保护等等。[3]4这也意味着公共行政研究将要涉及大量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问题。
怀特强烈反对那种对公共行政进行分层分类研究的作法。第一,他指出,公共行政的基本问题都是相同的,不论是什么类型的组织或者进行的活动: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系和什么样的政府中,现代行政都存在相同的行政程序和问题。无论大与小,它们都会涉及行政机构的组织和结构、财政的提供与控制、人员的招聘与管理、执法的具体方法以及责任体系——对立法机构、法院以及一定程度地对选民负责。从这些方面上看,行政在本质上是属于管理的。[3]6第二,他反对按照公共行政履行的功能对行政进行划分,因为组织的功能很少影响公共行政的性质或者说核心问题。第三,他反对按照政府层级对公共行政进行分类的作法。他认为,不管是在市、州还是在联邦政府,行政程序都是统一的,对行政作市政管理、州行政、国家行政的区分根本不符合现实,事实上,行政的基本问题例如人的能动性的培养、个人能力和品格的保护、责任、协调、财政监督、领导、士气都是相同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问题与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政治界限是无关的。[2]1
因此,怀特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即行政是一种通用的程序,无论在何处其基本特征大体相同,避免对分层分类的公共行政研究。既从正面强调了行政的统一性,也从反面提醒不要对公共行政作出不符合现实的区分。这也意味着公共行政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主题进行研究。怀特这种整合公共行政研究的作法,对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行政学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得人们改变了对公共行政分类分层的认识,能够把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体系来看待,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共识的学科。“行政是一种通用的程序”的观点,使得人们更加相信公共行政领域存在一种普适的行政原则,这个行政原则不同于以前的行政原则,在此之前的行政原则是指适用于公共行政各专业领域的个别原则,而现在的行政原则是指能够普遍适用公共行政整个领域的一般原则,而后来古利克所提出的POSDCORB原则,就是受到怀特思想的启发,怀特也对此原则表示了很大的赞同。怀特在第二版的《行政学导论》中写道:通用的行政管理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些职能,即关心政策的形成,协调和改善政府机器,管理和控制公共服务的部门。通用的行政管理是任何行政体系的基础要素,并且随着组织规模的增大,重要性也越突出……用古利克的公式来描述通用行政管理的特征的话,就是计划、组织、人事、指挥、协调、汇报、预算。[2]307-309
为了方便研究,在后来的书中,怀特对公共行政研究的范围作了缩减,比如在第二版书中,他剔除了军队与法院的公共行政问题,以及一些专业技术性强的公共行政问题;在第三、第四版书中,他指出公共行政必须是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活动,从而将一个人的活动排除在外。这些都丝毫不影响,也不曾改变怀特所认为“行政是一个通用的程序”的想法,并明确强调行政的艺术就是指挥、协调和控制很多人实现某个目标或达到某个目的,这个行政艺术存在于任何组织之中。[4]4
二、公共行政研究建立在管理基础之上
怀特非常同意古德诺的观点,即“公共法律最显著的问题(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和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宪政,这是以前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不断努力的目标。但是现在的首要问题是通常被称为行政的。被称为行政的政府功能是不同于一般的政府活动,而行政法就是管制这种行动的法律”。[5]但是待查阅了古德诺的著作后,他发现古德诺并没有将行政与行政法作区分,而事实上,两者是有差异的。怀特接受了古德诺有关行政法的定义,即“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规定行政官僚的组织及其权威的资格,并在个人权利受到侵犯时,给以救济”。[6]根据此定义,他认为行政法的目标是保护私人权利,而公共行政的目标是公共事务的高效执行,两者的目标不仅存有差异,甚至有时候是相互冲突的。在此基础上,怀特进一步阐释道:虽然受到行政法的管制和宪法的规范,但在设定的界限内,行政试图最有效率的实现公共目的。[2]4-5因此,怀特认为古德诺虽然看到了行政的重要性以及与行政法的紧密关系,但是没有认识到行政与行政法的不同逻辑,所以,他不关注管制行政功能的法律,转而研究行政内在的基本原则,认为公共行政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目标而对人和物的管理,公共行政的目标就是最有效率的利用公务员掌握的资源。[2]2这个定义强调公共行政的管理特征,试图减少法律对公共行政的影响。但是,怀特却补充到,法律是区分公共行政与一般管理的重要标志。给人的感觉是,他又回到了以法律为基础的公共研究,与他提出的第二个研究假设相冲突。赫伯特·斯托林在《伦纳德·怀特与公共行政研究》一文中就对此提出质疑。[1]38-5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第二版书中,怀特强调尽管法律设定了公共行政的边界,公共行政是管理的,与其他类型的管理是没有区别的。这部分内容主要在“公共行政的范围与性质”一章中阐述。怀特认为,法律提供了公共行政运行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公共行政的任务,确定了公共行政的主要组织结构,为其提供资金,并设定规则与程序。换言之,公共行政是嵌在法律之中的,行政学者经常与法律打交道。[3]11然而,怀特又认为这种对法律的过分关注的作法使得行政学者和行政人员对统一的公共行政过程和除法律以外的潜在的行政原则置之不理,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公共行政极力夸大法律的正确性,相应地,重视法学家或者律师在公共行政中的作用,忽视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
受第一个假设的影响,怀特认为在各种各样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都存在着一个通用的行政管理方法,而且行政的本质是管理,要求公共行政研究关注点应从法律转移到行政的管理元素上来,因为法律规定了公共行政的界限,这只会影响公共行政的外围属性,却改变不了公共行政内在的管理特性。相应地,他主张用管理者代替法律工作者作为公共行政实践的中心人物。
很显然,怀特从管理的角度赋予公共行政更加积极的角色,反映了当时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现状,是对科学管理运动和市政改革实践的总结。当时的科学管理运动和市政改革基本上按照政治—行政二分的逻辑进行推进的,认为公共行政也是管理,可以像企业那样运作,追求效率,因此,学者在研究上,把“管理”与“行政”等同对待,把公共行政看作是一种管理的科学。
但是,随着美国大危机的爆发和罗斯福新政的出台,一个强大的中央计划体制逐渐在美国发展起来,通过这一计划体制,行政部门对国民生活进行了全面的影响,也确立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甚至介入了立法和司法部门的事务,“行政国家”开始出现。古利克在《政治、行政与“新政”》一文中非常生动的描述了这一幕:“我们现在正面对一个新的形势和一种新的必然。政府正在并毫无疑问地注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掌握这个国家经济生活的超级控股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所承担的新的基本职能是设计与执行一个关于国民生活的一以贯之的总体计划”。[7]这表明行政开始入侵政治,随之,怀特也对政治—行政二分产生怀疑,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以管理为基础的公共行政的观点,这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以管理为基础的公共行政,改变了过去那种以法律为基础的消极公共行政角色,赋予公共行政更为积极的角色,不仅要追求效率,而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拥有行政裁量权,乃至参与政策的制定。这些在后两版书中体现的比较明显。怀特在第三版书中写道:“行政部门不仅执行立法部门的决策,不仅是一个在这方面服从于对其实施控制的机构;它也是一个协助后者完成决策的机构。”“公共官员由于同法律运用于生活的实际有着日常接触,很快就认识到了法律在某些方面的虚弱性,并在执行法律中认识某些价值是可疑的。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政府行动的有效性限度,也更明智地关注如何应用法律去解释自己的那些权宜措施。所以,不足为怪的是,在法律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部门的影响有时是非常重要的……行政部门对立法者的影响在今天无所不在;一个公共机构的报告很少不会敦促立法上的或由立法支配的行政办法的改进。”[4]31-32
三、行政基本上是一门技艺,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
怀特提出的第三个假定:行政现在仍然是一门技艺,但有一股转变为科学的重要趋势。科学不仅为现代公共行政提供先进的工具和设备,还将行政管理方法从传统的经验中摆脱出来,从而确立科学的行政原则。追求最佳途径的科学管理运动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怀特认为,在科学管理运动的影响下,公共行政取得了很多进步,以至于可以正当的宣称一种行政科学立刻就出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后来出版的《行政学导论》中,包含越来越少的科学管理与组织原则,并对这些原则做了更多的限制说明。比如,怀特在第一版书中,讨论权责配置问题时写道:“高效的政府必须依靠权责的合理配置。这个原则很容易发现,就是明确责任使每个人都有确定的职责,在这种条件下,成功与否就依赖于个人能否勤奋与智慧”。[2]59-60与之相关的就是权力配置原则,怀特认为,每个行政官员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法律的和财政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行政官员有效的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务。他还承认,这些原则应用起来有点困难,但是这些原则本身是比较明晰的。在第二版书中,他对权责配置做了限制,增加了统一命令的要求,具体说,在任何组织里,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威。古语云,一仆不能同服二主。统一命令是一个组织进行管理的基础,反之,只会带来混乱、无序、不负责任等等。考虑到这一点,怀特认为,在分配权力时,必须要明确,而且权力要与职责相匹配。[3]45-46到了第三、第四版书,这些原则又增加了更多的限制条件。在新增加的“寻找原则”一节中,怀特认为,从最严格意义上说,行政原则仍然在形成中。如果把行政原则理解为被广泛的经验证实的工作规则的话,还是有一些可以表述出来的原则。接着,他阐述了权责配置问题,坚持认为权力分配必须明确,尤其在科层制的底层,但是在高层,这样做不仅是困难的,也是有害的。怀特还指出,权力要与责任匹配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几乎没有在实践中实现过,应该以相反的方式说,赋予的责任不应超过使用的权力与获得的资源。[4]35-36从权责配置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怀特虽然不曾放弃过对行政原则的追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自身的经历以及学术界的讨论,他逐渐认识到以前所追求的行政原则,只不过是深思熟虑的经验法则,用西蒙的话说,就是行政谚语,与科学还有一段距离。
有学者指出,从“行政基本上是一门技艺,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怀特对行政科学的犹豫,并认为从一开始怀特就没有真正的把行政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8]他们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并不完全认同他们的观点。的确,怀特在主张行政科学方面,并没有当时的一些学者那么狂热,比如认为公共行政与任何科学相类似,具有某些普遍适用的基本原理的威洛比,但是怀特内心对行政科学具有认同感,他在第一版书中,写道“尽管我们有权利有所保留地使用‘管理科学’一词,我们完全可以正当的宣称一门管理科学立刻就出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方面,它已经很好的建立起来了”。[2]15-16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怀特对行政科学的认可,没有丝毫的犹豫。从他这个时期的实际行动,也可以看得出来。一是积极探寻行政组织中的原则,他认为这些原则应该是“通过观察或者实验得到充分检验的假设,而被提出来成为行动的指南或者理解问题的方法”。[9]从怀特对行政原则的定义,可以看出他的科学理念。二是他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决复杂的行政问题。怀特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究公众对公务员的看法与公务员的士气之间的关系,先后出版了《芝加哥公务员的声誉价值》《公务员声誉价值的再探讨》两部著作,他在研究过程中,首先对研究的问题进行量化,然后设计调查问卷并利用问卷调查来收集数据,最后依靠数量统计工具来处理这些材料,得出结论,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在行政学领域是开创性的,是对传统的完全依靠文本说明的研究方式的突破。最后,从他当时的时代与社会脉络看,怀特出版《行政学导论》时,彭德尔顿法案已经被推行了四十多年,进步主义时代刚刚结束,科学管理运动日渐式微,但是整个公共行政领域完全被进步主义者、科学管理者、文官改革者的广泛的理论倾向所覆盖[10],当然怀特也不例外,进步主义者、科学管理者、文官改革者,虽然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纯洁政府、提高效率,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政治—行政二分,而行政科学的出现无疑为政治—行政二分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作为早期支持政治—行政二分的重要人物,怀特不可能放弃这样一个机会,必然高举行政科学大旗,为政府改革作舆论准备。所以,在早期出版的《行政学导论》中,怀特对行政科学具有很强的信心,即使当时还没有做到,他认为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怀特对行政科学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没有了先前对行政科学的热情,与科学相比,他更倾向于技艺。在第三版书中,怀特非常失望地评价公共行政:“作为一门学科,公共行政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包括公共行政的历史发展的说明、行政原则的综合阐述、重要概念的准确界定、公共行政的心理学与社会学基础的的透彻分析,公共行政在政府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解释说明。另外,它还要跟一般的政治理论相联系,关注正义、自由、服从和国家在人类事务中的角色等问题”。[4]10怀特的这种失望态度与当时出现的关于行政学的学科地位、知识发展以及身份危机的争论有关系。
20世纪40年代,正统理论遭到前所未有的抨击:正统理论所宣扬的行政科学在内容上是不成熟的,在方法上是粗糙的,甚至是错误的;行政科学所追求的科学原则最多只是普通常识的总结表述;行政科学把经济和效率作为目标或者标准太过狭隘,不可思议的;政治—行政二分是人为虚构的,必须放弃或者从新的角度去思考。沃尔多将其称为“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11]面对这样的危机,公共行政学者不断的反思,并寻找解决之道。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西蒙和沃尔多。
西蒙沿着正统理论的路子,将逻辑实证主义引入到行政学研究之争,构建一门真正的行政科学,而沃尔多则与正统理论彻底决裂,构建一门以民主为中心的公共行政学,更好的反映真实的世界。西蒙所主张的行政科学与怀特的早期追求有着契合之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自身经历,怀特对行政科学的信心日渐式微,甚至感觉行政根本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而是更接近一门技艺,这在后期出版的《行政学导论》中体现的非常明显,所以说,在怀特看来,西蒙走的有点远。而且,在怀特看来,西蒙构建行政科学的基础:事实—价值二分,只不过是政治—行政二分的一个变体,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构建的行政科学,只能脱离实际生活,这不符合怀特的风格,也有悖于行政学研究的目的。因此,怀特难以接受西蒙的作法。沃尔多更多的是从政治理论角度对公共行政正统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希望抛弃公共行政狭隘的技术特征,认为行政是一种技艺,以此构建一个以民主为核心的公共行政规范理论。沃尔多的作法的确比较符合实际,但是在当时美国行政学会已经从政治学学会分离出来,行政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如果再拿政治理论说事,会使行政学者很难堪,也会面临这一个危险,使得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公共行政学再次陷入到政治学之中,而且这样会使公共行政的内容无限扩大,就会造成“什么都是公共行政,公共行政就什么都不是了”的尴尬境地。所以说,沃尔多的愿望是良好的,但是实际运作起来比较困难。正因为如此,有人就指责说,沃尔多更多的是公共行政的批判者和评论者,而不是一个建构者[12],他颠覆了正统理论的旧世界,却无力构建一个新的世界。沃尔多在晚年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点:“我的目标不是告诉人们思考什么……然而我会尽力去告诉他们如何去思考——当然,特别是关于公共行政”。[13]所以,怀特希望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作为公共行政学的出路。到了1955年,他摆脱沃尔多的观点,试图通过历史和文化的视角来调和行政中的科学与技艺所占的比例。怀特在第四版书中,增加了“美国公共行政的形态与精神”一章,主要描述美国公共行政的历史与文化,寻找美国公共行政体系的历史基础,这也是怀特后期的行政史研究的兴趣所在。他认为,就像历史长河一样,发生在公共行政历史中的事件是独一无二的,不会重复出现,它们的性质以及相互的关系也不能够被测量或者通过可控的实验测试。[14]8-9很明显,这些观点与他先前的所主张的行政科学的一般性相矛盾,但是他仍然预测行政会逐渐的变成一门科学,或者说,是一门受不同文化影响的科学。[14]10
综上所说,在第一版书中,怀特高度评价了科学对公共行政的作用,并对行政科学的构建充满信心,换言之,在他眼里,行政肯定能成为一门科学,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到了第三、四版书中,更多的强调行政技艺,而不是行政科学。
四、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
怀特的第四个假设就是行政已成为并继续是现代政府的核心问题。美国的行政思想只有在美国强烈的反国家主义传统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国家主义”是一些鼓吹强化社会中的国家机构的主权和功能的学说和观念。“反国家主义”则相反,它是对社会中的这些中央政府机构表示敌视的学说和观念,它主张减少、限制甚至取消这些机构的活动及其功能。[15]美国宪法只字未提公共行政这种有效促进政府行为的要素,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制约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美国政体是建立在严苛的加尔文宗教和洛克的自由政治观之上的,他们认为人性原本就是恶的,因此,没有人可以被长期委以权力,而是“野心必须以野心来对抗”[16],建立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府体制。正如尼古拉斯·亨利所言,美国公共行政传统所依赖生存的社会背景是独特的文化与智力两种力量的集合体。这些力量产生了美国公共行政传统,这一传统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制约。[17]这种制约传统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公共行政较少被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而得到关注。1835年,托克维尔游历美国大陆,非常吃惊的发现:美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差不多全凭口述和传统进行。没有成文的规定,即使写出过一些,也象古代女巫写在棕榈树叶的预言,遇上一阵微风,就被吹走,消失得无影无踪……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渗入人民的习惯……每个美国人都觉得这样合乎口味。谁也不打听在他以前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研究管理方法,没有人总结经验。收集文献本来十分容易,但也没有人收集。偶然落到人们手里的文件很少被保持下来……行政管理人员根本不互相学习……而且,他们在指导社会工作时,只凭自己积累的经验知识,而没有指导该项工作所必备的科学知识。[18]在美国,虽然18世纪80年代的《联邦党人文集》已经谈到了公共行政问题,但是其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关注。
美国建国后的一百多年里,地理隔离、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乡村居民、没有重大的外部威胁、很少需要大规模的军队或社会服务、拓荒精神以及没有工业革命,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国家不仅是邪恶的而且是没有必要的观念。美国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可能最恰当的描述了这一奇特的状况:早期的普鲁士与其说是一个拥有军队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拥有国家的军队,同样地,早期的美国与其是说是一个拥有邮局的国家,不如说是很受一个正在成长的国家欢迎的邮局。[19]除此之外,美国制约公共行政的传统,也限制了政府行政职能的扩张和发挥。因此,在早期,美国的政策制定权掌握在国会手中,而政策执行主要依靠法院完成,行政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迅速实现工业化,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美国也从一个农业社会快速地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变成以大公司为核心的公司资本主义。与之相伴随的是城市化和移民潮,美国迅速地由一个乡村社会转变为一个城市社会。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财富不断集中,社会公平问题凸显,以及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城市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食品安全等难题,迫切需要政府出手解决。而当时的政府受保持制约的传统,仍然奉行有限政府的理念,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并由政党分赃带来大量的腐败问题,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反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为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人掀起了一场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建立积极行政的政府以应对拓僵时代的结束、大量移民的涌入,以及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和劳资冲突。经过进步主义运动之后,美国国家的治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策的执行权由法院转移到行政部门,行政部门的职能和规模不断扩张,行政的自由裁量权也不断增长,行政部门对专业人士的需求不断增加,开始走向行政国家。人们对政府的理解也发生变化,政府管得越少就越好的理念逐渐被积极行政的理念所取得,人们开始向政府或官员寻求各种帮助,要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一个英国学者就总结到:“行政部门的权力在不断增长,因为国家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角色,用洛克的话说,作为一个守夜人,从严格意义的上讲,仅仅作为一个正义的分配者。而现在国家行动的理论依据是个人和社会的善可以通过社会理性和行动的过程来发现,并能够通过成文法很好的实现”。[20]因此,怀特认为,公共行政已成为并继续是现代政府的核心问题。
早在1887年,威尔逊就指出,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发展,政府都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绝对统治者时期,是行政系统与绝对统治相适应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制定宪法废除绝对统治者并用人民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时期,由于对这些高级目标的关切,而对行政管理有所忽略;第三个时期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在使他们掌握权力的新宪法保障下,着手发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期。紧接着,他认识到当前的美国恰好处于第三个时期,应该着手完善和发展行政管理体系。[21]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自身思考视野的限制,他既没有把行政管理放在核心的位置上,也没有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直到20世纪20年代,由怀特再次将这个问题提出,并把公共行政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在第一版书中,怀特首先讨论了宪法上的权力和政府功能的分立问题,但是他却认为传统上所宣称的立法机构位于政府中心的观点,没有准确描述现代政府的基本特征。他认为在早期、简单的时代,立法机构有时间处理大多数问题,这些问题适合非专业人员协商讨论,主要涉及政治伦理的重大问题的决定,比如废除公民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公共土地的部署、英国国教的废除、君主国家的自由化等等。现在充斥在立法机构的问题经常涉及,或者主要变成技术问题,非专业人员只能依靠专家才能处理这些问题,这些专家不仅仅对被日益增长的法案整的不知所措的立法者非常有用,他们甚至变得不可或缺,他们就是政府。在不久的日子里,传统的以立法机构为中心的权力分配设计,将被一个更现实主义的分析所替代,这个现实主义分析使政府成为行政的任务,行政在立法和司法机构设定的范围内运作。[2]6怀特主要表达两个意思:一是重大而简单的政治问题基本已经解决,现在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复杂而棘手的技术问题,而这些问题只能依赖于行政机关中的专家;二是公共行政虽然在立法和司法机关设定的范围内运作,并受其制约,但是不可否认,行政事务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主要内容,这里的行政主要是指技术层面的事务。接着分析了原因。怀特认为“工业革命及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导致公共行政成为政府核心的主要根源,因为“工业革命使得社会合作成为必需,而自由放任是无法做到的,新的环境正逐渐地在人的头脑中建造一个关于国家角色的概念,接近于现代生活赋予的国家功能。这些新观念接受国家作为促进社会合作的重要力量和社会管制的机构。因此,国家成为社会有效改善的重要手段”。怀特所说的国家更多的是指政府中的行政部门,因为“新的国家计划每个时期都体现了行动活动的增加”。[2]8-9>
在第二版书中,怀特并没有直接说明公共行政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而是回顾了美国行政体制的发展过程,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从一个适用于简单的、很少需要政府的农业社会的行政体制转变为一个适用于复杂的、处处都需要政府的工业社会的行政体制,并指出现在行政组织和功能的发展趋势:无论是管制,还是服务,行政功能急剧膨胀,相应的管理机构也不断增加;由司法部门单独掌握的法律行政权有相当多的转移到行政部门,与此同时,行政部门的自由裁量权不断增长;行政权力不断向中央集中;行政责任由早期的分散到最终的集中,并出现了行政首长的新概念;分赃制逐渐衰落,与此相伴的是专家、职业人士和科学家在行政部门中的人数逐渐增多;行政规划开始兴起。[3]25相应地,立法机关面临着超人般的任务,处理大量的社会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这需要更多的依赖经过科学处理得来的大量的数据,而不是广泛的直觉。所以,在这些解决措施里,行政人员的建议是最重要以至于立法机构不得不依赖,这样就导致很多法案都是由无名官员起草,行政人员倡议,立法机构同意。立法机构变成了社会政策的宣告者,而不是倡议者。[22]简单地说,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是越来越重要,相应地,行政部门在政府中的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政府的中心,再次验证了他先前提出的假设。
在第三、第四版书中,怀特重新阐释了行政的功能,除了以前的政策执行和政策制定中的专家角色,还有承担起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要求行政人员利用熟练的技巧,依靠专业知识,事实上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将各种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捆绑在一起。正如彭德尔顿·赫林所言,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行政人员肩上担负着调节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和达成有效可行的经济社会方面妥协的责任。[23]换言之,界定公共利益最终成为行政官员的工作,众多行政官员成为解释公共利益的无名氏。[24]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人员不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技术专家,而是在政策执行和制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行政问题不单单是技术问题,与政治密切相关,但这里的政治不同于以前的政党分赃制。
综上所述,怀特原本想把行政中的政治因素剔除,只把行政作为一门价值中立的工具,以此来突出行政管理的特殊地位,但是后来发现,行政并不是在一个真空中运作,不仅受到政党、利益集团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还要作为一个平衡各种特殊利益的政治力量发挥作用,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因此,他不再强调行政的技术性,更多的从行政史发展的角度,来阐述公共行政的崛起,并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有学者据此认为,怀特前后的想法是矛盾的,我们承认怀特论述的逻辑前后有所变化,但是他最终的假设始终没有变的,一直强调公共行政的重要性。众所周知,行政学是一门实用的学科,任何一门实用的学科,在没有必要了解它时,不会有人去研究它。而当时美国行政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变化,政府机构迅速增加,而美国公共行政研究却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也没有出现一门专门研究公共行政的学科或专业,所以,美国公共行政存在着许多没有经过认真思考、也没有有效实施的组织设计,这些组织设计往往是针对政治目标来制订的,没有将管理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这样的组织设计既不经济也没效率,因此,怀特提出行政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的假设,目的在于是希望人们能够更多的去研究公共行政,构建一门行政科学,从管理的视角研究政府,构建强大的公共行政队伍,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公共利益。
五、总 结
本文重点讨论了怀特在行政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也就是他在第一版书中提出的四个假设。行政学者们在论文和专著中,无数次引用怀特所提出的这四个假设,却鲜有人探讨这四个假设与行政学研究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本文尝试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假设:行政是一个通用的程序,使公共行政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或者学科成为可能。1926年以前的公共行政研究基本特征之一就是采用分层分类的公共行政。在这种状况下,学者直接由于关注点的限制,很难进行对话,更不可能形成统一公共行政的认识,这不仅阻碍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又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和资源的浪费。而怀特提出的“行政是一个通用的程序”的假设,破除了分层分类的公共行政之间的壁垒,促使行政学者和公共行政人员能够在统一公共行政的认识中,进行公共行政问题的研究,并相互交流与借鉴,对于公共行政共同体的形成和行政学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假设:公共行政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使公共行政学成为必要。在工业革命以前,公共权力主要掌握在国会和司法部门手中,行政部门只负责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保卫国家,根本不需要行政管理知识和专业人才,但是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社会事务越来越复杂,原有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行政部门开始掌握越多越多的公共权力,成为现代政府的核心,相应地,行政部门需要行政管理知识和专业人才,这就必须发展公共行政学,为政府管理提供智力支持。第三个假设;公共行政研究要以管理为基础,指出了行政学发展的基础。1926年以前的公共行政研究沿袭行政制约的传统,主要以法律为基础,使得行政机关按照司法的逻辑运作,行政机构完全淹没在大量的法律条文之中,难以发挥行政的力量,而怀特要求公共行政要建立在管理的基础上,公共行政的目标是追求效率,因此,公共行政研究重点在于行政机关内部是如何运作的,要积极借鉴工商业管理的优秀成果,而不是把大量精力放在法院的判例上。第四个假设:公共行政基本上是一种技艺,正在转变为一门科学,明确了行政学发展的方向。根据前文的介绍,看到怀特在这个观点上有所变化,尤其是后期,他更强调行政技能,多于行政科学。不论是行政科学还是行政技能,都是强调行政学的实用性和实践性,这与怀特的实用主义特性是相符的。怀特坚信:第一,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学者应是一个实践者;第二,行政的目的就是有效率、经济地使用资源。总之,怀特的四个行政学假设紧密相连,不仅指出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提供了行政学研究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第一部行政学教科书。在书中,他从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行政环境、行政组织、行政协调、人事行政、行政伦理、行政法规以及行政监督等方面对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构建。正因为他在《行政学导论》一书中完成了行政学研究的系统化这一历史性任务,公共行政学才在他的手里真正赢得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行政学导论》是当时使用最为广泛的教科书,怀特也被认为是公共行政学的奠基人。
[1]Herbert J.Storing.Leonard D.White and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65,25(1).
[2]Leonard D.Whit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st ed.[M].New York:Macmillan,1926.
[3]Leonard D.Whit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nd ed.[M].New York:The Macmillan,1939.
[4]Leonard D.Whit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3rd ed.[M].New York:The Macmillan,1948.
[5]Frank J Goodnow.The Principl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M].New York:The Knickerbocker Press,1905.
[6]Frank J.Goodnow.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2Vols)[M].New York:Putnam,1893.
[7]Luther Gulick.Politics,Administration and“New Deal”[J].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33(1):55-66.
[8]Khairy ElDin Abdel-Kawi.The Administrative Ideas of Leonard D.White[D].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1966.
[9]John M.Gaus,Leonard D.White,Marshall E.Dimock.The Frontier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6.
[10]Jeffrey A.Weber.Leonard Dupee Whit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1997(2):41-64.
[11]Dwight Waldo.Scope of the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James C.Charles worth.Theory and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cope,Objective,and Methods.Philadelphia: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1968:1-26.
[12]Brain R.Fry.Master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From Max Weber to Dwight Waldo[M].New Jersey:Chatham House Publishers,Inc.1989.
[13]Brack Brown,Richard J.StillmanⅡ.A Search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M].College Station:Ta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1986.
[14]Leonard D.White.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4thed.[M].New York:The Macmillan,1955.
[15][美]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第7版[M].竺乾威,扶松茂,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6]Hamilton,Madison & Jay.The Federalist Papers[M].New York:Signet Classic,2003.
[17][美]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10版[M].孙迎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8][法]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65-266.
[19]Theda Skocpol.The Tocqueville Problem: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J].Social Science History,1997(4):455-479.
[20]Herman Finer.The Civil Service in the Modern State[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25(2):277-289.
[21]Wilson Woodrow.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887(2):1997-222.
[22]Leonard D.White.Public Administration(Volume One)[G]//Edwin R.A.Seligman and Alvin Johnson.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Chicago:The Macmillan Company,1930:440-450.
[23]Pendleton Herring.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M].New York:McGraw-Hill,1936.
[24][美]杰伊·M·沙夫里茨,E.W.拉塞尔,克里斯托弗·P·伯里克.公共行政导论:第6版[M].刘俊生,欧阳帆,金敏正,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