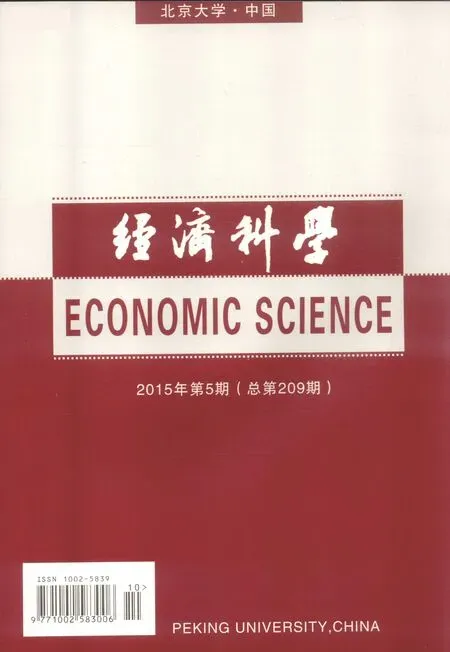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理论模型与跨国经验证据
林志帆 赖 艳 徐蔓华
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理论模型与跨国经验证据
林志帆1赖 艳2徐蔓华3
(1.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5)(2.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广州 510632)(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分行 广东韶关 512100)
是什么因素引发全球范围劳动收入份额的普遍下降?本文尝试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提供解释:世界各国持续的货币扩张使实际利率下降、信贷规模扩大,因此厂商使用资本品的成本下降,倾向于在生产中投入更多的资本;如果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资本深化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结论,我们基于中介效应检验使用跨国数据证明:无论是在表征短期均衡的动态模型中,M2/GDP与劳均资本上升均显著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深化是货币扩张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途径。分样本回归揭示,以上机理仅对发展中国家成立,部分传导机制对货币政策较为稳健的发达国家与欧元区国家不成立。这说明,遏制货币超发对于维持稳定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货币政策 资本深化 劳动收入份额
一、引 言
恒常的要素收入份额是Kaldor(1961)指出的现代经济特征事实(stylized facts)之一。可以证明,一个经济体在满足规模报酬不变、市场完全竞争和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由Cobb-Dauglas生产函数可以推导出各要素的收入份额恒等于其产出弹性。这一推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广泛地得到了来自欧美各国经验数据的支持(Solow,1958),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要素收入份额并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然而,近40年来,全球范围的劳动收入份额由稳定转而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Kaldor特征事实不断受到经验证据的冲击和挑战(Blanchard et al.,1997)。由于劳动要素的分布天然地比资本更为平均,要素收入分配偏向资本意味着国民收入集中于少数的资本所有者,这可能引发贫富差距的扩大,从而导致社会不安并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图1所示,1975年至2011年间,全球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由1975年的57%下降至2011年的53%。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学者们重新审视生产函数的合适形式,基于常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成为要素收入分配研究的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展开探索,以Acemoglu(2002、2003、2007)的一系列研究为代表,新古典框架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或中性技术进步的过简假设被逐步修正,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可能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因素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其实,早在八十余年前,Hicks(1932)便指出:当要素价格发生变化时,理性决策的厂商将倾向于使用成本较低的要素替代成本较高的要素,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成为生产技术改进的激励。基于此,Acemoglu(2002、2003)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技术进步的偏向受“价格效应”与“市场规模效应”两种机制的影响,前者诱发密集使用稀缺要素的技术,后者诱发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技术。要素替代弹性越大,“市场规模效应”就越大,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就越偏向于充裕的生产要素。可知,在长期,要素收入份额由劳均资本、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替代弹性联合决定。近年的一些文献如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Acemoglu和Guerrieri(2008)、Hutchinson和Persyn(2012)及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等也都确认了资本深化与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影响。但是,更为基础的问题是,如果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引发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重要推手,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下降,进而激励厂商改变投入决策使得资本深化持续发生?
我们猜想,全球范围越发普遍的货币扩张是资本要素供给增加、偏向型技术进步持续发生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图1显示,全球范围的货币发行量与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趋势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要素供给的角度出发得到的推断是:持续的货币扩张使得实际利率下降、信贷总量扩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诱使厂商调整技术选择与投入决策,在生产中使用更多的资本品,劳均资本的积累速度加快;在资本与劳动相互替代的条件下,资本深化将引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图1 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与货币发行量变动趋势
本文尝试运用理论模型推导与跨国面板数据对这一猜想进行证明。本文的边际贡献不仅在于丰富对要素收入分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证明,执行审慎稳健的货币政策、遏制货币超发、维持要素相对价格的稳定将有助于扭转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不利局势。相对于现有文献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所给出的产业结构变迁、贸易扩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不可干预”的经典解释而言,本文的结论具有更为明晰的政策含义。
二、理论模型
在本节,我们使用理论模型证明,在货币扩张增加资本要素的供给、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理性厂商将调整生产投入决策使用更多的资本品,而资本深化将最终引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由于Cobb-Dauglas生产函数的要素收入份额恒常,不适合本文的研究,因此我们以文献中常见的CES生产函数为范式展开分析,具体地:

在上式中,为产出,为资本,为劳动,A与A分别为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为分布参数(0<<1),表示资本密集度,为要素替代弹性,参考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的研究结论,我们假设>1。①
关于货币扩张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实际上涉及货币是否为中性的讨论。然而,在实证文献中,支持货币中性的经验证据非常少,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内是有效的。货币中性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仅作为一种理想的极端情形进行讨论。②
因此,令为实际利率、为工资率,当货币扩张发生时,资本要素的供给增加,表征资本价格的实际利率下降,而在短期内则往往由于合同工资粘性(价格粘性)、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信息粘性)等的存在而调整较慢,故要素相对价格(/)将发生变动,此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厂商的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如下:

(3)
结合(2)、(3)式构造拉格朗日方法求解,可得:

在上式中,为劳均资本,其上升表征资本深化。对其求关于(/)的偏导,可得:
(5)
可以发现,面对要素供给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理性厂商将调整投入决策,使用更多成本较低的资本品,从而导致资本深化的出现。从而我们得到待检验假说1:
假说1:货币扩张将使劳均资本上升,产生资本深化现象。
进而,假设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产品市场完全竞争且均衡出清,③结合(1)式得:

(7)
其中,()为生产函数的紧凑形式,为劳均产出,即为我们关注的劳动收入份额。同时,我们知道,资本收入等于劳均资本与资本边际产出的乘积,即:

因此,工资率可以表示为:
(9)
将(6)式与(9)式代入(7)式中,整理可得:

为得知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对上式求关于的偏导,可得:
(11)
于此,我们又得到待检验假说2:
假说2:劳均资本上升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如果考虑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根据复合函数求导的链式法则并结合(5)式与(11)式,可得:

从而,我们得到待检验假说3:
假说3:货币扩张通过影响劳均资本的途径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本节可总结为,由货币扩张引发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将使理性厂商的投入决策发生变化,这将使得劳均资本提升。在资本与劳动相互替代的条件下,资本深化将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第三部分将尝试为本节得到的推导结论提供经验数据。
三、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根据上节的推导结论,我们需要证明货币扩张通过资本深化的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可使用Baron和Kenny(1986)的中介效应检验进行研究。具体而言,中介效应检验的成立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1、货币扩张对劳均资本上升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路径显著);
2、劳均资本上升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路径显著);
3、货币扩张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具有显著的解释力(路径显著);
4、在控制劳均资本后,货币扩张对劳动收入份额解释能力消失或明显减小(即货币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与t统计量在路径中相对于出现明显下降)。④
图2 中介效应检验逻辑图示
参考张莉等(2012)的做法,我们设定反映短期均衡的动态面板模型以及反映中长期稳态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1、路径(对应模型部分假说1):

(14)
2、路径(对应模型部分假说2):

(16)
3、路径(对应模型部分假说3):

(18)
4、路径(对应模型部分假说3):

(20)
其中,LS为劳动收入份额,Money-1为滞后一期⑤的M2/GDP指标,ln()为反映资本深化程度的劳均资本指标。在动态模型中,τ与为劳均资本与劳动收入份额滞后期的系数,反映数据趋势中的惯性成分。此外,在解释劳均资本的模型中我们引入了人均GDP的对数值以控制不同经济阶段要素禀赋结构固有的差异;在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模型中则引入虚拟变量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进行控制。⑥至于模型的估计方法,对于动态模型,我们使用差分GMM方法以消除在模型中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带来的内生性偏误,⑦并使用Sargan检验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另外,我们根据AR(1)与AR(2)自相关检验结果确定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阶数,以消除模型扰动项的序列相关问题。固定效应模型中,μ与v为国家个体效应,反映各国诸如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对劳均资本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估计中使用“组内去均值”消去以得到一致估计量。
现有文献在进行劳动收入份额的跨国研究时主要运用两个数据来源:其一为联合国统计数据库(Jayadev,2007;李稻葵等,2009;张莉等,2012);其二为各个版本的Penn World Table(Rodrick,1999;Vreeland,2002)。然而,正如Gollin(2002)所述,世界各国通行的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NA)的劳动收入核算中忽略了自我雇佣者与创业者的收入,由于这部分收入在各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统计遗漏可能造成全球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假象。故运用宏观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可能得到有偏的结论。因此,我们使用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提供的各国企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CLS)作为实证检验的被解释变量,这个新的数据来源有两个优势:其一,规避统计核算中自我雇佣者与创业者收入的遗漏对分析的影响,避免对劳动收入的核算进行主观调整;其二,宏观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往往受到政府再分配政策的影响,数据中包含与本文研究无关的信息,而企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企业面对要素相对价格变动所做的决策调整的经济后果。
此外,由于劳动收入份额数值介于0~1之间,被解释变量的受限分布可能引发回归偏误,因此我们对其进行logistic变换,将数据分布范围单调地映射于(-∞, +∞)之间,具体地:

另外,M2/GDP与人均GDP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劳均资本数据由宾大世界表第八版中各国的资本存量除以从业人数后,再取自然对数得到。经过整理,我们得到涵盖56国从1975~2012年的跨国面板数据用于回归分析。
(二)回归估计
1、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1提供了基于全体样本56国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格的上半部分提供了动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反映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短期均衡关系,下半部分提供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反映三者在中长期的稳定关系。
我们首先关注短期关系的结果。在以劳均资本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的路径回归中,其滞后项系数为0.901且高度显著,这与资本存量调整速度普遍较慢的常识相符;残差均存在显著的AR(1)扰动,但不存在AR(2)及更高阶的扰动,工具变量联合有效性Sargan检验均不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了模型设定的正确性与稳健性。在控制经济发展水平(ln())的影响后,可以发现,货币变量对劳均资本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扩张的确能够加速资本深化的过程,理论模型的假说1与中介效应检验的路径得证。

表1 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全样本回归结果
注:(1)括号中为t统计量;(2)系数标准误使用国家层面聚类稳健估计法得到;(3)AR(1)、AR(2)与Sargan检验提供的是p值;(4)***、**、*分别表示1%、5%及10%的显著性水平。
第二至四栏的回归均以劳动收入份额为被解释变量,报告了路径、与的回归结果。在各个回归方程中,劳动收入份额滞后一阶的估计系数稳定在0.62左右且显著为正,且都通过了模型设定检验。我们发现,在第二与第三栏中,滞后一期的货币发行量与劳均资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均为负,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假说2以及中介效应检验的路径、。第四栏则报告了货币发行量与劳均资本同时进入模型的结果,此时货币发行量的估计系数大小与t统计量均出现下降,而劳均资本则变化不大。这说明,至少在计量层面上,资本深化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更直接原因。这便证明了模型部分的假说3与中介效应检验的路径。而且,在第四栏中,货币变量失去统计显著性,验证了完全中介效应,说明资本深化是货币扩张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唯一途径。
进而,我们关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所反映的中长期关系。可以发现,货币扩张对资本深化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理论假说1与路径依然成立;以劳动收入份额为被解释变量的三个回归反映:单独看,货币发行量与劳均资本均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两者共同进入模型时货币变量的系数大小与t统计量都接近于0,在中长期完全中介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资本深化相对于货币扩张而言仍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更直接原因,这与动态模型反映的信息是高度一致的。对比表2上下两部分的系数大小,可发现在中长期货币扩张对资本深化促进作用以及它们两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的作用力度都更大。
简而言之,我们验证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作用机制:货币扩张首先增加资本要素的供给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理性厂商进而调整投入决策,在生产中使用更多的资本品,资本深化加速;在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⑧资本深化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全样本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本文的经济机理与模型的推导结论。⑨
2、分样本回归结果: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欧元区国家
我们注意到,在过去数10年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Crowe和Meade,2008)。发展中国家的央行独立性相对较低,货币政策往往肩负了刺激短期经济增长、弥补政府财政赤字、操控汇率与贸易收支等本不应承担的政策任务。货币政策失衡的典型表现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与高通胀预期,加之名义利率管制的影响,实际利率往往偏低,企业使用资本品的成本较低。极端情形下,如果实际利率为负,便等同于对企业在生产中使用资本品进行补贴。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多以维持总体价格水平稳定为基本的甚至单一的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的调整需要经过严谨的论证,受非经济因素扰动的影响较小。我们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查阅数据发现,在过去数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样本;而尽管从要素禀赋结构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要素较为稀缺,实际利率理应更高,但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率相差不大。
我们认为,这一怪象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货币扩张引致高通胀与利率管制并存的现实。陈彦斌等(2014)使用数值模拟实验证明,尽管长期以来利率管制被视为不利的政府干预措施,它却具有一定的“增长效应”——偏低的实际利率降低了资金成本,强化了企业部门扩大投资的激励,因此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增加,从而促进总产出提高。⑩这应当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运用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以及利率管制将实际利率压制在较低水平的动机。在这一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的速度可能更快,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强度可能较大,劳动收入份额受侵蚀的可能性也更高。因此,有必要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子样本,⑪以探索货币扩张与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否表现出异质性。

表2 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发展中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续表2

中长期稳定关系被解释变量 ln(K/L)LSLSLS Crisis--0.011(-0.37)-0.011(-0.32)0.006(0.22) N1305457463451 R20.4890.0970.0160.100
注:(1)括号中为t统计量;(2)系数标准误使用国家层面聚类稳健估计法得到;(3)AR(1)、AR(2)与Sargan检验提供的是p值;(4)***、**、*分别表示1%、5%及10%的显著性水平。
表2提供了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回归结果。⑫劳均资本的滞后项对其本身的影响仍是显著的,体现了较慢的资本存量调整速度,而货币变量在短期内的影响为正,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验证了理论假说1与路径关于货币扩张促进资本深化的猜想。进而,观察以劳动收入份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滞后一阶与二阶的系数之和约为0.58,与全样本的大小相近,同样体现了良好的“惯性”。第二列与第三列报告了滞后一期的劳均资本与货币发行量单独进入模型的估计结果,两者均显著为负,这与总体样本的结论一致。第四列报告了劳均资本与货币变量同时进入模型的估计结果,此时货币变量的估计系数和统计显著性均出现下降,说明货币扩张通过促进资本深化的途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反映中长期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也呈现了相同的信息。略有不同的是,短期均衡关系中货币变量在控制了劳均资本后仍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资本深化为货币扩张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部分中介,而长期稳定关系中则为完全中介关系。另外,我们发现,无论是长短期回归结果,货币发行量与劳均资本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大小与统计显著性基本都高于总体样本,说明本文提出的经济机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表3 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发达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续表3

短期均衡关系被解释变量 ln(K/L)LSLSLS Crisis-0.019***(2.86)0.023***(3.22)0.025***(3.27) AR(1)检验0.002***0.001***0.001***0.001*** AR(2)检验0.1690.9860.9610.973 Sargan检验0.4190.1890.1460.173 中长期稳定关系被解释变量 ln(K/L)LSLSLS ln(K/L)--0.128*(-1.75)--0.147(-1.64) Money(-1)0.316**(2.53)--0.146**(-2.34)-0.031(-0.36) ln(PGDP)0.919***(5.20)--- Crisis-0.015(0.97)0.027**(2.63)0.035***(2.88) N865535483462 R20.6240.0670.0360.087
注:(1)括号中为t统计量;(2)系数标准误使用国家层面聚类稳健估计法得到;(3)AR(1)、AR(2)与Sargan检验提供的是p值;(4)***、**、*分别表示1%、5%及10%的显著性水平。
表3提供了发达国家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动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滞后项表现与前相似,不再赘述。这些结果反映了与前边的回归表格全然不同的信息:(1)短期均衡中,货币扩张对劳均资本存量的影响不显著,此时理论假说1与中介效应检验的路径不成立。但在中长期,货币扩张能够加快资本深化速度,估计系数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至少在短期,货币扩张、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的机理对货币政策较为稳健的发达国家分样本不成立,路径与理论假说1不能完全得证;(2)对于以劳动收入份额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而言,短期均衡中,劳均资本和货币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虽然为负,但也只通过了10%与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两者同时进入模型时都变得不显著,短期中介效应检验的路径不能成立。在中长期资本深化与货币扩张的估计系数也单独地体现出一定的显著性,但两者同时进入模型时也都不显著,路径仍不能成立。而且,各变量的系数大小和t统计量相对于总体样本与发展中国家子样本而言都明显较小。于此,我们证明了猜想,即在货币政策较为独立而稳健的发达国家,货币扩张与资本深化对厂商投入决策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侵蚀相对更低。
以上的结果启示我们,执行稳健审慎的货币政策、保持要素相对价格的平稳对维持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稳健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欧元区的设立为进一步深入检验本文的稳健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欧洲央行的运行独立于欧盟各国政府,货币政策以维持币值与物价的稳定为基本目标,自成立起欧洲央行的决策便以稳健而审慎著称。申请加入欧元区后,成员国政府失去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⑬我们预期,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扩张之手”被束缚,本文的机理可能也是不成立的。表4提供了欧元区国家的分样本回归结果。

表4 货币扩张、资本深化与劳动收入份额:欧元区国家样本回归结果
注:(1)括号中为t统计量;(2)系数标准误使用国家层面聚类稳健估计法得到;(3)AR(1)、AR(2)与Sargan检验提供的是p值;(4)***、**、*分别表示1%、5%及10%的显著性水平。
表格上半部分的动态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表现与前相似。这些结果显示:(1)在短期,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扩张对于劳均资本深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理论假说1与中介效应检验的路径得证。但在以劳动收入份额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中,劳均资本与货币变量无论是单独或联合进入模型,均不表现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的路径、与都不成立,这与发达国家分样本的结果是非常相似的;(2)中长期的结果与短期均衡相似,货币扩张对资本深化的解释力虽然显著,但劳均资本的增加和货币扩张均不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本文所提出的经济机理是不成立的。
总而言之,对于货币政策操作以独立、审慎而稳健而著称的发达国家样本或欧元区国家样本而言,“货币扩张→劳均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环环相扣的传导机制不能完全成立,而这一机理对发展中国家样本的解释力最强。我们从中得到的政策启示是,保护央行操作的独立性、执行审慎而稳健的货币政策、遏制货币超发冲动对于维持相对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与宏观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与启示
劳动收入份额的普遍下降是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失衡问题之一。扭转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需要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成因进行正确的解读。有别于经典文献所给出的产业结构变迁、贸易扩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解释角度,本文另辟蹊径,尝试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为其提供一个解释:世界各国持续的货币扩张使实际利率下降、信贷规模扩大,因此厂商使用资本品的成本下降,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诱使企业调整投入决策,在生产中使用更多的资本品;在资本与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的条件下,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劳均资本的快速深化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理论模型推导,本文实证检验的基本发现是:货币扩张与资本深化均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面影响,且劳均资本的上升是货币扩张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的作用渠道。分样本回归揭示,本文提出的经济机理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对于货币政策较为审慎稳健的发达国家与欧元区国家而言部分传导机制不成立。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非常明晰的政策含义:确立以物价水平与国际汇兑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导向、遏制为弥补政府财政赤字或刺激增长而超发货币的冲动,避免信贷规模的大起大落以及对厂商生产决策的扭曲对于维持要素相对价格与收入份额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左右的高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在高速发展背后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内外失衡的经济体——在解读这些失衡现象时,我们注意到两大长期并存的典型事实:
其一,与全球的情况相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成为一个突出问题。无论是根据Feenstra et al.(2013)在宏观层面上的测算或是本文的数据来源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在企业部门层面上的测算,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下降幅度均超过了10%。初次分配失衡导致总需求结构中消费偏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利益分配的矛盾频频诱发社会危机,广大劳动人民难以平等地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更有学者提出了“国进民退”的尖锐批评;
其二,快速的货币扩张与资本高积累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回顾过去十余年中国的每轮宏观调控,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截止至2014年底,中国的M2/GDP已高达193%,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在2015年,面对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央行频频降息降准“放水救市”已然成为常态。宽松的货币政策所释放的过剩流动性使得社会信贷规模快速扩张、实际利率持续偏低。陈彦斌等(2014)指出,根据国际经验,当实际GDP增长率在10%左右的时候,实际贷款利率应该在7%左右,而中国近十年的平均实际贷款利率仅为3.56%,这对企业生产决策的制定形成了严重的扭曲;陈宇峰等(2013)证明,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并在低位运行的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中国持续快速下降的劳动收入份额的背后推手之一为严重的货币扩张现象。过往二十年来的多轮信贷规模快速增长扭曲了微观企业主体的技术选择,引致了高强度的“逆资源禀赋”偏向技术进步;而且,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型背景下,这种技术偏向还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劳动力工资被压制,进一步恶化了要素收入分配状况。因此,我们认为,遏制货币快速扩张、提升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势在必行的改革。对于中国而言,执行审慎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均衡与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对扭转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不利格局亦具有“另辟蹊径”的作用。
1. 陈彦斌、陈小亮、陈伟泽:《利率管制与总需求结构失衡》[J],《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2. 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J],《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
3.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J],《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
4.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J],《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
5. Acemoglu D., Guerrieri V., 2008.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 Vol.116(3), pp 467-498.
6. Acemoglu D., 2002.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J]., Vol.69(4), pp 781-809.
7. Acemoglu D., 2007. “Equilibrium Bias of Technology”[J]., Vol.75(5), pp 1371-1409.
8. Acemoglu D., 2003. “Labor and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J]., Vol.1(1), pp 1-37.
9. Baron R. M.,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Vol.51(6), pp 1173-1182.
10. Bentolila S., Saint-Paul G., 2003. “Explaining Movements in the Labor Share”[J]., Vol.3(1), pp 1-33.
11. Blanchard O. J., Nordhaus W. D., Phelps E. S., 1997. “The Medium Run”[J]., Vol.2, pp 89-158.
12. Cobb C. W., Douglas P. H.,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J]., Vol.18(1), pp 139-165.
13. Crowe C., Meade E. E., 2008.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Transparency: Evolution and Effectiveness”[J]., Vol.24(4), pp 763-777.
14. Feenstra R. C., Inklaar R., Timmer M., 2013.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9255.
15. Gollin D., 2002,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 Vol.110(2), pp 458-474.
16. Hicks J. R., 1932. “[M]. London: Macmillan.
17. Hutchinson J., Persyn D., 2012. “Globalisation, Concentration and Footloose Firms: In Search of the Main Cause of the Declining Labour Share”[J]., Vol.148(1), pp 17-43.
18. Kaldor N., 1961. “[M]. Macmillan.
19. Karabarbounis L., Neiman B.,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J]., Vol.129(1), pp 61-103.
20. Rodrik D., 1999. “Democracies Pay Higher Wages”[J]., Vol.114(3), pp 707-738.
21. Solow R. M., 1958. “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elative Shares”[J]., Vol.48(4), pp 618-631.
22. Vreeland J. R., 2002. “The Effect of IMF Programs on Labor”[J]., Vol.30(1), pp 121-139.
(L)
①根据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与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的讨论,可将劳均资本引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模型中,如果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则>1成立。后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这一假设。
②详见Mundell(1965)、Tobin(1965)的讨论。此外,Fischer(1979)证明,即便在Sidrauski(1967)的货币中性模型中,在经济向稳态收敛的非均衡路径上,货币扩张速度越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也越快。
③这些假定是为了简化理论推导分析。审稿专家提醒,在产能过剩或需求不足的危机环境中,要素与产品市场无法出清,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能不存在——正如我们从图1中看到,在全球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长期趋势中,在数次影响较大的经济危机发生的时间点上,劳动收入份额都出现了轻微反弹。因此,实证部分引入虚拟变量对经济危机进行识别,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需求面因素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④我们还可以以货币变量是否失去统计显著性将资本深化在货币扩张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间所起的传导机制区分为完全中介效应(complete mediator effect)与部分中介效应(partial mediator effect)。
⑤我们将货币指标滞后一期的原因有二:其一是规避经济数据或多或少存在的同步性引发的内生性偏误;其二为考虑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时滞性。在各个回归中,我们尝试将货币指标的当期值、滞后一期以及滞后两期值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在大部分情形中滞后一期值具有更高的统计显著性。
⑥分别为两次石油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以及近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
⑦系统GMM估计法使用更多的工具变量以提升估计效率。我们也尝试了系统GMM法,但Sargan检验在大部分情形中拒绝了原假设,新增的工具变量非严格外生,因此我们仅报告差分GMM估计结果。
⑧回归中劳均资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这印证了理论部分假设 大于1是合理的。
⑨关注危机变量,可以发现其在短期均衡中显著为正,在中长期中虽不显著但仍为正,印证了我们从图1中看到的劳动收入份额在危机期出现的轻微反弹。后文的其他回归结果相似,不再赘述。这体现了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特征,该现象的主要解释包括合同签署交错、信息与工资粘性、劳动合同风险转移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Taylor(1980)、Calvo(1983)等。
⑩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居民部门“补贴”企业部门、或曰存款者“补贴”贷款者的扭曲制度安排,在这种情形下,总产出更高,但经济结构失衡、存款的财富效应不足、社会总福利水平反而受损。
⑪本文样本包括28个发达国家(地区):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香港、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其余28国界定为发展中国家。
⑫在分样本回归中,根据AR(1)、AR(2)与Sargan检验的结果,动态模型中引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两阶,如果仅滞后一阶,大部分情形下AR(1)、AR(2)检验结果都呈现显著,模型设定错误。
⑬我们知道,欧元区的准入标准主要为政府财政赤字、公共债务、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率几项指标,与各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无关,更不存在要素分配状况“倒逼”欧元区设立的可能性。因此欧元区分样本回归可以排除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有助于验证本文机理的稳健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下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机制研究》(编号:15CJL025)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工作底稿曾于首都经济与贸易大学第五届哈博·高校(经管)博士学术论坛报告,作者感谢华南师范大学李长洪硕士、北京大学赵秋运博士、南开大学刘铠豪博士的点评。芝加哥大学KarabarbounisLoukas副教授热忱地分享了实证研究数据,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的修改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作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