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猎人的哀歌》:关于历史与未来的对谈
许旺
中亚民族以猎牧为生,站在悬崖边缘,回看来路崎岖不平,向前远望却又无路可走,“悬崖猎人的哀歌”既是两位诗人的哀歌,也是整个中亚民族的哀歌。中亚民族历史上受到外族的压迫,展望未来依然前途艰辛,两位诗人正站在悬崖边缘,为民族命运苦苦求索。于是,这本谈话录定名为《悬崖猎人的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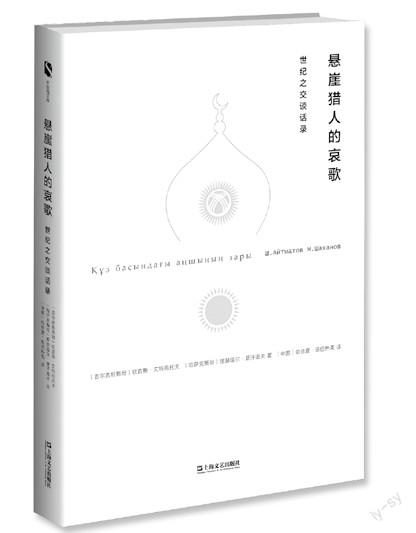
在2015年8月底的上海书展上,《悬崖猎人的哀歌》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曾经在国内的文学杂志上刊登过几个章节,但它的全译本却到今天才完整出版。这是两位作家的谈话录。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吉尔吉斯斯坦诗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100多种文字,对当代中国作家有深刻的影响;穆赫塔尔·夏汉诺夫是哈萨克斯坦作家,获得过很多国内外奖项。两位诗人虽不是兄弟,却胜似手足,夏汉诺夫亲切地称艾特玛托夫为兄长。两位精神上高度一致的挚友的对谈,为我们留下了这部优秀的作品。
在谈话的开头,夏汉诺夫提出,每个人除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还有四位母亲。他用诗歌如此表达:
除了自己亲爱的母亲之外,/每个人还应当拥有四位母亲,/她会使你的生命拥有主心骨,/她会一路激励着你鞭策着你。/故乡是你的根基,你的光荣,/母语是你的教养,你的骄傲。/习俗是你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支柱,/它会一路为你洒下灿烂阳光。/还有那母族艰辛悲壮的历史,/尽管回忆起它是多么地痛苦。
两位诗人围绕着故乡、母语、习俗、历史这四位母亲,展开了他们在世纪之交的谈话。
切克尔是艾特玛托夫的故乡。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艾特玛托夫的父亲托热胡勒被打为“人民公敌”,被捕前夕,托热胡勒让妻子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故乡切克尔,正是故乡庇护着“人民公敌”的妻子和孩子们活了下来。夏汉诺夫的父亲也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父亲总是抱着不到9岁的夏汉诺夫,给他讲述先祖抗击成吉思汗、保卫沃特拉尔城的故事。母亲问父亲,年龄尚小的夏汉诺夫能懂吗?父亲坚定地回答,他必须懂,因为不能植根于沃土的树终将短命。1992年,沃特拉尔为夏汉诺夫举办了文学创作庆祝晚会,三位老奶奶把用白绢丝手帕做成的护身符挂在了夏汉诺夫的脖子上,里面装着一抔故乡的黑土,这成了夏汉诺夫最为珍贵的礼物。就像诗人所说的那样,骆驼刺扎根于地下几十米,在干旱的沙漠依然顽强地生存着,而无根的蓬蓬草却注定只能随风飘摇,一个人永远不能忘记自己的故乡,否则他将无法认识生活的意义。

两位诗人没有专门谈到民族的习俗,但从他们讲述的故事里,却处处可以看到中亚民族的风情和神秘的中亚习俗。比如他们提到,在中亚广袤的草原上,各民族有一个习俗,七代之内不准通婚,因为他们认为近亲结婚不利于民族后代的茁壮成长。曾经有一对表兄妹相爱了,母亲无法阻止,只得写信请求夏汉诺夫劝说他们不要做出破坏民族习俗的事,因为夏汉诺夫是他们最崇拜的诗人。在龙卡吉尔人的部落里,男主人甚至希望客人和自己的妻子过夜,以此来让民族的基因更加多样,让民族的后代更加强壮。中亚也有诗歌朗诵的习俗,诗人重点介绍了几位朗诵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诗人,让我们看到了吉尔吉斯人对于民族文化的热爱。哈萨克族有200多种禁忌,但现在却越来越少地被人们遵守了,诗人对此感到痛心,因为民族禁忌是民族特征、文化、语言和信仰的标志,实质上是民族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要组成部分,忘却民族习俗也就失去了一个民族的独特性。
两位诗人在追溯民族历史的时候提到了民族的母语。突厥民族最早的文字是鲁尼文,比欧洲文字产生的时间更早,对此两位诗人都很自豪。可是自阿拉伯人入侵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都是以阿拉伯文为官方文字,直到1930年才改用俄文。中亚出土了很多碑刻,却因为保护不够而损毁,上面记录的各种文字也无法辨认,对此两位诗人又深感痛惜。民族母语的缺失和古代石刻的破坏,造成了中亚民族历史的断层,不得不从外族和周边国家史书的记载中去探寻自己民族历史的踪迹。由此可见民族母语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的重要性。没有母语或忘记母语的民族很难呈现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保护母语就是在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化。
我们不得不佩服两位诗人丰富的学识,他们谈到了突厥民族的历史,从两千年前到现在,两位诗人如数家珍般讲述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侃侃而谈不同部落之间的纷争。他们谈到了伟大的作家穆赫塔尔·阿乌埃佐夫,谈到了诗人江布尔和英雄夏布丹之间的崇高友谊,也提到了著名的学者乔汗·瓦利汉诺夫……通过两位诗人的讲述,一个个民族伟人更加鲜活、真实地站在了读者面前;不同部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共时的和历时的,都如地图般清晰地跃然纸上。正如艾特玛托夫所说,对于民族的历史,如果不能真实客观地描述,这将是无法原谅的罪恶,只有将本民族的历史和别国的荣辱兴衰史相比较,才能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两位诗人对民族历史的把握,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自己抗在肩上的民族责任。
对于历史上的统治者,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不会忘记。“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将各类人群聚拢在一起,寻找共同的利益,维护民族统一,发展民族文化,稳定内外政策,增强国力——这是艰辛而又崇高的职责,不一定每一位国家元首都能胜任”。无论贤明或昏庸,无论贡献卓著还是骂名昭著,统治者都会在民族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两位诗人在对谈中提到了几位中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有的振兴了国家民族,为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也有的因为战略性失误,让国家在动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作为统治者,他们最终会被千千万万的中亚人民记住,时间和历史会给出公正的评判。
说起历史,便不得不提成吉思汗。现在一些人盲目崇拜成吉思汗,两位诗人对这样的现象感到担忧。成吉思汗扫荡了亚欧大陆,他的西征成为所有突厥民族的苦难。成吉思汗所到之地无不是残崖断壁、哀鸿遍野。诗人反对神化成吉思汗,担心这样会带来战争的危险,战争是惨无人道的。因此每个民族都应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思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赞扬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君主,甚至以元代版图最大而自豪,却忽略了战争的残酷,忘记了征讨过程中的血腥屠杀。两位诗人对成吉思汗的评价,从一个受压迫民族的角度,向我们描述了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给突厥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让我们突破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站在世界性高度,深刻反思通过杀戮来扩大国家版图的非正义性,重新评论成吉思汗的是非功过。“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正反两面正确地认识和客观地评价成吉思汗,反思战争的残酷和非人道,才会更加珍视当今世界和平局面的来之不易,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指明方向。
除了对历史的回看,两位诗人也关注着现实。他们谈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环境危机,死海问题是夏汉诺夫为之呐喊的一个生态对象。他们的言谈之中充满了“万物有灵”的色彩,认为自然界的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生命都有像人类一样的灵魂,所以人类必须善待生命。他们也谈到了中亚国家青年人的精神现状,提及了一种叫“曼库尔特”的酷刑。古时部落纷争不断,被捕获的战俘会充当奴隶去放牧,但他们常常伺机逃走。为了防止战俘逃走,“曼库尔特”酷刑被发明了出来。常用的方法是在战俘的头上裹上一层骆驼皮,用绳子扎紧,然后把战俘拉到烈日下暴晒,骆驼皮因干燥而收紧,战俘的头被紧紧包在里面。战俘的头发由于无法向上生长而倒扎到头皮中,加上骆驼皮收缩的压力,会严重破坏战俘的脑神经,他们要么痛苦地死去,活下来的则不再妄图逃脱,成为一个“曼库尔特”。受到这种刑罚的人将会忘记自己的历史,永远受到精神的奴役。而当今的很多年轻人,也正在遗忘自己民族的历史,很少思考自己的生活,只是学着别人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变成了现代的曼库尔特。对于这样的情况,两位诗人颇感忧虑。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民族,不是一个正常成长的民族,这样的民族终将会慢慢走向衰亡,成为曼库尔特民族。这不仅仅是对中亚民族的悲思,也是对整个人类的悲思,当人类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整个人类也将变成一个曼库尔特。

最后,两位诗人还谈到了伟大的爱情——艾特玛托夫与布布萨拉的爱情,夏汉诺夫与库兰达的爱情,虽然他们没有进入婚姻的殿堂,但伟大的爱情却足以感动所有读者。布布萨拉是著名的歌剧演员,把一生献给了艺术;艾特玛托夫则是真正的诗人,把一生献给了文学。两个人一见钟情,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产生了伟大的爱情并相爱一生,直到十几年后布布萨拉因病去世。进入剧院,艾特玛托夫常常会想起过世的布布萨拉,哀婉欲绝。他们的爱情是纯粹的爱情,不是肉体的欢愉,而是灵魂的相悦。相比之下,夏汉诺夫的爱情则更凄惨。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两情相悦,他们的爱情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就在要修得圆满、喜结连理之时,库兰达在坐火车时出了意外,惨死在车轮之下,从此夏汉诺夫郁郁寡欢,心情久久无法平复。两位诗人都遇到了伟大的爱情,而坎坷的爱情之路又为人生平添了几番曲折。此外,他们还回忆了历史上的女性,回忆了历史上的爱情。没有爱情的生活是平淡无奇的,只有真正的爱情才能让生活变得伟大,这是两位诗人得出的结论。
故乡、母语、习俗、历史,都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传承不息的万河之源。因此,保护这四位母亲,就是在保护一个民族,让这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展现自己民族的独特魅力。
两位诗人的对话,是关于历史与未来的对话。他们畅谈古今,纵横捭阖,既不失对历史问题的深刻思考,又看到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忧国忧民。这不是一本深奥的史学著作,而是用简明易懂的语言传达的历史哲思。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敏锐的思辨眼光,给读者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