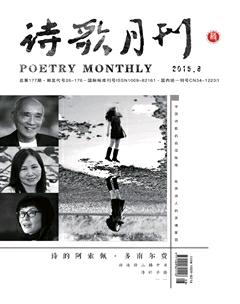张默访谈:诗路无涯
张默+朱育颖
主持人语:
张默,这位台湾《创世纪》诗刊创始人元老,被誉为两岸新诗推手。一个甲子以来,他写诗、读诗、评诗、编诗、抄诗,乐在其中,以卓然特立的风采,行使着诗歌的使命,诗路无涯,矢志不渝。而且,张默的籍贯是安徽,令我们顿感亲切。本刊借以推出合肥学院中文系教授朱育颖到台湾访学时对张默的采访,据朱育颖教授说,“这位愈老愈勇的前辈不像是85岁的老人,腰板挺得直直的,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如洪钟,略带一些徽音。”
一一兰坡
朱育颖:张先生您好,您是著名的诗人、诗评家,也是我的安徽老乡,记得去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2014年“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您,曾经一起合影留念,一起参加学术交流与联谊活动。又逢6月,再次见到您非常高兴。我想知道,20世纪中叶,什么原因促使您远离家乡渡海来台?当年,您“十八岁出门远行”,请您能否谈一谈青少年时期的家庭情况与个人经历?
张默:我是1949年春从南京到上海再到台北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大哥1946年就到了台湾,在海军做事情,1948年春节他写信给我妈妈,希望我到台湾来,那时候我在南京燕子矶读高中。1949年3月我离开南京到上海,住在一个朋友家里,然后从上海搭乘中心轮在海上漂流了三天,到了台湾。我六岁在安徽无为读私塾,老师也就是舅父孙国相教我读四书五经,背三字经,背古文观止,背唐诗宋词,练大小楷,他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每天早晨上课时磨墨四十分钟,我第一次磨墨没有经验嘛,弄得一身都是墨汁,妈妈还为此揍了我一顿。我很感谢六岁到十岁的五年,舅父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古文根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念古文,很多篇章,比如《滕王阁序》《秋声赋》《前赤壁赋》等我都会背诵。我先在家乡无为读简易师范,然后1946年到南京成美中学读书。现在变成24中了。成美中学有个老师叫虞诗舟,他教我们古文,讲解名篇,介绍五四时期刘大白、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使我对新文学产生了兴趣。他还介绍巴黎花都、伦敦大桥和海外风光。从小我就想将来如果有机会要环游世界。他仔细批改我们的作文,他的行书更是苍劲有力。初中毕业那年,他给每位同学写了 首诗,送给我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我如获至宝,并于1949年春天带到台湾,可惜后来搞丢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一个是舅父孙国相,一个是老师虞诗舟,这两个是我的恩人,假如没有两位前辈的启蒙,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了。
朱育颖:您在《无为诗帖》中多次提到故乡安徽无为孙家湾的老屋、池塘、风车,您认为自己的生命之根在哪里呢?无为、南京,还是台北?无为老家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张默:我想啊,一个人呐,特别是我们老一代的,不能够忘本,根本,刚才我讲了,假如当初不是我的舅舅教我读古文和四书五经的话,也就没有今天的我。家乡无为的点点滴滴都是我珍贵的回忆。我侄子第一次带我回无为老家时,那个小池塘还在,过去的茅草棚没有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在池塘里游泳,小河、断桥、老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个人来说,无为是我的老家,生我的地方;抗战时我到了南京上学,南京是养我的地方:在台湾的时间最久,台北是我的事业发展的地方。写诗呀,办诗刊呀,几十年投入新诗的写作与文学活动,希望为爱好诗的两岸朋友多服务。这三个地方对我来说是同等重要的,不分主次。
朱育颖:台湾有很多诗都是写乡愁的,1980到90年代您写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思亲怀乡之作,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乡愁与放逐之感,比如《家信》《白发吟》《包谷上的眼睛》《苍茫的影像》等,有思念母亲的、怀念故乡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您怎么看待乡愁呢?
张默:1979年我通过大哥在香港的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陆我老母亲健在的音讯,这个消息震撼了我的心灵,压抑了三十多年的乡愁,一下子爆发出来,含着热泪写了一些乡愁诗。乡愁是必然的,我少小离家,同大陆几十年没接触,1988年才开放,在台湾呆了几十年。乡愁是与生俱来的,基本上讲,并没有什么地域性,我在台湾常常想大陆,在大陆住一段时间,我也会想台湾的。
朱育颖: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到“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中国文人对于回归故乡似乎总是怀着迷茫、忐忑的复杂心情。1990年代以来,您曾多次回大陆参加文化交流活动,也曾重返老家一一安徽无为孙家湾,可否说说“回家”的感受?
张默:得知老母亲还健在,我们就开始想办法联系。1987年6月,那时我在台北一个杂志当主编,具体哪一天我记不得了,通过一个朋友,我在香港一个写字楼办了大陆入境证,先到广州,然后坐飞机到了南京。那时还没“解严”,没开放,我住在南京玄武湖一个大饭店,中午时分我母亲由我弟弟陪同到了饭店。我在电梯口迎接母亲,把母亲搀扶到电梯里,上了玄武湖饭店的8楼,到了房间以后,我抱住母亲不放,哭了十几分钟,开始我妈妈讲话我听不懂,后来慢慢就了解了。我们在玄武湖饭店请了一臬,那时候吃饭很有意思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外面有七八个人在等。38年不见,老妈妈还在,真不容易呀!老妈妈讲了老家的许多事情,我感慨万千。第二天下午我们回去,老妈妈就走了。38年不见,不容易呀!回来后我写了 首诗,叫《惊晤》,一字一泪写的,因为想不到还会见到老母亲。1988年我到北京开会,还朗诵这首诗。1988年9月,我离家将近四十年之后,终于回到老家安徽无为孙家湾,当时三垄头的老屋还在,年迈的母亲踉踉跄跄一步一步移过来,朴实的三弟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还有一些侄子辈、孙子辈的、一大群乡亲挤在门口,一股特别亲切的气息紧紧包裹着我,好像是在梦里。乡下那时很穷,南京的亲人就不一样了。1990年1月底,我回大陆陪老母亲过春节,她老人家高兴地合不拢嘴,那时南京正下着大雪,我和母亲特意在家门口大雪中照了 张相,非常珍贵。这一幕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忘记。2001年我和大哥回到安徽无为,探望几十年没有谋面的表弟孙大明,当年的池塘、小石板桥还在,风车在我表弟家里,老屋没有了。小的时候最喜欢老师出去,我好去游泳,怕老师看到湿头发,就用老屋的风车吹干。看到故乡的时候,尤其是故乡的一些人和物,心里感触还是很多的。在八卦洲有一座我母亲的坟墓,2006年,我大哥走了,他的骨灰摆在我母亲坟墓的旁边,田头有四棵松树,现在长得好大好大,哎呀,不得了!庇护海内外的两家人,我母亲是第五代掌门人,我告诉南京的侄女婿要把这座坟墓照看好。
朱育颖:您在台海两岸分别有“家”,无为孙家湾是您的老家,台北内湖区也有您的家,从照片上看您的夫人端庄贤惠,我在电话中听到她的声音和蔼亲切,她是河南开封人,您还有两个女儿。一个甲子过去了,您怎样看待两岸这两个“故乡”?
张默:我在海内外有两家人,两个女儿和女婿在台湾奋斗,小外孙已经10岁了,还有一二十个家人都很棒,其他在大陆的亲人也很好。侄孙女马婕很有才气,喜欢朗诵。这次我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参加新出的诗集发布会,她就朗诵我的诗。两岸的亲人虽然分开了,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都在各自的环境里创造着自己的幸福,都在快乐的生活。人在世间,快乐很重要,星云大师说: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这九个字太厉害了呀,人要有这九个字就够了,能长寿呀
朱育颖:您在海军服务多年,长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请问海洋有无给予您人生的启示与感悟?您是从何时开始诗歌创作的?
张默:其实我在南京读书时就学着写诗了,真正开始写诗是在民国,大概1951年左右。那时在台湾我就想法从军啊,从军后就被派到海军去。其实,小时候,在我的家乡无为,舅父经常带我们坐船到江上运米,当然海和江是不一样的。我在海军服务了22年,那种感觉又不一样。海呀,海的那种汹涌澎湃,那种冲击力,那种感觉是没办法形容的。
朱育颖:我比较喜欢大海,特别喜欢海的气势、海天一色的景观,看了您早期写的一些海洋诗,我觉得诗中的海有生命的质感,是您个人的独特感受与内心的风景,可以这样理解吗?
张默:对,是呀,海洋的题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早期写了很多海洋诗,但我在发表作品时都没用。到第11期,《关于海哟》,这首诗我比较喜欢,那种调子,那种旋律,那种气氛,把海的那种壮淘、深邃写了出来。不是别人的感觉,而是我个人的感觉。诗是感觉的投射,不是单纯地写海的风景,而是想用中国文字来展示海的生命,海的气势,那种变幻,那种魅力,没法形容的。
朱育颖:您认为“诗是意象的涌动”,不少诗中写了“田园”与“海洋”,这两种自然景观如何化作您诗中的意象?海洋与土地二者有无矛盾?您自己最满意的诗作有哪些?
张默:其实“田园”、“海洋”,实际上都是土地,讲良心话,“田园”不只是指无为,如《无为诗帖》,每个地方都可以写,到海外去,看到不同的海域,感觉又不一样。我觉得土地与海洋可以说是一体的,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这两方面没有什么矛盾,是一体两面。一首诗可以说是某种特殊经验的绽放,是生命意象的霍霍涌动,只要你多观察,多体验,多深入,就会使你的诗更丰富,更充实,更有魅力。
我自己喜欢的诗,这么多年,其实还是有的。我曾经写了一首《三十三间堂》不知你看过没有?
朱育颖:看过这首诗,实话实说,没有好好细读。
张默:这首诗与坐落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斜对面的“三十三间堂”毫无关系,它是我对社会的观察、历史的流变,对文化的、乡土的、个人的一个综合感受,具体的很难讲出来,这首诗我蛮喜欢。另外还有一首《贝多芬》我很喜欢,这是一首长诗,有六七十行。本来我不怎么喜欢音乐,为了写贝多芬,就买了一些专门研究贝多芬的书来看,不是光赞美他,而是用诗的语言来勾勒一位音乐巨人的形象,痖弦说我能够深刻体悟一代乐圣对音乐的执著精神,是贝氏音乐内涵的最佳展示,用诗把音乐巨人表现出来。这次我到南京开新书发布会,有两个女大学生朗诵了《贝多芬》,这首诗在台湾从来没有朗诵过。
朱育颖:您好像特别喜欢旅游,一直在路上奔波探寻,19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您写了许多很棒的旅游诗,能说一说您的想法和感受吗?
张默:是的,我喜欢旅游,写了很多旅游诗,比如《长安三贴》《黄山四咏》《昂首,燕子矶》《海德尔堡》《中秋莅日登巴黎铁塔》等等。你不是导游,你是写诗的人,旅游诗是通过诗人的眼睛对这个风景独特的观察,发现新的素材,新的感觉,抓住某一点,让别人去体会。
一个写诗的人,旅游也很不容易,我1988年退休后,也没有多少钱,为了想旅游,去周游世界,有一个朋友劝我买股票,赚了一些,全用在旅游上了,实在不容易呀。我到罗马去,到北欧去,领略异国风情。比如我们到埃及,看到金字塔,就想它当年是怎么建起来的?就像中国的万里长城怎么建起来的?俄罗斯有许多铜像,列宁图书馆前的铜像是谁?不是列宁,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小说大家,很厉害的,我没想到塑的是他的铜像,就写出来了。旅游诗咏景并不容易写,并非一个作者把他所见到的景物一一铺陈在诗里就算了事,必须努力使自己的灵魂进入他所表现的风景中,不能忽视“情”的吐露与“境”的造设,务必使景、情、境三者水乳交融。诗是语言的变貌,诗的语言是精炼的,一个优秀的诗人无不致力于语言的创新与意象的营建,开发语言,活用语言。写诗的朋友要发现新的素材,新的景象,一首诗的意象不要太多,不要太散,要集中一些,诗是精炼的,拉的太长就没有意思了。
朱育颖:《创世纪》诗社是台湾新诗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现代诗歌文学团体之一,1954年10月,您和洛夫、痖弦在高雄左营发起成立创世纪诗社的初衷是什么?
张默:《创世纪》发刊时的初衷很简单,我们就是想为台湾南部增加 本诗歌刊物,给写诗的朋友提供 个园地。1954年6月,我在左营带着小板凳到礼堂开会,结识了洛夫。有一天看书时,我看到“创世纪”三个字,萌发了创办一个诗刊的想法,我告诉洛夫,他说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就开始筹办,痖弦稍后加入。开始条件很艰苦,我们几人都在军中服务,薪资不高,一个月只有一百多元,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初期全由同仁自掏腰包,分摊印刷费。那时我们也不懂怎么编辑,就用纪弦的《现代诗》做样本,依样画葫芦,这是我们的演习阶段。出一期要四百多元,我们就四处凑钱。前10期搞了四五年,属于“试验期”,艰难运转,难以细说。
朱育颖:听说您为了筹措《创世纪》的印刷费还多次进当铺,都当什么呀?您被人称为“诗痴”,是什么动力支撑您为《创世纪》诗社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了一个甲子?
张默:哈哈,不好意思,当过单车呀,手表呀,怎么办呢?救急吧,常常想着下次该拿什么进当铺当作印刷费。那时是蛮辛苦的,出了这一期,就不知道下一期怎么办?《创世纪》出刊的时候,我和痖弦就把刊物放在大筐里,两人用一根扁担抬到邮局里去邮寄。我曾把诗刊一包一包从印刷厂往邮局扛,然后寄到各个书店。过程是漫长的,太困难了,其中的甘苦一言难尽。白先勇称赞《创世纪》是有九条命的长命猫,永远不会死。诗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爱诗,写诗,编诗,一旦我迷上它就无条件的付出。洛夫说我 生所供奉的神就是诗,衣带渐宽终不悔地信仰它,迷恋它,服役于它。
朱育颖:《创世纪》前10期主张“新民族诗型”,第11期改版以后,提倡“超现实主义”诗歌写作,生机勃勃地开始了艺术转向,展示出独特的精神与风貌,请您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说一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诗歌观念的变化呢?
张默:前10期是小本时代,不能与其他刊物抗衡。1956年洛夫在第五期的社论中提出倡导“新民族诗型”的构想,“反对诗是泥古不化的继承,但也不接受诗是移花接木式的横的移植之说。”1959年,台湾诗坛的情况和以往不同了,《现代诗》没有早期那么活跃了,《蓝星》也只剩下一个小本了,洛夫当时在台北外语学校学英文,在受训,认识了不少人。从第11期开始进行扩版,32开改成20开,许多重量级的诗人,如叶维廉、叶笛、季红、碧果、商禽等加入,壮大了阵容。《创世纪》成员除写诗外,还举办各种诗歌活动。当时纪弦是现代派的掌门,主张“现代诗是横的移植,而不是纵的继承”,以现代主义为师,向西洋全面倾斜,《蓝星》的覃子豪和余光中等一批诗人不以为然,主张回归传统,向古典学习,以致双方打了一场热闹的笔墨官司。我们把《创世纪》扩版后,收到余光中等人写的诗。有个评论家言曦在《中央日报》发表四篇文章,叫《新诗闲话》提到《创世纪》第十一期余光中的诗“夏与夜的可疑地带”,“用瓶的水供养”,说这两句话不通,批评新诗是象征主义的末流,这造成了余光中等人长期打笔仗。《创世纪》假如不改版是不行的,“世界性”、“超现实性”、“独创性”和“纯粹性”是我们的口号,到现在还用,我们还介绍欧美具有前卫性的现代诗名家,包括他们的理论与创作,12期出了特辑,13期出了里尔克专辑,以后对波德莱尔、庞德、艾略特、叶芝等人也陆续介绍,翻译、理论、评论全上。到29期,我在澎湖,洛夫在国外,痖弦在越南, 《创世纪》就休刊了。
朱育颖:《创世纪》诗刊是台湾最早介绍大陆朦胧诗的,当时两岸文坛由于政治历史原因断绝交流已经三十多年了,在台湾还处于戒严状态时,《创世纪》第64期就登载了“大陆朦胧诗特辑”,有创作有评论,还收入了“三个崛起”的文章,这是台湾文坛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大陆朦胧诗,可以说是“破冰之举”。《创世纪》后来还开辟了“大陆诗页”,关注大陆诗歌的现象与发展,为两岸文化交流互动做出重大贡献。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张默:好的,从63期开始,我们打算出大陆的朦胧诗,还发了预告,叶维廉把搜集整理的资料用航空挂号从美国寄给当时任《联合报副刊》主编的痖弦,考虑到《联合报副刊》对外的联络往来较多,在信函的接收上应当不会收到当局检查部门过多的干涉,但是寄了两次都收不到。既然有了要办这个专辑的想法,我就不想放弃,报名参加了赴泰国的旅游团,中途在香港停留一天,我就抓紧时间到书店去搜购,买了一本壁华等人编著的《崛起的诗群一一中国当代朦胧诗与诗论选集》,把它偷偷藏在袋子里带回来。1984年6月,我们隆重推出第64期“大陆朦胧诗特辑”,其中有叶维廉、洛夫、壁华等人的评论文章,还有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大陆朦胧诗选、青年诗人笔谈等等。我们不仅最先介绍朦胧诗,关注大陆诗坛,还开辟“大陆诗页”,登载了大陆诗人的作品一百多首,比如海子、韩东等人的诗,《创世纪》同大陆文坛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海子是安徽人呀,很有才气。《创世纪》第82期,收入了海子的诗作,洛夫还把海子的诗印到封面上去。1988年9月,我和洛夫、辛郁、碧果、管管、张堃等六位诗友,联袂赴大陆访问,先后到南京、杭州、绍兴、上海、北京、桂林等地游览并访晤大陆诗人,结识许多人,冯至、臧克家、艾青等都见了。我们还办诗歌朗诵会,台下有很多媒体,后来他们告诉我上电视了,心里很高兴。写诗、编诗,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们为了诗无怨无悔,也遇到一些贵人,得到帮助和支持。当然现在情况好多了,市政府呀、文学馆呀赞助一些。
朱育颖:您既是著名的诗人,也是诗评家,近年来通俗文化与大众传媒给诗歌创作带来很大的困扰和冲击,可以谈谈您对当下台湾诗坛的看法吗?
张默: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一直是在不断地实验、吸收、开创、修正以及一波接一波争辩的过程中生长着。诗坛早期打笔仗,现在各人搞各人的,诗的素材多元化,电脑资讯日新月异,寻求文字以外多媒体的呈现与组合。年轻人在网上写诗成名,并不是坏事,他们还是要出书的,这是好事。不是不能批评,找茬不太好,要找一些好的诗来谈嘛。
朱育颖:台湾有不少诗人是我们安徽籍的,不光有您,还有钟鼎文、羊令野、大荒等人,能否谈一谈您的看法?
张默:这几个人都已经走了,钟鼎文、羊令野两人的古文造诣很深,书法和诗也写得很好。钟鼎文是台湾诗坛三老之一,当会长,环境比较好。羊令野的诗有着东方色彩,痖弦称赞他是“画太阳的人”。羊令野家里的电视机摆得很高,站在椅子上开电视的时候一下子摔下来了,老人嘛,七十多岁了,三四天以后,隔壁邻居闻到气味时才发现,1994年走的,也没成家,走得很可惜。大荒的勇武豪迈的气魄早已是闻名的,《存愁》是他的诗集,《九声》是《创世纪》发的,这首长诗很不错,七八章,很有历史感。
朱育颖:您是台湾现代诗运动中挥汗最多的人物之一,被誉为“诗痴”,办诗刊,编诗选,注重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半个多世纪以来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为台湾诗歌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您打算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吗?
张默:是的,我喜欢诗,大半辈子和诗打交道,身体好得很,还编了很多书,有二十几本,没有手抄书,我抄了,刚出版不久,送给你。好了,我带你去《文讯》看看吧!
朱育颖:好的,谢谢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