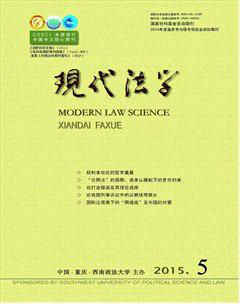杂家尸佼与战国法思想研究
摘要:战国中期的尸佼以“去私”为核心理念,循政治实用原则,折衷各家,“取合诸侯”而开创杂家学派。尸佼之学,提挈道家天地道论以立纲维,归旨于“事少功多”的理想治世;兼采儒、墨道德仁义之说,致力于道德伦理与功利效益的取舍整合;汇合名、法名实之论,呈现出治人层面之“用贤”与治法层面之“案法”的统合性阐释。尸佼之实用观念与折衷主义,乃商鞅变法前后各家学说沿道法转关、儒法融合的思想史谱系演变之先声,其治道法术合拢之旨趣,堪称先秦诸子思想融汇之范本,亦为汉代百家话语归一之先兆。
关键词:尸佼;杂家;商鞅;去私;道;仁义;正名
中图分类号:DF09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5.02
尸佼(约前390-330年),国籍不详。 尸佼生卒年钱穆有所考证。尸佼国籍争议颇多,《史记》记载为楚国人,刘向《别录》认为是晋人,《汉书·艺文志》认为是鲁国人,钱穆则推测尸佼是魏国人。(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16,695.)关于《尸子》,秦汉之际“世多有其书”,《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为二十卷,据《隋书·经籍志》,魏晋时己非全本。清人汪继培《尸子》辑本,综合古人各辑本之优长,详细注明佚文之出处,今人研究多本之。 文献学研究认为《尸子》汪辑本最优。(参见:王彦霞.《尸子》汪辑本初探[J].图书馆杂志,2005(1).)
《后汉书》、《宋史》将尸佼归入儒家 在《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李贤注曰:“尸子,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宋史·艺文志》子部儒家类:《尸子》一卷。,但刘向言尸子“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术”,虽非确当之论,亦可见其疏隔于儒门道统。按说尸佼与商鞅谋划计事,立法理民,似可并归法家行列。不过,史书大多收录《尸子》于子部杂家类,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等。近人金德建曾将尸佼誉为“杂家”创始人,曰:“尸佼年代较早,开创杂家学派。《广泽篇》的说明宗旨,树义如此明确;足为后来的杂家视为准则。”金德建还论证尸佼学说与《荀子·解蔽》、《吕氏春秋·不二》的共通性,以强化尸佼为杂家宗师之观点。(参见:金德建.先秦诸子杂考[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164.)盖为确论。
先秦杂家法思想的研究历来不足,武树臣先生的研究有开山之功,惜乎内容只及《吕览》。 武树臣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撰专“杂家(吕)的法律思想”。(参见:武树臣.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3.)观《尸子》之残篇,固难媲美《吕览》,但时代较早,成于一人,更可显现早在战国中期即有一种融合会通诸子学说的理论尝试。或因循古书辨伪之风气,或囿于儒法冰炭不容之成见,或罔于尸佼国籍界说之纷乱,或畏于其学之杂错漫羡,曾有论者推断《尸子》为伪书,或认为存在两位“尸子”。 “古史辨派”多以尸子为《伪书》,徐文武则认为存在两位“尸子”。(参见:张西堂.《尸子》考证[G]//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46-653;孙次舟.论尸子的真伪[G]//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1-104;徐文武.《尸子》辨[J].孔子研究,2005(4).)其实,尸佼学派属性之聚讼,抑或《尸子》真伪的争辩,反而映衬出尸佼学说之博通。阅者的姿态左右了对其学说的释读,“儒家看到的是仁义,道家看到的是道德,法家看到的是法术。”[1]
尸佼以为,儒、道、名、墨各创学说,为鸱张门户而交相攻讦,皆“弇于私”。有见其时出奴入主之风气,尸佼主张“去私”,摒弃一端之见,归于“一实”。故而,其学大有冲决学派藩篱,总摄各家大旨之气象,既吸纳各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又不拘囿于一家一子之学术立场。由此,发轫于商鞅变法前后的杂学,在先秦思想领域崭露头角,昭示着诸子之学朝向道法转关、儒法融合之趋势。核心理念之包容,学说范畴之圆实,知识方法之融通,治术手段之兼及,此四端盖为杂家学说之特征,亦可为今人诠释之框架,析论如下。
现代法学马腾:杂家尸佼与战国法思想研究一、去私:《尸子》的核心理念《尸子·广泽》云:
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匹夫爱其宅,不爱其邻;诸侯爱其国,不爱其敌。天子兼天下而爱之,大也。
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
在该篇中,尸佼集中阐明杂学宗旨,宣扬“去私”理念。所谓“去私”,既是一个道德论说、是非判断的客观性基础,消除成见、综合学说的共通前提,也意在实质性地从“公私之辩”的角度凝合儒、道、墨之核心精神。
一方面,尸佼“去私”的第一要义在于对智识障碍与认识前见的审视。当代正义论大师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理论模型,精妙地构设一个人们在“原始平等地位”前提下订立“社会契约”的程序,经由对正义观之前见的深刻反思,启示人们冲决现实拘囿之思维定势。(参见: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10.)中国先哲确已有见于自身情境与个人私欲对正义标准的扭曲与消解。尸佼譬喻道:“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私心拘囿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视阈,公心则铺设起人们认知事物的最优平台。因此,“无私,百智之宗也。”(《尸子·治天下》)广博智识的获致与高尚道德的体悟,都根植于去个体化,超越自我前见的平恕之心。表达任何诉求、辨明一切是非,都必须以公心为支撑才能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进而,“去私”的理念,清晰表达了将林立的学术派别与“相非”的学术观点加以提炼统合的抱负。尸佼举例阐释了语义表述的多样化与概念实质内涵的相通性,同理,“若使兼、公、虚、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充类至尽,儒、道、名、墨各家的某些主张,乃至根本精神名异实同,均可在道的统摄下获得统一。 道论与杂家姿态关联密切。(参见:郭齐勇.《尸子·广泽》、《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与《吕氏春秋·不二》中的真理史观之异同[J].中国文化复兴月刊,1990(12).)endprint
另一方面,与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一样,“去私”警惕一种因私而致使正义法则支离破碎的倾向,竭力倡导以天下公利为本。孔子言“仁”,墨子贵“兼”,尸佼则认为“去私”这一语词更能直截明了表达同一义涵。“去私”蕴涵着人性论点:“私”虽为人之本性,但人皆应努力培养“公心”。杂家去私之精神,使得尸佼拒斥杨朱式的绝对个人主义,更偏向于墨翟式“无我”的集体主义。 当然,尸佼也是在承认“私”的前提下言“去私”,毕竟“公”与“私”是相对存在的,绝对的“去私”是不可能的。(参见:徐文武.《尸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学派属性[J].长江大学学报,2007(10):22.)
尸子既沿袭道家“天道无亲”的思想,又吸纳墨家“天志兼爱”一义,故曰“天子兼天下而爱之,大也”。从推天地以明人事,推己而及人的原理出发,自然得出人君“去私”之结论。尸佼亦祖述圣王,认为“舜不歌禽兽而歌民”、“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都是以“大私”为“无私”的典范。《尸子·绰子》说:“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也”,无不渗透着道家“辩证趋反”思维之妙用。所谓“大私”,是“私万方”、“私万国”,将所私之畛域扩充到天下万国,以天下为“私”,亦返为“公”也,故“大私”即“公”。于是,这种逻辑自然演绎出天子之“私利”即天下之“公利”的结论。这又隐约可见儒者进谏君王的情境,天子欲维护自己的“私利”,必以实现天下之“公利”为路径。有感于私见私利对公共生活的妨碍,尸佼以现实主义的眼光关注社会政治中的公私问题,实为对“家天下”之国家秩序与政治形态的写照与诠释,亦为君王制树立一个崇高的政治原则。概言之,尸佼的“去私”论,是彰明一种矫正偏见、倡导包容的学说姿态与伦理情怀,凝合儒、墨诸家之核心精神,并以辩证思维检视历史与现实的公与私的矛盾统一。“去私”论虽有消磨儒、墨诸学精神差异之嫌,但在当时不失为对国家社会与个体生活之间关系的深刻洞见,也构成其“制分正名”之法制言说的伦理基础。
二、道·仁·义:《尸子》的基本范畴近人张琦翔曰:“杂家者,杂取众说而能自立宗旨,杂而能成家也,此所谓杂即调和意义。调和并非凑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众长,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为一,此之谓调和,杂家之意以大矣。”[2]《尸子》融会贯通诸家学说之抱负,自当诉诸一个纲举目张的统合架构,为百家学说的融通提炼出理论基点。尸佼建构了天地、四时、德性与政治合一的宏大框架,将天道、治道、人道联系起来编织其思想体系的大网,“是先秦杂家在内容与形式上构筑大体系的最早尝试。”[3]
(一)“天地之道”:“事少功立”的治世境界
与道家如出一辙,尸佼阐发了“道生万物”的创生论,描述了“天地之道”对万物的玄妙支配,诠释了“道法自然”与“天道无私”的自然平等观念。而且,尸佼也推崇道家“无为之治”,憧憬“事少功多”之治世境界。尸佼本“从道必吉”(《尸子·佚文》)之见,以无事为宗旨,奉行不争原则,不以强行力争天下,拒斥阴谋智巧权术,均不失为对道家道论的继承。兹列下表对照《老子》与《尸子》中的道论言说:《尸子》与《老子》道论对观表《老子》《尸子》创生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地生万物。(《尸子·分》)实存论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老子》第十四章)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莫见其所以亡物,而物亡。(《尸子·贵言》)无私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五章)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袭此行者,谓之天子。(《尸子·治天下》)无事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尸子·分》)反智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执一之道,去智与巧。(《尸子·分》)柔道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水有四德……柔而难犯,弱而难胜,勇也。(《尸子存疑》)在《老子》中,存在着“道-德”的脉络或从天道到人道的思维,经由“德”的外化作用,形而上的“道”本体便落实为具体而普遍的社会规则。 陈鼓应释曰:“落向经验界的‘道,就是‘德。”(参见:陈鼓应.老子今译今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4.)尸佼云:“夫德义也者,视之弗见,听之弗闻,天地以正,万物以遍,无爵而贵,不禄而尊也。”(《尸子·劝学》)在“劝学”以进于“德义”的倡言中,尸佼赋予了“德义”如同天地之道的本体论色彩与普遍性特征。于是,在天地之道落于人间之德的映射轨迹中,尸佼沿用了道家“道-德”的脉络,同时也在天地之道的本体论框架注入儒家的重要德目与实质精神。 另外,《尸子》一书也糅合了阴阳、四时学说。见《尸子·君治》、《尸子·仁意》、《尸子·佚文》。
《尸子·处道》云:“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者谓之大仁。”德、义、礼之训诂,均不离“天地”二字,尸佼旨在构建一个综合性诠释:“德”即是“得”,是天道在人间的折射,是自然之“道”的社会镜像,故曰“天地万物得也”;“义”释为“宜”,同《礼记》之说,实为将“义”诠释为中庸适度性;“礼”称为“体”,阐明了“礼”作为规则整体的形式化义涵。三者之间,义(宜)是德的精神内容,礼是德的体系框架,三者涵义的整合便进于尸佼所谓“大仁”。从《尸子》对道论的沿袭,确可窥见“在道家强大形上系络的统摄之下,战国中晚期的思想特色已然有了一个共识——朝向统治术的整合。”[4]而在这一整合中,尸佼虽借用道家“无为”的话语,但只保留其博大精深的天道本体论,在“治道”层面更多注入的是儒家之“仁德”、墨家之“义利”。吕思勉说:“杂家兼容而并苞之。可谓能揽治法之全。所以异于道家者,驱策众家,亦自成为一种学术,道家专明此义,杂家则合众说以为说耳……后世所谓学者之先驱也。”(参见: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5:158.)胡适说:“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参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C]//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294.)由此看来,“揽治法之全”的《尸子》,纵跨形上道家与儒、道、法统治术之间,一方面,将道家“道生万物”、“执一”的“道—德”形式架构,接续上儒家内圣之仁德与外王之德治的实质内容,以及墨家“兼爱交利”的功用观点与经验主义;另一方面,尸佼的名论凸现了道、儒、法之间的理论接榫,以道家“事少功多”为意旨,综合各种“法”思想,制分且正名,因智而因贤,案法并赏刑,皆在通向“无事”之政治理想的路径中获致其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杂家的集大成著作《吕氏春秋》思想体系之特点,如高诱所说“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尸子》相类。(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3.)endprint
(二)“四仪之德”:儒家“正己治人”的德治理路
尸佼认为,不只万物为天地所化生,伦理道德也是天地之道的人间投射,进而尝试将儒道之义理融于“道-德”系络中。尸佼言“事少功多”,虽有不恃强力、不行间谍等观点,但仍与道家无为之真貌大殊。在德治的范畴中,尸佼转向了儒家的修齐治平,即从圣王自我修德到天下大治的德治理路。《尸子·神明》云:
圣人之身犹日也。夫日圆尺,光盈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烛远,圣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纲苟直,百目皆开。德行苟直,群物皆正。政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则人不从。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诸心而彼正,谓之至政。
考察《尸子》可以发现,彰显于前儒家时代,光大于孔孟学说的传统德目,亦在尸佼之学中层见叠出。陈来的研究揭橥前诸子时代“德行”观念与话语的意义。(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2009:311-368.)《尸子·君治》言“仁则人亲之,义者人尊之”,将仁义奉为君王安身立命、安邦定国的重要原则。《尸子·四仪》曰:“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四仪”之“仁”、“义”、“忠”、“信”无非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范畴,尤其《恕》篇推崇“仁恕”,重视内心修养,均符合儒家之精神。此外,《尸子·佚文》引孔子“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诗诵书,与古人谋”之语,流露出对儒家“法先王”,重诗书的尊重传统姿态的认同。尸佼还讲“守道固穷,则轻王公”,亦不失保有子思恪守道义、傲视权贵的儒者风骨。
既深通儒学精义,谙晓儒家后学,尸佼自然对儒家君民关系论亦推崇备至。他阐明“夫知众类,知我则知人矣”的道理(《尸子·佚文》),着实体现了无异于孔孟推己及人之仁学、仁政思路。而且,《尸子》熟谙儒家式的贵民修辞,如《尸子·处道》引孔子言:“君者盂也,民者水也。孟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尸子·君治》援引子夏将君民关系比作鱼水关系的言说,《尸子·佚文》将民众看作天子、诸侯兴衰灭亡的根本所在。也须承认,尸佼亦流露出将民众视为客体、工具的倾向,竟谓“民者,譬之马也”。(《尸子·佚文》)这已显露出富国强兵变法中驱策民众的功利色彩。故论者指出,尸佼学于儒家,《尸子》是“子思子之学传入秦晋的重要线索”、“儒学通向法家的栈桥”。(参见:魏启鹏.子思之学[G]//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636-641.)
在诸德目之中,尸佼意识到“义”的多向度特征可以统合诸德。他用一番形象比喻加以阐明:“十万之军,无将军必大乱。夫义,万事之将也。国之所以立者义也,人之所以生者亦义也。”佚文中还坚持富、贵、生皆不能易“义”,堪称儒家式舍生取义的崇高命题。可见,尸佼的“义”论,仍保有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色彩,强调个人的道德之自律与内省[5]。
《尸子·贵言》曰:
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
尸佼认识到“一天下”之关键在于令行禁止的法令实效性。然在对社会秩序的审思中,尸佼将“令行禁止”的法律理想治理模式内转到个人内心层面,经由个体自身对“义”的认识与反躬自省,方能获致一种真正的法令实效,最终是为了阐明“心者,身之君也”的结论。所以,在尸佼的法思想中渗透着儒家式的“德治-人治”思路,也与墨家所言“义者,正 《天志上》篇作“政”。孙诒让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义者,正也,言义者所以正治人也。”(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193.)也”(《墨子·天志下》)相类。
(三)“义必利”:墨家“兼爱交利”的实用观念
诚然,尸佼言不离圣王、仁义,却掩盖不住学说的实用特征与功利色彩,反映了战国初期政治道德论的显著发展。尸佼的“义”,虽在“心者,身之君也”的映照下呈现出“内圣”的心性学取向,但也在“治己则人治”的合释中具有“外王”的政治化向度。 尸佼之“义”具有归宿实利的倾向,往往能融入到实践活动中,外化为社会准则,凸显出社会效应。(参见:朱海雷.尸子及其杂家思想[G]//汪继培辑,朱海雷撰.尸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其实,《尸子》中的德性言说,已更多显现出群体秩序的面向。所谓“人待义而后成”,凸显的是人的社会性而非自然性,“义”透露出群体性意味,获得丰足的秩序性义涵。在外转为社会实践,归宿于社会效应的言说中,这一道德尺度又经由个体的自省,参验于主体间而凝合成共识的通用准则,并构筑法律秩序的伦理基石。《尸子·恕》云:“虑中义则智为上,言中义则言为师,事中义则行为法。”“事中义”为“法”,意即“义”在实践运用中发挥其社会效应,外化为法律规范。逆言之,能够称其为“法”的,必须中“义”,这就为“法”的检验树立了一个道德尺度。“事中义”的思路,也就与墨家的“法仪”之说异曲同工。
更重要的是,尸子的道德论,尤其是“义”论,与“利”已不再呈现为紧张对立的关系;相反,尸佼以“义”为核心的“德”染上了浓重的功利色彩,故云“兼爱百姓,务利天下”,且拾墨翟之说以节葬、非乐为中“义”之道。(《尸子·佚文》)有论者指出:“在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上,(杂家)既坚持以义为最高准则,又能注重现实,以利为归宿。”[6]《墨子》有《贵义》篇申“万事莫贵于义”之旨,而《经上》又曰:“义者,利也。”商君亦言:“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商君书·开塞》)同样,《尸子·发蒙》云:“夫爱民,且利之也,爱而不利,则非慈母之德也。”“义”的道德准则与其实际效果常合而言之,“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天下以生为神”。(《尸子·贵言》)其实,不管是商鞅的“利者义之本”,还是尸佼的“爱民且利之”,无不表明以利释义的思路,无不闪现墨家“兼爱交利”之精义。故有论者认为,“尸子把墨子的兼爱塞进孔子‘仁的概念中了。”[7]endprint
蒙文通认为《尸子》“其书十九者通乎儒墨之义,是周秦之间,合儒、墨于一辙者,固未有先于尸子者也。”[8]因而,尸佼在义利观层面确展露一种游移于儒墨之间的思想形态:既倡导儒家仁学,却不重申义利之辨,而是标揭“义必利”的客观效果。胡适指出,从墨子“爱利一体”、“自苦为极”的功利主义,到杂家尸子、《吕氏春秋》构建在使人民得遂其欲的功利主义,逐步递嬗衍化出传统文化中秩序进路的乐利主义政治哲学[9]。在这一思想谱系中,法制原则与正义标准的道德伦理色彩渐渐褪去,呈现出着眼于人民利害与社会实效的利益特征。
三、制分正名:《尸子》的承转媒介先秦名论异彩纷呈 先秦名学有多种范式。(参见: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7-14.),与政法关联者约有三脉:其一,孔子的正名主义,逐渐衍化出刑(形)名学或称名实之论,成为后来一以贯之的“法理学基础。”[9]237、252-253其二,作为法家先驱,邓析精通刑名之学而作竹刑,从形式到实质均与后来法家的思想紧密相关。梁启超说:“名与法盖不可离,故李悝法经,萧何汉律,皆著名篇。而后世言法者亦号‘刑名。”[10]刑名之书正是宪令不一、刑律繁杂的时代所催生[11],如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缪”(《韩非子·定法》),则有申子刑名之书“三符”。其三,黄老之学皆重名论,史家常目之为法家刑名学之源泉。 《经法·道法》云:“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人们认识事物,也经历从“审其形名”、“循名穷理”到“名实相应”的认知过程。(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239.)《管子·白心》 郭沫若认为《白心》出于尹文,仍属稷下黄老的思想。(参见: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C]//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47-572.)中关于名实之论核心命题——“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与申韩刑名论颇为接近,盖为道法名论之接榫。
名实之论,往往是论政之架构,诸学之媒介,故自然成为杂家之焦点。在先秦名论的发展衍变中,经历了一种杂糅儒、法的过渡形态,呈现于尸佼的思想中。钱穆说:“正名以治,为法家师,如吴起之流矣……则尸子之学,固当与李悝吴起商鞅为一脉耳。”(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16.)尸佼之名论少有逻辑名辩的色彩,承袭儒家政治化的正名主义,以经验主义与实用观点审视名实关系,反映了政治化、实用化趋向的名论由儒入法的趋势。李泽厚说:“儒道法均讲‘无为而治,均讲名,此名非语言、逻辑,乃实用政治。”(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178-179.)
(一)“裁物以制分”:尸佼名论的基本内涵
《尸子·分》曰:
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
所谓“裁物以制分”,制分之“分”,有“名分”、“份额”之义,是所分配之名分,也蕴涵分量适宜之虑。孔子以前,即有关于德目之适度性的阐述,而儒家以中庸哲学将这一思想系统化[12]。爱、施、虑、动、言,本身只是一个关于举动或行为的中性描述,而是否“得分”则包含着价值判断,由此决定了能否升格为褒义色彩的德目范畴——仁、义、智、适、信。值得注意的是,尸佼将适度性考量的中庸观,顺洽地接上正名主义并归旨于“事少功立”的政治理想,是对儒学义理的创造性发挥,也揭示了中庸之道的制度原则面向,即朝向关于法制创立之正名范畴的过渡或联结。《尸子·分》云:“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
在注重制度的尸佼看来,既然存在符合中庸主义的适度性标准,那么,在治国治民的问题上,就应当以制度设计与秩序建构将这一状态稳固下来,所谓“得其分曰治”,制分、立官之说意即在此。在这种以“制分”为核心词汇的正名论当中,尸佼之学反而消隐孔子对“礼崩乐坏”的批判视界,而富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期待现实社会中推进政治阶层分化与新“分成”秩序的,以立法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制分”,将剧烈变法形成的新等差秩序合理化并以法律秩序的形式确定下来,所谓“天下之可治,分成也”。
在用贤与治吏的意义上,“制分”逻辑上意味着权力与责任的合一。《尸子·分》言:“诸治官临众者,上比度以观其贤,案法以观其罪,吏虽有邪僻,无所逃之,所以观胜任也。”所谓“君明则臣少罪”,“制分”要求合理而清晰地划定臣属之职责,自然能够促使臣下对自身职责有明晰的认识,对违反职责之制裁有足够的警戒。对法律制度客观性的秉持与强调,显示出道德判断观点向法律制度思索的转变,这是先秦名学谱系从宏大的权力之“名”缩聚于专门的法令之“名”的转折点。
(二)“名实合为一”:尸佼名论的转捩关键
在《尸子·分》“裁物以制分”的叙述中,“正名”凸显出鲜明的政治价值,可达致“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世。《尸子·发蒙》曰:
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明王之所以与臣下交者少,审名分,群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故有道之君其无易听,此名分之所审也。
尸佼讲“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尸子·发蒙》),佚文中亦论及君臣上下森严之礼制,承儒家正名主义余绪,申调整君臣上下权利义务之义,并无二致。不过,尸佼以“用贤”、“明分”、“赏罚”诸论,将正名主义广泛付诸具体的政治统治实践中,其言“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尸子·发蒙》),契合法家“循名责实”之考绩术。“审名分”从正面讲是突出“名”以界定官吏的权利义务之内容,反映了建立一种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新秩序之愿望;从反面讲则是突出“分”而为官吏的职责划定边界,包含一种治道层面分权委任的“明分”思想。endprint
一方面,尸佼憧憬一个圣王来做实质性的审慎建构与设计,为君权秩序提供一套富有哲理根基的制度保障,在“名”为“人君之所独断”、“圣之所审”之表述中,法家“术”论的韵味已经开始弥散。“审名分”是为了让臣民产生“戒慎戒俱”的心理,使臣下“莫敢不尽力竭智矣”,“情尽而不伪,质素而无巧”,君主能更好驾驭利用臣属以掌控最高统治权。
另一方面,诸子“贵名之正”,大多无意于申说法律之“名”对社会之“实”的反映,而在于强调法律之“名”对社会之“实”的统制地位与决定性质。《尸子·发蒙》云:“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所谓“判为两”,名实本是可分离的理念与现实,尸佼则强调“合为一”,真正发挥其辨别是非、施以赏罚的实效。结合尸佼“去私论”中“一实”之说,“名实合为一”反映了墨辩“取实予名”、“志功合一”对名论的改良 《墨子·贵义》曰:“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辩名论之研究,参见: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26-232.,显示了从儒家偏重“虚名”到名实相当的递嬗轨迹。《尸子·分》中“正名去伪”毕竟并举了“以实核名”与“正名覆实”两个层面,与申、韩“刑名参验”之名论近在咫尺。 胡适认为,名与法其实只是同样的物事,两者都是全称,都有驾驭个体事物的效能。孔子的正名主义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就忘了名是为“实”而设的,故成了一种偏重“虚名”的主张……后来的名学受了墨家的影响,趋重“以名举实”……如尸子的“以实覆名……正名覆实”,如《韩非子》的“形名参同”,都是墨家以后改良的正名主义了。(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C]//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253.)概言之,作为诸学之媒介、言法之根基,尸佼名论偏向实用法术,蕴含着道法转关、儒法融合之征兆。
四、“用贤”与“案法”:《尸子》的综合治术
《尸子》有治天下“四术”,即忠爱、无私、用贤、度量。尸佼认为,“因智”而“因贤”可以“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尸子·治天下》),貌似与“去智与巧”的反智论相龃龉,却意在以有为而致无事,“用贤使能,不劳而治” 尸佼曾引孔子与子贡对话,阐明先王“尚贤”之功:“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见《尸子·佚文》。;另一方面,“案其法则民敬事”,以“贵因任法”阐弘南面之术。然“用贤”与“案法”,儒、法常各执一端使其互相排抑,而在尸佼之学中,两者却共融以名学,归旨于道论,而辐辏并进。
(一)“以贤举贤”与“以才为仪”:选贤的主客观标准
在选贤的主观标准方面,尸佼强调人才的发掘选拔必赖专才,“比之犹相马,而借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也”。(《尸子·治天下》)身为贤才,方能慧眼识人,举荐贤才,此为“以贤举贤”的“众贤之术”。他进而主张“便进贤者有赏,进不屑者罪,无敢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尸子·发蒙》)由此,尸佼为“以贤举贤”之术设计了一个法律保障措施,即将举贤作为考察官吏的政绩,以所举之人的能力来论功行赏或论罪处罚,终能以制度保障举贤而靡有孑遗,堪称后代选官举措之思想源泉。在尸佼看来,这种颇具连带责任色彩的机制,不仅是一种“选贤之策”,还是一种“考绩之术”,举贤与赏刑皆归旨于“事少功多”的效益原则。当然,这种吏治思想与配套制度不免理想化,高估治人的能动性而苛求之,连带机制亦缺乏正当性基础。后来秦法正是采用了这一吏治原理,《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秦之法,其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在选贤的客观标准方面,尸子游移于诸家理念之间。一方面,尸子反对注重出身、宗法世袭的“爵列”,而以实际“德行”为主要标准。首先,名为“劝学”,实则承儒家余绪,力倡德行之修;所谓“贤者之治,去害义也”(《尸子·恕》),仍向往德教意味的贤人政治。其次,与亚圣一样,尸佼津津乐道于先贤事迹,坚信人才德行常可冲破爵列出身之宿命。再次,尸佼认为,同具普遍化效用的爵列与德行,仍存在效力范围之差异。《尸子·劝学》曰:“爵列,私贵也;德行,公贵也。”最后,“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对于人的社会地位与美德懿行,尸佼以形式与实质的关系论之,诚为金玉良言而垂范后世。
另一方面,他将选择事物的形式标准称为“仪”,并“以才为仪”。尸佼说:“人知用贤之利也,不能得贤其故何也?夫买马不论足力,以白黑为仪,必无走马矣。买玉不论美恶,以大小为仪,必无良宝矣。举士不论才,而以贵势为仪,则管仲、伊尹不为臣矣。”(《尸子·佚文》)以马、玉等物譬喻,尸佼凸显的是“用贤之利”。
孔子提倡“举贤才”,设想于世卿世禄之外另辟蹊径;孟子宣称“惟仁者宜在高位”,却眛于“仕者世禄”之旧识。而墨子憧憬“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旨在彻底打破氏族血缘界限,颠覆世卿世禄的世袭旧制,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下的“举贤才”貌合神离。这昭示了战国时期的贤能观从理论到实践已发生了一些微妙转变:为真正实现“贤能面前人人平等”杨俊光认为,墨子提出了“在贤能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参见:杨俊光.墨子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83.),“尚贤”从一种与“亲亲尊尊”相配套的改良方案,转变成一种旨在颠覆世卿世禄制的批判观点,与之相应,“贤”也从相对疏阔空洞的伦理德性标准,渐次具备一些契合政法实践之要素。
尸佼的“尚贤”游移于“德”“才”之间,既有意延续孔孟道德观念,又援用墨者与前期法家的新尚贤论,体现了对儒、墨、法的兼收并蓄。如果说“德行,公贵也”意在宣扬“去私”观念,那么“以才为仪”则更直截地表明其贤能观点。在尸佼看来,德行与才能,在政治实用情境本应综合考量。有论者说:“对于这个议题,《尸子》采取的观念可能与墨子较为接近,试观《尸子》的贤能政治主张也是才能的意义大于道德的意义。”[4]40,44所谓“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禄”(《尸子·佚文》),“以才为仪”的政治实用转向仍不言而喻。战国时期的思想界,在表面一致的“尚贤”话语中,“贤能”的标准,悄然透射出从“贵”到“德”与“才”的转变轨迹。而在尸佼学说中,道德理想与事功实践的张力,传统美德与现实才干的权衡确昭然可见,也反映当时政治社会阶层的流动、变迁乃至重置现象背后的法制转型——以才能、功勋为实质内容的新爵禄制。endprint
(二)“比度观贤”与“有所委制”:用贤的制度性原则
在孔子时代,虽有正名观念以界定君臣权利义务,但对于臣下之品行与才能却未见一套可供实践的考核理论。“循名责实”的考绩之术,借用刑名论之框架得以推衍阐发,以申子之学为前驱,为战国法家之通论。大概同时,《尸子·分》言:“诸治官临众者,上比度以观其贤,案法以观其罪,吏虽有邪僻,无所逃之,所以观胜任也。”与法家一样,尸佼从尚贤进于吏治,并秉持法律制度客观性而阐发吏治之术。他指出吏治对治国的重要性,“必有所委制,然后治矣”(《尸子·佚文》),“委制”也以“制分”前提,是“制分”在用贤层面的观照。
贤能政治观点在《尸子》残篇中举足轻重。尸佼言:“虑事而当,不若进贤;进贤而当,不若知贤;知贤又能用之,备矣!”(《尸子·发蒙》)确也,“进贤”依赖“以才为仪”,“知贤”诉诸“比度观贤”,“用之”则当“有所委制”,而“仪”、“度”、“制”三者都直接指向“尚贤”所不可或缺的举贤与考绩制度。概言之,尸佼在举贤方面顺应潮流,承祧儒宗,吸纳墨学,展现了从“爵”到“德”到“才”的转向,在用贤方面契合现实,运用名学,开启了法家考绩之术。有论者评曰:“尸佼的忠爱、用贤、无私和量度治世四术中,以用贤即人才为根本,并置于‘从道之中,看成是不可动摇的规律性这是卓知灼见。当时的思想家都看重人才这个问题。尸佼由于其亲身的丰富经历,则看得更为深远。”[13]
(三)“案其法”与“刑以辅教”:治法的特性与功能
据《汉书·艺文志》,尸佼为商君之师;据《史记·孟荀列传》刘向《别录》载,尸佼为商君之客。不管是“师”是“客”或兼而有之,商鞅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对那场叱咤风云的商鞅变法,尸佼自然厕身其间,全程参与。携《法经》入秦,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不管从理论上重法学说的阐释,还是从实践上变法改革的施行视之,皆堪称先秦法家巨擘。然而,商鞅见秦孝公,竟能先后说之以帝道、王道、霸道,对诸家学说亦可谓运掉自如,甚至有人认为商鞅之重法农战只是“一时之利”,之后必然走向礼治[14]。商鞅深通儒家之学,也谙晓博通诸家学说的经世价值,或许正是他与尸佼一道“谋事划计、立法理民”的因缘吧!水渭松就断言:“尸子在学术思想上曾给商鞅以一定的影响……他们是一脉相承的。”[15]这也反映出融汇各种统治术的尸佼杂学,有将多种治国理念加以法制化的倾向。
就广义之治法而言,韩非“抱法处势”的法势结合论已在尸佼学说中初见端倪。正如法家之慎到、申子、韩非、儒家之荀况都以蓍龟、书契、度量、绳墨、规矩、尺度、镜、权衡、椎锻、榜檠等器物类比法,以器物之标准精确的基本属性比照法之公正特性,尸佼阐释了法的普遍性、客观性:“古者倕为规矩准绳,使天下傚焉。”(《尸子·佚文》)而《尸子·贵言》言:“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前文已述,尸佼紧扣令行禁止的法律秩序实效性问题,将其终极价值指向君王“一天下”的功效。尸佼曰:“夫高显尊贵,利天下之径也。非仁者之所以轻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烛远,势高也。”(《尸子·明堂》 《大戴礼记·盛德》云:“明堂,天法也,礼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恶,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刘师培说:“然吾观上古之时,政治、学术、宗教,合于一途,其法咸备于明堂。……而有周一代之学说,即由此而生。”由此可见,《尸子》以“明堂”为篇名,寓意学旨归一,统合礼度德法。(参见:刘师培.左盦外集·古学出于官守论[C]//刘申叔遗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483.))唯有处在权力金字塔的上层乃至顶端,以“高显尊贵”的阶层或势位,方能向下位之阶层、芸芸之众生颐指气使。“若夫名分,圣之所审”,所有关乎权利义务内容的名分皆不可超出君王的掌控。对于治理政事的官吏,尸佼强调居官守法,《尸子·发蒙》谓:“若夫临官治事者,案其法则民敬事”。 《黄帝四经·称》亦言:“案法而治则不乱。”意即“用法度来治理就不会混乱”。(参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48.)“案其法”的规则之治,才能真正让百姓遵守秩序,服从治理。
就狭义而言,尸佼的“治法”专指刑罚,有统合儒家德教与法家刑治之旨趣。如后来韩非把赏刑奉为“二柄”,尸子将“赏罚”视为治道应有之义:“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发蒙》)与法家一样,尸佼聚焦于刑罚的威慑力与制裁特征,“鞭策之所用,远道重任也”(《尸子·佚文》),刑罚是一种制裁工具,其存在意义乃是在通向治世的漫漫路途上充当一种如同鞭策般的驱动工具或保障手段。然而,尸佼也以儒家的口吻说:“为刑者,刑以辅教,服不听也。”(《尸子·佚文》)刑罚仍被置于德教之下,作为一种违反道德教化的法律制裁。“《尸子》一方面将孔子的‘仁学视为统治上的重要凭著,一方面却也不忘强调刑的重要性,这里宣示出《尸子》的统治术是德与刑合一的。”[4]45-46
《尸子·佚文》载:
秦穆公明于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缪公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借秦穆公“明于听狱”之典故,尸佼阐释其刑法观:其一,由于可归咎于统治者的原因,儒家式的德教有可能“不至”,这是刑罚的合理性基础;其二,基于对刑罚的谦抑认识,统治者应意识到“使民困于刑”是戾政信号。所以,其刑罚观虽有法家式“刑期无刑”之逻辑,但“刑以辅教”的认识又使其并未完全认同一味重刑的霸道。
余论吕思勉曾说,《尸子》“确为先秦古籍,殊为可宝”。吕思勉还指出,《尸子》“实足以通儒、道、名、法四家之邮”。(参见:吕思勉.经子解题·尸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94-196.)另外,有学位论文全面研究《尸子》之文献价值。(参见:李文锋.《尸子》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9-31.)然而,观《尸子》之断简残篇,却不及道家之博大、儒家之深邃、墨家之雄浑、法家之犀利。上卷之篇目颇为旁通曲鬯,偶有微言大义,惜乎语焉不详,未免“术通文钝”(《文心雕龙·诸子》) 刘勰谓尸佼在思想上“兼总于杂术”,而在文学上“术通而文钝”。(参见:刘勰.文心雕龙[M].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201-206.);下卷所辑录后人钩沉寥寥数语,多为上古掌故,义理贫瘠,岂非“杂错漫羡”?endprint
然而,诸子时代,官学失守,道术为天下裂,百家蜂出并作,纷立新说,“彷佛各有一把开启各自房门的钥匙却没有通用于各个房门的万能钥匙,不足以应付日新月异的历史变化与瞬息万变的社会需要。”[16]尸佼杂学之价值正在于“通众家之意”,显露出以“王治”为原则,整合“取合诸侯”的诸家法思想之学术抱负,且能以政治实用为原则,不固持成见而能平等汲取[3]105。古人常谓杂家“无所指归” 《隋书·经籍志》曰:“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无所指归。”《刘子·九流》曰:“杂者,孔甲、尉缭、尸佼、淮夷之类也。明阴阳,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纵横,纳农植。取与不拘一绪。然而薄者则芜秽蔓衍,无所系心也。”,近人或曰“家而曰‘杂,实为不词。”[17]然就实际政治而言,学术的杂糅是思想进程之需求,折衷主义是实用价值之显现,是学问术化、经世致用之必然,亦是政治智慧发展的标志之一[18]。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百家,从诸子百家到汉代儒术,恰是一个随政治态势亦步亦趋的文化思想分裂复统一的历程。凿王官学之窍而突破创发的各家子学,兼采它家别说力图话语覆盖范围的圆融完满,并朝向治道法术领地拓充合流,是中国思想发展史的本质特征。博通宏旨之标揭(“去私”)、思想范畴之圆融(“道仁义”)、知识方法之整合(“制分正名”)、治术路向之合拢(“用贤”与“案法”),乃是圆实意识形态主旨、填复官学总貌的必由之路,杂家尸佼之学,盖能一一发其端绪。此种融合诸家的思想综合取向,尸佼创议于前,荀卿、贾谊、董仲舒踵武于后。唐君毅说:“诸家分流以后,左右采获,以求反于一本之思想潮流,秦汉之际之一转捩思想也。……唯汉兴以后,乃实现先秦诸子所向往之文化凝合之理想。”[19]汉代百家学术终趋向治道法术拢合,观诸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思想、汉家“霸王道杂之”的意识形态(《汉书·元帝纪》),“其统一的旗帜是儒家,统一的精神是杂家。”[20]回观先秦杂家尸佼之学,扬“去私”精神,陈杂家旨趣,既博采众家优长之说,又能提挈精义以立纲维;既融洽凝合千端万绪,又能独出机杼而发治道王晓波更强调尸佼之学的创新成分:“(尸子)把老子要求对待人民的‘去智与巧,改造成要求统治者的‘执一之道。他把孔子要‘克己复礼的‘正名,改造成客观的‘令名自正,令事自定。他把儒家义务论的‘仁义,改造成效益论的‘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他肯定了法家的‘自为,更要求统治者能以‘大私为‘公”。(参见:王晓波.兼儒墨、合名法——《尸子》的哲学思想及其论辩[J].台湾国立大学哲学论评,2008,36:71.),实于战国中期开启治道学术合流之先河。甚者,其学深合儒法递嬗之态势,尽现治术融通之时风,或许预示着秦汉“道术为天子合”该语引自雷戈书名。(参见:雷戈.道术为天子合——后战国思想史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31,90-120.)的思想史趋势。ML
参考文献:
[1]李守奎,李轶.尸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
[2]张琦翔.秦汉杂家学术[M].北平:金华印书局,1948:1.
[3]潘俊杰.先秦杂家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5:108-109.
[4]林俊宏.《尸子》政治思想[J].政治科学论丛,2000(12):52.
[5]陈复.由内圣而外王:尸子心学的意蕴与启思[G]//林文华.第四届先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2001:221-247.
[6]许青春.先秦杂家义利观探微[J].济南大学学报,2006(5):75.
[7]王晓波.兼儒墨、合名法——《尸子》的哲学思想及其论辩[J].台湾大学哲学论评,2008,36:56.
[8]蒙文通.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M]//蒙文通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222.
[9]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C]//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302-305.
[1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62.
[11]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C].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1: 594.
[12]马腾.儒家“中庸”之传统法文化观照[J].北方法学,2011(2):139.
[13]魏宗禹.尸佼思想简论[J].山西大学学报,1990(2):12.
[14]钟泰.中国哲学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9.
[15]水渭松.新译尸子读本[M].台北:三民书局,1997:2-3.
[1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210.
[17]蒋伯潜.诸子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8.
[18]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511.
[19]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9.
[20]孟天运.杂家新论[J].哲学研究,2001(11):66.
Abstract: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Shi Jiao set up Zajia School (the Eclectics), which advocated Qusi (denouncing selfishness) as its core idea, and incorporated other schools theories suited for various states based on political pragmatism. His theory centered on the Taoist philosophy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aimed at an ideal world with “few undertakings but full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included the idea of Ren Yi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mor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hence featuring a fusion of morality and utilitarianism. Moreover, he incorporated the discussion of name and nature of Mingjia (the Name School) and Fajia (Chinese Legal School) and came up with an integrated interpretation of “employing talents” and “conforming to the laws”. His pragmatism and eclecticism were a reflection of the thinking of Warring States before and after Shang Yangs reform, which followed the trends of Fajias development from Taois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Fajia. He also suggested a tendency of formulating pragmatic political and governing philosophies, hence a model of incorporation of various schools in the preQin period, also forecast the convergence of all schools in Han Dynasty.
Key Words: Shi Jiao; Zajia(the Eclectics); Shang Yang; Qusi(denouncing selfishness); Tao; righteousness and morali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