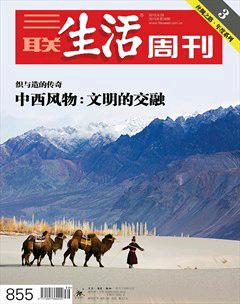在爱丁堡过艺术节
石鸣
时尚界有一句名言,每个女人都要拥有一条小黑裙。《爱丁堡艺穗节幸存指南》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每个人有生之年都要来爱丁堡演一次戏。”这本书是业内人士写给业内人士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这句话或许应该改成:每个人有生之年都应该来爱丁堡过一次艺术节。

8 月7 日,一些参加艺穗节的演员在爱丁堡老城区最著名的街道——“皇家一英里”上为自己的戏做宣传

爱丁堡艺穗节的街头演出——《爱上月亮的女孩》
如果你在8月来到爱丁堡,你会惊讶地发觉这里的人似乎什么事儿也不干,除了过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丁堡艺穗节、爱丁堡军乐节、爱丁堡国际书展……统统挤在这四周。每年参加这些艺术节的人超过400万,卖出的门票数量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世界杯,然而,后者是四年一次,前者可是年复一年,年年都有。8月想在爱丁堡寻找清静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不合时宜的。对于这座纬度比漠河还要高的苏格兰首府来说,此时最值得做的,就是享受弥足珍贵的“最后的夏日时光”。艺术节的海报、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不必管它,垃圾桶满得已经快要溢出来,也不必在乎,平时午夜之前就要打烊的酒吧,凭着法律许可,营业至凌晨5点,有的酒吧甚至对成功“刷夜”的人有特别奖励(奖品是一件纪念T恤)。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规模上来说,爱丁堡艺穗节无疑都是这个节日季中最重要的节。它持续的时间最长,占据整整三周,再加上开幕之前有一周的预演,我们可以说,整个8月的爱丁堡都是属于艺穗节的。
两个艺术节的70年对决
没有来过爱丁堡的人,不容易搞清爱丁堡艺穗节(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以下简称Fringe)和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以下简称EIF)的区别。就连当地媒体也不对这两个节做特别的区分,报道它们的版面极其类似,只在长长的文章末尾用小字注明剧目来自何处。或许只有在买票的时候,才会遇上麻烦:“不好意思,这个戏不是我们这里的,是国际艺术节的。”这便是我拿着刊有希薇·纪莲大幅照片的《Fest》杂志兴冲冲赶到艺穗节票房抢票时的遭遇。同理,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安提戈涅》也不是艺穗节的剧目,而是国际艺术节的,尽管朱丽叶·比诺什的巨大头像占据了双层巴士的整个车身,穿梭在满是艺穗节广告的中世纪街道上。

爱丁堡艺穗节剧目《爱情课本》剧照

爱丁堡艺穗节剧目《房间里的大象》剧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作为爱丁堡最重要的两个艺术节,Fringe和EIF彼此敌对的关系是英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这也是它不同于另一个名气相当的艺术节——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和“IN”单元的地方。对于阿维尼翁戏剧节来说,“OFF”单元是后来派生出来的,是1968年那个“反叛的年代”的产物,因此“OFF”一开始就具有某种从属于“IN”的特征。然而,Fringe拥有与EIF、阿维尼翁戏剧节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都创办于1947年,从一开始,Fringe和EIF就是彼此独立的,尽管“Fringe”本身具有“边缘”的含义,但是参与Fringe的艺术家们从一开始就从未自视“非主流”,而只是“不同”。的确,成立60多年以来,Fringe和EIF各自的特色一度相当鲜明:Fringe的演出高潮往往在深夜,EIF的演出大多集中在白天至傍晚;Fringe演出的大多是话剧,EIF更加侧重古典音乐和歌剧,话剧很少,几至于无,且EIF的历任艺术总监直至2014年为止,全部具有某种音乐和歌剧背景,却对话剧、舞台剧没有什么涉猎。
将Fringe与EIF,以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艺术节区分开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没有艺术总监,没有策展人,没有哪一个个人或者哪一个委员会握有某个戏能不能在Fringe上演的决定权。的确有一个爱丁堡艺穗节协会(成立于1959年),但是这个协会仅仅承担为参加Fringe的各演出团体、媒体服务的职能。任何人只要有自己的创作,愿意申请,找得到场地,付得起场租和衣食住行的费用,就可以来Fringe演自己的戏。
事实上,这条被Fringe视为自己立身之本的原则,也是其最终与EIF分道扬镳的一个原因。早年,Fringe的艺术家们曾经想和EIF合并:后者有钱、有组织、有政府支持、有全英国乃至欧美最知名的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参加,而Fringe当时什么都没有,不过是由8个地方剧团、戏剧协会(其中6个来自苏格兰)拉起来的草台班子。那个时候,是EIF瞧不上Fringe,认为其不过是小打小闹的“编外活动”,而且无组织无纪律,还不服管束,大概也没有什么前途。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Fringe的剧目和演出时间,只能以给EIF填空的方式来进行,而EIF凭着策划和资源方面的优势,专门盯着Fringe的特征与之竞争:Fringe演话剧,EIF也演话剧;Fringe以深夜演出出名,EIF就搞一个午夜时分的《秀场之后》;Fringe的娱乐性强,EIF就搞一个娱乐性更强的《边缘之外》(Beyond the Fringe),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误以为这个戏是Fringe的,甚至Fringe自己出版的50周年纪念图书上也收录了这个戏的剧照。
谁能想到,70年之后,Fringe竟然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艺术节呢?Fringe的规模扩张,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有了资金支持之后,它的宣传也越来越高调,人们逐渐开始把Fringe视作一个有公众性质的艺术节,而不仅仅是一小撮艺术家们自娱自乐的行为艺术,参演的剧目数量从三位数突破到四位数,几大支柱演出场地开始固定下来。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2008年以来,Fringe急速膨胀,2014年上演的剧目数量是3193台,演出场次4.9万多场,2015年的剧目数量攀升至3314,演出场次超过5万场。如今,Fringe的节目册比一本字典还厚,戏剧节开幕后前三天,全城开演的戏超过500台,这比一个普通的戏剧节的全程剧目要多好几倍甚至几十倍,整个英国的戏剧圈人士都汇集在这里了,以及世界各地的演出团体。回想1959年,那时参加Fringe的剧团数目从8个增加到19个,便已经有人私底下觉得Fringe“太大了!”
有趣的是,当Fringe的体量从小老鼠膨胀成恐龙之后,原本是大象的EIF开始不知不觉有自惭形秽之感,二者之间俯视和仰视的关系渐渐颠倒过来。以前,Fringe想向EIF攀关系,EIF置之不理,如今,EIF却开始有某种主动示好、向Fringe靠拢的意思。从前,EIF总是比Fringe晚一周才开始,似乎毫不介意姗姗来迟会扫观者的兴致,而且持续时间也比Fringe少一周,然而,近年来,EIF的开幕日期一再提前,持续时间也一再延长。去年的EIF尚比Fringe晚两天开幕,今年,两个艺术节开幕在同一天,且并非巧合。今年的EIF还有最大的一个改变,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摒弃剧目策划的概念:之前每一届EIF,总是具有某种主题——启蒙、战争与和平、技术等等——来总领所有剧目,这一届却不再有这样一个统一的主题。
这与2014年新上任的EIF艺术总监弗格斯·莱因汉(Fergus Linehan)有关,他不愿意看到“某个戏非常棒,仅仅因为不合一个预先确定的主题,就不能入选EIF”。在EIF的漫长历史上,他是首位具有戏剧背景的艺术总监,也因此今年的EIF大幅增加了舞台剧的分量,传统古典音乐和歌剧的演出范畴也被拓宽了,开幕音乐会不再端着“皇家”的架子,被移到了户外,免费参加,没有座位,采用了形式颇为先锋的多媒体投影——从表面上看,EIF似乎越来越像Fringe了,它的剧目选择越来越少地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并且借助充裕的预算,它还能够请到朱丽叶·比诺什、希薇·纪莲、安妮·索菲·穆特、郎朗、捷吉耶夫等大腕儿,简直变身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升级版Fringe。
事实上,今年EIF的主打剧目里有一台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是英国1927剧团和柏林喜歌剧院合作的作品(9月10~12日刚刚在上海演出完毕,票房爆满,大获好评),而这个1927剧团,便是在2007年从Fringe上脱颖而出的。另外还有一台新编歌剧《最后的酒店》(The Last Hotel)和一个舞台剧《遭遇》(The Encounter),其主创当年也是来自Fringe。事实证明,在Fringe上大受欢迎的,换到EIF的舞台上,照样赢得掌声雷动。两个艺术节经过那么多年的争斗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观众只管演出的质量好坏,并不在意某台演出的出身高低。
艺穗节的“大”与“小”
对于爱丁堡艺穗节来说,它的“尺寸”(size)一直是一个常辩常新的话题。一方面,它已经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艺术盛会;另一方面,组成如此大的体量的每一个元件,却又如此之小——如今在艺穗节上演的戏,一般都不超过一个小时,而自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为止,大部分艺穗节的戏都至少有一个半小时。
这些戏不得不“小”。没有来到爱丁堡的人,或许对艺穗节的“尺寸”问题没有概念。3000多台剧目,要挤在300来个演出场地里演出,其中90%的场地并不是专业剧场,而是临时搭建或者改建而来。单单一个Assembly剧院,上演的剧目数就等于整个EIF的容量。对于演出人员来说,戏与戏之间要有足够的拆台、装台时间,对于观众来说,要想办法安排足够的时间穿越大街小巷上汹涌的人群,从一个剧场到另一个剧场。演出从早上10点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午夜,一个人一天能够看多少台演出呢?极限纪录可能是7至8台,实践经验证明,如果每天都看戏,4到5台是比较实际的数据。而且除了艺穗节之外,还有国际艺术节的剧目。有人测算过,如果每天看5个戏,其中国际艺术节的戏和Traverse剧院(艺穗节的四大堡垒剧院之一,致力于严肃戏剧)的戏一个不落,那么就只有很少的时间空当和注意力能够分给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创作者和小戏了。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剧目《费加罗的婚礼》剧照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艺穗节上争夺观众的竞争何等惨烈。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家十几家大户——有的是艺穗节的常客,有的是作为剧院常年以来形成了选戏风格,因此较容易被观众认知——之外,绝大部分“散户”之间达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竞争状态。因此,爱丁堡艺穗节也被戏称为“资本主义戏剧节的最佳典范”。有钱才能去爱丁堡,这成了戏剧圈内的共识——不是说必须家财万贯,但口袋里绝对不能只有几个铜板。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攒上好几年钱然后去一次爱丁堡的剧团比比皆是,如今鼎鼎大名的1927剧团当年也不例外。2012年在中国大陆巡演时,主创曾经接受过本刊的采访,在聊到当初去爱丁堡的过程时说:“我们动用了我们过去几年在伦敦卡巴莱表演里攒下来的所有的钱,这种表演赚钱并不多,一个晚上50镑或者100镑,就已经很可观,这些钱我们都没花,存进了一个小的银行账户,平时另外打工来维持开销,存了一年,大概有几千镑,于是去爱丁堡这件昂贵的事情变成了可能。”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剧团都能够像1927剧团这么幸运,能够在爱丁堡艺穗节的平台上一炮打响,进而红遍全球。对于许多戏而言,观众席里的人数甚至不一定比舞台上的演员数目更多,而大部分剧团的诉求仅仅是在艺穗节上亮相同时不至于破产,“如果还能引起一些关注就更好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爱丁堡艺穗节协会每年发布各种指南,并且隔几年就修订一次,除了提供艺术指导之外,这些指南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从经济方面指导剧团如何筹款、如何宣传、如何卖票、如何削减开支。2012年,一位名叫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英国记者兼编剧写了一本《爱丁堡艺穗节幸存指南》(The Edinburgh Fringe Survival Guide),立即被大家奉为宝典,或许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一想到爱丁堡艺穗节,就让人满心恐惧,就像上了一辆挤满人的公交车,你觉得自己很孤单,然后发现车上每个人其实都和你感觉一样。因此即便只有站位,也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大家相信,尽管爱丁堡艺穗节是个赌场,但总有人赢得彩头。
有不少人对艺穗节的“资本主义化”和商业化倾向持批判态度,理由是艺术家们辛辛苦苦地创作,赚来的钱还不足以果腹,然而受惠于艺穗节的当地服务业却赚得盆满钵满,实属不公。从消费角度来看,这的确是实情,艺穗节期间,整个爱丁堡的酒店、餐馆、酒吧的价格都大幅上涨,一杯平时卖2.5英镑的啤酒,艺穗节期间要卖到4英镑。像宜必思这种普通连锁酒店,平日里30多英镑一晚的房间,艺穗节期间甚至有可能飙升到200多英镑,因此各种指南都会不约而同地建议艺术家们通过蹭、挤、露营甚至住到隔壁格拉斯哥(火车到爱丁堡只需一个半小时)的方式,来解决住宿问题。相比之下,价格下跌的唯有戏票,各种打折优惠之后,艺穗节戏票的平均价格不过10英镑,在伦敦看一场戏的钱,在艺穗节上可以看5场,而一场演出的观众人数很少超过150人。这样的剪刀差,导致即便一个剧团的报表在艺穗节结束之后显示有赚头,最后平均下来很可能每个人的收入也不超过100英镑。据统计,每年艺穗节给爱丁堡创造的收入超过2亿英镑,其中90%留在了爱丁堡本地人的手中,这些人包括爱丁堡的房产主,咖啡店、餐馆和酒吧老板,商店店主以及爱丁堡大学——因为大量的剧院都是爱丁堡大学的产业。
还有人认为,艺穗节的体量过于庞大,逼迫个体剧团不得不收缩自己的创作,他们对“一小时时长”这个艺穗节惯例发起攻击:一个小时就足够把要讲的事讲完吗?所有的戏都限定在一小时,会不会难免削足适履?换句话说,是不是应该对艺穗节的准入门槛加以更多的限制,以便进入艺穗节的戏能够得到更多的发挥空间?今年的爱丁堡艺穗节上,就有一场专门的讨论会,讨论艺穗节的戏是不是太“小”了。认为艺穗节的“小”有害于戏剧发展的人最终成为态度保守的少数,他们的反对者理由很充分:更大并不一定更好,更小也不一定更差,“小”只是一种条件,而不是束缚,想象力和创造力终将以自己的方式显现,那个时候,甚至不需要一小时,只需要15分钟、20分钟。
另一个实例是,爱丁堡艺穗节并不是容不下一小时以上的“大”戏,Traverse剧院的戏基本上都在一个半小时左右。2013年,易立明导演在爱丁堡看戏时选中了一部《尤利西斯》,且在今年4月引进到中国巡演,这部戏的演出时长便达到两个半小时,演出场地甚至都不是专业剧院,而是当地的一个护士学校礼堂。记得导演在采访中谈及演出时长问题时只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如今想来,这种逆流而上的行为实属特立独行、令人钦佩。导演的底气恐怕也在于这的确是一部好戏,且幸运的是,它是一部没有被埋没的好戏,对于真正的好戏来说,既成的惯例和规则都是云烟。
戏剧的未来
2010年,一个名叫马修·萨默维尔(Matthew Somerville)的伯明翰戏剧人创造了一个艺穗节看戏纪录:三周时间里,他看了136台戏。然而,这只占当年艺穗节全部剧目的5.54%。
没有人能够穷尽爱丁堡艺穗节,即使你大名鼎鼎如《卫报》资深戏剧评论人琳·加德纳(Lyn Gardner)也不例外。艺穗节是个海洋,广阔而包罗万象,每个人尽其所能,也只能接触到其局部碎片。然而,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戏剧专业人士,有生之年都应该来爱丁堡看一次戏,因为在这里你能以空前的密度,接触到自己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东西。
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艺穗节中大海捞针,选出值得看的好戏?如果是业内人士,那么早早就已经收到了各种消息推送,势必要去看朋友的戏、合作伙伴的戏、邀请方的戏以及自己关注的艺术家的戏。英国文化协会、BBC、苏格兰当地的戏剧协会等等都会组织自己的板块,板块内的剧目是按一定的思路策划选择的,也会有自己的侧重点。艺穗节期间,大大小小有几十种报纸杂志每天发布相关的剧评和剧目介绍,英国各地的媒体都派出了自己的记者蹲守艺穗节。最值得关注的当然还是来自伦敦的《卫报》,这家报纸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发布当年艺穗节的潜力好戏戏单,艺穗节开始之后,若干个评论人轮流上岗,个个都有着丰富的行业经验,有人专门负责话剧,有人专写舞蹈和肢体剧场,有人专门报道音乐,还有人专写喜剧和脱口秀,剧评间隙,还夹杂各种采访手记和心得,如果你发现自己喜欢某位剧评人的口味,那么跟着他/她的文章看戏,不失为一种聪明省力的选择。
然而,所有这些“纸上谈兵”的秘籍,都比不上一条人人皆知的原始经验:看口碑。艺穗节上,成千上万的观众对好戏的需求如同嗷嗷待哺的婴儿,一部戏如果好看,风声马上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几个钟头内就从城东传到城西。层层叠叠的艺穗节海报、蜂拥的人群将爱丁堡鱼骨状的中世纪老街淹没得看不出原本的形状,你要做的,就是把自己变成一尾鱼儿,潜入这片深海,凭直觉来感知潮水流动的方向。今年艺穗节上第一部口碑爆棚的戏《开诚布公》(Man to Man),就是这样来到了我的面前:先是有个别朋友推荐,随后陆续在不同的咖啡馆、餐馆、剧院前厅反复听到有人提起这部戏,最后,我竟然在离这个戏上演的剧院1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剧院的厕所里发现了这场戏的传单掉在地上。走出厕所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个有网络信号的地方用手机买了这部戏最近一场的票(值得一提的是艺穗节开发了自己专属的APP,名为Fringe 2015,最强大的两项功能就是即时买票和查找剧场和演出时间等信息)。第二天,在去看戏的路上,《卫报》的剧评发表出来了,再往后,这部戏就光荣地登上了“售罄”榜。
艺穗节的“售罄”榜(Sold Out Board)也是一桩值得一提的壮观景象。任何去过Pleasance Courtyard剧院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里的“售罄”榜尤为巨大,挤挤挨挨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剧名,榜首“售罄”两个大字触目惊心,又带着某种骄傲,炫耀性地告知匆匆赶来剧院的人:今日、明日以下剧目均已售罄,请君自行查找,不必再劳神询问票房。艺穗节的票一旦售出不退不换,很少有人会提前很多天买票,因为潮水和风声天天在变,看戏计划自然也不断调整,“售罄”榜也仅仅预告未来两三天的情况。聪明人把“售罄”榜当作最好的选戏指南,哪些票今天卖光了,那么就订它明天、后天演出的票。然而,对于一些真正热门的戏来说,“售罄”榜也不顶事,因为它不仅是未来两天,而是已经全程售罄了。《装下去,直到你真的做到》(Fake It'til You Make It)就是这样一部戏,它后来得了今年爱丁堡艺穗节的“先驱天使奖”(Herald Angel Award),开戏不到一周,三周的票就全部售罄,晚到的人就只能扼腕叹息了。
在艺穗节上,最受欢迎、上座率最高的,永远是喜剧、马戏、脱口秀。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喜剧(comedy)最终超过了话剧(drama),成为爱丁堡艺穗节最大的表演门类的原因:普通人进剧场,主要还是为了找乐子。“艺穗节十佳笑话”、“艺穗节十佳搞笑段子”之类的评选,是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哪位艺术家在自己的戏里说了一句什么妙语,很快就会风靡。剧场在这里并没有被神化,也因此演出现场总是保持了一种自发的、原生态的戏剧气氛,台上台下,常常处于心领神会的默契状态,艺术家发出的消息,观众接得住,观众席散发的信号,艺术家也能反射回来,看戏本身便成为一种无法复制也无法替代的体验。所谓戏剧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的“现场的魅力”,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体验吧。
纵观艺穗节的“话剧”,一个感触是,在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发轫的国家,戏剧作为一门工业——制造业,已经发展到了何等成熟、专业的程度。独角戏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这种形式是艺穗节演出的主流,初衷当然是为了节约成本。然而,艺穗节的独角戏有本事把只有一个人的舞台做得有好莱坞大片的观感,上文提到的《开诚布公》就是最好的范例,一个女人在台上讲述自己扮演男人的故事,“一战”、“二战”、西德、东德、“冷战”、偷渡、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个人、国家、历史,没有什么是独角戏不能承载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气场和带来的体验一点儿也不输今年国际艺术节上的两部主打剧目——大剧场独角戏《遭遇》和《887》。
在艺穗节看戏,总能感觉到戏剧与日常生活的关联之紧密:普普通通、常常在公共叙述中被忽略、简化、扭曲的个体,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以为意以至于抛诸脑后的情绪和问题,却在这里得到了最认真、最诚实、最妥帖的对待,因此不免对做出这一番努力的艺术家们满怀感激。例如今年艺穗节上获得苏格兰艺术俱乐部“最佳苏格兰戏剧奖”的《吞咽》(Swallow),不过就是三个普通女孩的故事,一个患有幽闭症和抑郁症,一个刚刚被男友甩了想自杀,还有一个是努力想要“出柜”的女同性恋,相当平常的主题,相当平凡的小人物,很容易就变得庸俗的痛苦和绝望,却在这部戏里被挖掘得深入骨髓,不带丝毫故意和做作,最后竟然现出了某种具有诗意的悲剧的崇高感。
“自爱丁堡艺穗节成立以来,人们就一直在预言它的衰落。”琳·加德纳说,“但人们总是到艺穗节上来寻找戏剧的未来。”甚至连“艺穗节”这样一个名称本身,也成了人们对戏剧的未来的期许:爱丁堡艺穗节之后,从都柏林到布莱顿,从阿德莱德到温哥华,从纽约到北京,世界各地都陆续拥有了自己的“艺穗节”。但是仍然只有爱丁堡,汇集了那么多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的戏,持续挑战着我们关于“什么是戏剧”的认知。“前两年,谁能想象一个男人小心地在舞台上一块一块垒石块也能成为一出戏?或者看着塑料袋在空中飘浮也是一出戏?”类似的,今年获得艺穗节最有名的奖项“全面戏剧奖”(Total Theatre Award)的两出戏可以如此描述:《活动的肖像》(Portraits in Motion),把家庭相册一张张投影到大屏幕上并进行讲解;《我能重新开始吗?》(Can I Start Again Please?),翻完一叠纸,就演完了一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