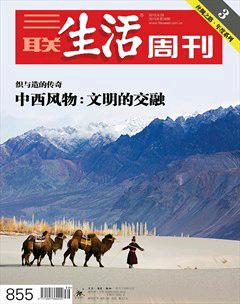丝路之丝:一种重新认识世界的方式
王恺

2009年,第一次在新疆考古所看到大批的丝绸织物的遗存,这个以往不算珍贵文物的东西,在现在的考古研究中越来越发挥重大作用。之后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敦煌丝绸遗存展览上,见到了中国的丝绸学者赵丰,他向我介绍了丝绸文物的价值,以及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里存留的丝绸文物的状况,这时候才真切感觉到:原来,丝绸之路上的“丝绸”部分,是活生生的,并非抽象意义上两个字,从这些文物上,既可以看到东西方怎么交互影响,又可以从这些丝绸,包括毛织品和麻织品的遗存物上,全面观察人类文明史上“衣”的发展进程。
后来才知道,赵丰从小在海宁长安镇长大。那里曾经建设有浙江缫丝一厂,所以他从小就从在丝绸厂工作的父母亲身上获取了很多关于丝绸技术的基础知识,大学时期,他学的是丝绸工业技术,后来又转学丝绸科技史,加上成年后在世界各地漫游的经历,使他成为兼具丝绸工艺专业知识及专研物质文明史的专家。在研究文化史的专家中,这种文理兼通的学者并不多,采访他数次,他从文献结合考古实物的讲述,帮我理清了关于丝绸的许多困惑。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这是个庞大的课题,刚刚兴起,很多研究成果尚无定论,但是成果颠覆了很多以往的认识:比如丝绸之路很早就开始,甚至在中国刚出现丝绸的时候,草原游牧民族就开始使用了。再比如,丝绸传播并不是单向的,粟特帝国的粟特锦,就曾经反向传播到中国,影响了唐代的丝绸制造。
丝绸是从何处起源的
2009年,在新疆和阗的达玛沟文物挖掘现场,看到了很多壁画的残片,色泽鲜艳,很多拼接不出来当年的样子,不过上面还是有各种人物线条,依稀可以猜测当年的故事;比如《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的东国公主将蚕种带到瞿萨旦那国的故事。当年东国公主将蚕的种子私藏在花冠里,然后偷偷带到瞿萨旦那国,在路过关卡的时候,因为检查人员不敢搜她的花冠,所以顺利地将蚕种带到了她出嫁的瞿萨旦那国,当地的丝绸业因此发展起来。
这个题材,在新疆很多地区的壁画上都有反映。最有名的一块,现存大英博物馆,目前新疆博物馆里面有它的复制品。画面的正中央是东国公主,头戴非常漂亮的花冠,右边有侍女正在用梭机纺纱,而另外一边的侍女则用手指向公主的帽子,似乎暗示帽子里面藏有玄机,在公主前面,还有一只碗,碗里面有一颗颗圆形的物质,很像蚕种,画面展现得很详尽,几个画面联系在一起,故事就完整化了。
按照《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当时位于现在和田地区的瞿萨旦那国后来学会了养蚕,但是因为当地是佛国,不肯杀生,所以没有学会中原地区的缫丝工艺。当地都是将破了的茧子抽松,然后进行纺线,和棉纺织类似,但是这样就不能抽出长丝来了,与中国做法完全不同;另外一种说法是,当地珍惜来之不易的蚕种,所以不肯杀死茧蛾,一定让它飞出来,再产卵,进入下一轮培育新蚕中。
斯坦因在新疆找到的不少版画上面,都有丝绸织造的过程,包括用竹片工具,也有拿割刀割断丝绸的。但是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型是什么?文献并不清晰,《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很多只能算是传说,按照赵丰的分析,这个东国公主应该是当时丝绸之路上一串小国的某国公主,有可能是楼兰公主,但应该不属于中原体系。“当时中国对丝绸技术的封锁并不严密,所以不太会出现这种故事,相反,丝绸之路上各个国家为了从丝绸贸易中抽取高额税收,所以严格控制蚕种往西边传。”
这个故事,也反映了中国的丝绸传播的不易,先可能是丝绸实物传播,然后慢慢是技术的传播,但最早技术可能用于纺织棉毛等制品,之后是蚕种、桑树等的传播,落地生根后,当地有了自己的丝绸制造产业,再之后才是双方艺术风格的相互影响。
中国是最早发明桑蚕丝织的国家,这在历史上已经有定论,因为中国内陆广泛存在桑树和野蚕,所以能结成各种野生的蚕茧,人们再慢慢驯化成家蚕,从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大量资料来看,这个应该不会有误。
赵丰说,1926年,中国早期的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找到一个存在于仰韶文化时期的半颗蚕茧,因为被刀刃切去了一半,所以一直被称为半颗茧,当时出土就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考古学家李济找许多学者看了蚕茧,开始既没法确定是,也没法确定不是。后来找到中国昆虫学的创始人刘崇乐先生,才确定是桑蚕茧。但是因为距离今天有5000年,所以人们很难相信那么早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养蚕技术,也有人认为这个茧是食用的,并不能证明当时中国人已经会养蚕了,这半枚茧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1958年,在湖州钱山漾地区找到了半筐丝绸织物,一下子把中国的蚕桑文化提到了4000年前左右;1980年,在郑州青石村又挖掘出一些丝织品的残物,发现是典型的桑蚕丝纺织品,还有染色痕迹,丝绸在中国的起源被推到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而早期的希腊文明也记载了中国的丝绸,不过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丝绸的制造过程,他们把丝绸理解为羊毛树上采集的羊毛纺织成的漂亮织物,一直到公元2世纪才慢慢弄明白真相。
这并不能怪希腊人,即使在中国早期,因为蚕的复杂习性,人们对它寄托了很多神秘含义,首先认定蚕不死,破茧化蛹是羽化的意思,甚至羽化一词都是从这里面来的。而桑林也被赋予了复杂的含义,包括人们在里面举行生殖狂欢,而纺织成的丝绸早期也只作为尸体所穿的衣服,却不是悲哀的含义,而是吉祥的意思,认为只有穿上这种衣服才能升天,这也是早期中国的墓葬群中发现大量丝绸织物的原因。

从现在的考古资料看,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肯定早于西方没有问题。因为只是到了拜占庭时期,波斯僧人才把中国的蚕种带到西方,西方国家才明白丝绸的由来——此时距离丝绸之路的开通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波斯人不希望西方国家与中国直接做生意,这样他们可以控制中间商的巨额利润,所以一直控制着丝绸之路。以至于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被波斯人盘剥,很多商人开辟了北方丝绸之路,而不再走欧亚草原。这时候,西方有了相对准确的丝绸知识,查士丁尼大帝向突厥人讲了蚕的相关知识,非常准确。
但是,丝绸之路上的靠近中国的国家,包括当时的西域诸国,以及中亚的国家,是否原本就拥有蚕种和桑树?这个疑问是我在新疆碰到的。新疆有很多古桑树,当地人对桑树的利用有漫长的历史,不仅仅提供养料给蚕,也用桑树皮造纸,和新疆邻近的中亚国家如乌兹别克斯坦也是蚕桑丝绸的重要产地,现在,当地也还留存大量古老的桑树。赵丰说,他在当地一些13世纪的遗址上,也看到很多古老的桑树。那么,这些桑树是原生种吗?还是从中原而来?
另外,在丝绸之路上,蚕种就一定来自中原吗?印度有学者认为,印度的野蚕也曾经影响过丝绸之路,的确,无论是希腊书籍的记载,还是玄奘的记录,都曾经提到过野蚕丝的纺织品,但是,这些野蚕丝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丝绸之路?
赵丰说,光靠文献记载已经难以辨别真相。唯一的方法是科学地分析出土的丝绸之物的遗存,他们找了很多遗存的丝线,发现家蚕丝和野蚕丝确实不同,家蚕因为营养丰富,吐的丝粗壮,而野蚕丝偏细,结果发现,很多丝路上的丝织物的成分很复杂,里面既有家蚕丝,也有野蚕丝,很多丝绸制品不是从中原运过去的,而是在当地生产的。这点很容易看出来,因为当地生产丝绸,是先把丝打成棉线,再用平纹重组织生产,和内地的织法不太一样。但是,即使是这种在当地生产的丝绸织物,也会发现里面包含既有家蚕丝,也有近乎野蚕丝的很细的蚕丝,这就更增加了复杂性:并不能就认定当地也有野蚕丝生产,也许是传过来了蚕种吃了当地的桑叶后,吐出了细丝?中亚等地的丝绸,究竟是受中国工艺的影响学会了生产,还是整体传播,连物种、植物群落一起从中原移植而来?这还是个无法特别清晰化的问题。总之,在没有更大量的物质材料前,中国和印度,包括中国和中西亚之间的丝绸交流,还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要进一步下结论,需要更多的材料。
丝绸之路上的著名的丝绸文物
在新疆和中亚尚未出现丝绸生产的早期,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就有丝绸输送到西方了,当时的路径已经很难彻底清晰化,但是根据猜测,基本上走的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喀尔巴迁山脉的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通道。这条通道纬度平直,北有森林,南为耕地,最早活动在这里的是游牧民族,但是因为交通不便利,所以基本上不属于后期频繁的丝绸贸易,大约起止时间为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也有学者把这段文明称为“库尔干文明”时期,“库尔干”指的是草原文化中特有的用石头垒起来的巨大的墓葬群,中国的新疆北部、北面的俄罗斯,还有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等地,都有这种墓葬群,说明在阿尔泰山两侧早就有交流,丝绸也就是顺着这条道路流传出去的。
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发明了提花织机,能够织出精美图案,刺绣也很发达,当时,北方地带、中原,包括长江流域都能生产出丝绸,也就是因为丝绸的流行,才可能一直被贩卖和馈赠到那么遥远的阿尔泰山的北侧。靠近阿尔泰的冰雪覆盖的深山,也就是巴泽雷克的谷地,从1929年开始,苏联的考古学者一共挖掘了六座大墓葬,一般认为,这里是早期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墓地,一共发现了五片丝绸,其中三片是比较普通的平纹织物,另外还有织锦,以及一片蔓草纹刺绣,当时只有中国有这种技术,赵丰在圣彼得堡的博物馆看过这几片残片,整个巴泽雷克墓葬群的珍宝都收藏在这里,包括大量的马具,还有完整的马车,里面还有布满刺青的人皮,墓顶上吊着几只天鹅标本,这是当时在墓葬中流行的意向,就像在草原中天空真实飞翔的天鹅一样。但是这几片丝绸丝毫不弱于这些珍贵文物,那件蔓草鸟纹刺绣非常漂亮,应该是在绢上刺绣,用的是中国传统绣法:锁绣。之后,在天山的吐鲁番地区,也出土了凤鸟丝绸刺绣,而且和内陆的凤鸟形状很类似,可以肯定,战国时期,这一类丝绸就到了新疆,然后再通过阿尔泰山,到了另外一侧。
除了丝绸,在这里流通的还有其他的纺织品,比如世界上最早的地毯,也是巴泽雷克墓葬中出土的,细部的图案很漂亮,包括草原民族喜欢的高帽子,说明当地的纺织技术也很成熟,有没有受到中原影响尚不清楚,但是草原民族流行的动物捕食图案也确实在中原出现过,包括草原流行的鹿、狮子等,说明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单向的,反过来也在影响中国。
中国的丝绸遗留,在西汉和东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分野。原因在于墓葬结构的变化,西汉之前,内地的墓葬基本都有大量木头做棺椁,外加挖得很深,所以保存的丝绸都比较好。但是西汉后期,因为内地改成了砖室墓葬,保存状况就很差,这时候,能保存下来的丝绸制品基本都在干燥的西北地区,加上之前也出土的西北地区的一些丝绸残片,构成了中国丝绸文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大部分丝绸制品,都出现在新疆和甘肃地区,因为这里彻底的干燥,使这里的丝绸制品在千年之后仍然保存了原来的许多特征,这里也是当时汉朝的势力所在,在嘉峪关外的阳关和玉门关,有许多烽火台,附近有很多垃圾坑,考古学者在这些坑里发现了很多丝绸制品,玉门关附近的花海墓地,也发现了很多漂亮的丝绸文物,包括用扎染工艺制造的丝绸,这属于汉人地域所发现的丝绸文物。
玉门关以西,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地界。1900年,斯文·赫定重新发现了楼兰,之后是斯坦因的进入,他在高台墓地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丝绸织物,包括各种锦囊,其中一件毛织品上面还有希腊的神像。说明早期这里属于东西方交流之所在;斯坦因把大量丝绸文物放在了英国和印度;在他之后进去的只有少数日本人,如桔瑞超等人;1949年之后这里被设立为禁区,一直到2003年,新疆文物部门才再次进入,发现了楼兰王陵,里面有大量保存不错的服装,后来经过考古学界复原后发现,与壁画上面的古人服装非常类似,都有宽大的袖口。
楼兰附近的营盘和尼雅也发现过大量的丝绸文物,尤其是尼雅墓地,十几具棺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汉代织锦服装。根据专家研究,这系列墓主人里面很可能包括精绝国王。这里面发现的大量汉锦很多属于东汉和魏晋时期,一般称为“云气动物纹锦”,这是在早期东周织锦图案上发展而来的,但更加自由多变,在各种云气造型中间穿插有神气的动物纹样,并且还有带有吉祥意义的汉字。

9 月15 日,中国丝绸博物馆2015 年度“丝路之绸”特展展出一具身着绸衣的“新疆营盘男尸”
1959年,当时的考古学家在尼雅墓地短暂挖掘过一次,挖掘出一件漂亮的云纹服装,没有动物,里面穿插了汉字“万世如意”,所以叫万世如意锦,这和史书记载的“云锦”有所类同;之后在楼兰出土的很多锦上面也有各种形状的云纹,有团状,也有小朵状,里面穿插有神奇的动物,应该是汉代求仙理想的反映。在动物之外,也有文字出现,比如斯坦因带到印度新德里的一件云锦。这和后面的很多云锦图案可以对照观看,但是这件相对完整,之所以存放在新德里博物馆,是因为当时印度资助了斯坦因到中国的考古,所以也有部分存在了那里。
赵丰看到了这件,大为欣赏,整个云锦非常完好,上面有完整的图案和铭文,是我们第一次在丝绸文物上看到了人名,上写“韩文绣文佑子孙无极”。后来,1995年再次在尼雅墓葬群挖掘,陆续发现了一批有铭文的锦绣,基本都是东汉生产,陆续运到西域国家的,不少是汉室赏给当地国王的。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从东汉到魏晋时期,图案也在变化,尤其是云的形状,后期的山状云越来越多,而且铭文也有了变化,除了祈福文,也有一些表达特殊含义的铭文。比如1995年在尼雅墓葬群出土的著名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诛)南羌”,这是一块五色锦,和汉代流行的五行包括五味观念相符合,用四重丝线在不同区域变化,最后就变成五种颜色。这是一块长条状的物品,发现的时候,分成两段,上半段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按照我们当代人的理解,这句话听起来很吉祥,和现在五星红旗暗合,而且又有“利中国”的字样,因此被定的文物级别很高,在新疆博物馆也有了重点待遇。
但是真实的情况没这么简单。考古学者在附近发现了纹样一样的小织锦,上面有完整的“南羌”,还有半个言字旁,所以学者们推断这应该是同一块织物。整句话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诛)南羌”。按照考古学家,也是墓葬的挖掘者于志勇的研究,当时打仗时候要观察星向,这应该是一句鼓舞士气的话,尽管“五星出东方”的例子在天象上极其少见,但是当时很多文书有记载,应该是统治者鼓舞人心的话。后来赵丰又在国外的私人藏家手中看到了类似的残片,均为五色织锦,非常精美,在文物价值上,可能五色织法的重要性,比那句吉祥话的意义更大。
根据学者研究,这块织物整件应该是护膊,缠在胳膊上,供老鹰站住,所以使用者是出外狩猎所用。
在这个阶段,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也并非单向,而是双方互相影响的。公元前300多年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导致了漫长的希腊化时代,约在公元2世纪开始,丝路上的希腊文化开始显现,而犍陀罗艺术的影响持续更为深远,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丝绸文物,充分显示了这一特征。赵丰说:“比如尼雅出土的蜡染棉布,同样是1959年那次考古挖掘的结果,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注意,后来在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做走向盛唐的展览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两块棉布应该是一块,里面的主题很受西方的影响,里面的半裸女神也许是希腊女神提喀,或者也说是中亚当地的女神阿尔多喀洒,而棉布中间的图案,应该是希腊神话中与狮子搏斗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这是一块中国发现的早期棉布,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蜡染作品。”
1995年在营盘发现的一件锦袍,更能说明这点。营盘属于大罗布泊地区,靠近楼兰,整个墓葬在一片戈壁滩上。1995年在其附近的一片山脊上,发掘了15号墓葬,考古人员立刻觉得很不一样,挖掘出一具戴有麻面具的男性尸体。1996年运到上海的丝绸之路展览上展示,立刻震动世界,被称为“营盘美男子”。他的面具上面有白色涂层,表情很安详,面部表情俊朗,眉眼细长,额头上面还有金箔,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衣服,非常鲜艳,保存完好。因为后来要把他的衣服剥离下来,赵丰看到过他的尸身处理,很奇特,用丝绸捆绑,像处理木乃伊一样,手指上也捆绑丝绸,为什么这么处理,没有答案。因为当地的考古发现中没有这种处理方式。现在也没有办法弄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国际上通用“营盘美男子”来代称他。他身上的裤子本来以为是毛的,后来发现是当地的丝制造的;而衣服是双层锦,正面是红地黄花,反面是黄地红花,上面的童子图案,按照专家的考证,有可能是希腊神话里的爱神厄洛斯。但手中拿着武器,是盾和剑,比较奇特;另一件在附近发现的锦袍,上面也有厄洛斯的形象。事实上,不仅有爱神形象,在青海都兰墓地发现的北朝晚期的织锦中,还发现过太阳神的形象,不过是接近印度传过来的太阳神形象了,用中国技术完成,并且添加了一些中国的想象,和希腊的太阳神已经不太一样。

唐 托盏侍女绢画(吐鲁番阿斯塔那187 号墓出土)
从西方倒过来传播的丝绸文化
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传播,先是实物传播,后来是原材料和技术,再后来,是整体的艺术风格。生产技术落地在中亚和新疆一带的时候,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最典型的是中亚的暂丹尼奇,也称为粟特锦,大约是中国的唐代开始生产,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居住,慢慢地从乌兹别克斯坦,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西北和内陆地区,他们的织锦和中国传统的纺织技术互相影响,提升了双方的丝绸生产技术。
根据中亚史料记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附近的赞丹那,一直到很晚还生产赞丹尼奇。赵丰去到那里的时候,只发现很多几百年历史的古桑树,可是已经没有人会纺织丝绸了。之后又去了邻近的库卡村,在那里找到一位老农,才知道附近的村落在过去分工合作,都生产丝绸,有的村庄负责纺织,有的村庄负责染色,但是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到来,要求停止私营经济,赞丹尼奇的生产在当地就停滞了。
现在只能从遗址里发现关于赞丹尼奇的奥秘了,粟特的都城虽然被毁灭,但是考古学家发现了很多精美的壁画,比如布哈拉附近的瓦沙拉遗址,上面的壁画里面所绘的纺织品有明显的赞丹尼奇的联珠花纹,另外在撒马尔罕的宫殿遗址里面,也发现壁画上的人们穿着粟特锦,上面的图案有绶鸟,有长着狗头和翅膀的怪兽,还有双人骑骆驼的图像,骆驼鞍和马鞍上也有大量的联珠纹。随着粟特人的迁移,在中国敦煌的壁画上也出现了类似图案,比如隋代洞窟里就出现了类似的图像,但是在其他年代洞窟则没有,联珠纹画得很精细,里面还有驯虎图,说明当时很多人已经习惯于粟特锦的存在,而且基本就是那个时代开始传入,画工觉得精美,所以用在壁画里面。
中国管粟特锦叫波斯锦,西方却习惯叫赞丹尼奇,主要是因为在比利时的辉伊大教堂发现团窠对野山羊纹锦,上面直接写赞丹尼奇,因当时中亚最著名的生产村落赞丹那而出名。
赞丹尼奇纺织方式很有特点,与中国传统纺织方式完全不同,一看就能看出来。在中国的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发现了大量的波斯锦,其中野猪和马鹿造型都很流行,而在敦煌的藏经洞里也发现了大量波斯锦,不过目前,价值高的基本藏于英国。赵丰去看过很多次,发现了敦煌波斯锦很多不同的特点,有的完全是波斯传来的,比如一块分藏于英法的野外山羊纹锦,和著名的辉伊教堂的那块很相似,有的是中国唐代自己制造的,比如一块红地团花锦,织法是波斯的,图案风格却是唐的,说明在隋唐的时候,中亚的纺织技术已经反过来影响了中原地区。最后,中原的丝绸织品吸收了中亚风格,又促进了大唐新样,其中有两位工匠何稠和窦师纶,在其中功不可没。
最早的传播,应该是中国的丝绸生产上,有了很多胡风题材,包括狮子、大象和大角羊,这是照西方人的图样来生产的,慢慢的,开始在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形成自己的特点,逐渐把外来文化吸收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过程里,生长在中亚何国的何稠起了很大作用。何国靠近粟特,何稠的父亲是玉雕大师,他自己到长安后,先在隋朝做到太府丞,后来在唐为将作少匠,管理丝绸生产的诸多事宜,最早是仿制波斯锦,后来使用了很多中国技术,织出来的锦绣比粟特锦要精细。在新疆墓葬里发现过这种中原织锦,也有传到日本,收藏于法隆寺的“四天王狩狮锦”,非常精美:骑士头戴装饰有日月纹的皇冠,马有翅膀。这件唐联珠纹锦是波斯风与唐风的结合,据说7世纪由遣唐使带回,做过圣德太子的御旗。
传说中李世民的表兄窦师纶,被封爵为“陵阳公”,他所创造的很多样式,也就成了“陵阳公样”。样,指的是风格和模式。当时唐流行的变形联珠纹、宝相花外环,还有动物纹夹缬,都是他设计并突出的。而且不仅仅在丝绸制品上,慢慢还在金银器物上显现,特别具有唐代特点。
在他的领导下,大唐创造出很多新样,在很多诗人的诗歌里都有提及。不过保存大唐新样最多的,还是敦煌。敦煌的丝织品,先是被斯坦因带到英国和印度,然后又被伯希和带往法国一部分。其中日本大谷探险队拿走的丝绸文物在大谷破产后,卖到韩国,也有部分后来辗转流到了中国旅顺,所以有部分后来收藏在了旅顺博物馆,也算是幸运。这些丝绸文物,大部分赵丰都观摩过。敦煌的丝绸文物,以幡为最多,幡分为几部分,头、面、手、足和身,每部分都有不同的图案和纹饰,其中法国的吉美博物馆收藏了许多,很多都有精美的花朵图案,其中有一只上面的花鸟图样,和诗人王建提到的“蝶飞参差花婉转”是近似的。花鸟图样在唐晚期,已经是敦煌丝绸的主角,敦煌的丝绸文物可以和壁画形成对应关系,是一种丰厚的遗存。
法门寺地宫里的丝绸品也为数不少,可是很多尚未整理出来,有很多被包起来的尚为打开。其中有一包从侧面看足足有几百层,因为当时一件服装就有多层,表里垫、多件层就更多了,很多还能看出花样。比如一件蝴蝶和穗状花卉对排的,也算是大唐新样。按照发掘人员的说法,刚进地宫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金线,一碰就会断,应该是地宫里悬挂着大量丝绸帐子,织进了金线,丝绸因为潮湿而腐烂,但是金线没有烂,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形。
地宫旁的物账碑上面有详尽的记录,说地宫有多少宝物。但是目前尚无法一一对应。其中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一件绣裙,说是武则天的绣裙,但是根据赵丰的研究,这件团花纹样的精美织物更可能是件包裹皮,近年和德国科学家合作打开的裙子与此完全不同,腰部的织金锦绣一对喜相逢的凤凰,下面用银手绘了裙脚,已经氧化发黑了,但是还可以想象这些裙子当年的艳丽。
尾声:日本留存的中国丝绸名物
隋唐年间,中国的丝绸开始向日本传递,使日本成为丝绸之路的最东端。遣唐使带回大量的宝物,很多都存放在正仓院和东大寺里,中国由于改朝换代的频繁,导致很多文物都被破坏,许多丝绸文物都是通过考古挖掘而出现的,而且集中在西部地区,但是日本因为自己的系统,保存比较完好,在正仓院能看到很多唐代的丝绸文物,尤其是圣武天皇年代正好是唐鼎盛年代,所以能看到很多唐物风貌。
在“国家珍宝账”里面,记载有袈裟,其中有件仿照树皮色制造的,造工非常考究;装载正仓院紫檀琵琶的宝花织锦袋子,也是一件传世文物;屏风是另外一件与丝绸有关的珍宝,现在保存的山水夹缬屏风十二叠,属于唐代的夹缬,这种特殊的夹缬织物,既有屏风作品,也有普通作品。除了山水外,还有鹿纹,鹿头上戴有花盘,应该也是中亚风格的影响,说明胡风跨越了整个中国,又传到了日本。
夹缬属于一种唐代宫廷发明的特殊印染工艺,传说是唐玄宗宫廷里柳才人的妹妹所发明,最初是秘密制作,后来传遍天下,在丝绸之路上逐渐流行。日本保存的这些夹缬非常珍贵,因为在中国只能找到若干不完全的类似文物,但是日本在盛唐时代只派遣了两次遣唐使,何以有这么多夹缬丝绸制品,实在难以明白,日本并没有自己的夹缬工艺,所以这些制品应该明确来自唐。
另外一个藏有大量丝绸文物的地方是法隆寺,正仓院有17万件染织品,法隆寺只有3000件,但是里面也不乏珍品,比如悬挂的3米左右的幡,虽然纬线都断了,但是经线还在,还能窥探出原来的面貌。目前法隆寺的展品基本都在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因为保存条件更好,所以定期会拿出展览。其中有几件特别能看出中国、日本和整个丝绸之路的关系:比如一件黄地龟背纹绫,和青海都兰出土的很相似;另一件兽面纹绫,上面有飞天的形象,这应该是北魏时期的产品,何时去了日本,并不清晰;还有一件著名的佛殿纹绫,上面织有少见的建筑物形状,周围还有几个人,可能是早期佛教题材。很多纹样在当时广泛流行,在日本的丝绸文物和新疆出土的文物上都能看到,可见当时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的广泛性。
还有一些丝绸制品,也能说明各个不同区域文明复杂联系。比如新疆现在还在织的艾德莱斯,是一种扎经线的染色绸缎,但是在日本被叫作广东裂,说明当时是从广东一带传入的。东南亚也有类似的纺织方法,朝鲜也生产类似的织锦,还专门进贡唐朝。但是据考证,这种织法的起源地可能是在印度,说明某种丝绸文化的流行,在当时是席卷整个亚洲大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