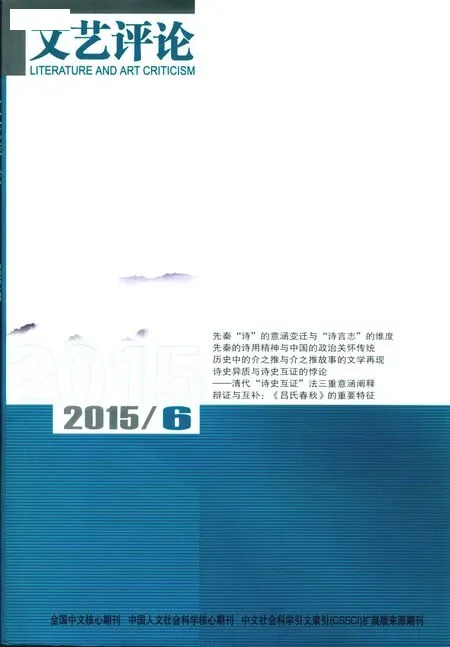玄奘晚境之我见
——从玄奘死无塔铭谈起
李谷乔 李明非
玄奘晚境之我见
——从玄奘死无塔铭谈起
李谷乔 李明非
在国人心目中,高僧玄奘取经归国以后,受到了唐朝皇帝极高礼遇,其生存境遇也极顺意,各地电视台播放的有关玄奘的纪录片,都是沿着这一思路制作的。然而,笔者经过深入研读现存的有关玄奘晚年的文献,发觉真相绝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一代圣僧玄奘,在亡故时是没人给他刻写塔铭的,而且时隔五年,即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下令发棺迁葬玄奘时,竟也没有命人为他树碑立传。我们现在看到的刘轲撰写的《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作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距离玄奘亡故(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已经173年了。又过了两年(即开成四年,839),此塔铭才得以镌成,立于坟前。作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高僧,玄奘不仅是在圆寂之初没有塔铭,后来高宗迁葬他于樊川时,仍旧没有塔铭,直至其圆寂后整整175年,才有塔铭树立,这着实令人倍感诧异。
要知道,唐代甚重“饰终之典”①,当时佛教的丧葬观念受民俗影响,通常在僧侣圆寂以后,都会在其坟前树一块塔铭以记述一生的功德行迹。玄奘生前得到了唐太宗、唐高宗的莫大荣宠,太宗曾赐予玄奘价值百金的衲衣,以示对其独一无二的恩典。高宗对玄奘的德望和才识也是极为肯定的,他在《答元奘请入少林寺翻经书》中称赞玄奘“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皎心灯,定凝意水。”②另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还是唐中宗李显满月时的剃度高僧③。如此功德崇高的玄奘,何以两次下葬都无人为他写塔铭呢?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人们都极力回避为玄奘盖棺定论呢?
而且,我们还须注意到,这块迟来的塔铭完全是佛教界依靠自身力量一步步争取的。先是安国寺和尚义林,以“见(玄奘)塔上有光,圆如覆镜”④的灵异现象而奏请唐文宗,经皇帝批准后,义林得以重修玄奘墓塔。但工程并非官给银两,而是义林“与两街三学人共修身塔”,即费用是义林召集长安东西两街寺院的内供奉僧、三教大德僧共同捐集的。当玄奘塔“修毕,林乃化,遗言於门人令检曰:‘而必求文士铭之’”⑤,后来令检颇费周折,最终才说服刘轲撰写了这篇玄奘塔铭(刘轲开始也是推辞的,在《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中,他自述是“三让不可”)。如此看来,这篇玄奘塔铭可谓来之不易了!
那么,高僧玄奘的晚年究竟经历了什么?笔者依据刘轲撰写的《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道宣撰写的《续高僧传·玄奘传》,慧立、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冥详撰写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以及佚名辑录的《寺沙门玄奘上表记》,认为玄奘生命的最后十年,即从永徽六年(655年)至麟德元年(664年),皇权一直在不断打击玄奘的佛教权威地位,以至后来竟对其生存境况漠视不理。事实上,盛名之下的玄奘,晚境相当困顿,且身后凄凉。
一、五品尚药奉御挑战佛教权威
玄奘於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645年)回到长安,到麟德元年二月五日(664年)在玉华寺圆寂,共二十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6执政。总体讲,玄奘在贞观年间是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太宗驾崩后,继任者唐高宗,在其统治早年,尚能坚持礼敬玄奘,譬如派朝臣慰问,频施财物等等。但是,随着高宗逐渐剪除掉太宗朝的辅政旧臣势力,以及武则天地位的不断提升,玄奘与皇权的关系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双方关系变化的起始时间定在永徽六年(655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吕才事件”,玄奘归国后的佛教权威地位,正是因这一事件而遭遇了严峻挑战。
永徽六年(655年)五月,尚药奉御吕才著书,质疑玄奘译场中三位高僧——神泰、靖迈、明觉对《因明论》、《理门论》二经的义疏互有矛盾,进而攻击玄奘的译经和授业之法。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中,吕才的措辞犀利,他说:“然以诸法师等虽复序致泉富,文理会通,既以执见参差,所说自相矛盾。义既同禀三藏,岂合更开二门,但由衅发萧墙,故容外侮窥测。”吕才在这里甚至由神泰、靖迈、明觉三人的义疏互有矛盾,而将矛头直指玄奘,指责其译场组织不力,众僧各行其是。在序文最后,他甚为傲慢地教训起玄奘:“法师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择善而从,不简真俗,此则如来之道不坠于地,弘之者众,何常之有。必以心未忘于人我,义不察于是非,才亦扣其两端,犹拟质之三藏。”⑦毫不客气地要玄奘“择善而从”,俨然一副师者形象了。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玄奘在面对吕才的公然挑衅,竟两个多月未做出任何回应,以至吕氏之论“媒炫公卿之前,嚣喧闾巷之侧”⑧。最后,还是玄奘的译经僧慧立作书向左仆射于志宁求助,才使得“其事遂寝”。但仍有朝臣认为此事不能就此不了了之,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致书玄奘的僧徒,期望僧人们能对吕才的攻击做一个说明,柳宣在《檄译经僧书》中称:“若其是也,必须然其所长;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朝野俱闻吕君请益,莫不侧听泻瓶,皆望荡涤掉悔之源,销屏疑忿之聚。”⑨玄奘一方在三天后,由明浚回复,严厉批评吕才“岂得苟要时誉,混正同邪”,意即吕才乃沽名钓誉之徒,其著述也是胡说八道以混淆视听的。这激起吕才辩论的冲动,经高宗准许,“群公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最终的结果是“吕公词屈,谢而退焉”⑩。
其实,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觉该事件里有疑点。第一,吕才仅仅是五品的尚药奉御,无论官阶还是学识都算不上优等,如若不是有强大的后台支持,何以能如此突兀且十分嚣张地挑战圣僧玄奘的权威呢?而处境尴尬的玄奘,又为何在半年多时间里一直保持沉默呢?众所周知,玄奘无比珍视自己的佛教学说,且拥有圆通无碍的辩才,在印度“无遮大会”期间,他极自信地表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难破者,请斩首相谢”⑪。然而,这个为了学术尊严不惜以死相谢的玄奘,为什么这一次面对吕才的肆意侮辱,却一再隐忍吞声?玄奘的顾虑究竟是什么呢?第二,这件事的解决方法,也着实耐人寻味。先是玄奘的学生慧立实在不忍,挺身替老师向于志宁求助,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记载:“(慧立)闻而悯之,因致书于左仆射燕国于公论其利害”⑫,在于志宁的干涉下,“其事遂寝”。这种不了了之的解决,似乎也很合玄奘的意愿(至于后来双方论辩,则是吕才自不量力主动请求的结果)。那么,处在斗争焦点的玄奘,为什么一直回避正面处理这件事呢?第三,“吕才事件”仅见载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代的其他文献都没有相关记载,甚至连确知此事的道宣⑬,后来在撰写《续高僧传·玄奘传》时,也绝口不提此事。凡此疑问,都让我们隐隐觉得是有更强大的势力在暗中参与,以致当事人和旁观者都三缄其口。
“吕才事件”应该就是高宗、武后幕后设计的,由近臣吕才充当“打手”,陷玄奘于难堪,以图最终迫使玄奘理屈词穷而主动屈服皇权圣意。从结果来看,事件的“落败者”——表面看是吕才,实则为高宗、武后,确乎由此更加体察到玄奘智慧的高深及其思维的难以驾驭,以至在此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玄奘管控。至于事件的“胜利者”——玄奘,只是暂时赢回了面子,其日后的遭遇却越发困顿了。“吕才事件”的第二年,即显庆元年(656年),朝廷派六大臣监督译事⑭,这是皇家对玄奘监控的加强,也侧面反映出统治者对玄奘宗教权威地位的恐惧。
二、伴驾洛阳的凄苦处境
巧合的是就在高宗皇帝加强监管玄奘的这一年夏五月,玄奘旧疾——冷病复发,以致几乎不起。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记载:
法师少因听习,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岭,遂得冷病,发即封心,屡经困苦······今夏五月,因热追凉,遂动旧疾,几将不济。道俗忧惧,中书闻奏,敕遣供奉上医尚药奉御蒋孝璋、鍼医上官琮专看,所须药皆令内送。⑮
玄奘此番大病,文献记载是由旧疾复发而来,也许玄奘因忧惧自己与皇家的紧张关系而旧病复发,亦未可知。不过,从文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唐高宗当时还派了御医给玄奘诊疗。玄奘也在病愈后不久便以武后临盆为契机,积极为武后祈福,以缓和与皇家的紧张关系。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记载:
(显庆元年)十月,中宫在难,归依三宝,请垂加祐。法师启:“圣体必安和无苦,然所怀者是男,平安之后愿听出家。”当蒙敕许。其月一日,皇后施法师衲袈裟一领,并杂物等数十件。⑯
另据《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记载:
(显庆元年)冬十月,中宫方妊,请法师加祐。既诞,神光满院,则中宗孝和皇帝也。请号为佛光王,受三归,服袈裟,度七人。请法师为王剃发。⑰
玄奘为武后祈福,并借机祈请皇子出家,一方面是出于缓和自己与帝、后的紧张关系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将来能得到一位皇室成员的庇护。围绕着“佛光王”一事,玄奘受到的最高礼遇是在显庆二年(657年),他奉命随驾洛阳,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记载:
二年春二月,驾幸洛阳宫,法师亦陪从。并翻经僧五人、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给。佛光王驾前而发,法师与王子同去,余僧居后。即到,安置积翠宫。⑱
另据《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记载:
显庆二年春二月,驾幸洛阳,法师与佛光王发于驾前,既到,馆于积翠宫。⑲
由上述记载可知,玄奘因在武后诞子的过程中“护佑有功”,故而,得以在帝后驾幸东都时得到随驾的殊荣,且礼遇非常高,是“法师与佛光王发于驾前”。
然而,唐高宗和武后这次优礼玄奘,似乎有更深远的打算。事实上,在洛阳的一年时间里,帝、后对玄奘的态度十分疏淡,玄奘住在城西的积翠宫,而帝、后住在城北的洛阳宫,双方近距离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无依、无助、无援的玄奘,生活陷入窘境,以至患病都得不到医药救治,竟被迫私自出宫求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记载了他事后给高宗的表奏:
玄奘攝慎乖方,疾疗仍集。自违离銮躅,倍觉婴缠,心痛背闷,骨酸肉楚,食眠顿绝,气息渐微,恐有不图,点秽宫宇。思欲出外自屏沟壑,仍恐惊动圣听,不敢即事奏闻。乃有尚药司医张德志为鍼療,因渐療降,得存首领。还顾专辄之罪,自期粉墨之诛。⑳
事实上,高宗对玄奘此次私自出宫求医,是极为不满的,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帝闻不悦”㉑。而玄奘的进表称:是因为自觉病情深重,恐有不测,害怕玷污了宫廷,所以才悄悄离宫的。玄奘的解释诚惶诚恐,让人觉得既蹩脚又可怜,不难推想平日帝、后对他是极为漠视的。再从这一次高宗派的御医等级看,是尚药司医张德志(正八品)较前一年武后怀孕期间,为玄奘治疗冷病的尚药奉御蒋孝璋(正五品)等,已经明显是怠慢和轻忽了。其实,居洛期间,玄奘玄奘是受到严格管控的,连他要回乡改葬父母,高宗也仅给了三天假,由于时间实在局促,迫使玄奘又再次奏请皇帝延长假期。
三、权威地位之最终丧失
从洛阳回到长安后,高宗对玄奘的错位安排,更是匪夷所思。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记载:
显庆三年(658)正月,驾自东都还西京,法师亦隨还……秋七月,敕法师徙居西明寺……敕遣西明寺给法师上房一口,新度沙弥十人充弟子。㉒
玄奘在慈恩寺建成就被诏定为慈恩寺上座,至此时回长安,他的身份仍是慈恩寺上座。而新落成的西明寺(显庆三年夏六月营造功毕)的上座是道宣,寺主是神泰,维那是怀素㉓。那么,高宗让慈恩寺的上座玄奘住进西明寺,身份只是一名普通和尚,这样的人事安排实在匪夷所思。而且,道宣原来就与玄奘不睦,很早便从玄奘的弘福寺译场退出,他后来撰写的《续高僧传·玄奘传》,其中也明显含有对玄奘的不满和人格攻击㉔。高宗任命道宣担任新落成的官方寺院——西明寺的上座,将玄奘充为该寺普通和尚,一方面是使用行政手段强行打压玄奘的佛教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也有扶持玄奘对立面,借道宣之手监管玄奘的意图。而且,玄奘住西明寺期间,身边没有既往追随他的弟子,只有十个新度的小沙弥,也显然是皇帝有意架空玄奘。
离开慈恩寺的译场,看不到取经带回来的梵经,身边也没有译经僧的协助,住在西明寺的玄奘,无奈之下,于显庆四年(659年)奏请高宗,主动要求去陕北的玉华寺,据《重请入山表》载:
自奉诏翻译一十五年,夙夜匪遑,思力疲尽,行年六十,又婴风疹,心绪迷谬,非复平常,朽疾相仍,前涂讵几?今讵既不任专译,岂宜滥窃鸿恩?见在翻经等僧并乞停废。请将一二弟子移住玉华,时翻小经,兼得念诵,上资国寝,下毕余年。并乞卫士五人依旧防守,庶荷宸造,免其□戾。无任恳至,谨诣阙奉表以闻,轻触威严,伏深战惧。谨言。㉕
在表述了自己老迈衰朽之后,玄奘便自贬自疏,一方面他说不愿再“滥窃鸿恩”,请求皇帝停废翻经译场;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去陕北的玉华寺,仅带一两名弟子同往,可于空闲时翻些小经,以聊此余生。玄奘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自愿离开京城,去僻远的玉华寺终其余生,实是相当于主动放弃慈恩寺主之位。这其中到底还有何隐情,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后来玄奘给高宗的书信落款——“玉华寺僧玄奘”来看,玄奘的僧籍已转至玉华寺,且身份就是一名普通僧人。从现存文献,我们可以看出高宗的反应还是很乐意让玄奘就此悄无声息地淡出人们视野的,诏敕回复得很痛快,“即以四年冬十月,法师从京发向玉华宫,并翻经大德及门徒同去,其供给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置肃诚院焉”㉖。虽然准许玄奘继续翻经,但高宗仍旧严密监控玄奘,除了派“卫士五人”防守玉华寺外,还规定译经僧要定期回长安觐见述职。据《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记载:
至正月三日,法师又告门人:“吾恐无常”······其有翻经僧及子等辞向京觐省者,法师皆报云:“汝宜好去,所有衣钵经书,并皆将去,吾与汝别,汝亦不须更来,设来亦不相见。”㉗
由这一段文献,我们大体可以推知,直至玄奘圆寂的麟德元年(664年),高宗一直都要求译经僧定期“向京觐省”,目的是对这个“逊位”的佛教权威严加监控。
玄奘於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在玉华寺圆寂,从正月初一玄奘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到正月初九跌倒伤足、卧病不起,直至最后迁化,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唐高宗对玄奘都是极冷落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均记载高宗派遣的御医是在玄奘去世后才抵达玉华寺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载得更详尽:
法师病时,检校翻经使人许玄备以其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师因损足得病。”至其月七日,敕中御府宜遣医人将药往看。所司即差供奉医人张德志、程桃捧将药急赴。比至,法师已终,医药不及。㉘
玄奘圆寂后遗体被送回慈恩寺安置,至四月十五日下葬,除了“葬事所须并令官给”㉙外,唐高宗竟没有赐给玄奘任何追荣,也没有一位皇室成员或当朝官员参加葬礼,更没人为玄奘写塔铭。然而,刘轲在《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中,不知是出于何种原因,却对皇家给予不合事实的美化,其原文是:
初高宗闻法师疾作,御医相望於道,及坊州奏至,帝哀恸,为之罢朝三日
事实上,高宗在二月三日得知玄奘病危,但他当时并没做出任何善举,直到四天之后,即二月七日,他才敕御医前往探病,而此时玄奘已离世了。基于文献的可信度来判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作者慧立、彦悰,以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的作者冥详,都是追随玄奘弟子,他们的记载更真切、翔实,要比170多年后刘轲的塔铭更有权威。
玄奘的坟就在白鹿原,没有塔铭或碑志,仅仅是“苕然白塔”罢了。但到了总章二年(669年),高宗又下诏迁葬玄奘,理由是皇帝每每望见玄奘的白塔就伤心不已。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记载:
至总章二年四月八日,有敕徙葬法师于樊川北原,营建塔宇。盖以旧所密迩京郊,禁中多见,时伤圣虑,故改卜焉。㉚
高宗发坟改葬玄奘的理由是“伤圣虑”,这着实难让人信服。因为白鹿原隶属蓝田县,是长安东南方向,灞水与浐水之间的一处小小的冲积平原,南北长约10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玄奘坟就是其中一个覆钵式的白塔,并非什么高大的建筑。从地图上看,白鹿原距离长安皇城至少有25公里之多㉛,唐高宗在没有望远镜的情况下,且又患有严重风眩病,他的肉眼应该看不到25公里外的玄奘的小白塔。再退一步说,如果高宗真是出于“伤情”之心而迁葬玄奘,那最起码也应该给玄奘一些追荣,然而事实却是,皇帝这一次连名分上的哀荣都没赐予玄奘!那么,高宗到底是出于内心何种考虑而又去折腾一下玄奘的遗体呢?
皇权险恶,在正面进攻玄奘无果的情况下,高宗、武后便在显庆二年(657年)带玄奘去洛阳,表面上看似乎是无比的恩宠,但实际上却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恩典,玄奘更像是被皇帝近距离地监管,至于回京之后,对玄奘故意错位安排,更是明显的贬抑,并最终迫使玄奘“自省”,主动请求去僻远的玉华寺翻译佛经。应该说,这是玄奘的识时务之举,相当于变相让出了佛教权威地位,满足了皇家的心愿。
四、皇权厌弃玄奘的原因
纵观玄奘一生,他把宏通传译印度佛教原典作为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又因为十分清楚封建皇权对佛教抑扬之巨大作用,即他所说的“外护建立属在帝王”㉜,故而,从印度归国的玄奘是很清醒地去争取皇权的支持。在玄奘心中,只要能够进行着自己最珍视的翻经志业,他什么都可以舍弃,也愿意为皇家效劳。然而事与愿违,小心谨慎周旋在皇权与佛国理想之间的玄奘,并没有得到皇权的长久眷顾,他生前就切身感受到皇权的冷落,也很清醒地预测到其死后事业的惨景,所以在圆寂前他会说:
“吾恐无常”……其有翻经僧及子等辞向京觐省者,法师皆报云:“汝宜好去,所有衣钵经书,并皆将去,吾与汝别,汝亦不须更来,设来亦不相见。”㉝
言下之意便是玄奘已经预知他死后,皇家必然会撤销玉华寺译场,遣散相关僧人,事实也确乎如此,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记载:
至三月六日,又敕曰:“玉华寺玄奘法师既亡,其翻经之事且停。已翻成者,准旧例官为钞写;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其奘师弟子及同翻经先非玉华寺僧者,宜放还本寺。”㉞
实际上,玄奘是超尘脱俗的高僧,有着自己人格的独立性,他矢志不渝地追求自我精神的完善,以期最终涅槃成佛。为此,玄奘情愿过着青灯古佛的孤苦寂寥生活,也甘愿不远万里孤身西行,求取佛法,并将翻译印度原版佛经作为自己后半生的志业。又因为深知皇权是得罪不得的,出于弘法的需要和自危自保的复杂心理,这位追求理想人格的高僧,从心底里是被动地、而在表面行动上却又是积极地,去应酬了皇家各种祈福除灾的法事。
但是,唐高宗和武后则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得到这位有着神秘色彩的“超能活佛”的护佑,他们还希望将这位宗教领袖纳入自己新政治格局的权势范围之内,对此,玄奘是无意参与的。
在佛学理论上,玄奘秉承印度佛学教义,认同一切众生先天具有五种本性的学说,即人有声闻乘种姓、缘觉乘种姓、如来乘种性、不定种姓、无种姓。因为是人与生俱来的,所以不可改变。其中,声闻乘定姓、缘觉乘种姓、如来乘种性、不定种姓都可觉悟佛法,修得果位。只有无种姓(又称“一阐提”,意即没有菩萨心的人),因无佛种姓,将永远沉沦生死苦海,永远不能成佛,这让玄奘的佛学论说具有了贵族化倾向。然而众所周知,武氏本是前朝宫女,一步步地谋取后位,并最终成为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她从政治实用主义出发,是非常希望意识形态方面能为其行为的正当性提供理论支持的。但是,“五种姓说”,恰恰忽视人的后天努力,而直接以人的天生性体判定果位,并把“无种姓”这部分人永远排除在佛门之外,这无疑让武则天这位出身并不显赫、不具菩萨心肠的铁腕政治家,十分不屑。应该说,唐王朝的实际统治者——武则天,对“五种姓”理论的厌弃,是玄奘晚境困顿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此外,玄奘声望极高,深为百姓敬重归信,其信众数目惊人㉟,也在一定程度上,令统治者感到不安。既然玄奘不能助力新政治体系,又恐于其风靡天下的佛教权威性的威胁,统治者最终便做出了一系列摧抑玄奘的行动。由最初授意吕才挑衅;到命其伴驾洛阳,近距离监管;再到放入西明寺,由佛教旧派势力统领;最后以至远放陕北玉华寺……可以说,高宗和武后一步步地实现了削弱玄奘影响力的目的,终迫使其悄然淡出公众视野。朝廷官员们应该是对“圣意”心领神会的,故而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玄奘的遭遇都讳莫如深,以至玄奘下葬时,竟无一位当朝官员亲临送葬,也无一位朝臣愿意为玄奘传述功德懿行。事实上,唐初不乏崇佛高官,据《续高僧传》记载:秘书监萧德言为大庄严寺保恭撰碑;中台司藩大夫李俨撰《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东宫洗马萧钧为普光寺玄琬制铭……而玄奘的塔铭却是在他圆寂后175年才得以镌成树立。足见,高宗、武后时期的崇佛且能文的达官显贵们,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存利益之间,不约而同地都倾向择取俗世的富贵荣华。
【作者单位:李谷乔: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30117);李明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30024)】
①据《唐会要》记载的唐代丧事仪礼,出殡队伍中要有“志石车”,就是在一个彩扎的车子里装上墓志石,公开送到墓穴里。我们由此可知,唐人饰终之典是相当讲究的,只要条件允许,为墓主造刻墓志铭,记述家世门第、生平事迹,已成唐时的社会风气了。
②《全唐文》卷一五,第176页。
③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1页。
④⑰⑲《全唐文》卷742,第7681、7681、7684、7684页。
⑥据《资治通鉴》卷二百,载:“(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2页。
⑦⑧⑨⑩⑫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68-169、170、172、178、169、178页。
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8页。
⑬道宣在《广弘明集》里收录了柳宣的《檄译经僧书》和明浚对此的答书。
⑭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高宗敕曰:“大慈恩寺僧玄奘所翻经、论,既新翻译,文义须精,宜令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兼检校吏部尚书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汾阴县开国男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检校右庶子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中书侍郎杜正伦等,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若须学士,任量追三两人。”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79页。
⑮⑯⑱⑳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91、196、202、211、211页。
㉒㉖㉘㉙㉚㉞《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4-215、215、225、225、227、225页。
㉓《佛祖统纪》卷四十:“二年(657年),敕建西明寺······诏道宣律师为上座,神泰法师为寺主,怀素为维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21-922页。
㉔在《玄奘传》里,道宣说:“今所翻传都由奘旨,意思独断出语成章。”此外,《续高僧传》卷四将《玄奘传》与《那提传》并举,实也暗含有诋毁玄奘之意。《那提传》中明确说:“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声华腾蔚,无有克彰,掩抑萧条,般若是难。既不蒙引返充给使······(那提)所赍诸经,并为奘将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凭。”意思是那提在慈恩寺受玄奘压制,玄奘不仅没有汲引那提,还将其充为役使,并把那提携来的梵文经卷携至玉华寺,故造成那提意欲翻经时,无所依凭的窘境。《续高僧传》卷四,《大正藏》(50),第456-459页。
㉕㉗㉝《大正藏》(50),第826、219、291页。
㉛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五),上海: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社1975年版,第35-36页。
㉟据《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记载,玄奘在民间有巨大的宗教感召力,其回国伊始,便是“自朱雀至宏富十余里,倾都士女,夹道鳞次”。后来玄奘回乡改葬父母,“洛下道俗赴者万余人”。《全唐文》卷七四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683-7684页。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唐代佛教碑刻文化研究”(编号:吉教科文合字〔2015〕第35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