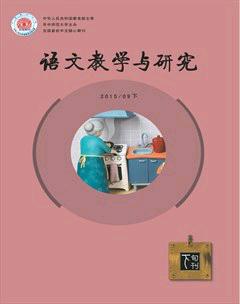有关别离的故事
杨绛《我们仨》
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
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龙应台《目送》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林海音《城南旧事》
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
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
“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
我对老高说:“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爱克苏佩里《小王子》
泪水爬满他的脸。我也无力地坐在沙地上。
他轻轻地倒下去,一点声音也没有。
关于爱、忧伤和成长的哲学,这样的告别带给我太大的震撼。风、沙、星辰,永远都是最美。
杜拉斯《情人》
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车子的那些特征她是熟知的。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她的手臂支在舷墙上,和第一次在渡船上一样。
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她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她看着那辆黑色汽车急驶去。最后汽车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等到看不见她了,他才感到自己心里给那道陌生的目光挖了一个窟窿。他不明白为什么,可是明明有个窟窿。半阖着眼皮,蒙蒙眬眬地靠在车厢的一角,他觉得自己眼睛里深深地印着那一对眼睛的影子。
别的思想都静了下来,让他仔细体会那个感觉。高丽娜的形象在心房外面转动,好比一只飞虫伏在窗子上,但他不让她进来。
门罗《亚孟森》
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某件几乎让他发笑的事。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
片山恭一《倘若我在彼岸》
我们偶然又碰上一次,是在车站的站台上。她在轨道对面的站台上,她、她的丈夫还有两个孩子。我想她们可能是在等上行的列车,我在等下行的电车。
因为只是隔着一条路轨,所以她也马上就发现了我。我们默默地看着对方,就像是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那样,就像是两个在什么地方碰到过又怎么也想不起来的人那样。
不久,广播响起来了,她乘坐的电车就要进站了。我突然想了起来,就做出了曾经约好的暗号。用一只手摸了摸鼻子,又摸了摸耳朵。电车进站了。
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她好像是在流泪。又好像是在冲我微笑。就要确认的时候,她和她的家人已经一起上了电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