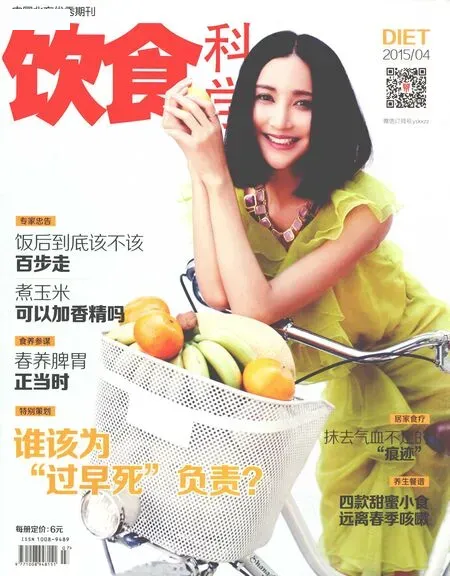饥饿的萧红
◎安东
饥饿的萧红
◎安东

与许多中国作家一样,萧红也喜欢在文章里写食物,但是态度完全不同。看周作人写《北京的茶食》:“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多么雅致的情趣!萧红不一样,有一篇文章《饿》,写她夜半醒来,想到相邻房客门口已经挂上了“列巴圈”,牛奶也已经规规矩矩地等在房间外,只要一起床,就可以随便吃喝,她便饥饿起来,再也无法安眠,仿佛受了人世间最大的诱惑,几次起身,甚至打开房门,想要去偷。
与民国时那些养尊处优的文人美食家不同,萧红始终是饥饿的,我甚至认为萧红最好的文字就是描写饥饿的那些感觉——好比古龙擅长写酒醉第二天的痛苦与幻灭一样,这些都是他们最真切和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萧红的文集《商市街》里有一篇《雪天》,写自己的饥饿:“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睡的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饿了。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悠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里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一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你看这些文字,带着黑暗和荒凉的气息,仿佛两只手,自空洞的胃里伸出。
她与萧军初识,因才华一见如故,可才华填不饱肚子。两人买了一块黑面包回家吃,萧军在面包上掘了一个洞,连帽子也没顾上摘就开始吃;萧红拿了刷牙缸子去楼下倒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了。萧军说:“我吃的真快,怎么吃的这样快?真自私,男人真自私!”又说:“再不吃了。”可说着说着,他的手又凑到面包壳上去了,扭下一块送到嘴里。这段话见自萧红的描述,或许是萧军真的自私,更大的可能则是萧红这颗饥饿的心,对哪怕丁点儿食物也太过在乎。
萧红借到钱,和萧军走了十五里路去小饭馆打牙祭,不等老板招呼就已开始点菜,“我很有把握,我简直都不用算一算就知道这些菜也超不过一角钱。因此我用很大的声音招呼,我不怕,我一点也不怕花钱”。透过文字几乎都能看到她的欢欣雀跃、趾高气扬。她把菜名背得滚瓜烂熟,可也无非是辣椒白菜、雪里蕻豆腐这些便宜菜,其中有一道酱鱼令她耿耿于怀:“怎么叫酱鱼呢?哪里有鱼!用鱼骨头炒一点酱,借一点腥味就是啦!”两人饱餐了一顿,回到家里一面喝着开水一面说:“这回又饿不着了,又够吃些日子。”然后闭了灯,又满足又安适地睡了一夜。这段文字读得人几欲泪下。食物在这里不再是文化,不再是审美,而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人之所以还能生存下去的一个条件。知道饥饿为何物的萧红,始终以最底层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这是她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的最大价值之一。
萧红一生漂泊,这种漂泊源自于她无处不在的饥饿感。饥饿是萧红的第一性,而漂泊最多只能算是她的第二性。不停漂泊是因为她不断面临生理或心理的饥饿,是因为她永远不甘于现状的挣扎与艰难寻找。她渴求食物,也渴求情感,而相对飘渺又无从把握的情感,食物反倒成了唯一切实可触的存在了。
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里,对萧红饥饿感表现得颇为到位:她去投奔未婚夫汪恩甲,两人见面时,她不停在吃,卖力地啃鸡腿,桌上堆满骨头和点心。她在冰冷的小屋里等萧军归来,想的是:“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萧军赚了钱两人下馆子,半毛钱的猪头肉配二两烧酒,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丸子汤,两人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在哈尔滨结识新朋友,她在吃饼干。在上海拜访鲁迅,她在吃荸荠。就算到了弥留之际,拿着端木蕻良弄来的红苹果,她一口咬下去,蜡黄的脸上也透出了光。
出现在萧红感情生活中的每个男人、每段关系,似乎都与食物密不可分。或许,吃与爱一样,是人类最接近本能的欲望吧。
还记得萧红初涉文坛打动萧军的那首诗吗?“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你看,就算自怨自怜的时候,她都惦记着吃。
责任编辑/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