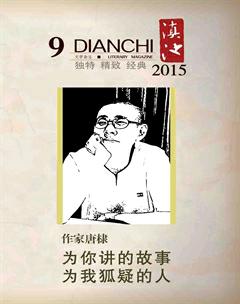我们的越剧,我们的团
尘埃
一、昆明的江南人
云南爱上吴侬软语的越剧就注定会是小众、
遥远而又孤独的。2012年底的一天,在网上看
到有一个叫“剑阳”的人发了一个帖子说她们
昆明飞花群艺越剧团(下面简称飞花越剧团)每
周六下午在云南省文化馆排练厅排练,准备演
出。我才第一次听说昆明还有个业余越剧团,第
一次知道就在我身处的城市还有一群和我有着共
同爱好的人,赶紧问问,剑阳告诉我:这个团是
在 2012年 3月 23号刚刚成立。听说我也是个越
迷,她热情地邀请我去看她们的排练和演出,就
这样有缘结识了这些爱越之人,自己也有幸成为
了飞花越剧团的一员。
2009年浙江绍兴演艺公司来昆明演过一场
明星版《梁祝》后,再没有任何一家专业越剧团入滇演过越剧,我印象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茅威涛带领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来昆明演过一次,再早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越剧刚刚解禁由越剧徐派宗师徐玉兰老师和王派宗师王文娟老师率领的上海越剧团红楼团来演过当时风靡一时的越剧经典名剧《红楼梦》。可惜观看这两次难得的演出我都没有身在其中。
不过就因为这几次屈指可数的越剧演出,把越剧艺术的美好深深地印在了许多云南人的心中,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喜爱越剧的戏迷们。我们的团长沈娅君和副团长李玉梅有幸现场观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徐玉兰老师和王王文娟老师现场演出的《红楼梦》,并荣幸地参加了与老艺术家们的座谈会。
当时年轻的沈娅君是云南省京剧团的一名专业旦角演员,看了徐老和王老她们的演出后,迷上了柔美的越剧,她甚至利用同是戏曲演员的便当,追着徐玉兰老师和王文娟老师,去上海学习了一段时间的越剧。
那年,李玉梅也很年轻,出生在上海,老家是浙江绍兴的,从小喜欢越剧,也有那个天分,十四五岁的她随父母支边,来到昆明,由此错过了成为一名专业越剧演员的可能,可喜爱越剧的心一直没变。1979年看了两位宗师的现场演出,勾激起她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越剧梦。
80年代初,有些喜爱越剧又有点戏曲演绎基础的人,在昆明的工人文化宫里,自发组织了一个越剧队,越剧队里多是些江、浙人,从小就听的乡音,多少都会唱,学起来也不像云南本地人有语言上的障碍,也有少数昆明人加入学习,沈娅君和李玉梅当时都在这个越剧队参加演出。
据说这个越剧队那时有一定规模和影响,行当较全,可以演绎全本的《红楼梦》。随着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市场经济及文化快餐的冲击,传统的戏曲渐渐落入低谷,许多正规的专业剧团不能生存,何况业余的,越剧队就自动解散了。队员们热爱越剧的初衷不改,怀着将来有机会要成立一个越剧团的梦想,各奔前程。让她们没有想到的是,梦想在近三十年后的 2012年实现了。
机缘巧合,2012年,已经退休了的李玉梅身边又集聚起一群喜爱越剧的戏迷,她们聊越剧、唱越剧,想要组建一个越剧团,苦于没有活动地点,经常在各大公园辗转占地盘,还缺乏专业老师指导。这时,沈娅君从云南省群众文化艺术馆退休,不再有繁重的演出和教学任务,想起当年跟徐玉兰老师学戏时,老师希望她能在昆明组建个越剧团,让越剧在昆明开花,现在退休了,正好有时间。群艺馆也很支持,能提供免费的排练厅使用,可以实现老师的期望和自己的梦想了,成立业余越剧团了。
万事俱备,只差喜爱越剧的戏迷的时候,沈娅君和李玉梅这两个在越剧队就认识,已有二十多年没见的老朋友相逢了,一拍即合,昆明终于诞生了自己的第一个业余越剧团。
沈娅君任团长兼艺术总监,李玉梅任副团长,飞花越剧团的顺利成立,与许多老戏迷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其中一个叫刘思玲的老戏迷,跑上跑下地牵线联系,付出了许多辛苦。
二、登场首演
我第一次去飞花越剧团,正赶上她们彩排,服装、道具样样俱全,剑阳告诉我,都是她们自己出钱买的。她把我介绍给团长和副团长,她们很热情,说非常欢迎喜欢越剧的年轻人参加。剑阳一直鼓动我加入,其实没去之前,我一心想加入的,去了一看,那阵势吓到我了。每个人的唱和表演都有模有样,我什么也不会呀,除了爱看戏,别说表演身段了,就是唱,我也一句不会呀。
舞台上有一个唱《琴心》演崔莺莺,唱和身段都不错,剑阳介绍说她叫陆佳丽,演完下来和我聊天,一口浓重的官渡腔,像开心蒙太奇一样,搞得我差点没忍住笑。她说:“怕哪样,我才来还给是只会唱,动作身段也不会,跟着沈老师学噻。”她的口音给了我不少自信,后来跟她熟了,开玩笑告诉她:我之所以有勇气加入越剧团,完全是因为听了她这一口浓烈的官渡腔,她都能唱越剧,我就不信我会唱不出来。
她心宽体胖,呵呵笑也不在意。这陆佳丽可是个土生土长的昆明官渡区福海乡人呵,正宗农民。我奇怪她为什么不去唱滇剧或是花灯这些云南本土的地方戏,偏偏爱上越剧?她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小时候在广播里听过就喜欢上了。别看她年纪不算太大,戏龄可不短,上世纪 80年代,就在工人文化宫越剧队跑龙套,是一个资深票友。为了帮助我尽快上戏,她不但经常指点我身段动作,还把她一直演的《琴心》拿出来教我。这个莺莺小姐,甘愿降身丫鬟红娘,来陪我练戏。
说起我的第一次登台,挺有意思。越剧有一个与其他剧种非常不同的特点,就是她的小生多由女子扮演,爱上越剧,也是因为非常喜欢女小生的潇洒柔美。进团之初,就决定了要做一个风流倜傥、英俊帅气的硬派小生,跟在小生队伍后面练了没两次,团里要演出,差一个跑龙套的花旦,团长问我能不能扮个花旦?有什么不能的,反正我什么都不会。在团友们七手八脚的捯饬下,当场再教了我几个花旦的动作,我就以一个漂亮花旦的形象,完成了登台首演。
救急演出之后,都说我扮相是花旦,很漂亮,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她们就把我从小生队伍里开除了,说实在的,我也被自己的花旦扮相美到了,原来自己还可以这么美呀!
三、娘子和相公的不同来路
刚进团没几天,剑阳一本正经的让我叫她“师姐”。她的真名叫黄燕,是越剧尹派女小生王君安的粉丝,网上看她写的帖子规规矩矩,我还以为是个老学究,其实是个热情、直率又有些固执、孩子气的人,认死理。比我小,还要让我叫她“师姐”?我问为什么,她说要以入团先后时间算,我说那不行!她说她都是这么叫的,我大笑,告诉她:你怎么叫我不管,在我这里行不通,“我比你大,要你叫我姐姐才对。”
她不理我,自己闷头想了几天,有一次排练时严肃的对我说:“我决定叫你师姐了。”之后就一直很认真的叫到现在。其实,大家在团里熟了以后,都很随便开玩笑乱叫的,小生叫所有花旦都是娘子,花旦也管和自己配戏的小生叫相公,我“被”花旦后,一段戏还没演呢,就有了一个相公,她叫张刘云,因演《王老虎抢亲》“戏豹”一段中的王老虎演得像,人送外号“张老虎”。
她叫我娘子,开始我还以为是对我特别好呢,后来才知道,这团里每来一个花旦,她就先霸为娘子,能不能配戏,以后再说,还真有点“王老虎”架势。不过,生活中她也真有点相公风格,是个女汉子型的人。记得有一回排练完,晚上她戴着八、九百度的近视眼镜,飞快的骑个电单车穿城而过,送我回家。各种逆行,占道呵,吓得我一路上不停尖叫加怪叫。她平静地安慰我说:“娘子你放松点,你把我的腰掐的生疼。”我才发现自己的双手正把她的腰当刹车使劲捏呢,哈哈,有性格吧。
这个张老虎,她戏路宽广,扮个老旦也有模有样,由于我念念不忘想演小生,最近她对我说:“你去演小生吧,我来演花旦。”我窃笑,想她五大三粗(与花旦比)我可不看好她的花旦扮相。我说:“你还是演王老虎这样有点坏的小生,比较适合,或者演个花旦的妈妈也挺好。”她说:“好吧,那我俩来演《戏豹》,演周文斌适合你呀,你有花旦的扮相,小生的情怀。”这个主意对我来说真是太妙了,团里英俊潇洒的尹派小生王溪也给我打气,说愿意来为我们助演家丁“王彪”。哈哈,我终于找到可以努力的目标了。
我们这个团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有像陆佳丽这样的淳朴农民,也有大学老师、公司职员、电视台编辑、工厂工人、自由职业者,还有少数民族,两个纳西族,一个叫木丽华,一个叫和红燕。她们俩在一起讲方言时,我们完全像听天书。讲浓重昆明地方口音的人,能唱好越剧我很奇怪,讲根本听不懂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越剧也唱得那么好,更叫我好奇呢。想我学唱越剧那么难,她们是怎么学的?
和红燕从小在丽江长大,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越剧的?”“从小。”我又问:“你什么时候才会讲汉话的?”她说:“上小学。”“在你小时候生活的环境里,你怎么会接触到越剧的?我生活在昆明,记得小时候都很少有机会听到越剧。”她说:“第一次听越剧是在一个同学家听的唱片里有一小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迷上了。“当时在老家,只能偶尔从广播里听到,后来上大学,可以买到磁带跟着学唱,一直走在孤独的爱越路上,总梦想着昆明如果也能像江、浙、沪一样,有戏迷的业余组织,可以一起玩,现在梦想成真了。有专门的排练厅、有老师教、还可以上台演出,现在不单单是玩,学到了许多东西,得到提高,能在昆明这个地方宣传越剧艺术。”电话里听她的声音满是喜悦和满足。
四、在上海拜望大师
越剧以女小生为主,男小生很稀缺,连专业团队都是这样,在我们团就更是这样了。一堆女子和假小子,唯一有一个男小生,真正的纯爷们,相当宝贝。看他也不是那种奶油小生型文艺范儿的人,一个四川人,怎么就会喜欢上越剧呢?
有一天,我特意找他聊了聊,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从小喜欢戏曲,川剧、黄梅戏、越剧都看,以前唱黄梅戏多些,在网上看到昆明有个业余越剧团,就来参加了。”其实,喜欢某种艺术,真的不需要什么理由,也许是深藏在你骨子里面的某种基因作祟、也许就是上天的指引,突然你体会到了它的美,突然它打动了你的心,就是这么简单,只需这么简单。
我们团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以 60后、70后为主,也有 80后。有一个叫许文娟的 80后小妹妹,对越剧简直是痴迷,和我差不多时间进团,又聪明又刻苦。不但老师教的身段动作学的快,化妆从什么也不会开始,到现在,变成全团的化妆小老师了。这还不算,她还手巧,能自己做戏服和头饰。年轻人高科技也懂,电脑玩得好,每次演出,我们团漂亮的电子背景和字幕,都是由她自己做的,为我们的舞台效果增色不少。
加入飞花越剧团后,就有了找到组织的感觉,平时和团友一起学戏、演戏、聊戏,一起相约结伴去追戏、看戏。以前我都是独自背着行囊去北、上、江、浙这些大城市和越剧发祥地追星,看越剧。2014年 8月,我约了我们团的赖玉英、潘磊和我们团长沈娅君,汇集在上海,一起看上海越剧院经典越剧嘉年华系列演出。
这次非常幸运,在团长的带领下,我们拜访了越剧王派宗师王文娟老师,团长给王老汇报了昆明飞花越剧团的情况,王老非常高兴,欣然提笔,为我们飞花越剧团题赠寄语:“要有坚实的积累,要有开阔的视野”。我们还荣幸地被允许进入后台跟当今越剧界最好的大青衣,我的偶像单仰萍老师学习花旦的化妆技术,这也为我的看戏生涯留下了欣喜难忘的一幕。
五、我的宿命
现在想起来,我与越剧的遭遇,是偶然,也是必然;是血脉中的那份相承,也是冥冥中的那份趣缘。
2009年,在昆明很难得的上演了一场明星版越剧《梁祝》。我一直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情有独钟,赶紧去看了。这一看啊,用“震撼”一词形容我的感受,一点也不夸张。彼时,各种“假唱”、“快餐娱乐”、“肥皂泡沫剧”充斥舞台银屏,我居然有幸看到一场真实、真情、真正的舞台艺术。
我很感慨。以前,我以为只有聊斋中的狐狸精能勾人魂魄,看了明星版越剧《梁祝》,我突然发现越剧能勾人魂魄;其实不是越剧,是越剧中的尹派唱腔勾人魂魄;其实也不是唱腔,是唱尹派唱腔的那个人;其实也不是人,是这个人鬓角流下的一滴汗、眼里噙着的一泓泪;其实也不是汗、也不是泪,是汗水、泪珠背后的那一份“真挚”的艺术魅力,勾走了我的魂魄。
透过这晶莹光洁而又有点咸的两滴水,我看到的是舞台上光鲜亮丽、饱满丰富的艺术形象背后,演员们十几年的苦心修炼、孤独坚守和倾心付出。她们心中有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纵使台下只有一个知音,她们也会真情投入表演。她们为观众演、为自己演,更是为心中圣洁的艺术理想而演出。真正的艺术,永远都不会是大众娱乐。
艺术可以追求完美,但不是虚假中的完美,就像人类可以挑战极限,但不是在兴奋剂中的超越。我就奇怪了,为什么真正的艺术都像戏中那些才华横溢而又纤弱乏力的白面书生呢?守着清贫和纯粹,独自超凡脱俗。有时我想,中国戏曲与文艺的孤独和中国诗歌与文学的孤独,确有许多雷同之处。中国戏曲人与中国诗歌人对艺术的寂寞坚持、执着追求,也是相通的 ,估计都是血液里流淌的某种成分在作祟。作为在文学艺术中被逐渐边缘化的诗歌人,真正触痛我心的是那种:“惜惺惺,怜同命”的同类归属感。
为一场演出震撼,被一个微小的细节打动,跟随一个演员的牵引 ,走进越剧艺术之门,是偶然,但文、艺的相通相融、相辅相成,它们对美的发现、理解、诠释与坚持 ,这些共通之处,让我与越剧的遭遇,又变得必然。
我可以在越剧动听的唱腔中发现诗歌的律动;我可以从诗歌悠远开阔的意向张力中,体会出越剧的古老柔美典雅来。我用我的感官去感触越剧;用我的心灵去体会越剧;我更用我的笔端去书写、理解越剧和越剧人。掐指算来,这几年写过有关越剧的诗文不下三十篇,真可谓:爱之深,感之多啊。
因着追星看戏,也因着和越剧的这份情缘,我还结识了许多素不相识的戏迷朋友。每次在不同的地方,为着同一个目的相遇时,不需要语言,相视一笑,就有了一种自己人的感觉。怀揣一份共同的爱好,莫名的你,就会对他们多一份信任、理解和友善。这大概是只有戏迷才能体会到的默契吧?
虽然我们很业余,但是我们很用心。虽然我们演得不太正规,但在正规的越剧团很少走到的地方,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向大家述说:还有一种艺术、一种美的享受,如果你遭遇了,也许会被勾走魂魄,那就是——越剧。
我想,这就是我与越剧在偶然中必然相遇的宿命。
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