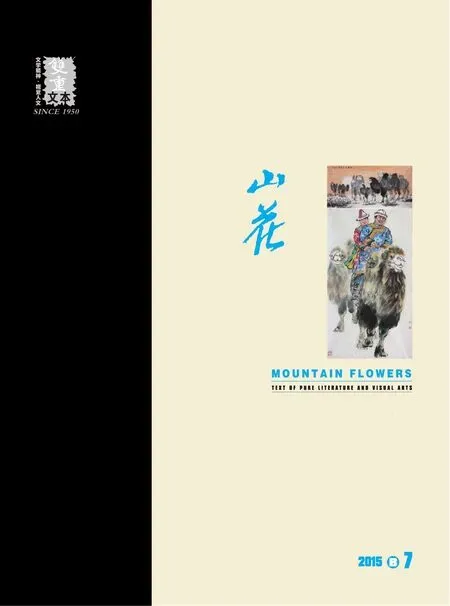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的经典化过程
屈原自沉汨罗江之后,“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可见其事迹及其作品曾在楚国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却没有任何相关记载。这里面不能排除相关文献资料被秦火焚毁的可能性,但可能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地域性特点,使得其传播及其影响都是在楚地这一小范围内进行。屈原及其作品(主要是《离骚》)被经典化是在汉代得以完成的,然而中国古代文学史当中的许多经典作品和作家是可以分离的,但屈原与其作品则是重叠的,作品和作家紧密结合成为一体,谈到屈原定要谈及作品,谈及作品也无法不涉及其身世,可以说是“人文合一”的特殊经典。重新分析这一特定对象的经典化过程可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经典形成过程中的诸多复杂因素。
由于西汉统治集团爱好辞赋,特别是刘邦等故楚政治领袖对故土文化的推崇,“楚声”、“楚辞”等地域色彩极为浓厚的文化因素迅速扩散传播开来,由楚地推向其它地域,并最终风靡汉代文坛。屈原及其作品无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产生影响的。这种影响在汉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骚体的大量出现;一是围绕屈原及其作品引发的争论。然而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尽管屈原的作品已经成为模仿的对象,但在讨论层面,屈原及其作品的精神质素最早成为关注的焦点,其文学的经典意义则是晚些时候才被真正意识到的。
屈原与“悲士不遇”
汉初贾谊是在作品中写到屈原的第一人,其经历与屈原最为相像,同病相怜之下,“悲士不遇”的主题吟唱也从此拉开序幕。在《吊屈原赋》中,他指斥现实社会对方正贤良的倒植,悲悼屈原的人生遭遇,哀叹自己的身世命运。文章对屈原没有择主而仕表示遗憾,“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故都”,并流露出对战国纵横之世和纵横家的向往,“凤凰翔九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贾谊《吊屈原赋》)贾谊处在汉代初年,战国纵横家的辉煌时代虽然已经渐行渐远,但仍然在文人心理上有着很深的影响,而且,从枚乘、司马相如早期的经历看,择主而仕在汉初几十年里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可能性。所以,择主而仕成为贾谊在仕途焦虑中寻找的一条可能的通道。
然而,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贾谊对屈原宗族情感的隔膜。与北方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在其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诸多方面都远为浓厚地保持着氏族社会的传统,有着浓厚的宗族意识。这种情感来源于本民族特殊的地域与文化,如王逸《九歌序》:“昔楚南郢之邑,阮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祀必作歌舞以乐诸神。”同时,这种情感也在因文化差异而受中原各国的长期歧视和侵害中得到更大的激发。
屈原对本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我们在其作品里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比如他在《离骚》中对祖先深情的追认,认为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是楚国大族的后代;在《橘颂》中,热烈地赞扬“生南国兮”的橘树所具有的“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品质以自励;在《哀郢》中,还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表明心志等。①这种对楚国本土的执著眷恋决定了他在被疏遭贬、理想破灭后仍不忍离开楚地他就,因此也就注定无路可走。战国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士人凭借才华另谋高就十分常见,也并非难事。即使是处在春秋时期的孔子也还都有周游列国以图施展抱负的经历。然而屈原却固守旧土,徘徊不忍离开,最终处境绝望自投汨罗江即根源于他强烈的宗族情结。
因此,从贾谊对屈原的评述看,我们可以说他是不够“知人论事”的,缺乏对屈原更为细心地体察,存在一定的隔膜。然而,借他人酒杯浇自身块垒,这在文学接受过程中是常有的现象。贾谊在和屈原的交流中,舍弃了对方经历身世情感中的个性因素,而是在最具共性的经历感受上与之达成共鸣,“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贾谊《吊屈原赋》)在这种解读下,屈原的悲剧就被提炼为一种生命悲剧,是士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与现实发生尖锐冲突的结果,因此也就带有极大的典型性。哀叹生不逢时,悲士之不遇遂成为汉代士人对屈原生命悲剧产生共鸣的精神基础,这一主题在楚辞体的赋作中被反复吟咏,甚至成为一种格套和传统。吊屈、拟骚、反骚,遂成为汉代文人思考生命问题的特殊方式。他们在形式上拟骚,屈原的悲剧也常常作为叙写内容,如严忌《哀时命》、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径直以“士不遇”命题,将“不遇”之感归属于整个士人群体,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专制政治下普遍性的怀才不遇境况。
可见,经典的形成首先要具备相应的个性化的内部质素,即属于个人的独特经历以及独特创造,这种独特性吸引着后世的解读者,同时也因时过境迁造成两者之间的隔膜。然而,这种个性化因素又以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性内涵而揭示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困境,由此在特定时代、特殊人群中产生共鸣。我们看到,屈原在被更广泛的接受过程中,一些异质性的因素在消淡,共性因素被放大加强,这是屈原及其作品在更大程度上获得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屈原与“发愤著书”
与贾谊受政敌排挤遭受准流放的仕途焦虑不同,司马迁所遇到的焦虑首先是职业性的。
作为史官世家的司马迁,职业尊严已受到极大冲击,遭受李陵之祸后,司马迁形体精神更是受到摧残,心境发生极大变化,于是,修史便附加上浓重的个人身世之叹。《史记》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②他对那些支配着人的历史活动的力量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究,这使得人的主体地位被充分地意识到和表现出来,个体在生存中的各种矛盾、困境遂一凸显。他根据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从创作动机的角度重新体察和揭示了屈原创作的意义。在司马迁看来,文章著述是足以驰骋的“舒愤”、“自见”途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样自觉而明确地对著述给予深切而丰长的生命寄托。而司马迁把屈原的创作放置在一个经典创作序列当中,这也进一步有效地提升了屈原及其作品的典范意义。
对屈原行为的伦理道德评判以及“辞赋宗”身份的确立
在文人竞相与之对话、模拟其作品的同时,也有人开始在价值层面对其地位进行定位。最早的研究者是淮南王刘安,据班固《离骚序》云:“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③将《离骚》与《诗经》相并提。同时还从道德层面对屈原进行评价,赞扬屈原“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与日月争光可也”,可谓推崇备至。④根据《汉书·淮南王传》的记载,刘安好书、鼓琴,辩博善为文辞,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刘安为《离骚》作传解说是在时好艺文的武帝的要求下进行的,可见,以帝王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群体在受到屈原作品吸引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赋予其恰切的名分。
然而,随着汉代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诗》教也成为文学创作的首要评价标准。屈原及其创作都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从其行为看,他愤而沉江,行为激烈;从其作品看,“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⑤这就难怪后世忠心信服《诗》教的或诋毁甚至废除它。
与西汉前期刘安、司马迁等人的大力推赞针锋相对,班固对屈原提出了远较扬雄激烈的批评:“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③认为屈原因为露才扬己才受到谗害,沉江而亡,行为狂狷;作品多虚无之语,也不合法度。这些评价显示出一位正统经学史家的价值立场,也将对屈原行为的批评推向极致。
对于班固的批评,之后的王逸也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他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恚自沈”,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屈原及其作品被接受的过程中,从伦理道德层面、君臣关系的层面对其进行褒贬的评述占有很重的分量,屈原与其作品在汉代特殊的社会氛围中已经“人文合一”,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经典符号,这一经典符号有着强烈的影响力、震撼力和感染力,并以其多义带来丰富的阐释的可能,吸引着人们进行一轮又一轮的评说和争议。
“然而,班固并未到此为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班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为《离骚》的经典意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即特别揭示出屈原在辞赋发展史上的成就和影响。在同一篇文章里,班固紧承上述严辞批评之后说了以下这段话:
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⑤
这段评价,显示出班固作为学者的敏锐。“其文弘博雅丽,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这句简单的评语,概括性极强,既有对屈原创作特征的准确描述,又对其文坛地位做了定性,肯定其泽被后世的影响力。在上述论述中,班固建立了一个从楚国宋玉、唐勒、景差到汉代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先后相续、不断以《离骚》为宗的“辞赋”传统⑥,这一说法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也有相类似的表达,可以说,至此为止,屈原在文学上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有趣的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要声明屈原之作“有恻隐古诗之义”,以此尽量减少其创作与主流评价体系的冲突,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至班固为止,近二百年来,有关屈原与屈作的模拟和争论中,屈原及其作品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象征性符号,它持续延传、反复出现,不断被塑造和定位,内在潜力也逐渐得以开发,其文学的经典意义也最终被揭示出来。四百年之后,南朝梁代刘勰对班固的论述多有继承,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就《离骚》及其相关问题再次加以系统讨论,他认为《离骚》在“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词”等四个方面与儒家经典相符合。但是其文中多“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又与儒家经典不相符合。⑦他明确提出屈原“自铸伟辞”泽被后世的特殊成就,同时也描述了相类似的辞赋承传系统。而在班固之后,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更是深入到作品的细部特征,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就进一步给后人提供了理解作品的钥匙。同时,王逸还进一步揭示屈原与屈作“人文合一”的文化价值,“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汉代对屈原作品的整理也是其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随着楚辞影响的扩大,逐渐出现单篇整理的热潮。如刘安《离骚传》,刘向、扬雄分别作《天问解说》,班固、贾逵各自作《离骚经》章句等,西汉末年刘向典校经书,把屈原、宋玉、贾谊、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以及自己的作品编辑成《楚辞》十六卷,这对建立楚辞的承传谱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东汉王逸又在此基础上撰成《楚辞章句》十七卷,统一进行注释解说。尽管王逸解说中多附会经意,牵强穿凿,致使文意滞碍难通,但由于汇集了汉代学者关于楚辞的评说,全面注评屈宋辞作及其拟作,可以说是集此前楚辞研究成果之大成,至此,屈原及其作品的经典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了。
注释:
①伍大荣:《屈原诗歌的故土情志》,《船山学刊》,2001年第3期。
②沈秀芳:《角色塑造与作者本位意识——浅析<史记>中的人物描写》,《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又见苏高岩、刘春芳:《<史记>中的人文精神》,《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
③班固:《离骚序》,《全汉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④韩经太:《论汉魏“清峻”风骨》,《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冬之卷。
⑤鲁迅:《鲁迅全集(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⑥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⑦伏俊琏:《也说<辨骚篇>中的“博徒”》,《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4期;又见谭勇民:《论刘勰的<诗经>学思想》,《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杨景霞(1970— ),女,河北武强人,文学硕士,海南省琼州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文体研究与教学。
——王逸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