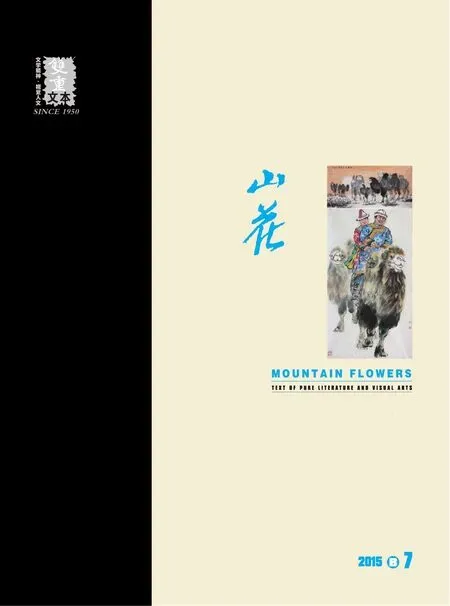一条百褶裙的记忆
潘洪波
家乡蒙加“玛嘎”苗寨坐落在崇山峻岭之中,波光闪闪的梯田,不知何时就被勤劳的人们用双手点缀了一条条绿色的秧苗。一场雨过后,天渐渐晴朗起来。田里的秧苗与山野的青山绿成一片直到天际,显然,夏天即将来临。这时,家乡苗寨的妇女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身上时常还带着一身泥气,她们捞脚挽手地在自家门口的屋檐下,支起一架架纺棉车和织布机,支起一口口小铁锅,加上清水,点燃柴火,就开始抽丝染线。姑娘们在一旁一边挑花刺绣,一边哼着婉转动听的情歌。
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在我幼小的时候常常在母亲和祖母的身边看着她们精心制作百褶裙。制作百褶裙与花衣盛装可算是苗家妇女和姑娘们的一项浩大繁杂工程,也是她们一生重要的课题和梦想。制作百褶裙首先是要自制土布,而土布原料来自自家种植的棉花,棉花进入苗寨不知是何年何代,总之历史是比较久远的了。我曾经与母亲和祖母上山种过棉花、摘过棉花,每当我们把棉花收回家后,趁着火辣的太阳暴晒,使其更加出棉,然后脱壳取其棉花。每当入夜,祖母就在火坑边,一边讲述民间古老的传说或吟唱苗族古老的歌谣,一边不停地将棉花捻成一根根五六寸长的棉条,然后架起纺棉车,套上一节节用过的竹简,一边转动纺车,一边不停地在滚动的竹筒上增添棉条,于是一个个纺锤式的竹筒棉线放满了箩筐,直到半夜三更,这个简单的程序还在不停进行着。
天一亮,母亲和祖母就在堂屋里或在屋檐下调整好自制木架织布机,就像一位严谨的司机师傅,系好腰带后,双脚再不停地换档,左手不断地来回推动梭子,右手则不断地将梳架加紧线条,于是一毫米一毫米地推进,慢慢地,使棉线形成固定均等的经纬交合,土布开始“生长”——一般一块土布宽二尺许,长多为十二、十六或二十六丈不等。土布出来后,也就意味着染料的工序开始了。
不知何时、何因缘,祖上就学会了自制原生态染料。一直到了我们的高祖“晚免”这一辈人,他们搞的蓝靛产业就非常兴旺,至今在蒙加苗寨山脚还遗存着蓝靛池,该池到了农业学大寨时期仍然存在,不久后才被填埋,改成农田。
祖上的蓝靛池就置在古老的碾房边不远的地方,一是看管方便,二是能充分利用山沟换水。蓝靛池直径大约一丈许,深两米左右。周围都是用比较规整的石条砌成,大池边还置有一个小过滤池。通常,蓝靛草都是自己种自己采,一般发酵一次需蓝靛近三百斤,经过浸泡后再加上一定比例的石灰进行,发酵后再加工成蓝靛膏。
祖上除了将蓝靛膏销售到周边苗乡苗寨外,更多的是通过舞阳河、重安江运到湖南洪江、常德等地销售,余下的就自染自用。染布是很讲究的,往往要将十几丈的布经过染缸、染池浸染后取出晾干,晒干,颜色多为蓝白或黑白相间。土布一经染池中取出,要用山上的香柏树叶进行烟熏火烤,这道工序主要是为了定色,再把定好色的土布放在石砧上用木棰轻敲细打,这样经纬线不仅平整,而且土布也会柔和、光亮起来。
一直到我母亲这代人,土布染料才开始退出市场,由于美国、德国的化工原料从舞阳河、重安江运到黄平变得容易,紫色染料也开始进入苗乡。但这之前,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苗寨的姑娘们起早抹黑,在老人的指导和监督下抓紧挑花刺绣,有时还忽略了游方坡上小伙子们激情的拍掌声和木叶声,往往这时的屋檐下、吊脚楼上、美人靠上、大树脚都坐满了挑花姑娘。即便姑娘受了引诱,上了游方坡,她们一边与客人,那些小伙子唱歌交流,一边还不停地运动手里的针线,忙个不停,就这样,在你来我往的情歌声中,姑娘们已将一张张构图精美和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刺绣图案绣了出来,有的图案表现花虫鸟兽,有的表观平原田阡、黄河长江、湖泊高山等,内容极为丰富。
一次,我终于有幸看到了祖母带领大家制作百褶裙的大场面,通常这种带仪式感的劳作并不多见。那天一早祖母走出屋檐下,抬头看了下天气,就十分有把握地在大门口的小院坝上铺开了一张竹晒席,并把晒干了的一块最长的,染好的蓝靛土布放在竹晒席上,再将一块块刺绣连接起来放在布边缀牢,之后再用丝线一针针缝起来。布有多长,刺绣就有多长,一般为四道花纹,虽然工序繁复,但祖母心细地把布料及刺绣图案逐个折皱,然后再用棉线逐个串连起来拉紧,使折皱固定,再穿四道棉线。为了预防下雨淋湿,祖母又将布裙收起来,倒悬挂在竹竿上,最后,抬到堂屋内或厢房或楼上晾干。
几天之后,裙子上的褶皱就基本定型了,抽去棉线,把布铺平在竹晒席上,再用手指和脚指踩踏逐个褶皱,同时用白芨汁喷洒晒干,加固定型,最后,再加上裙首便于捆腰,这样,一条百褶裙才算制作完成。
祖母制作好了的一条百褶裙,寨上的人们都来观看,为她的杰作而啧啧赞叹。一些人不清楚百褶裙的来历,祖母就向大家解释:那是很久以前,苗家人特别是苗族妇女穿的是树皮、树叶、棕皮。有一天,一对母女俩上山采蘑菇时发现了五颜六色的青冈菌和松木菌,她们摘来看了半天,很受启发。这时候,世上已经有了土布,母女俩就按照青冈菌的模样把布折成褶皱,制作成裙子,又把花虫鸟兽的图案缝在裙边——这样,第一条百褶裙诞生了。母女俩穿在身上很好看,于是寨上的人都纷纷效仿。而定居在黄平地区的苗族人多数住在半山上,百褶裙多为中长型的,既方便生产生活,又能美化自身。
祖母一边讲述百褶裙的来历,一边总结自己制作这条百褶裙的经验,虽然,寨上的妇女们评价较高,但祖母还是不满意。她说:我的手艺与上一辈的祖母“巫晚”的手艺相比还差得远。于是祖母就告诉我,那是我的高祖母“巫晚”吴氏,她生于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卒于公元1919年,享年69岁。她17岁就从白保“嘎江”苗寨嫁过来,不久就生了我的曾祖公海晚和翁晚两兄弟。27岁又生了我的曾祖姑仰晚,而仰晚到了六七岁就开始挑花刺绣。她悟性很高,不仅学习了传统图案,而且大胆创新,能把刚从河沟中捉来的螃蟹和田里捡来的田螺表现在刺绣中。这样,既可以避邪,同时又发挥了对生活美好的想象。
当时,高祖母看到自己的姑娘仰晚的刺绣这么精彩,非常高兴,她说这姑娘聪明,有出息。到了仰晚长大成人快要出嫁时,高祖母特地把祖上留下来的一条百褶裙呈现在大家面前,大家看到都很惊奇。高祖母铺开竹晒席,将这条百褶裙摊开,由原来十多丈长增加到数十丈,而裙边由原来两层花边增加到四层,她将大姑娘仰晚的刺绣图案缝在裙边上,内容更加丰富。高祖母仍然用白芨汁进行定型,晾干后,这条百褶裙仍然保留着古老的黑白和蓝色相间的色彩。
据说,这之后不久曾祖姑仰晚就出嫁了,她要嫁到遥远的重兴半山苗寨。按苗家历来的习俗,嫁娶都是在夜里进行。而曾祖姑出嫁的这一天,天刚黑就出门了,由于要翻山越岭,路途遥远,于是高祖母特地吩咐,把自己这条百褶裙陪嫁给大姑娘仰晚一起上路,至于陪嫁的银首饰就留下来,等到翻年的二月二时再派人送去。按习俗高祖母的百褶裙要留下来,伴随着高祖母到去世时作为陪葬品,一般很少送给下一代人,可高祖母这样决定,目的是为了让这条极其宝贵的珍藏能给大姑娘带去好运。就这样,重兴半山寨来接亲的人肩挑各种陪嫁和一条百褶裙上路了。
那是公元1894年,曾祖姑嫁到重兴半山苗寨,成为苗名叫九高杨氏之妻,而九高生于公元1881年,仰晚比九高大4岁。仰晚嫁到半山苗寨后生了两男两女,而两个姑娘长大成人后又嫁回蒙加寨,一个嫁沈氏苗名叫龙,一个嫁给潘昌礼苗名叫拢。而潘昌礼是我们蒙加苗寨第一位考取黄埔军校的学员,之后他弃武还乡成为一名私塾先生,也是苗寨的文人。
仰晚的满儿子合九,曾在黄平县供销社做会计工作,他活到九十多岁,在一篇日记中他这么写道:我的母亲是黄飘蒙加苗寨人,苗名仰晚,有三姊妹,一个嫁白记,一个嫁蒙加大寨沈家。三舅公叫海晚,二舅公叫翁晚,从军未归。大舅公家的经济比一般人家富裕,按现在称得上“小康之家”。母亲仰晚中等个子,是绣花、纺线、织布、缝衣能手……
据说,曾祖姑嫁到半山苗寨后,这条百褶裙也伴随她形影不离,每年一次的芦笙会或寨上的婚丧嫁娶,她都穿出来亮相,深受大家的关注。一次回娘家,仰晚身上背着小孩,肩上还挑一挑粽粑,身上依然穿着这条百褶裙,当她走过重兴半山和马鞍山高石坎梯田时,阳光明媚,层层田梯水光反射,人们正在忙于插秧时节,正在田里插秧的妇女们抬头看到仰晚身上穿的百褶裙,竟像一只翩翩飞来的凤凰,大家忙丢下手头的活路向仰晚围拢,纷纷赞叹这条百褶裙少有的精美!据说那天,仰晚回到蒙加苗寨娘家天已黑尽了。
之后,仰晚常常在半山苗寨给姑娘们和妇女们传授制作百褶裙的技艺,一直到了1950年7月,她去世前一两天还特地交待,她的后人要将这条百褶裙传下去,送给子孙媳妇们做纪念!
仰晚去世入葬时,只得重新制作了一条百褶裙陪葬,这条从黄飘蒙加苗寨陪嫁过来的百褶裙就留下来了,一直到了仰晚去世四十多年后,她的后孙媳妇们才想起家中还有一条古老的百褶裙,于是翻箱倒柜把它从沉入柜底的遗物中翻捡出来……
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个重安江街上的商人,带着两个黄发碧眼的外国人,走了近两个小时的山路,来到半山苗寨,寨上很多人都来看稀奇。通过重安江商人的介绍,寨上人们才知道这两个是法国人,主要是来收买苗寨古老陈旧的东西,特别是要收购苗族的古老盛装。这时,曾祖姑遗留下来的这条百褶裙,被她的后孙媳妇们拿了出来,当时,她们认为搁下去也要烂掉,加上这条百褶裙没有现在流行的裙子好看,若需要再制作一件即可。这样,通过重安江街上商人再三劝诱,最终以极低的价格出卖给了法国人。法国人拿到这条百褶裙,自然如获至宝般眉开眼笑,高兴得伸出大指连声赞好。
法国人一走,寨上的人们还在议论。有的说,这陈旧东西不卖掉,搁了也会烂掉的。有些人说,法国人买回去的这件老百褶裙一定会很值钱。
几年后,我的一位搞民族文化研究的朋友到法国学习考察,有幸参观了巴黎盖布朗利博物馆。该馆的一位负责人十分自豪地介绍:研究中国苗族文化遗产,请到法国来。该博物馆负责人还指着陈列馆中的一条百褶裙,这是从中国贵州黄平苗寨购买来的,十分精美与古老,很有价值。通过我的这位朋友介绍与宣传,我才想起了我曾祖姑仰晚的这条百褶裙。而祖上的百褶裙与苗寨现代的百褶裙相比,让人无法想象它们之间在历史上的流变过程。原来苗族古老的百褶裙是蓝白和黑白相间色,而现在则以紫色和褐色及朱红色相间——这么大的变化,也勾起了我对祖上制作百褶裙的好奇。不久,我就动身实地走访了重安江那位商人,向他了解了我家乡蒙加及半山苗寨这条百褶裙的去向。果然不出所料,当地老人告诉我,当时是有两个法国人来这里收购了一件古老的苗族百褶裙。于是我又来到亲戚家询问,出卖这条旧百褶裙可感到可惜和后悔?她们倒答得干脆:不可惜,后悔什么,这土布做出的东西,搁久了也会烂掉的,再说卖出去了,需要时重新做一件就是。
我问她们知不知道这条百褶裙至今还在法国巴黎陈列展示?她们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现在能不能再做出和那条一模一样的百褶裙?她们纷纷表示,真的做不了,不会做。现在年轻姑娘和媳妇们都在外打工,刺绣都很少有人绣,更谈不上百褶裙了。
离开苗寨,重新融入繁华与喧嚣的城市中,令我久久难忘的那条远在异乡的百褶裙,虽然它是祖上一生心血凝聚所在,是生命中的珍藏,现在它却成了巴黎盖布朗利博物馆别人的藏品了,从结果看,当然是苗族民间文物的流失。但如果它还留在苗寨,就能得到完好的保存,得到最起码的重视吗?在一个缺乏保护措施的地方,它可能早已像一块破布那样朽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老百褶裙能入恒温室,成为殿堂级的藏品,享有它应有的地位也是一桩幸事。
只是,我真的希望,需要我们民族的这些民间文化不要慢慢地消亡了。那么,对于那些还散落在民间,我们还来不及意识到它的重要的物品,我们又如何来传承、抢救、保护呢?这似乎不仅是某个部门,某个地区面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