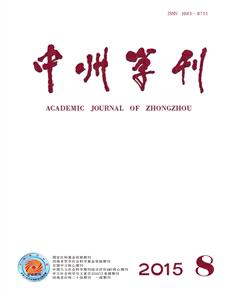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王四达 孙力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各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派生出一些消极现象,如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早在改革初见成效但问题初露时,小平同志就忧心忡忡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①为此,中央曾先后推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重要举措,但由于所提倡的内容较空泛,与民众的生活结合不紧密,故多年来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习近平指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让13亿人的每一分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②要弘扬传统美德,就必须使之符合人性、贴近生活、易于普及,而“孝道”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古人所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百善孝为先”等,即精准地揭示了“孝”在道德教化中的优先性与基础性。甚至可以说,古人的“以德治国”是以“孝治天下”为前提的。因此,以家庭为载体,以孝道为抓手,借鉴古代把孝道文化社会化、政治化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成为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的突破口。
一、古代“孝道”文化及其社会化、政治化
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形成的文化系统,必定有一个能使该民族维持内部稳定有序的基本价值,是一种能把社会控制内在化的思想工具。这种价值与工具又必定有它在特定环境中发育的生成逻辑。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政治型社会,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笔者认为,如果把“仁”作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核心概念的话,那么“孝”的观念就是扎根在宗法社会土壤中原初的文化基因。因为与后起的“仁”相比较而言,“孝”毕竟是先在的文化元素,它源于氏族社会中天然的血缘亲情,其中已包含着亲对子的爱与教育及子对亲的敬与依赖。由于“孝”具有内在的凝聚力与外在的辐射力,所以在氏族社会向国家演进的过程中,“孝”就成为从亲情伦理走向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逻辑起点。美国学者赫斯科维茨认为,一个民族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可以视为该民族的文化焦点,也是该文化讨论最多的问题。“孝”可以说就是古人讨论最多的问题。汉代大儒扬雄在《法言·孝至》中说:“孝至矣夫!一言而该,圣人不加焉。”“孝”被强调到兼该(包容)百行,连圣人对此也无以复加的地步。从这一点上说,它又是传统中国的文化焦点。
所谓”孝道”,是从“孝弟”(通“悌”)两种亲情伦理发展而来的尊亲敬长等善德的通称。朱熹曰:“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弟。”“亲亲”即是血缘亲情最直接的体现。而在亲情中又以父母兄弟最亲,因此,孝亲顺兄就成为社会推崇的美德。从文献上看,这一亲情伦理可上溯至尧舜时代,《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尚书·尧典》称帝尧“克谐以孝”,帝舜“以孝烝烝”,命司徒“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③。在圣王看来,如果人人皆能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便能实现家“内平”而国“外成”。可见古人很早就懂得良好的家庭伦理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功能。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成为孝文化最有力的倡导者。《论语》对“孝”的解释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奉养。“事父母,能竭其力”,且“唯其疾之忧”。二是恭敬。《论语·为政》曰:“今谓之孝,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但“敬”还是有是非的,《孝经·谏诤章》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三是“慎终”“追远”。《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与“孝”密切相关的是“弟”(悌)的兄弟伦理,“孝”与“弟”共同构成家庭教育的内容及个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孝弟”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弟”被置于诸行之先。有子则进一步把“孝弟”强调为“仁之本”,如果一个人从小能行“孝弟”,凡事专注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
孔子之后,孟子对“孝弟”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他敏锐地看到,“孝弟”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之中。《孟子·尽心上》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由于“孝弟”以人性为基,又是仁义之本,因此它可以推广到父兄辈及一切年长者身上。《礼记·曲礼上》曰:“年长以辈,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虽说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仁”是比“孝”更根本的核心概念,但由于“仁”的内在精神是“爱人”,《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故最初的“爱人”便是“爱亲”。《孝经·天子章》引孔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因此,只要把“爱亲”“敬亲”之心扩展开来,“爱人”就在其中了。以这种“爱人”精神为基础,还可以借助社会伦理培育政治伦理,成为国家推行道德教化的重要工具。《礼记·祭义》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由此,古人构筑了一个以“爱”为起点、“孝”为核心的社会伦理系统,它“孝于父”“慈于子”“尊于师”“敬于长”“顺于兄”“友于弟”“恕于友”“慈于幼”“忠于公”(后来渐被扭曲为“忠于君”)。它既贯穿在各种人伦关系之中,又渗透到政治生活之中,所以朝廷有“以孝治天下”之宣示,杜甫亦有“孝理敦国政”之主张。对此,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有一个总结性的阐述:“人之全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爱之源泉在于亲子之间,而尤以爱亲之情发于孩提者为最早。故孔子以孝道统摄诸行……则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皆得统摄于其中矣!”④于是家庭伦理就扩张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这就是“孝道”的社会化和政治化。通过这样的过程,“孝道”已演变为全民族的集体意识,无形中对其他价值观起到整合、协调的作用,由此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系统发育。可以说孝道是个纲,纲举目张。
所谓“社会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通常是指人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即个人在社会生活中通过对社会文化的学习与角色知识的认同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也是基本人格的培养过程。从个人的角度说,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从社会的角度说,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文化熏染,既可使主流价值观获得认同,又可使文化传统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亦得以维持和发展。应该承认,古人在推广“孝道”文化的社会化这一点上是有战略思维的,它以父权为工具,以孝弟为价值,利用从小的家庭教育和上一辈人的示范作用(如孩子天天看到父亲孝顺爷爷),对孩子进行“润物细无声”的孝道教育;孩子读书知礼进入社会后,又接受圣人之书的熏陶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会激发他们的道德欲望,使他们自觉进行价值内化,以符合社会的期望;成家立业后他们同样以自己认同的这套价值观教育子女。这就实现了文化的代际传递,而同时国家也达到了政治稳定的目的。因此,社会化客观上兼有政治化的作用。
“政治化”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其实质是“政治的社会化”。就“面”而言,它是某种政治价值、政治秩序、政治制度被社会接受的过程;就“点”而言,它是个人认识所处社会的政治秩序、制度并接受和适应其秩序、制度的过程。通过社会化和政治化过程,个人才能成为被该社会认可的合格社会成员,而“孝道”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纽带作用。孟德斯鸠曾敏锐地指出,中华帝国是以治家为基础的,“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帝国的太平是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他们看来,服从是维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此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孝敬父母,他们并且集中所有力量,让人们恪遵孝道”,而“尊敬父亲就自然包括尊敬所有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一个儿媳妇是不是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样那样的义务,此事的自身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假如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惯不断唤起一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感情,并且正是由于人人均具有此种感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统治精神”。⑤通过日常生活持久地潜移默化,“孝道”就由社会化发展为政治化,成为古代政治秩序最坚实的社会基础。而这种社会基础与政治秩序的一致是超越王朝政治变迁的,不管历史上如何改朝换代,“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都是不变的。所谓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并不在于哪个王朝能千秋万代,而在于数千年伦理秩序的持久稳定。
二、传统“孝道”文化的现代价值新审视
当然,如果从现代眼光来看,古代“孝道”文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鼓吹“家无二尊”,导致对宗法家长专制的维护,使子女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二是宣扬“移孝于忠”,导致对政治家长制的强化,使臣民成为愚忠的牺牲品。因此,清末民初以来,“孝道”文化与家长制受到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批判。应该说,在当时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这些批判确有进步意义,但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弊。即使如孙文、黄兴等革命者,也看到了传统道德的价值。孙中山曾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道德规范,重新赋予其新时代的新内容。黄兴也批评那种以为提倡新道德就必须否定旧道德的谬论,他说:“夫以孝悌忠信为戒,则必不孝不悌不忠不信,自相残杀而后可。以礼义廉耻为病,则必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论为禽兽而后可。循是以往,将见背父弃母,认为自由;逾法蔑纪,视为平等;政令不行,伦理丧尽。家且不齐,国于何有?孟子所谓猛兽洪水之害,实无逾此。”⑥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后传统文化再次被全盘否定,孝文化也被“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的“领袖爱”“阶级爱”所取代,结果造成人性的扭曲与虚伪。但“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应该说在今天的中国,家长专制的宗法土壤与帝王专制的政治结构均已解体,并不存在这两种专制复辟的危险,经过扬弃,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成分完全可以“古为今用”。恩格斯曾批评近代欧洲“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没有看到它的成就,“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⑦其实,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悠久灿烂,更需要接续古今之间的“伟大历史联系”,只有这样,时代性与民族性才不会脱节,新文化建设才具有民族心理的依托。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号召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而在这一点上,孝文化具有不可否认的现代价值,它可以成为重建传统道德、形成家庭美德、培育个人品德、推及职业道德、惠及社会公德的最佳起点。
1.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
《诗经·小雅·蓼莪》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覆我,出入腹我”;“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诗中感念父母生养我们的辛劳,他们细心照顾呵护我们,出入都把我们抱在怀中。若没有父母,我们就没有依靠。父母之恩如天无穷,不知何以为报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世间最伟大的,儿女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也最真诚。普天之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任何政治说教所无法比拟的,只有这种天伦之爱能在所有人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例如,康有为虽然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但他仍非常推崇孝道,他说:“父母之劳,恩莫大焉。身由其生也,体由其育也,勤劳顾后,子乃熟也。少丧父母则饥寒困苦,终身贱辱。普天之下,计恩论德,岂有比哉?”⑧所以古人有“孝子爱日”之言,称孝子最能珍惜与父母共处的日子,只为能及时行孝,以免父母殁后抱憾终生。在社会高度流动的今天,“孝子爱日”更具现实意义。从一曲《常回家看看》风靡全国,到每年的春运返乡大军,反映出人们对回家团聚的执着,表明亲情与孝心仍存在于出外谋生的人们心中,由此可见,古代的孝道文化在现代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2.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
由于爱亲萌生于幼儿心田,这就把道德教育前置到孩提时代,它会对人一生的品德产生良好影响。一个有孝心的人必定对自己的行为格外慎重。《礼记·祭义》曰:“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一个孝子如能时刻谨记所作所为不能辱没父母,这既是对自己的警诫,又是对自己的激励。所以《礼记·祭义》又称:“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能让国人对自己有这样的夸赞,就是对父母生前最大的褒奖。即使父母殁后,“孝亲”的自我警诫与激励仍须始终如一,既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又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于是,在孝的陶冶下,个人品德和职业道德皆得到淬炼。《礼记·祭义》曰:“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这就是由孝生发的道德力量。古人甚至强调连仁、义、礼、信等道德亦由此(孝)而起:“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⑨——顺此将得乐,反此可犯刑,这种忠言对治疗当前中国社会的“官腐民败”仍具有警醒之效。
3.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
孝道虽是一种源于亲情的私德,但它却是公德的源头活水。蔡元培先生认为,私德不健全,即难有健全之公德。孝道作为“仁之方”,最可贵的就是“能近取譬”,推己及人:爱父母可以生发出爱他人、爱自然、爱生我养我的故土故国,爱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情感。《礼记·祭义》曰:“大孝不匮。”所谓“不匮”就是“博施、备物”,即把这种博爱源源不断地施于万物。“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古人对此的注解是:“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故由爱亲之心而推之,则虽一物之微,有不可不爱者,而况其大焉者乎?”⑩可见爱心可以由小及大,由近及远:对父母的孝心和对家的责任,可以转化为对他人的爱和对社会的责任,扩大为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均表明中华民族的孝道经过升华可以成为一种“民胞物与”、充塞天地的大爱。所以《礼记·祭义》又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于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它能否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准则姑且不论,但它确有能“施于后世”的永恒价值,因为它所包含的博爱精神即使在今天也并不过时。
三、古代“孝治天下”的战略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示
不可否认,现代中国社会与古代宗法-政治社会已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孝弟”的亲情伦理比“忠君”的政治伦理更具有超时空的特性,它并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消失。“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这正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例如,古代帝王推崇孝道当然是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秩序,如果我们撇开这个政治目的不说,把孝道的推广看作古代的社会道德建设,那么其整体化的战略思维和人性化的贯彻手法还是非常有效的。今天我们同样面临着如何有效地推进思想道德建设的问题,古人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特别具有启示意义。
1.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
任何一个社会想要稳定并延续下去,都必须力求使它的成员尽可能地在基本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趋于一致,用主流的信念来引导人们的思想,用统一的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动,以便塑造合格的“公民”(古代则为“臣民”)。塑造过程包括价值施化与价值内化两个方面:价值施化一般是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完成的;价值内化一般是通过个人道德修养完成的,因为个人为了有效地适应社会,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用家庭和社会的期待来塑造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升华,所谓“理想人格”就是这样炼成的。除了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差别外,上述社会化的过程古今并无不同。
然而,“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又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社会化是政治化的基础。《礼记·哀公问》引孔子言:“爱与敬,其为政之本与?”“爱与敬”虽然是为政之本,但它们却是借助社会化扎根的。另一方面,政治化又是社会化的目的。所谓“孝治天下”,表明“孝”只是手段,“治天下”才是目的。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1]所谓主流价值观,通常就是官方倡导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体现现实政治的需要,又以家庭、社会为依托。《大学》有言:“其为父母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此谓治国在齐家。”《孟子·离娄上》又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就是贯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化与政治化的现实载体。清末维新派思想家文廷式称:“古代圣帝明王皆以孝为教,而政辅之以孝,故不必假于鬼神之吉凶,而教不肃而成,政不严而治,此中国政教合一之大端也。”[12]把“教”与“政”建立在人性亲情的基础上而不必用鬼神来威慑恐吓,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的体现。于是,古人通过这样的战略设计实现了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的无缝对接,也为“以德治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
“倡”虽偏于宣传,但它起到树立价值坐标的作用。《孝经·三才章》引孔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被提到“天经地义”的高度,这便是官方推崇的价值坐标,故须“导”民力行之。“导”则侧重贯彻落实,只有倡导有方才能收到实践这些价值观的效果。总的来说,古人倡导孝道的做法主要有三方面:官方制度建设、君子以身作则、民间教化配合。
官方制度建设主要是通过礼乐制度来推广孝道。《孝经·广要道》指出:“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内则》从“礼”的角度对孝道做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如在家里,“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左右佩用”,“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在外头,“见父之执(“父执”谓父之朋友),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13]在社会各领域,比如在朝堂上、在行路中、在乡村里、在狩猎时、在军旅间当如何尊长敬老,规定得非常细。对此,《礼记》的结论是:“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军旅,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意为“众人以孝弟为所宜行,故宁死而不敢犯不孝不弟之事也”[14]。
君子以身作则要求精英们皆应率民以孝。《孝经·三才》指出:“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所谓“师尹”泛指朝廷官员,他们的所作所为民众都看着呢。《大学》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这种榜样作用可产生社会效应,所以古人说“爱敬之道,既立于此,则爱敬之化必形于彼,始而一家,次而一国,终而四海之大,莫不各有亲也,各有长也,亦莫不有爱敬之心也”;“爱敬既立,则由家而国而天下……以感化之也”[15]。《大学》所谓“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民间教化配合则发挥耳濡目染、“习以性成”的作用。古人很早就懂得“习以性成”的道理,认为人之生性会因长期的习惯而养成:它既可以因习善而养成善性,也可能因习恶而助长恶性。《尚书·太甲上》曰:“兹乃不义,习以性成。”而政与教就是“习以性成”的决定因素。《荀子·大略》曰:“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据史书记载,为了加强孝弟的教化作用,周时即在朝廷设“三老”“五更”之官。所谓“老”“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弟也”。[16]所以古人有“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之说,因为培养尊老敬长之风可以带动孝弟之道。秦汉以来,朝廷又把“三老”“五更”设到县与乡,使之掌乡民教化。《汉书·高帝纪上》载:“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为三老,乡一人。”又设“孝弟”乡官,其职责是劝导乡里,以助成风化。由于措施得力,教化有方,民间尊老敬老亦蔚然成风。以“乡饮酒礼”为例,《礼记·乡饮酒义》载:“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豆,古代食器),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白居易《策项》曾曰:“臣闻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程颐《四箴》则说:“习与性成,圣贤同归。”要做到“圣贤同归”也许不现实,但在民间推行一些切实的教化措施并持之以恒,必定能收到移风易俗的良好效果,其道理即使在现代也不例外。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德,国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中国当前已有“坏基”之虞,特别需要以国基养护为务。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并非不重视道德建设,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到“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再到最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内容并无不对,但社会道德状况仍无明显好转。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官方的政治“天话”不接民众的生活“地气”,难以引起民众情感上的共鸣;二是道德目标泛泛罗列且不断变换,既缺乏头绪也缺乏一个现实的抓手;三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缺乏相应的同步改良,使健康的社会意识无法在不良的社会存在中顺利生长。在这三方面古代“孝道”文化均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有所启迪。
首先,一种文化价值观只有贴近人性,源于情感,才能深入人心并成为构建社会道德的基础。古人看到孝道乃人之天性,天性之理可顺而不可逆,如果舍弃基层的亲情伦理,忽视中层的社会伦理,上层的政治伦理必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故历代帝王皆不遗余力地倡导孝道,并没有把政治伦理凌驾于亲情伦理之上,甚至不惜允许“亲亲相隐”来维护社会基础价值,这当然不会引起民众的暗中抵制或虚伪以对。
其次,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心灵结构,该结构的道德品质有层次性的逻辑关联。在古人那里,“孝”就是这个心灵结构中的逻辑起点。孔子以孝道统摄诸行,孟子指出“孝弟”植根于人天赋的“良知良能”,圣贤对各种德行的内在逻辑、主次先后,皆梳理得清清楚楚。古人关于孝为“仁之本”“本立而道生”的论断是很有见识的,其道德教育以孝为抓手,再循序渐进地培育君子人格,也是切实可行的。
最后,一种道德之所以能够扎根,必须有适宜的社会土壤。古代也曾因恶政而产生周期性的“官逼民反”,但由于孝道扎根于血缘亲情的社会土壤中,政治生态变坏并未导致民间“孝弟”之风丧失,所以即使改朝换代,新王朝也无须进行道德价值的重建。而现在由于缺乏扎根于民间的道德基础,所以当社会存在恶化时,我们应致力于社会生态与社会意识的同步改善,而“孝道”即是一个最适合的突破口。古代以“孝治天下”作为“以德治国”的基础条件是很富有创见的。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②参见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③崔爱芝、宋鹏主编:《世界通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3页。④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页。⑤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中华书局,2006年,第209页。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94页。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页。⑧康有为:《大同书》,中华书局,2012年,第175页。⑨[13]《四书五经》,线装书局,2007年,第160、99页。⑩[14][16]孙希旦注:《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第1227、1227、576页。[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12][15]吴枫主编:《中华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52、346页。
——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