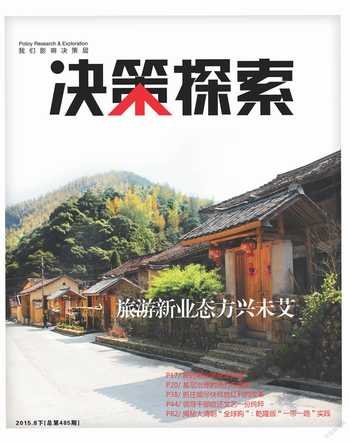迈进现代社会,“道德良知”不能缺失
葛晨虹
现代社会治理中,政治精英、制度学者容易强调制度建设及其功能,这是对的,没有制度和法治,国将不国,但制度治理不是唯一的。我们在强调大力发展外在制度性规范建构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现代人的内在心灵秩序问题。
转型期人们的心灵秩序往往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现代化带给人们诸多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心灵秩序的“碎片化”和“无意义感”,个人的无意义感、无归属感、无认同感、孤独感,是许多现代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伦理思想史上提出三问:什么是好生活?为了好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人应当成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仿佛我们更关心“应该如何行为”而不是“成为怎样的人”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规则功利主义导向的世界,往往使人忘记了人性的高贵、人的美德的意义,丧失了人的精神家园,沦为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物化”的“单面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片面“物化”的发展忽略甚至放逐了精神家园、意义价值和人性的追求,社会出现大量道德问题,也因此人们把由现代“物化”生活模式、规则功利主义而发生道德社会规导的局限,称作“现代性的道德困境”。
此外,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构,人际关系建立在了一种非血缘、陌生人的利益关系基础上,交往活动不再囿于亲缘范围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体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公共交往。陌生人交往或现代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友爱德性即公共精神的普遍化,其中就包含着对陌生人的友爱和他人意识、责任意识。而在市场化大潮下,原有血缘关系社会基础和精神文化被冲破后,新的契约关系和适应陌生人际的公共精神还未准备齐备,这就容易出现“道德冷漠”“低信任度”等社会道德问题。以“道德冷漠”为代表的转型期道德困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公共精神”或者“公共社会德性”。也就是说,现代公共生活中陌生人之间的人际相处,需要更多的“他人意识”和“共在意识”,需要更多的对他人、陌生人的尊重和友爱,即需要道德公共精神来调整。外媒对“中国人的分析报告”说:“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中国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祉,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这类分析报告虽然不全面,但也不失深刻,触及到中国人公共精神、他人意识、友善能力方面一定程度的缺位。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表明社会治理进入系统治理、制度治理的语境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简单陷入“唯制度主义”单向解读中。对于现代社会治理与现代人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而言,仅有物质不够,仅有制度也是不够的,要想建立真正公平而和谐的社会,在制度正义、依法治国基础上,还需要社会德性、公共德性和人性良知作为重要补充。社会秩序应该是制度、法制、规则、秩序加上“心灵道德秩序”“他人意识”和“公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