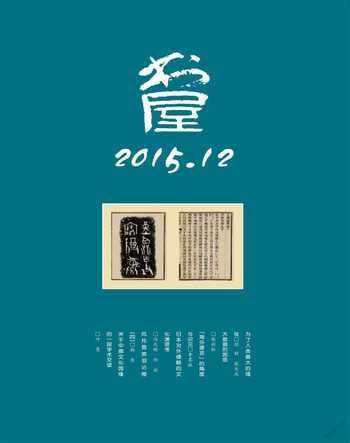阿伦特论法国大革命失败
陈国战
汉娜·阿伦特的革命观集中体现在出版于1963年的《论革命》一书中。此时,距离第一次为她带来极大声誉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的出版已经十多年过去了,在这十多年中,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考日益成熟,并形成了坚定的古典共和主义政治理想,《论革命》一书即可以看作是她政治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具体操演。众所周知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分是阿伦特政治哲学理论的一块基石,因而,她早期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论述就成为支撑其革命观的理论基础。在《论革命》中,阿伦特运用自己的政治哲学理论烛照沉睡的历史材料,不仅发展出独树一帜的革命观,而且清理了法国大革命由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最终演变为恐怖统治的内在逻辑。
在阿伦特看来,革命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政治事件。据此,她在《论革命》中为革命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即“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构建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根据阿伦特的界定,革命是现代社会以来才出现的历史现象,它不同于前现代时期的各种政变,因为政变并没有发生“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它只不过是权力的易主,使历史进程重新回到循环的另一个起点而已。更为重要的是,阿伦特把革命与解放区别开来,她认为,革命的起码目标是“构建自由”,而自由只存在于公共领域,因此,革命就是要缔造一个保障每个人都能平等参与的全新政治体;而解放的目标则是保障私人领域的自我完足——既摆脱物质匮乏的奴役,又挣脱各种人为的压制。解放的成果或许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条件,但我们绝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一方面,解放实现不了革命的目标,因为革命的目标要求建构一个公共领域,而解放则只关心一个免于压制的私人领域;另一方面,革命的手段也实现不了解放的目标,因为与解放有关的事务是应该“交托给专家来处理的行政问题,而不是以决定和劝说的这种双重进程来解决的争端”。因而,一场革命要想取得成功,革命者就必须具有明确的“公私分明”意识,即必须能够区分解放与革命这两个不同的目标以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尤其要警惕属于私人领域的诉求过多地参与到革命这一政治事件的进程之中。
然而,阿伦特也意识到,在历史上发生的革命事件中,解放的目标与革命的目标几乎总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虽然“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每一次尝试都会导致恐怖,而且正是恐怖把革命送上了绝路。然而几乎无可否认的是,当一场革命在大众贫困的条件下爆发时,要避免这种致命的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正是在这里,阿伦特找到了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即试图“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与马克思认为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完全相反,阿伦特认为,贫困问题是非政治性的,它不仅不能促成革命,反而会败坏革命;寄希望于通过革命手段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是不可能成功的。不管是贫困,还是由贫困引发的同情、暴力、必然性观念等因素,都应该严格限定在私人领域中,不幸的是,恰恰是这些因素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并使它由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走向了恐怖统治。
正如许多历史研究者提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由苦大仇深的贫苦大众发动的,在向凡尔赛宫进发的人群中,为面包所困扰的家庭主妇是主要力量。因而,从一开始,对面包的需求就成为压倒一切的革命动机。在阿伦特看来,贫困来自生存必然性的诅咒,它是应该交由专家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能够通过言说和行动来解决的政治问题。然而,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所说,“胃的造反是最糟糕的”,相比于政治自由的缺失,物质匮乏显然具有更大的紧迫性,要求人们饿着肚子去追求政治自由是不现实的。于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是,自由这一革命的目标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为消除贫困这一解放的目标所取代。于是,人山人海的法国革命群众跟随罗伯斯庇尔振臂高呼:“共和乎?君主乎?我只知道社会问题。”贫困成为法国革命的强大动力,并始终主宰着革命的进程。
贫困引发了革命者同情的激情,而同情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暴力。不管是同情还是暴力,都内在地具有一种无言的性质,因而是不适合出现在公共领域中的。同情作为一种“善”必须绝对隐藏起来,一旦公开显现,就势必变成伪善并对公共领域形成破坏。暴力也是这样,如果说在私人领域中,人们为了对抗生存必然性,暴力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手段,那么,在公共领域中则应该严格杜绝使用暴力。不幸的是,在革命这一政治事件中,同情和暴力常常纠缠在一起,并最终成为败坏革命的因素。首先,同情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不平等关系,暗含着对公众行动能力的贬低和否定,受同情心支配的革命者必然会把公众看成缺少独立行动和言说能力的人,从而把自己置于某种代表或统治的位置,这种观念与公共领域中的平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是把公众排除到了公共领域之外。其次,同情与暴力仅一墙之隔,因为,同情和暴力都是无言的,如果借助同情来减轻人类的痛苦,“它就会尽量避免那冗长乏味的劝说、谈判和妥协的过程,即法律和政治的过程,而是为痛苦本身发言,这就要求快捷的行动,这不外乎付诸暴力手段”。最后,也是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革命者一旦为同情的激情所主宰,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残暴——他们感到自己面对重重苦海,任何精打细算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坚信,为了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推翻重重压迫,牺牲一些无辜的生命将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就好像要医治身体的疾病就必须忍受暂时的疼痛。于是,为了某种远大的、抽象的、整体的利益,革命者就丧失了与眼前的、具体的、个别的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一方面对某种看不见的抽象的民族或人类利益满腔热忱,另一方面却对眼前的具体个人麻木不仁,即使将个人牺牲掉也毫无悔意。
阿伦特进而认为,法国大革命由暴力崇拜滑向恐怖统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由于驱动革命群众的是对面包的需求,而“吵着要面包的声音总是一样的。就所有人都需要面包而言,我们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同样可以联成一体”。于是,革命者就想象出一个同质化的革命主体,他们借用卢梭的“公意”概念来指称革命群众整一的革命意志和利益,并以“公意”的代表自居。这样,革命就完全丧失了政治行动的对话和协商性质,所谓“公意”就成为一个可以任意挥舞的杀威棒。日常经验告诉革命者: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在遭遇共同的敌人时会自动团结起来。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只有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至少存在一个潜在的敌人,内部团结才是可能的。于是,革命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不断揪出反动派的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就成为革命过程的常态,即使在消灭掉一切外部敌人以后,依然不肯停止下来。
没有了外部敌人,革命的目标就演变为不断地“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敌人,制造这种敌人有一种普遍有效的手段,那就是认定这种敌人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即个人的特殊意志和利益。从罗伯斯庇尔到斯大林,革命者都坚信,整体利益与公民的特殊利益天然敌对,公共意志与公民的个人意志永远矛盾。革命者将个人利益视为最大的敌人,将个人意志视为最大的罪恶,这样,践踏个人利益和意志的不义暴行就获得了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他们近乎荒唐地相信,一个人的行为越残暴、态度越决绝,就表明他们的革命意志越坚决、道德境界越高尚。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私,就必须不断地坦白、交代,将个人动机公开呈现出来。阿伦特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求不可能之事。因为内心的动机是不可呈现的,一个动机无论多么真诚,一旦公开呈现出来就会成为“纯粹表象”,其背后的深层动机就会自动隐藏起来。因而,公开展示的动机总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怀疑的对象,这就使得一切行动者都变成了伪君子。于是,革命发展到后来,其主要任务就成了向伪善开战,成了无休止地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而且,革命者对内部乔装者的痛恨与严酷程度要远甚于对待外部敌人,在清除了旧世界的遗毒之后,革命转而开始吞噬自己的孩子。
如此一来,革命就一步一步演变为恐怖统治,其显著特征就是统治者的自我清洗。由于后来的革命几乎都以法国革命为教材,阿伦特甚至发现,恐怖统治几乎成为革命的必然归宿。这种“美德的恐怖”在俄国革命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恐怖不再针对潜在的敌人,而是不断制造出“乔装者”,将叛国罪加诸任意选定的人群头上。
在法国大革命走向恐怖统治的过程中,必然性观念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革命”(revolution)原本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指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循环往复和不可抗拒的。在法国大革命及其效仿者那里,“革命”一词所表达的不可抗拒性得到了强调。在他们看来,革命犹如一股“洪流”,任何个人意志都无法将其逆转,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我们发现,在革命者身上常常会出现两种相互矛盾的气质:一方面,他们宣称人的精神力量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战天斗地;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人毫无能动的余地,只是受控于必然性的匿名力量,所能做的只是顺应自然法则或历史法则的自动运作而已。阿伦特总结说,“这些人敢于藐视一切现存权力,敢于挑战一切世俗权威,他们的勇气毋庸置疑,但他们常常日复一日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召唤,不发出半点义愤填膺的呼喊,不管对他们而言必然性的外表看起来是多么愚蠢和不合时宜”。在必然性观念的主导下,革命者将革命与自然进程等同起来,在他们看来,革命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就像自然界中有“分娩的阵痛”、“黎明前的黑暗”一样,革命中的暴力也不过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的阵痛”。这样一来,革命者就被武装上一副铁石心肠,可以对显而易见的暴力麻木不仁,在他们看来,自己的行为不管多么残暴,都只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已,那些受害者不过是螳臂当车,其毁灭完全是咎由自取。
不可否认的是,阿伦特的革命观具有一定程度的乌托邦色彩。如果以她的革命观为参照,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一次成功的、完美的革命。后来的革命大都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为社会问题的紧迫性所压倒,为贫困大众的幽灵所纠缠,革命者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暴力,希望借助于暴力征服贫困,而这最终被证明是一种绝望的诉求。即使是被她引为典范的美国革命,也在胜利之后随即就遗忘了它最初的革命精神,成为一种“失落的珍宝”。如今,人们对自由和公共幸福的遗忘是如此彻底,以致在大规模移民潮的影响下,所谓“美国梦”也不再是以自由立国,甚至不再是人的解放,而是变成了一种古老的穷苦人的梦想,即对流着奶和蜜的“应许之地”的期待。
虽然阿伦特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切实际的虚幻色彩,但它却为我们反思现实中的革命提供了一个理想参照,为我们带来了多方面的启发。首先,阿伦特区分了革命与解放,强调革命的目标是政治自由,即创造一个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参与的共和政体;而解放的目标更多是经济性的,即消除贫困和剥削。在阿伦特看来,如果它们成为革命的首要动机和动力的话,那么,革命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而且,解放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成功,如果没有为每一个体创造出平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即构建出一个共和政体,革命就没有完成,在这种时候谈论所谓“告别革命”或“后革命”是奢侈的,也是不合实际的。
可以看出,在阿伦特革命观的对照下,以上这些长期以来被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革命观念,就变成了一些可以讨论的问题。它不仅为我们反思历史提供了契机和可能,而且也为我们认知当下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