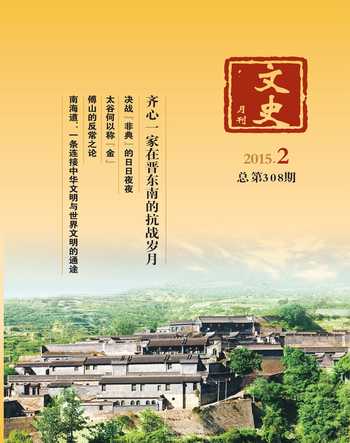南海道:一条连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通途
丛小荷



“花屁股”船模型。(高150厘米,长178厘米,宽32.5厘米)此船主要运输木材及货物。在宋至明代已远航高丽和日本。因船尾绘有精美图案而得名。现藏澳门海事博物馆
南海道——从内陆向海洋的进发
南海道,一般也称海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是从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上船,从水路通往印度的孟买,中国商人通过这条航线带去丝织品、黄金,换回美玉、琉璃、奇石“异物”。我国《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的南海道:“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杨少禅在其《试论徐闻、合浦港的兴衰》一文中提到,岭南人早在春秋战国时便开发徐闻、合浦港,开拓海外市场。以广东为代表的岭南文化,在皇帝的眼中,一方面因其远儒性和多元性而是中原正统封建文化的异端。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朝曾派50万大军兵分三路苦战三年,欲统一岭南地区。孰料岭南人骁勇顽强,杀尉屠雎,秦军“伏尸流血数十万”而退。虽最终拿下,但也损失惨重。另一方面,这个异端的蛮夷之地又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贡献奇异珍宝之地。那里的稀世奇珍如珠玑、玛瑙、玳瑁、象齿、犀角、能言鸟、宝石、美玉和名贵香料等,早在汉以前就是向中原统治者进献的贡品。
然而,直到汉武帝时,中央政府才得以对岭南那片水域投去了正式的一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作为最初的政府行为,汉武帝设黄门于番禺(今广州),有译长。这个专司对外贸易事务的官方贸易机构的出现标志着中央政府的关注。汉武帝还曾多次组织中国的商船队,从番禺出发,经合浦、徐闻,过南海,分别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及印度半岛的沿海口岸进行贸易,先后到达七个海国,远及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和斯里兰卡的已程不国,中国商人用黄金和丝织物换回了异国的明珠等大量奇异珍宝。然而,“厚遇关市”的汉武帝,还是把他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来自北方的威胁,并利用匈奴贪图汉朝财物而用关市“和战相济”了,一方面使张骞出西域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再无暇南顾。
以至于到南北朝时期,南朝“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自励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③如果说身处南中国的割据政权为与北朝抗衡,断断离不开来自滨海贸易的“岁中数献”的话,那么唐始置市舶使,是国家政权第一次直接派遣市舶使到岭南代表皇帝意志,向海外藩商采买舶货。从此打破了国家长期无视海外贸易的格局。在皇帝贪图“市舶之利”的诱惑外,我们还能感受到唐朝的自信与活力,同时也叹服于玄宗皇帝的勇气与魄力。正是这种从临时差遣到相对固定的官制,标志了我国封建统治者的目光开始从中原转向南部海洋。
广州“夷道”——南海“互市”局面的创新
从广义上讲,“南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皆是对中国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称谓。狭义的区别则是,“南海道”可以被视为秦汉时期的丝绸之路,始于汉代,从番禺出发,目的地以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印度东南海岸和斯里兰卡等为主,航线较为单一。而“广州通海夷道”之称的出现,则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中期,可以视为是隋唐之后的丝绸之路。据《新唐书》卷四三记载,这条“夷道”从广州出发,经屯门山、七洲列岛、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进波斯湾,可以直达东非海岸。较之“南海道”,“广州通海夷道”虽也以南海诸国为中心,但航线不仅大大西延,而且也由单一转向多条。事实上,隋文帝早在594年就在这“夷道”的起点上,建了一座南海神庙,作为祭南海神的所在。更为有趣的是,到了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南海神居然被册封为“广利王”。自此,南海神庙不仅是出海涉洋的精神象征,还多了“一份招财进宝的广告”效应。④也正是“广利王”的世俗精神,使得唐后期的岭南文化较之重儒轻商的中原文明多了一份活泼与生机,也从此创新了九世纪的南海“互市”的局面。
究竟是什么让唐王朝的统治者如此看重这条通海夷道呢?其重要原因当然离不开一个“利”字。其实,从唐高宗显庆六年的《定夷舶市物例赦》可以看出,当时南中国海的舶货贸易已经影响到中原统治者的政治制度。舶货已经进入中原的官府,为官员所接受,成为朝廷经济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每年舶货到来之前,皇帝要下赦令,集中采购,以免落后民间而利减。有学者认为,随着舶货的走俏,中央与地方官在舶货的采购问题上已有矛盾。高宗的赦令,实际反映了中央与地方在海外贸易管理权上争夺的开始。此前,广州从秦汉到唐初已经长时间和海外的舶商发生贸易了,只不过所有交易的管辖权在地方官,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不过每年数次贡献罢了,而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过问。所以,玄宗起设市舶使也就包含了国家行使主权之意义。
从《旧唐书》卷八的《玄宗本纪》中可以看到,在开元二年十二月乙丑任市舶使的是身为右威卫中郎将(四品武官)周庆立,周武官将与波斯商人交易的奇巧舶品进献皇上,玄宗很高兴地就收下了。根据唐代惯例,周庆立的官职自然由皇帝亲自任命,但是聪明的玄宗绝不会让固定的人常任这一肥缺,以免其中饱私囊。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在开元四年的某日,皇帝听一外国人说海南有太多珠翠奇宝,如果派人去交易,一定能得丰厚的市舶之利,此外他还想从师子国的善治病的老太太那里购回灵药,以丰富宫掖药房,于是命令一个叫杨范臣的监察御史与那老外同去寻求。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玄宗对市舶之利极为关注,一有传言就派使前去寻求;另一方面,从他对市舶使的临时差遣的特点看,选择贴身近侍不仅代表了皇帝的最高意志,而且充分保证了市舶之利的“中间截流”。这种临时差遣市舶使直到唐德宗时才初成制度,有了比较明确的簿记和固定的官署。
唐朝以前的历代君王以中原大陆为中心,把周边四方各族蔑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并不重视周边贸易的发展。将周边各国前来互市的统统视为向往帝国文化或是来进贡的。因了这个历史积习,即使开市舶制度风气的大唐王朝也没能脱去朝贡贸易的窠臼,这种隐藏在政治与外交接待形式层面下的贸易,由中央政府一手操持,实为官方贸易,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经济意义越来越大,名为朝贡,实为贸易。比如朝贡使团留在入境口岸的人员照样可以把带来的货物与民间交易,难怪马端临在其《文献通考》中说:“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尽管市舶管理仍带有浓厚的陆地帝国的色彩,但毕竟以最高统治者之名正式开了海外贸易之风气,是皇帝对海外贸易投去了最初的认同的一瞥。
活跃的宋朝在政治上是个积弱的政权,一直受北方边境的辽金夏蒙元的战争威胁,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但也正是因其“不能拥有广大的内陆,却占有了舟楫之利的沿海,于是他们不得不重视航运贸易。”⑤所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后立刻南下,攻打广州,在开宝四年(971年)打下广州,便立即设立市舶司。由此可见对南海贸易的重视。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记载,宋太祖在开宝四年六月就命令任广州同知的潘美和尹崇珂建市舶使之职,而这两人皆为北宋的开国大将,以保证南方的财富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北方输送。宋王朝一开始就派遣重臣兼任海外贸易管理,并在其后多次对市舶官制的变更等持积极介入的态度,确立了中央对市舶的绝对管辖权。一改唐代中央政府派遣市舶使只是以皇权的力量与地方帅臣分割海外商业利润的状态,而把所有的海外贸易权收归中央政府。
为了招徕大量蕃舶的到来,宋朝的皇帝一方面派使臣四出,发诏令,鼓励蕃舶来华贸易。据《宋会要辑稿·职官》记载,太宗在雍熙四年五月就遣内侍8人,拿着诏书金帛,到海南各个蕃国招诱安抚,并大量买进香药、犀牙、珍珠、龙脑等。另一方面对招徕蕃商来华贸易有功的市舶官使按规定加官进爵。《广东通志》就载有历任广州知府兼转运使的杨克礼受到“诏生殿慰劳,面赐金紫” 的荣誉。
北宋如此,偏安于长江以南的南宋小朝廷更是依赖舶商之利。贯穿于宋朝始终的就如皇帝宋高宗所说:市舶的利润最厚,如果实施得当的话,所得到的银钱动辄就可以百万计算,难道不比从百姓身上出更强吗?“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⑥
所以,“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始终是宋王朝坚持的经济原则。事实证明海外贸易丰厚的利润,不仅解决了财政支出以应对北方的军事需要,而且每年百万左右的可观收入,令南宋王朝沉浸在一片对市舶之利的希冀中,可以安心地沉迷于“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醉生梦死之中。
正是宋朝皇帝以诏令的形式允许国内商人前往蕃国贸易,这种自由的互市贸易体制,使两宋出现了海外贸易的空前繁荣。
至于元朝的市舶制度,已然不再如唐宋,而被看作是海外军事扩张的工具,市舶提举也由军人身份兼任。“诱诸蛮臣服”⑦一直是蒙元帝国的国策。这种畸形变态的市舶制度,可以被视为海上贸易史的倒退。而且,福建泉州在被确立为对外扩张的沿海基地后,几乎成了当时全国唯一的口岸。尽管元朝造船业和海上交通非常发达,但就商业经济原则来看,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
朝贡贸易——海禁与“怀柔远人”
对于海上贸易,明王朝的心态是怪异而且矛盾的。
明初就推行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海禁政策,且终明一代民间“片板不许入海”⑧都是作为铁律来实施的。但又允许蕃国在朝贡的名义下来互市,所谓“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互市”⑨。以政治的承认,换取贸易的实惠,这是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明王朝进行海上贸易的真实用意。
据《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七一所载,洪武五年有朱元璋诏谕琉球的诏书,其大意为:我已平定四边,赶走蒙元,建元洪武,各国应承认朱明正统,前来接受册封。为迎接各蕃国来使,在南京设“四夷馆”培养翻译,从事接待工作。日本学者田中健夫所著《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提及,为鼓励各国贡使来朝,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朝贡完毕后,朝廷赏赐往往多于贡货。以至于当时一些国家的财政来源都寄托在了与明的朝贡贸易上。在明朝廷的“怀柔远人”的策略之下,是极尽细密的利益追求,在制度上则体现在勘合文书上。勘合文书是以勘验为目的,盖有朱印“某字某号”的骑缝章的文簿,是留给贡受双方的证照凭证,目的是验证蕃国朝贡使者身份的真伪,同时也防止明朝这边的人假冒朝廷使者到蕃国去。文书一份留存内府,一份发给蕃国。贡使每次出发前,要具体填写进贡人数、物品等。如果明朝派出使者,对方也要比对文书,出使回来,蕃国有回赠礼物的,也要在文书中写明,以防官吏私吞。
如此精细的算计是以朝贡贸易下的“官给炒买”制度为支撑的。对明王朝来说,买的目的就是要垄断卖。蕃国使船到广东、福建等处,当地的布政司、会同馆都司、按察司官,一面检查货物,封船待命,一面送蕃使赴京城,承报所携物品数目。据《明会典》卷一〇八记载,除了蕃国国王的进贡外,蕃使附搭的买卖货物,一律由官方给价收买。而且,“厚往薄来”的明王朝所给炒买的价格还高于时价,蕃使何乐不为?于是,各国的“朝贡”更积极了。然而,这种制度必需以强大的财政做后盾。到了明景泰年间,财政不佳,各国进贡仍“来者不止”,明初的炒买制度逐渐走向衰亡。此后,随着明中期海禁的松弛,在“广东沿海地方多私通蕃舶,络绎不绝,不待比号,先行货卖”的利益驱动下,民间私自通蕃蔚然成风,从而掀起反海禁的高潮;同时,沿海地方官也与蕃商勾结,蕃舶不论是否贡期,只要行贿,就可以不断地进入广东交易;甚至有勾结蕃国制造假勘合文书以逐舶利者。对于朝廷来说,这个时期所呈现出的“私舶以禁驰而转多,蕃舶以禁严而不至”的局面,标志了朝贡贸易体制在社会下层的崩溃。
事实上,明王朝既想立“唯我独尊”的“天朝上国”形象,又希望施行利益尽得的朝贡贸易体制,随着“郑和下西洋”这一海上壮举的结束而一去不返。从此,明王朝彻底从南洋和印度洋撤出,自觉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海上联系。“这一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⑩
粤海关——一口通商的“天子南库”
如果说唐以前实行的朝贡贸易,在宋初自由贸易的体制下向自由贸易顺利过渡已初见成效,元朝以军事扩张为目的的海上贸易是对历史的倒退,明代的朝贡贸易的复行则彻底摧毁了中华帝国成为海上经济强国的可能。这一代价,就是有清一代的夷情愈少而夷务愈多。终于被洋枪洋炮的强力撕开了一道切口,耻辱与创伤并存。
清王朝初年,一如明朝,实施禁海政策:顺治十三年(1656年)朝廷颁布禁海令:“不许片帆入口”。康熙皇帝也在1665年到1675年陆续颁布了5次禁海令;同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值得注意的是,在海禁期间,海外贸易并未停止,以清王朝控制的朝贡贸易为唯一合法贸易。海上贸易的历史在毫无创意的惊人相似中进一步退两步。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清廷宣布“开海贸易”,允许四口通商,以粤海关为重。据姚梅琳的《中国海关史话》所记,康熙皇帝决定开海贸易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征收关税,增加财政收入,以供军需费用。而且他说,出海贸易本来就不是贫民所能做的,只有富商大贾才有资本进行,朝廷如果对这些富商征收商业税,可以用来补充闽粤两省的兵饷。于是,广州开海贸易的第二年设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进入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由官府培植的封建政府对外贸易的官商组织,充当着国内商人与外商的中间人,虽然作为朝贡贸易的另一种垄断表现形式,是贸易制度的倒退,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广州的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贡献。据刘圣宜、王燕军在其《抵抗与吸收》一书中的统计,开海后,广州的外国商船和商馆越来越多,尤其1757年清朝廷宣布广州单口通商后。例如,1714年到1720年英法等国商船来广州贸易有68艘;1785年到1795年,平均每年57.5艘;1796年到1820年则平均每年达76.2艘;1821年到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1764年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总值为55万多两白银,1837年增至39万多两白银。
一口通商,是清王朝无法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做出的退缩举措。这一举措在表面上看,的确让广州城成为全国最大的百货荟萃地、茶叶出口港,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全部货物都集中于此,为广州赢得“天子南库”的盛誉和其实不堪一击的繁荣;但也因此让西方殖民者通过这个单一的窗口,看清了在顽固、守旧、闭关下的清王朝的腐败和虚弱,以及无力真正控制外贸的现实,加之因中国独口贸易带给洋人的对华贸易逆差是任何一个殖民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于是一个日后用炮口打开中国大门的侵略政策进入酝酿之中。
18世纪30年代,英国通过广州往中国输入鸦片,使中国每年外流白银七八百万两。清政府严禁鸦片的行为,引发了鸦片战争。从此,和平贸易被商业战争所取代。黄遵宪曾在《人境庐诗草》之《锡兰岛卧佛》中言:“迩来耶稣徒,遍传新旧约,载以通商舶,助以攻城炮。”中华大陆在唐以后的历代王朝,一直摇摆于大陆和海洋的认同和利益追逐之间,自此,这一不断重复着的历史旧梦被彻底击碎。作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的广东,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