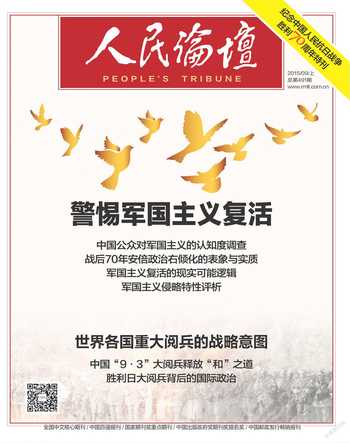军国主义侵略特性评析
吕耀东
【摘要】日本的明治维新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随之构筑起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了军国主义的警察、监狱和武装力量等国家机器,并对外实施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日本明治维新后的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及事件,均是军国主义的具体实施。
【关键词】军国主义 历史修正主义 侵略性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虽然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但其历史文化却源远流长。古代日本就有尚武的精神,幕府时代武士集团首领曾掌控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六百多年。明治维新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质变点。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还处于积蓄力量、小试牛刀的准备阶段。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了有预谋、有计划地对外扩张。7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破产,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仍未彻底肃清,现代日本社会依然弥漫着否认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原生性源流
日本“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思想可追溯到远古时代。进入中世纪之后的一位实际统治者丰臣秀吉曾提出“欲治大明国之志”并付诸实施,成为日本开疆拓土扩张主义的最早启发者。随后,江户时期学者山鹿素行发表著作贬低华夏文明,倡导“日本主义”。他毫不掩饰地提出“中朝”(指日本)论,宣称圣人(孔子)的道统到宋朝就已经泯灭,应该认定日本是“中国”,“唯有日本才确实可谓中国之地”。①山鹿素行把日本称作“中央之国”,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独自的国际秩序。他歌颂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把丰臣秀吉“征伐朝鲜”和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相提并论,称“秀吉晚年,征伐朝鲜。其勇敢胆略,冠于古今……显示本朝武威于异域者,神功皇后之后即在秀吉统治之时”。②在他看来,日本已俨然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山鹿素行的上述思想为后来建立力图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军事学说被幕府末期的长州藩士吉田松阴所继承,其传承的侵华思想对明治维新时期的军国主义形成产生很大影响。
18世纪70年代,日本“集国学之大成”者本居宣长反对儒学,进一步发展了山鹿素行的“日本主义”。山鹿素行和本居宣长倡导的“日本主义”与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思想,深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推崇,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到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俄国等西方列强“东渐”,不断对日本造成“冲击”,日本出现了一批通过研究荷兰了解西方的“兰学”学者,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上书大名或幕府,就当时的日本内外政策发表见解。其中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主张“开国”,学习西方,进行对外扩张。林子平在《海国兵谈》(1791年)中称颂“神功皇后使三韩臣服,丰臣秀吉征伐朝鲜使之至今仍服从本邦”的“光辉武德”;羡慕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布德张武”和“一统五洲”,希望日本出现一个像他们那样“文武双全”的“将才”,来建立他所设想的“武装体制”。③同林子平相比,本多利明的对外扩张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把眼睛转向欧洲,主张向欧洲各国学习。他在1798年撰写的《经世秘策》和《西域物语》著述中,主张实行对外扩张的“开拓制度”。可见,幕府末期,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与幕藩体制的危机,日本的扩张主义意识与国际乱局相结合,使得日本对外扩张理念逐步强化。
继山鹿素行、本居宣长、林子平和本多利明之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学者成为日本对外扩张思想的奠基者。佐藤信渊意图吞并中国、称霸世界,先提出了同时进攻北京和南京的侵略计划,后迫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压力,又提出“存华挫狄”的主张,希望中国成为日本的屏障。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同列强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吉田松阴作为明治维新的启蒙者,提出了以攻击弱邻、补偿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偿论”。尤其是当他看到积贫积弱的清王朝任由西方列强宰割,便开始产生对华蔑视感,并更加觉得日本的出路在于己为中介,促成得失互偿。这表明他逐渐形成了通过侵略朝鲜和中国来对抗西方的战略设想。1855年,吉田松阴在给其兄长的信中称:“与俄美和亲条约已定,我决然不可破坏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其间,培养国力,降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之损失,以鲜、满土地补偿之。”吉田松阴关于入侵中国和朝鲜,“控制南洋而袭印度”,甚至梦想“并吞五大洲”的民族扩张思想,勾画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思想的雏形。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特性
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维新启蒙者关于皇国史观及对外侵略扩张等思想主张,给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日后明治政府领导者以深刻影响,被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完全继承并加以广泛宣传,演化为日本向外扩张的目标与步骤,成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把吉田松阴的扩张思想相继付诸于指向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行动。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侵华理念由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人的书斋设想,演变为军国主义侵华思想与侵华战争互动并进的形态。一方面,奉行“富国强兵”、力图摆脱对欧美国家的屈从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侵略道路,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另一方面,以被称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民间报人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倡导者,大肆鼓吹弱肉强食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明治政府军事扩张和侵略亚洲的野蛮行径摇旗呐喊。他在近二十年写的四十多篇鼓吹侵华的文章里,把日本“文明开化”的近代化与侵略中国联系起来,公开标榜侵略合理合法。他积极支持的侵占朝鲜、吞并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的一系列侵略构想和实施方略,被后世的军国主义者全部付诸为侵略行动加以实施。
1874年5月,日本陆军司令官西乡从道出兵入侵我国台湾地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北京专条》,以赔款50万两白银作为日本侵台军退出台湾的条件。虽然侵台战争的规模不大,但由于清政府的软弱和英美对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战而胜刺激了军国主义分子的侵华欲望。这次入侵台湾是日本走上明治维新之路的首次对外用兵,其中包藏着侵略朝鲜、侵吞琉球的武力试探。1875年,日本武装入侵朝鲜,逼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79年吞并琉球,并更名为冲绳。
1890年,山县有朋以首相名义写就关于“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外交政略论》。他主张在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外侧,设想出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地区”。他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如果别国侵入利益线,则必须以强力排除之”。他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也就是说,把日本国疆域称为“主权线”,把朝鲜作为“利益线的焦点”,将中国等邻国的疆土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的势力范围。山县在1890年12月第一次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称,在列强争霸的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他极力宣扬“利益线”理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可以说,山县有朋已把朝鲜、甚至中国纳入日本“利益线”的势力范围,以防止对抗沙俄侵占。按照这样成行的“大陆政策”战略构想,为了“防守主权线”,占领和侵略朝鲜、中国等“利益线”势力范围就成为历史必然。
山县有朋的这一“利益线”理论标志着日本“大陆政策”战略构想的基本成型,并为后来日本历届内阁及军国主义者所继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1894年甲午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0年吞并朝鲜、1915年对华“二十一条件”、“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侵略战争及事件,均是军国主义“大陆政策”关于“利益线”理论的具体实施。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承接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承接性从日本政要对于日本战败投降纪念谈话可见一斑。譬如,安倍“八一四谈话”中妄言:“日俄战争鼓舞了许多处在殖民统治之下的亚洲和非洲的人们。”这样无耻言论再次唤起中华民族悲惨伤痛的历史记忆。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侵略者完全无视中国主权,把中国东北变成争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杀戮战场,无数无辜中国民众死于非命。安倍所美化的侵略历史就是山县有朋的军国主义“大陆政策”,其当年对华侵略扩张的“利益线”理论,如今已“华丽变身”成为安倍美化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国际名片”和“正义招牌”。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思想演变过程是与“大陆政策”的演进及实施互动发展的。从发展历程来看,随着对西方列强“弱肉强食”侵略行为的认同,日本从昔日“存华挫狄论”实现向“得失互偿论”的彻底转变。同时,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的“富国强兵”政策,进一步激发了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的膨胀与发展。日本完全无视几千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力图仿效西方列强的做法侵略中国等亚洲邻国。从“脱亚论”到“大陆政策”构想的产生,为日本最终寻找到了发动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现实主义理由和行动依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又给了日本军国主义确立“在东洋的权利”的战略时机和侵略空间。从对华“二十一条”到“田中奏折”的侵华政策推进,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利益线理论”已经转变为侵华的具体战争行动。
随着二战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彻底破产,但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仍未彻底肃清,现代日本社会依然弥漫着否认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近年来,生于战后的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盐崎恭久、高市早苗、前原诚司等右翼政治家群体,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因而普遍存在历史修正主义言论。
历史节点的中日关系“变局”
中日两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维护双边正常国家间关系的正确路线。2014年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的第二点也再次明确:“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
能否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关键。《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消除了二战后中日两国的隔绝状态,中日邦交正常化揭开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新篇章。但作为曾经交战的双方,从立法程序上说,政府间联合声明的内容还必须通过签定和平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中日友好条约》签订后,中日双方领导人在互访和会谈中不仅涉及中日双边关系、对于共同关心的亚太地区的形势及其他国际问题予以高度关注。
冷战结束凸显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两国在钓鱼岛及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摩擦表面化。为了维护冷战后的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1998年,中日两国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发表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的联合宣言》。 该《宣言》指出,力求中日关系克服和适应国际格局变动的冲击。
2008年5月7日,《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两国“第四个政治文件”。该《联合声明》维护和巩固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构建中日 “战略互惠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该《声明》宣布,中日“双方相互视为合作伙伴,不是威胁” 。可以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的确立,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构想。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义日盛,中日两国关系就此进入了历史认识问题纷争时期。日本内阁成员不断出现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翻案的言行,恶化了中日关系,是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相悖的。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曲折历程来看,若仅仅发展经贸与民间交往,而不能在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增强互信,要想从根本上改善中日两国关系是很困难的。中日关系仍然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如何把握机遇,有效缓和两国矛盾与分歧,寻求共同利益,保持双边良性互动的长久性,还需要两国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发展中日关系。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两国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显现,双方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时有发生,并将可能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通过中日对话与磋商,缓和分歧与矛盾,累积政治互信,仍将是考验日方能否维护中日两国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试金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注释】
①【日】广濑丰编:《山鹿素行全集思想篇》第13卷,岩波书店,1940年版,第42页。
②③【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1-52页,73-74页。
责编/刘瑞一 谭峰 申唯佳(见习)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