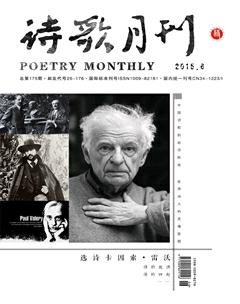中年书(组诗)
洪放
小松林
松果将那片黄沙狠狠地擂响。而风在偷窥。
一两个没入松林的人,背影被钉在松树的干上,那些皴裂的老树皮
很久已经没有接受雨水了。此刻,云淡风轻,天地寂静我却驻足于松林后那黄土的坟墓。简朴的碑,近于无字;
一丛半黄的野草,从坟里生长出来,带着幽冥与骨殖气息。诗歌被多年前的寒鸦啄破,成为碎片。诗歌因此也注定无法不朽
而真正不朽的,其实早已腐烂在最深的黄土之中
小松林。野浆果抬走头来的下午,墓碑上漫漶出或深或浅的字迹
仿佛一个人从松树的枝头伸下手,一笔一划,一撇一捺一张一弛,一收一放。最后,在松果擂响的黄沙上一张一望,一笑一哭,一生一死
过故人庄
我不是有意要过故人庄,我已经忘记了故人,是故人庄猛然撞到了我的脚下。目光生疼,膝盖生疼,手麻木,庄边没有炊烟
阡陌成了草场,一人多深,足以淹没我的生出白发的头颅。大门紧闭,如此而已,我不会想起故人庄。江淮之间,村庄星罗棋布
如今都是荒凉。庄内不比庄外热闹,庄内大门紧锁,人语不及狗吠。而庄外,那宗族的大坟,一到夜晚,萤光流落流磷四散,旷野里一片光明。人影憧憧,笑语喧哗。世俗之欢。天伦之乐。
一切影像都只在庄外。故人庄,徒有虚名
故人早已不知踪迹。江湖高远,谁能蹈尽盈虚之数?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与庄外大坟招呼说——
若见故人,告诉他我已来过。
与小弟
黑漆的脸,因为灯光,成为一片我不忍直视的阴影。
我只听着笑声,你的,大哥的,孩子的。窗台上那些花朵的
从窗棂里透过来的那些月光的。室内电视里的
高高垂落下来的绿植的,虚掩的门的,门上贴着的动画的还有那些躲在暗处的药水与正在愈合的刀口的……
小弟,我听着这些。我只听着这些,笑声,被你一千倍放大
而我的心,却一万倍的收拢。
我已哭过了。
我已颤抖过了。
我已祈祷过了。
我已写了无数遍《金刚经》。
我已将所有的结局都重写了。
同学会
她抱手在胸前,望着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她看见闪烁的光
细看,那是同学们正在往上生长的白发。她挂着轻轻地笑,她看见一些她想
看见的人,也看见一些她不想看见的人。她卷曲的长发正好遮住
一半的风景。她不言语,不回答。她抱着兔子,倚着香樟
她正好四十,皱纹才刚刚萌动,便被粉饼消灭。
她收拢春心,淑女样。她漫不经心,时光一般。
她能准确地回忆起那些人的鼻涕,泪水,恶作剧……
却只能回忆起他一个人的笑容,字迹,和体育课后浓重的汗渍味。
她看见他。她微微地耸了耸肩膀。他站在最前一排,身材高大
却影像模糊。他在说话,却没有声音。
他在做着手势,却没有动弹。他望了她一眼
却让鸽子的翅膀停止了扇动。她转过头,秋天的叶子
一直沉落进老教学楼的林荫道。
后来,大家说着故事。二十年,谁都说自己,却不着边际。
再后来,演出开始。她扎着小辫子,挎着篮子,低眉细眼。
她说:“落花人独立”
没人应答。她看看幕后,一地落红。
告别时,他不在。大家说他早已离开了,在演出之前。
他送给所有同学每人一只特产烧鸡,而送她的只是一张卡片。
卡片是二十年前的,字也是二十年前,有些发黄,写着:“微雨燕双飞!”
落款是“1994年元旦”。
白马
我首先要说到那个小镇,半边街道,一座小庵子,里面有白马的塑像
白马不高,显然不是北方物种。它来自江南,鬃毛柔顺,它昂着头
事实上,它存活于传说里。而传说在七公里的上游。
前面是供销社,糖的气息,清甜,迷人。整整三年,我在这气息里盘桓。
女营业员姓马,面如桃花,转瞬却面色苍白,渐渐挺起肚子
毕业那年,她敞着胸襟,一边看我们拍毕业照,一边给孩子喂奶。
小镇中间,从部队转业的王老师,刚刚失恋。他脾气暴躁,打班上女生
而那女生居然不哭。多年后,我们听说他们结婚了
再后来,女生在小庵子里提水诵经。
一切俱成过往。白马,我再要说到芦花。
那条长长的沟渠,被芦花隐蔽。失踪的人,归来的人,逃跑的人
说书的人,弹棉花的人,乞讨的人,流浪的人,从北方下来的放蜂的人
沿着沟渠,沿着芦花,他们成为小镇的赘肉。
同时带来戏谑,皮条,酗酒,骂街,赌博,同性恋,梦游者。
当然,他们也带来芦花。
芦花隐蔽沟渠,也隐匿小镇岁月。如此,小镇成为内外木鱼声响。沟肆风光。
最后,我要说到白马与芦花。白马入芦花,禅宗因此不语。
白马非白马,芦花非芦花。
白马在上游七公里的水库那边,数百年前的大雨,祈雨,
山洪,白马被泥沙
裹挟,沉尸下游此地。白马不知后来的小庵子,听不清那诵经声。
芦花后来消失。那些失踪的人,归来的人,逃跑的人
说书的人,弹棉花的人,乞讨的人,流浪的人,从北方下来的放蜂的人
一夜之间钻进了芦花的根,他们从泥土里折断了芦花
从寒霜里压折了芦花。
从最低的世俗里解放了芦花。
今夕何夕
我遇见很多年前的人,面目如池塘之水。
我不跟他们言语,我接不上他们的话茬,而他们并不停留,一直
在村庄上行走。他们脚步轻飘,头颅偶尔消失。
他们往往站在树下或月光里,手里拿着秋天的豆子
鼻孔里缠绕着苍绿的树根。
都是很多年前的人。我不认识。
我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唯一的印象是:他们都理着同样的发式
做着同样的手势。他们,从南往北
又从西往东。他们总是与我的方向一致
因此,在村庄的所有地方,遇见都成为一种平常。
今夕何夕。人日,清明,七月半,冬至,除夕——
我问他们中的一个:最终何往?
这是个刚刚被送进祖坟的长辈,他性情古怪,喜欢算命。
他拄着拐杖,点着桂花树下的石头,说:直到死了此心才安。
小酌
其实,上帝知道我是喜欢小酌的,但往往是大醉。
这不怪我,要怪就怪那些酒,那些令人迷醉的酒香
还有那火锅里跳跃的菠菜,墙上淋漓的书法
桌底下交错的脚,被酒杯发酵的目光。
小酌有小酌之美。三两至友,最好是你,或者不期而至
当然要有雪,要有雨。阳光不宜小酌
只宜恣意。小酌宜小,小杯子,小桌子,小菜肴,小月亮
小竹子。小酌宜浅,浅斟,浅饮,浅拥,浅说浅归。
但往往是大醉。酒杯翻转,酒气四溢
与李白喝,与杜甫喝,与东坡先生喝,与定庵先生喝,与大道喝
与小寺喝,与青桐喝,与文庙喝,与紫来桥喝与南大街喝。
一醉千秋。其实,我都忘了。我只记得那年
我们在和平菜市场,三个小菜,一瓶老酒
喝着喝着就把酒瓶挂到了人民旅社的大门上。
大门朱红,如今正对着我心里的方向。
过武昌湖
下午四点的武昌湖,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的朋友李俊平说的
他是武昌湖边的散文家,漫不经心,写着一个大湖的四季。我现在
不说他。车过武昌湖,我想起
离此一百公里的安庆城里的振风塔。
我为什么由湖想到塔?湖波浩渺
塔影迷茫。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整个下午,我心思重重。
晚上酒后。华阳镇灯火通明。大船都在湖里休憩
歌厅里面孔陈旧。点歌,上酒,说话,一切都被强大的喧闹所遮覆。
我们唱了一曲《海滩别》。
后来小羊说我唱的有些意味。其实那一刻,我想到
振风塔。想到那个与我唱歌的诗意的女人,她曾与某个从塔上坠下的灵魂
相爱。如今她在文化馆的小屋子里,独守光阴。
预测者
我愿意写下所有的字,愿意预测这已经到来的新的一年。
我手掌发红,脸色虚肿。我内心里开满忍冬
耳朵里撞击着香樟树籽。我从前一个人独自行走
如今我有了同道。我们在透明的尘埃里彼此支撑
修正,切割,完美。
像革命者,经营着爱情。
我写下的字,只有你能解。
我预测到的一切,只有你能破译。
你是我的更深层次的我。
你存在于新年的空气、植物、雨水、月光与芭蕉。
我们建筑秘密的城市,街道,四合院,我们建筑巷子
鹅卵石花园小径,格子窗,天井;我们建筑书房,小轩,长长的走廊
然后种树,写诗,过日子。我们建筑预测者的天堂
却不得不委身于流亡者的地狱。
老诗人
快八十岁的老诗人激情四溢,他站在人群之中朗诵
他中气十足,却忘记了诗句。他回头,站在他身后的女人给他提词
他吸了口气,又响亮地诵出。他面色红光
却失明。他唯一的光明,他说:是诗。
女人年轻,刚刚三十,依旧站在身后,这回她没提词,
而是牵着他的衣角
前面过道上杂物重重,她不便提醒
有人告诉我老诗人复杂的一生。
我没听完就了然一切。
他自以为活在诗里,自以为一辈子风光无限,革命,云游,诗
喝酒,性。他放任他唯一的光明,事实上,已不堪一击。
多年后,老诗人已逝去。女人回忆他说一一
我把他当作孩子,我们从来都不是情人。
秋日山坡
铁红。紫红。由绿到红。由黎明之日光
到黄昏之暮色。红色的秋日山坡,语言被风和低矮的
蕨收藏,那一闪而过的光一一去年秋天的人
早已走远。我们不过是踏着消逝之脉络而来
而何人能避开如许?山果坠落,野花凋零
不需要悲哀,更不需要怜悯。万物自有来去
一切荒凉,无非是人心!
靠西边,松林里有狐出没。它无视山坡上渐次覆盖的秋色
如同那些行走的人,无视我正在颓唐的中年
早点夫妻
点火开灶。老城墙脚下,油条的香味钻进烧饼。好多年了
他们做早点,养着上学的孩子。他们背对着背,各自工作
和粉,下锅,起锅,包扎……然后两个人不期而至地战争。
男人说:知道你这样,早就离了。
女人用手抹了下脸,说:离嘛,离啊!现在还来得及!
她的脸上有白粉的白,而男人的手一直在团着烧饼
他的语言有烧饼的味道。而女人,自言自语:要不是你,我哪会下岗
来做这生意?
天天做早点。
天天吃早点。
天天吵嘴。
天天说要离了。
今天早晨我去早点摊上,只有男人在忙碌,灶是冷的
油是冷的,油条还是团状的面粉,烧饼还未成形。旁边
等着一圈圈的食客。
大家都说:有些冷清。女人呢?
男人蹲着身子点火,头也没抬,说:唉,不争气的,早起时脚崴了。
彼岸花
首先要有岸。往往是:岸在花之前消失了。
那么,花只能是花。我们为之忧伤,流泪,思考,甚至抚摸
它们浑然不觉。飞舞的花瓣,因为终生不能相见的绿叶
它们在湿润的溪流边,独自守贞。我看它一眼,它便
开放一朵,然后滑落。如此数年,彻夜漫漫。它为之开放
显然已不是一世两世。
佛来了,说它是佛。
道来了,说它是道。
书生来了,说它是经卷里的娇喘声,发香,和闪着绿光的吃心的眸子。
说话
早起时,她走出栽着木槿的院子,然后喊邻居的名字。
一只狗,跟在她身后,她老蓝的衣服,清丝,简单,她慢慢走路
与村里的人打招呼,告诉他们昨夜下雨了,南山岗上那棵
老桐树开花了。夜里梦见他二爷了,正站在月光里抽烟
“那烟呛人呢,死鬼!”她一遍遍地说着,且笑
狗也跟着叫了几声。然后是村头的大槐树,树上系满红绸子,一条条的
她抬头望着,伸手将红绸理了理。她动作轻缓,目光沉静
她念着红绸上的名字,说:日头起来了,都得下地去了呢!
一整个村子走遍了,快到中午了。她择菜,做饭炊烟成了唯一的生动。
下午,她走出栽着木槿的院子,然后喊着邻居的名字。
一只狗,跟在她的身后。她老蓝的衣服,清丝,简单,她慢慢走路
与村里的人打招呼,告诉她们自己现在也一天天老了,真的老了,
“唉,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有那些孩子们,要是哪一天我真的走了
这村子里还有谁说话呢?”。当然没有回答,她永远自言自语
村庄里摆满她亲手制作的布人,每个都是他们离开村庄时的样子
她同他们说话,村庄因此年年返青。
夜游者
雨水闪光,道路敞开。
路旁的合欢树上,那些绒绒的花朵,让过敏的人咳嗽。
而夜游者,此刻在心里吹着笛子。
早晨,他刚刚送走了发小
中午,他骑车跟在一个女孩后面时挨了顿骂
黄昏,他找了家酒店,却囊中羞涩
他在小卖部里卖了一瓶烧酒,一碟花生。他一个人喝完酒,吃完花生
出门看了看天。雨停了。
雨停了,正好走路。
夜游者没想到雨水能闪光,而道路敞开着
那黑暗高远的天空上,合欢居然开放着璀璨的烟花。
望城岗
我们都走那一条路,都过那一道岗,都踩过岗上的黄花
闻过岗上的草香,在岗头的溪水里,我们都照过影子,诵过诗
或许我还说过:骑着大马到你们家!喝酒,拜天地,入洞房。
我们都十一二岁,青皮,不言笑。害羞,总觉得岗上有目光
如桃花般灼灼。岗下种田,岗上栽树,树是桐树,淡黄的花
青色的子,那是老家的树,那是接婆娘的树。
望城岗。离城七里,望得见城墙上飞起的垛口,望得见文庙
响着的风铎,望得见紫来桥上戏子漫长的水袖,望得见
一大片云朵,从城里往外飘,云朵上坐着小小的小羊……
忘掉那些名字吧
我喜欢在豆田里来回奔走,听着豆子爆裂的声音,一个个黄色的小人
蹦了出来。阳光照耀,河水清且涟漪
豆子,跟着我回家。
总有些东西在引领着。
总有些气息在引领着。
总有一种叫做热爱的感情,从豆田里长出来
一寸一寸的。每一寸都是一个名字,那些名字
曾在盛夏的豆田里,男欢女爱。
但现在,请忘掉那些名字吧!
豆子回到了天空。豆田里空空荡荡。那些黄色的小人沉睡着
像死去多年,再不能唤醒。
西风禅寺
我进去过吗?
我出来过吗?
禅寺,有吗?
它的名字,叫西风吗?
进去过
出来过
说有,便压在了肩上
说它名字,便跌进了尘埃里
只是那些台阶有意思
一级一级,总不到头
只是我们坐着的时光有意思
参着禅,暖着心
大寒
阴极阳生。路从那些流水旁渐渐没入暮霭,从前的人
在此刻点亮篝火,借以温暖流星。
而村庄上,中年的树,裂开第一道口子,如同
破损的手掌。寒气往下,落叶旋转
我独自饮一杯酒,在心里重写一遍那些名字。
我已经把要走的路都走了。
把要唱的歌都唱了。
把要喜欢的人都喜欢了。
在大寒之前,我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
剩下的,就是那些从上往下的寒意,我已学会将
它们放逐。我开始珍视那微小的从脚底下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