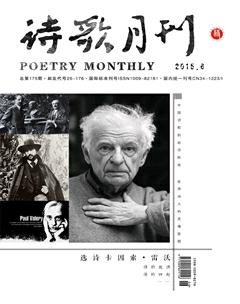杨角的诗
杨角
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沙滩上
把一个大活人拆卸在沙滩上
就是这个样子
横七竖八的朽木,一撇一捺的断石
连蓝天都不认领这样的废墟
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好比一首诗
横遭肢解。一个历尽沧桑的人
在水边走一百遍,也回不到童贞里去
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沙滩上
让活着的自己瞻仰死后的自己
在被浑浊的江水领走之前
千万别让那堆骨头,哭出声来
说出心中的虎豹
千万别让水怪,看见你额上
“王”字里那一把刀
立夏
春天用90个落日
把我蛊惑成一根火柴
三月脱去了我的外衣
四月又把我的内衣脱去
现在是五月
我仅剩一条裤衩
季节,要我用燃烧说话
积蓄热量的过程如此艰难
像一次怀孕
一首反复琢磨的诗
六月眼看就要到了
我像一名等待献身的战士
骑着阳光的马驹
满世界寻找——
那张涂有磷片的纸
暴雨夜我是那根被淋湿的火柴
雷声见证了一根火柴
黑里透红的天幕上,它拼命地
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
风的嗓子都喊哑了
疯狂的雨点根本不听
它们一浪一浪地涌过去
直到占领完一张磷纸
使一根火柴,毫无用武之地
暴雨夜,我做过疯狂的雨点
但更多时候,我是那根
空怀激情的火柴
背着灯光去旅行
我想起我的童年,我站在一盏煤油灯前面
看祖屋的土墙上我张牙舞爪的影子
墙上的影子被抽去了表情
我无法看清自己的嘴巴、鼻子和眼睛
但我从此相信:我的身边始终有一盏灯
人生就是一场背着灯光的旅行
无论走到哪里,灯都不离你左右
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有时是星星
一个活着的人就是不停地搬运自己
不停地寻找一面墙,安放自己
甩也甩不掉的灵魂
哪一天灯熄了,影子就是你的遗像
你留给世界的一张模糊的脸
你只能看着一个个后来人,在一个黑框内
不停地变换着嘴巴、鼻子,和眼睛
秋后的田野
稻谷被收走了,稻草却留了下来
像一个人的肠子,东一堆,西一堆
被扔得到处都是
一次次从田埂上走过,我突然有了
一个刽子手的心境
我真的不忍说出,秋后的田野
像一个身首异处的人,一个被开肠破肚的人
坐在良知的石头上,我直白地
说出大地的疼痛
秋后的田野虚弱如产后的孕妇,人呀
不能如此对待一个向你掏出了心头肉的人
感谢秋天保留了夕阳的火种
我愿做一个疯子,一点点
唤醒那些沉睡的精灵
让它们跟在我身后,燎原成一片海
用一场焚烧和焚烧升起的孝布
为当下的现场,守灵
有组织的人
大姑今年九十岁了
体重,不超过50斤
这个本身就矮小的女人,正咬牙
缩小着她在大地上最后的阴影
她是我那个家族父亲那一代人中
唯一的干部。尽管
只是生产队的妇女主任
那也是一个队里所有妇女的领导人
土地还没下户的时候
队里一社员病重
一个身高不足1米5的女人
带着几个大男人,分文未带
要闯宜宾,救人
到了孔滩,客车早已远去
一辆货车在站台上喘着粗气
大姑闯进了站长室,说明原委
站长说:货车不能搭人
大姑桌上一拍——
“你还是不是组织的人”?
那辆货车嘶吼着,一路绿灯……
乡下来话说,大姑身体很差
一个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
要回归泥土,没什么好悲哀的
这个有组织的人,到了那边
泥土是她新的组织
一碗土烧
我就是那个把一碗土烧喝成嚎啕的男人
这些年,我常常坐在五粮液隔壁
喝着宜宾城最廉价的土烧
一个人哭给自己听
一想到自己可能是这座城市
为数不多的写分行文字的人,我就
又哭了几声,将碗里的土烧一饮而尽
每次哭过,我都相信土烧是医治灵魂的银针
喝得越高,扎得越深
我常常自己笑话自己,五十岁的人了
端不住一只酒碗;在一碗酒面前,我看见自己
在人间养虎,放虎归山
喝着土烧,泪水领着原罪嚎啕
我常常看着手里的一只空碗,破涕为笑
哭过了,笑过了,内心就干净许多
就会有一场酣睡替我拆去栅栏
从此不再养虎,不再用酒精和泪水
驱赶内心的孤独
汽车在暴雨中行驶
不把那块挡风玻璃想象成一张白纸
就无法相信那汹涌而来的雨滴
是史书中砍掉了头颅的文字
汽车在暴雨中行驶
跟历史的推进非常相似
那些粉身碎骨的雨滴
已经不是简单的字,和简单的词
它们就是扑火的飞蛾
前赴后继,一不怕死,二
也不怕死
我看到了风,风才是雨的领袖
或罪魁祸首
没有它的蛊惑和召唤,那些
单纯的自发状态的雨滴
不会一波又一波地摔碎自己
成为史书中黑眼球无法看见的
白眼仁一样的文字
雨说停就停了
挡风玻璃复原为明净的天空
那些密密麻麻的水渍
像极了一双双挂着泪痕的眼睛
我不能强迫一个沉浸在阳光中的人
说出那张纸上,究竟
还有多少不要命的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