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嵌与悬浮:越南媳妇的关系网络的建构及其困境
——以鄂东北四村为例
郑 进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基于地缘、亲缘及族缘等关系之上,如今的中越、中缅等西南边境山区即存在着正常的通婚,即使1949年后边境山区基于同源民族的跨境通婚仍在进行,仅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特殊的政治事件暂停了数年之后即恢复,此后一直呈现出增长之势。近年来中国与越南、缅甸等国的跨境通婚开始由边境地区扩展到中东部省份,诸如湖北、山东、河南、湖南等地,跨境婚姻也演变成为远离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戴波、赵德光在《云南省跨境婚姻实证分析及社会学思考》中对“跨国婚姻”与“跨境婚姻”以是否发生在边境地区(边境30公里范围以内)做了区分,笔者沿用这一区分,将发生在距离中越边境约1500公里之遥的湖北省鄂东北地区的中越婚姻界定为跨国婚姻,将一般意义上发生在边境附近的中越婚姻称为跨境婚姻。参见戴波、赵德光:《云南省跨境婚姻实证分析及社会学思考》,《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18页。,这一现象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江日报》《黄冈日报》《楚天都市报》《楚天时报》《农村新报》《鄂东晚报》等报纸,湖北经视直播、湖北网络电视台等电视媒体,新华网湖北频道、长江网、凤凰网、中国日报网、湖北网络电视台网、大楚网、荆楚网、新浪新闻中心、搜狐网等网络平台均报道或转载过关于红安县、大悟县的中越通婚现象。 2013年1月12日,腾讯网以《40天娶回越南媳妇》为题,配以19张图片和解说文字,在首页报道发生在红安县华家河镇的一桩中越婚姻。。相较于跨境婚姻,延展至内陆地区的跨国婚姻在生成原因与功能、女性的身份认同、子女社会化及法律困境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共性,然而由于异族通婚和通婚半径的极大延长,在关系网络的建构及影响上则呈现出跨境婚姻所不曾面对的现象和问题,给跨国婚姻以新的研究空间。
跨境通婚问题早在数年前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也为跨国婚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地缘、族缘及文化相似性等因素讨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的生成基础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并在经济因素、人口性别比等因素探讨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戴波、赵德光:《云南省跨境婚姻实证分析及社会学思考》,《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孙卫:《云南省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研究—以临沧市为例》,《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4期;罗文青:《和平与交往: 广西边境地区跨国婚姻问题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最近王越平、陈民炎从资源整合和情感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边境城镇跨境婚姻发生的主体性实践*王越平、陈民炎:《资源整合与情感理性——滇越边境河口县城跨国婚姻的个案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5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也有学者从社会认同的角度剖析跨国婚姻中女性及其子女的群体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困境,以及其子女的社会化困境,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周建新:《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女性及其子女的身份困境:广西大新县A村个案为例》,《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龙耀、李娟:《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还有学者关注到跨国婚姻所面临的法律困境和制度困境。*蒋德翠:《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之法律探析》,《人民论坛》2012年第20期;李娟、龙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法律探析》,《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反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就研究地点而言集中于中越、中缅边境之地,而鲜有关注非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现象;就研究视域而言,结构性的研究多而细节性的剖析少;就分析路径而言,通婚现状描述与成因分析多于深层问题探讨。跨国婚姻在延续了跨境婚姻的生成机制及所面临问题的同时,因跨国婚姻而产生的关系网络及其变迁即属于被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之一。
越南适婚女性进入中国中东部地区,在扩展传统的通婚空间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小社会内部形成的独特社会关系网络。由于远离故土,进入与原生活区域相距数千里之遥的异文化的他乡,必然对围绕其所形成的关系网络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她们因为离开原生活环境而与此前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发生了分离;另一方面,由于新的婚姻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进而形成了新的关系网络。然而,由于进入中东部地区与进入边境地区有着重大区别,特别是因为分属不同的民族身份、语言系统、文化圈层,对关系网络也产生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影响。因而,扩展至中东部地区的跨国婚姻会形成何种格局的关系网络,越南女性在本国和当地的关系网络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远嫁中国中东部地区之后越南媳妇怎样保持与原国亲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来到中国生活后维持何种互动并产生什么样的关系网络,对跨国婚姻有着怎么样的影响,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所系。故此,本文选取了华中鄂东北地区越南媳妇最为集中且相邻的H县和D县进行调研,以期回答此问题。
早在2006年,越南媳妇先后出现在D县和H县 ,这也成为鄂东地区最早出现越南媳妇的县域。官方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10月,H县共有越南籍媳妇83人,成为湖北省越南籍常驻人口最多的县,其中73人在此次调查的华家河镇*罗京:《红安小镇来了80名越南媳妇》,《长江日报》,2013年1月24日,该新闻被众多媒体所转载,如凤凰网、中国经济网、腾讯网、大楚网等。,而方刘冲村则为H县越南媳妇出现最早也是最多的村,并被《长江日报》《楚天金报》、腾讯新闻等专题报道。截至2011年4月,D县共有越南媳妇57人*中共大悟县委办公室:《大悟信息》总192期,2011年4月6日。,其中约50人在吕王镇,亦被“孝感市妇女网”等报道。最近数年,两地的越南媳妇亦多次登上各大媒体的页面。此次选取了两个乡镇中跨国婚姻较为典型的4个村庄进行了田野调查,其中方刘冲村、陈家楼村、张寨村等三个村庄位于H县H镇,吕王村位于D县。四个村共有越南媳妇37人,此次调研16人。其中,方刘冲村共有越南媳妇13人,调研4人;陈家楼村共有越南媳妇8人,调研4人,张寨村共有越南媳妇6人,调研3人;吕王村共有越南媳妇10人,调研5人。
二、鄂东北四村跨国婚姻家庭的基本情况

1.年龄情况
调查中发现,婚姻中双方的结婚年龄整体偏大,男女之间的差距亦较大。娶越南媳妇者结婚时的最大年龄为46岁(方刘冲村),年龄最小者28岁(方刘冲村),方刘冲村和陈家楼村娶越南媳妇者的结婚平均年龄均为39岁,张寨村的娶越南媳妇者的结婚平均年龄为38.3岁,吕王村的娶媳妇者的结婚平均年龄为35岁。
嫁到两地的越南籍女性结婚时的最大年龄为40岁(张寨村),年龄最小者为17岁(吕王村),嫁到方刘冲村的越南媳妇的结婚平均年龄为29.3岁,嫁到陈家楼村的越南媳妇的结婚平均年龄为29岁,嫁到张寨村的越南媳妇的结婚平均年龄为32.3岁,嫁到吕王村的越南媳妇的结婚平均年龄为25岁。
婚姻关系中均为男性的年龄大于女性,男性大于其越南籍妻子的最大年龄差为23岁,最小年龄差为2岁;所调查的16名越南媳妇平均比娶越南媳妇者小约9岁,其中方刘冲村的年龄差平均为8.25岁,陈家楼村的年龄差平均为10.5岁,张寨村的年龄差平均为4.3岁,吕王村的年龄差平均为11岁。
2.经济情况
此次调查的16户娶越南媳妇者的家庭条件在各村普遍属于中等偏下。有7位娶越南媳妇者的双亲中有一人在其年幼时过世,因此家中劳动力不足,经济来源少,以致家境较差。从住房情况看,所有娶越南媳妇家庭都没有在当地乡镇上购买住房,并且在村庄中也只有1户有独立的两层以上的楼房,另有6户人家的房屋为老式土砖房,其他9户人家均为一层的楼房,家中的家具布置也较为简单。这一情况对于目前普遍以有两层以上的新楼房为结婚条件的当地农村而言,确实难以娶到老婆。如方刘冲村有1户家庭中有兄弟3人,老二和老三均娶越南媳妇,两兄弟共一栋两层的普通楼房;张寨村中一户兄弟二人同娶越南媳妇,虽然兄弟两人及父母已经分家,但共住5间瓦房;张寨村另一户兄弟三人,老大和老二娶越南媳妇,兄弟两人同住一栋两层楼的楼房。
此外,娶越南媳妇者全部有过在建筑工地工作过的经验,且均有过在越南的务工或旅游经历,除一人以外,其他人在最近的一年内仍在建筑工地务工,调查时仍有2人在国外建筑工地工作,还有一人在两个月后将赴越南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
越南媳妇娘家的家境普遍差于在中国婚嫁后的家境,仅一个人家境条件好于其丈夫的家境条件,其父母为村庄公务员。越南媳妇中父母几乎全部为农民,以从事农业、畜牧业为主,被访谈的媳妇中只有两个人的父母当干部,一人的父亲经商。在越南时越南媳妇从事农业种植、养猪与家禽的占28%,出去打工的占45%,做小买卖的占19%,其他8%。从整体而言,越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北部逊于南部之态,因此在地域分布上,原居住于北部的占75%(12人),中部的占18.75%(3人),南部的占6.25%(1人)。
3.婚姻情况
已有研究发现,在边境婚姻中男女双方均为初婚的比例较高*戴波、赵德光:《云南省跨境婚姻实证分析及社会学思考》,《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而此次调查发现,虽然同为中越通婚,但发生在鄂东北地区的跨国婚姻中的初婚比例并不高。越南媳妇中有10人曾在越南结过婚,其中8人所生为女孩,7人均由于没有生育男孩而被迫离婚,婚生子女均由女方或其姥姥抚养。越南媳妇中所生子女最大年龄为17岁,最小者为2岁。1人由于幼年时患病而丧失生育能力而未结婚。其他6个越南媳妇由于家境贫穷、兄弟多、长相等原因而没有结过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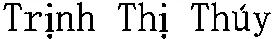
4.语言问题
由于越南媳妇在越南时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仅2人接受过高中阶段的教育,小学及以下的占37.5%(6人),初中毕业及以下的占50%(8人),接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占18.5%。而且接受小学教育最少的越南媳妇为小学一年级毕业后即辍学,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两人中也只有一人毕业。这一情况也造成了她们在越南时基本上没有掌握汉语和英语,书写能力也较差。越南媳妇中并没有人在来到中国之前接受过系统的汉语培训。越南媳妇中除2人于2007年来到中国,她们的汉语水平达到可与中国人正常交流的程度外,其他越南媳妇均难以与当地人沟通。整体而言,来得早的越南媳妇的汉语水平强于后来的越南媳妇。有越南媳妇在决定来中国之后,在越南购买《中越实用会话1200句》《中越字典》等语言工具学习,她们主要是通过与丈夫的交流学习汉语,另外通过看娱乐节目、同胞之间相互交流等方式学习汉语。如嫁到陈家楼村的越南媳妇黎氏锦亨在2012年嫁入中国之前并没有学习过汉语,而是在准备来中国之时才去买了《中越实用会话1200句》。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与发生在边境地区较为常态化的跨境婚姻相比,发生在鄂东北地区的中越跨国婚姻呈现出非常态化的特征。在年龄分布及差距、家庭经济情况对比两方面异于常态化分布;双方的婚姻状况则是出现了非初婚比例偏高这一现象;相较于基于族缘、地缘等之上的跨境通婚,语言与跨国因素成为该地婚姻走向常态化、生活化过程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正是这一特征,导致了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关系网络上面临着脱嵌的风险与悬浮的无奈。
三、脱离与难融下的脱嵌
中越跨境婚姻中双方主要集中在两国边境上的山区,而出现在鄂东北地区的跨国婚姻中的越南媳妇却远嫁千里之外的异文化区域,加之边关阻隔,这些因素使得跨国婚姻所面临的关系网络有着迥异于边境上的与婆家相对较近、往来相对方便的跨境婚姻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之处。由于上述客观因素,远嫁中国的越南媳妇在关系网络上面临着脱嵌的危险,这种脱嵌既表现在越南媳妇被迫脱离其国内的原关系网络,也表现在越南媳妇无法融入到新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1.与原关系网络的脱离
就越南媳妇而言,原关系网络中的主体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前一婚姻关系中所生育的子女。由于远嫁他乡,越南媳妇客观上脱离这些关系网络,主要表现在由于婚后回国次数少,与原家庭的联系下降到了最低程度。因而她们与原生活地域的关系网络面临着脱离的风险;她们的丈夫除了同越南媳妇一同赴越南探亲外,平时与媳妇在越南的亲人缺乏有效沟通和联系。
此次调查中的越南媳妇中有3人没有回过越南;16名越南媳妇中仅有1人因从事婚介工作而回越南较多外,其他越南媳妇一般为约两年回一次,一次居住时间约1个月左右。

除了与家人的情感交流外,部分越南媳妇还寄钱回国供养她们前一次的婚生子女。在嫁入中国后她们的父母仍需要继续供养这些未成年孩子,因而在打电话交流之外,这些越南媳妇仍大约一年两次向父母寄钱。
边境婚姻中越南媳妇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亲属一般会到她在中国的家庭来做客。这一保持关系网络延续的方式在发生在H县、D县中的跨国婚姻之中却难以见到,除了越南媳妇回越南以外,她们的家人鲜有到中国者。在此次调查的4个村的37位越南媳妇中,直到2015年6月才有吕王村越南媳妇Hà的母亲来到该地。
2.难以融入家庭关系网络
一般情况下在农村社区,女性嫁入男方家庭后,由于长时间生活于家庭之中,会融入原家庭所属的关系网络之中。然而,由于语言这一关键性问题,到目前为止越南媳妇都无法顺利融入到新的关系网络之中。
首先是难以建立良好的婆媳关系。虽然《长江日报》等媒体竞相报道“家务全包揽 体贴丈夫孝敬老人 家中基本消除婆媳矛盾”*罗京:《红安小镇来了80名越南媳妇》,《长江日报》2013年1月24日。,然而此次调查发现,越南媳妇和中国婆婆之间的关系并不比传统的婆媳关系好。整体而言,此类家庭的婆媳关系呈现出交流少、生活习惯相异等特征。由于嫁入该地的越南媳妇在来到中国之前均不会讲汉语。到中国后基本上不能与已到高龄且不会说普通话的中国婆婆正常交流。此次调查中有3位已经来中国约4年的越南媳妇均表示只能与婆婆做简单的交流,不能与婆婆商量家庭事务,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用手指点、比划等方式进行沟通。此次调查中询问公婆是否懂越南语时都是得到否定性回答。即使在婆媳关系上被树为榜样的方刘冲村刘红兵家,刘红兵的78岁母亲说到:“她(媳妇)说的我听不懂,我说的她不懂,她有时候对我说越南语,我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但听口气就知道不好,反正我也听不懂,就装作不知道。”*方刘冲村,刘母,访谈时间:2015年7月1日上午。在笔者与其母亲交流过程中,老人在提到了一句“对儿媳妇还满意”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过其儿媳妇一句,而是全部讲述不在场的大儿子如何优秀之类的话。由此其婆媳关系的情形可见一斑。
其次饮食习惯也影响着家庭关系。越南媳妇普遍喜好清淡,因此做饭极少用油,不惯吃辣,而喜欢煲汤、煮菜及酸的味道,特别偏好鱼虾、河蚌之类,这也造成了一家之内出现两种饮食习惯。与此同时,在越南北部女性坐月子的时间一般为3个月,其间多吃鱼虾等,而鄂东北地区农村坐月子一般为1个月,其间多吃猪肉、鸡肉等,不同的生活习惯加重了婆媳矛盾,制造了嫌隙。

四、悬浮的新关系网络
在越南媳妇脱离于原关系网络的时候,也有关系网络再造的现象发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婚介网络的形成及在华越南同胞的关系建构。然而,由于婚介中存在着相当的灰色因素和经济利益的矛盾,这两种关系网络极其脆弱,因此无法实现越南媳妇在地化而处于悬浮之态。
1.“滚雪球”式的婚介网
从2004年开始,两地的农村未婚中青年开始以务工为契机,赴越南寻找媳妇,此间的婚姻多由在工地上充当翻译的越南人介绍而成。因此2008-2011年为越南女性进入吕王镇、华家河镇的第一波高潮,此次调查中的16名越南媳妇基本在这一时间段进入,其中有7人由越南本地中间人介绍,因此她们来中国的平均时间约为5年。


2.基于感情建立同胞网
王越平发现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出现了一种壮族媳妇拟制姻亲关系的“拜后家”现象*王越平:《中越边境壮族跨国婚姻中的“拜后家”研究——以云南河口县中寨村为例》,《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由于鄂东北地区属于汉族聚居区,当地人与越南媳妇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区域,在与当地社区存在着关系网络脱嵌类的情况下,类似于“拜后家”的民俗习惯缺乏生长的土壤。面对这样的情况,越南媳妇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加强交流和沟通,在小范围内建立起新的关系网络。
随着近年来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进入门槛降低以及通讯工具价格的下降,智能手机及微信、QQ等聊天工具日趋普及。此次调查的16名越南媳妇均有一部智能手机,并且都注册并经常使用微信、QQ等。据多位受访对象介绍,她所知道的当地越南媳妇都有手机和聊天工具。在越南媳妇较为集中的方刘冲村、陈家楼村、吕王村的越南媳妇们还建立起了微信群、QQ群,加之当地“中国联通”2012年开始推出“随意打”业务,联通用户拨打省内联通用户全免费,越南媳妇均办理的是联通号。
除了日常的联络外,越南媳妇之间在春节等重要节日时还相互拜年。平时遇到越南媳妇的生日的时候,还相约到她家为其过生日。正是由于越南媳妇之间互相往来较多,促使她们在现实中形成了相对紧密的共同体,在农活上组成合作组互相帮助,一些家庭矛盾亦是请个别先来的越南媳妇帮忙从中调解。这些途径都加强了越南媳妇之间的联络,特别是在她们无法融入当地社区关系网络之中的情况下。

五、结 语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通过婚姻而缔结的关系属于强关系网络。然而,对于发生在远离边境地区的跨国通婚而言,是否会产生强关系网络则尚待商榷。整体而言,越南媳妇在脱离了原有关系网络之后并未很好地融入到原本应属于关系网络较强的新家庭和社区关系网络之中,再造的新关系网络似有强度更强之感,却因制度、现实等因素亦出现了难以消解的困境,因而使得处于脱嵌与悬浮状态之中的关系网络的内在强度明显较弱,而这一关系网络的存在将会使出现在非边境地区的跨国媳妇面临着日益“孤岛化”的尴尬境地,进而使已有研究中所提及的社会化、身份认同等困境更显突出,所以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并不仅仅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和制度上的困境,因此关于这一发生在中东部地区的跨国婚姻现象亦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孙秋云教授的指导,在田野调查中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硕博研究生马媛、高氏春桃、卫文凯、谭春雪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