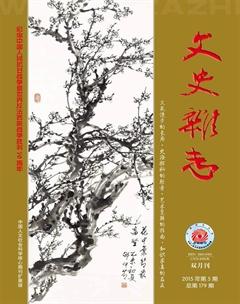明亮世界 净洁心灵
王定璋
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文学家李白,以其敏锐的感知、细微的观察、精深的剖析、饱满的情思和审美趣味独到的眼光遗留下近千首诗歌和65篇文章,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诗人置身的时代的社会状貌与人文气质。本文不拟对李白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把握,只就李白诗文中咏及月亮或涉及明月的篇章作一探寻,进而研究其文学意义和文化价值,不妥之处,识者匡之。
一
月球是宇宙中十分独特的天体,它虽不直接发光却能反射太阳的光辉,从而给人以既赐与地球万物以明亮而又非光芒夺目,令人不敢直视的柔和清凉。月球如此的秉性与特征,铸就其在自然界的特殊地位与独特的影响。因而在传统的文化典籍中,其重要意义比肩太阳。《易》曰:“日月丽乎天”,即将太阳的光辉与月亮的美丽相提并论,足见赐万物以温暖光明的阳光和普洒大地以如水月色都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美丽景色。古人所称誉的日、月、星三光中月光自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太阳和月亮的不同特质与日月交替阴晴变化,形成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人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演变为兴亡更迭的漫长活动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月亮的明洁剔透,清辉柔媚,其地位与影响似乎比太阳更可人意,受到多愁善感的文人墨客青睐与爱恋,以致于成为文学作品吟咏不衰的文学母题与寄托载体。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出现频率最高,最为美丽动人的表意对象,当是月亮。《诗经·月出》首导其先,《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两见继其后。《文选》中的月亮形象更是数见不鲜,谢庄《月赋》更是专门咏月之章。唐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堪称咏月巨擘。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而李白的咏月诗歌,更是光彩耀眼,美轮美奂,令人目不暇接。现存其咏吟月亮的诗歌据不完全的统计竟有三百多首(其中包括涉及月亮的作品),占其现存诗歌总量超过三分之一还多。而这些诗歌质量上乘,审美情趣隽永。李白咏月诗的文化意蕴也极为丰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展现:
首先是诗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光明前程的向往。他那首豪情激宕、愤懑悒郁之情不得其泄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是在月夜美景中才稍得纾放的:“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此诗题又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见《河岳英灵集》),当为李白失志于宫阙,赐金还山之后漫游齐鲁之作。徐梦麟称“白天宝元年曾游会稽,此诗或在‘五噫出西京’后,追怀剡中山水而作。”(《颓废之文人李白》)良是。观此诗结尾“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可知,当时李白心绪是多么激愤与抑塞!显然李白怀着云锦般的美好愿望步入朝廷,短暂的宫廷待诏政治生涯,倏然结束,无异美梦一场,醒来却是令人迷茫的浊恶。而只有在镜湖月的旎旖氛围里,才能获得片刻的宁谧与温馨,在如幻的梦境里麻醉诗人敏感的神志。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舍人贾至游洞庭五首》中,就有两首咏月之章: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
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
醉客满船歌《白苎》,不知霜露入秋衣。
前首于浩渺无际的洞庭月色美景之下,钦美酒于任其飘荡的轻舟之上,何等适意舒心!后一首则为醉客放船酣歌湖上的快乐。二者的共同之处是月色沐浴下的个性的舒展。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展示的是诗人月下徘徊,久吟沉思的兴致:
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
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
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谢朓名句“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的意境一直是李白所心折的独创。龙蟠虎踞的古都金陵,见证了历史的兴衰治乱。古往今来的文人骚客清词丽句,想必是使诗人盘桓沉吟回味未已的缘由吧!
其次则为李白通过吟咏月亮以表达对亲人、友人、情人的思念与祝愿。此类作品极多且佳,是诗人咏月诗的重要内涵。
明白晓畅,语浅情遥的《静夜思》是传诵不衰的佳作: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这首月光下的思乡思亲人之作几乎表达了所有在外漂泊的游子的共同感受,赢得千百万人的激赏是不必多说的。而“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当然是对享有诗家夫子美誉的王昌龄因被贬黜,太白对其遭遇深表同情,而以诗宽慰,托明月以表思念之忱。至于《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可谓咏月诗之瑰宝。诗人透过咏月送友人并抒发其飘泊异乡的复杂感受: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
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
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
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
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
黄金狮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
我似浮云滞吴越,君逢圣主游丹阙。
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
此诗是送蜀中僧人入长安之作。据诗题“中京”云云,可知其诗歌为至德二载至上元二年之间的作品。长安改为“中京”是在这时间段内的事情。(见《新唐书·地理志》)此时已年届五十九岁的李白虽遭贬黜夜郎,但半道遇赦放还,却还豪情不减,飘逸仍存,写下了这首既咏月又抒情的佳作。皓皎的明月是此诗清丽的背景,流畅的音调和喷涌的情思是诗歌灵魂。诗中明月六见,并不觉得雷同重复,莹洁清辉为此诗着上了明亮色调。与友解携并不悲切,饱含着强烈的诗人情感的月光是扫除离别友人惆怅的心灵良方。《严羽评点李集》谈此诗时指出:“是歌当识其主伴变幻之法。题立峨眉作主,而以巴东、三峡、沧海、黄鹤楼、长安陌、秦川、吴越伴之,帝都又是主中主。题用月作主,而以风云作伴,我与君又是主中主,回环散见,映带生辉,其有月映千江之妙。巧转如蚕,活变如龙,回身作茧,嘘气成云,不由思议造作”,道出了李白这首咏月诗因月生情的妙处。诗人与僧人同为蜀人,虽在巴东三峡,见明月而忆峨眉,峨眉月普照神州大地,虽同为异地流徙之郁闷,却有故乡明月相随……确可谓流寓中不乏逸致豪情之杰构。
《峨眉山月歌》是李白咏月诗中之精品:“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半轮形状的峨眉山月,流淌和缓的平羌江水,诗人在万籁俱寂的夜幕下,顺江而下的船帆,在不知不觉中离别了故乡和父老乡亲,淡淡的愁思和不可名状的惆怅似乎伴随诗人去向他乡,远适异地。这也难怪,夜阑人静之时,万物休息,只有高悬天际的月光,还不知疲惫地将其柔和的清辉,沐浴大地,引发多情的诗人无限遐想:“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畅饮万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长川泻落月,洲渚晓寒凝。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据《太平寰宇记》板桥浦在江宁县南40里,谢当年经此地时赋《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中即有“江路西南永,归流东北骛。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名句。而其诗中“即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则恐怕是引起独酌于月下的李白向慕的人生志趣了,也是他曾慨叹过的“月下沉吟久不归,古今相接眼中稀”的罕有对象。
李白常以明洁剔透的月亮称誉他所亲近的人:“鱼目高太山,不如一玙璠。贤甥即明月,声价动天门。能成吾宅相,不减魏阳元。”(《赠别从甥高五》)而当他得知日本友人渡海遇难(误传)时,也以明月为喻为其叹惜:“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哭晁卿衡》)
此外,李白诗中的月亮是其永恒不渝的朋友,是倾述孤独寂寞的对象。似乎在人间遭遇的喜怒哀乐和挫折失意,他都可以无保留地向其倾吐发泄。此类作品中,最典型无过于《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真是出神奇于平淡,发异想于突兀。当诗人月下置酒,怅饮无绪之际,皓月当空,悬挂于无垠的湛蓝天空之上,如水的月晖笼罩着万物,时奇思奔涌,浮想联翩,突然间觉得自己并不孤独:蓝天中的明月,自己身边的影子与诗人岂不是三人组合了吗?虽月不解饮,影子无言,可是酒酣兴起的诗人,起舞于月下,弄清影于花间,此情此景,确非常人所能理解;个中乐趣,也非庸人所晓。只有宋代同为蜀人的苏轼是其古今相接的后代知音。他在《水调歌头》中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体味到月下独自跳舞的乐趣,妙不可言,清影随人,真是仙人羽客才领略得到的。这里不消说是受谪仙人的启发获得的灵感。
至于《把酒问月》则表现了诗人对月发出的一连串美妙奇特的追问,值得把玩: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玉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月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
唐代的科学技术虽然较之于上古有一定的发展,生产力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要回答李白在此诗中提出的关于月亮一系列的问题,似乎还不能寻求到圆满的答案。破题所云青天中的月亮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明月高高在上,人类是否可以借助利器而登上月球?为什么人行走,月亮始终不离地跟随着……如此等等的问题谁又说得清楚呢?
此诗的妙处不仅仅是问题的提出,而是诗人富有哲理思索的智慧展示。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白兔捣药的民间传说,让李白这首咏月诗显得如此神奇灵幻,较之于屈原《天问》更具有文学情趣与审美价值。而《苏台览古》则以昔日苏台的繁华与当下的荒芜予以对照,以月的永恒无恙讥刺吴王的荒淫误国的历史教训:
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此诗针砭荒淫失国之意甚明。李指出:“一二句但写今日苏台之风景,已含起吴宫美人不可复见意,却妙在三四句不从不得见处写,转借月之曾经照见写,而美人之不可复见,已不胜感慨矣。”(《诗法易简录》)可谓知言。
李白咏月诗的另一特征是突发遐想,给人以莫名其妙的感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古朗月行》)小儿懵懂,识见有限,对蓝天高挂的圆月,呼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玉盘,比喻生动,形象鲜活。这不就是仙境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么?
令人感到奇妙神秘的是关于神奇月圆的神话传说,是谓月中仙人桂树、白兔捣药之类,吴刚被罚砍桂树等故事。《初学记》卷一引虞喜《安天论》云:“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初生,见仙人之足渐已成形,桂树后生。”此是李白诗中“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之所本。
至于“白免捣药”之事,则晋代傅咸《拟天问》即有“月中何有?白兔捣药”之说,古辞《董逃行五解》云:“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服此药可得神仙……”(《乐府诗集》卷三十四)此外,蟾蜍蚀影,后羿射九乌等神话传说都是与月亮关系密切的故事……李白将这些美妙奇幻十分诱人的内容,巧妙地融入其中,确实给人以莫名奇妙、不可捉摸的感觉。可是,结句之“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直露此诗命意所在,即诗人以月之变幻,暗指天宝晚年政局之昏乱。萧士赟指出:“此诗借月以引兴,日象君,月象臣,盖为安禄山之叛兆于贵妃而作也。”未确。倒是陈沆《诗比兴笺》颇协诗旨:“忧禄山将叛时。月后象,日君象。禄山之祸兆于女宠,故言蟾食月明。以喻宫闱之蛊惑。九乌无羿射,以见太阳之倾危,而究归诸阴精沦惑,则以明皇本英明之辟,若非沉溺声色,何以安危乐亡而不悟耶!危急之际忧愤之词。萧士赟谓禄山叛后所作者亦误。”参合李白全诗,显然陈说为胜。
这里,又引出了李白咏月诗的另一文化蕴含,即透过咏月诗干预朝政,针砭时弊的重要价值。月亮有其自身不发光而只能反射太阳光线的特征,故古人常将日比君,月喻臣。《说文》云:“日,太阳之精;月,太阴之精。”《淮南子·天文训》:“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则是对日月特征进一层的阐解。因而月亮又以阴精称之。李白《古风·蟾蜍薄太清》是其咏月诗以月喻政的另一类型:
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
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
入紫微,大明夷朝晖。
浮云隔两曜,万象昏阴霏。
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
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
沉叹终永夕,感我啼沾衣。
毋庸讳言,此诗绝非简单地咏月蚀的诗歌,而是另有深意者。月之蚀乃自然天象,蚀过之后,月亮的光亮依旧美丽迷人。然而,诗人显然另有所指。杨齐贤云:“按《唐书》王皇后久无子,而武妃有宠,后不平,显诋之,遂废。武妃进册为惠妃,欲立为后,潘好礼谏止之。太白诗意似属乎此。”萧士赟解之更详:“蟾蜍薄太清,月为之蚀,以喻武妃入后宫而卒为王后之蠹也。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晖,以喻武妃既得幸而玄宗卒为所惑也。……万象昏阴霏者,意谓自后卒不正中宫浸成女宠之祸也。萧萧长门宫者,王后事全与汉武陈后事迹相类……太白引以此证,最为切当。桂蠹花不实,是采废后制中语。天霜下严威者,事发觉时,帝自临劾也。”大体切合诗意。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云:“前人但见诗中长门宫一语,遂附会为指王皇后之被废,其实唐人诗中托宫怨以喻士之见弃者已成常调,李诗中亦不止此一首。王氏更据开元十二年七月月蚀,同日王皇后被废,遂指此诗为是年所作。然是年李才二十四岁,远在蜀中,无由知之,即知之亦无缘关心此宫闱中之事。若云事后追咏,则天下事大于此者甚多,李意恐不在此。”此又未必然。愚以为,文学创作涵容极广,不必泥于一时一地,也不必拘执于一人一事。李白此诗,以月起兴,因月蚀而触发创作激情,将其所闻所见,所思所念,围绕月蚀天象,将其欲抒发的情感融入其中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参合众说,当以萧说最富胜义,即此诗乃以月喻政,抨击时政错乱,宫闱易后之诸弊端而发也。
李白咏月诗内涵极为丰厚。月球天体长存宇宙。而自人类存世以来,历经岁月沧桑,人事代谢,变化未已,美丽的月亮却始终那么宁静安详地高悬天际。这不免引发了多愁善感的文人骚客的好奇与揣测。如果人类也像月亮那样永恒存在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早《山海经·大荒西经》就有月神常羲的出现,称她为帝俊之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美女嫦娥。而《淮南子·览冥训》中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在古人心目中,月亮之所以那么美丽动人,永恒不灭,原因是嫦娥获取了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而得以居住于月宫。既如此,人们是否也能像嫦娥那样去寻求、制造不死药以求青春永驻,长生久视呢?于是,古往今来的寻求延年益寿秘方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李白寻仙访道,采丹砂以合九转金丹的经历在其《题雍丘崔明府丹灶》里表现出来:“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叶县已泥丹灶毕,瀛洲当伴赤松归……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相信合九转金丹服之就会像玉乔、赤松子仙人来去自如,乘云驾雾,超越生死,永享人间幸福欢愉。葛洪《抱朴子·金丹》指出,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并进而指出:“一转金丹服之,三年得仙……九转金丹服之,三日成仙。”李白不仅深信不疑,而且也在赐金还山,政治上受排挤之后,入道成为具有“方士格”的道士(参见其诗《草创大还》)。他认为服食成仙后就会像服用了玉免捣药的月中仙子一样年华永驻,与日月同辉。他的这种飞升成仙的幻想常受月辉的启迪:“融融白玉辉,映我青蛾眉。宝镜空似水,落花如风吹……安得黄鹤羽,一报佳人知。”(《拟古》)而《感遇四首》其三则明谓:“昔余闻姮娥,窃药驻云发。不自娇玉颜,方希炼金骨……”认为嫦娥永驻容颜的秘诀是不老药使然,因此也要取法之。在永恒不灭的月亮启示下,诗人寻求服药成仙的追求是那样的执著与不倦。
夜幕降临,皓月临空,清晖笼罩大地,最能勾起怀人思乡的情愫。闺中少妇的幽怨,情人遥夜之思念,是李白咏月诗最为惊艳的题材。“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吴歌》其三)此乃戍妇思念远征良人之词,语浅情深,月下思念久别的征夫,诚挚动人。唐汝询云:“此写戍妇之辞以讥当时战伐之苦也。言于月夜捣衣以寄边塞,而此风吹不尽者,皆念我思念玉关之情也。安得乎平胡而使征夫稍息乎?不恨朝廷之黩武,但言胡虏之未平,深得风人之旨。”(《唐诗解》)颇有见地。《初月》云:“玉蟾离海上,白露湿花时。云畔风生爪,沙头水浸眉。乐哉弦管客,愁杀征战儿。因绝西园赏,临风一咏诗。”也是见月生情,从征战将士远离故土亲人的角度出发吟出的反对穷兵黩武的佳构。《拟古十二首》其一:“青天何历历,明星如白石。黄姑与织女,相去不盈尺。银河无鹊桥,非时将安适?闺人理纨素,游子悲行役。”也是望月色而思念远在他方的亲人之悱恻缱绻情愫。其二更觉深沉凄切:
高楼入青天,下有白玉堂。
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
遥夜一美人,罗衣沾秋霜。
含情弄柔瑟,弹作《陌上桑》。
弦声何激烈,风卷绕飞梁。
行人皆踯躅,栖鸟去回翔。
但写妾意苦,莫辞此曲伤。
愿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
这是一首睹月思情的弃妇诗。今人遗憾的是她所思念之人早已另有所属,将其遗忘,不免使人为之叹惋,因而才有弦声激烈,行人踯躅的强烈反响。
离人乡思,游子客愁,也因月色的朦胧而倍增离忧:“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玉露生秋衣,流萤飞百草。”余如“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长相思》)等等,就不一一胪列了。
二
李白咏月诗的文学意义与审美趣尚极为丰富多样,其文化价值也十分独到。因其内涵深厚而涉及面广阔,具载的情感几乎涵容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重要特征即为展现在读者面前一片光明世界,呈现的是诗人净洁心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银辉普照,纤尘不染;“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柔和清晖,捣衣忙碌;“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塞下曲六首》之三),表现的是戍边将士的武勇。“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则是塞上月色照耀长剑下将士的英姿,其豪迈气势则有“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的雄壮。“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朦胧月色笼罩下的幽静环境,思念情人的主妇还独自静心地盼望着什么呢?婉约深沉。
至于“更怜花月夜,宫女笑藏钩”以及“昭阳桃李月,罗绮自相亲”,“莫教明月去,留著醉姮娥”(《宫中行乐词》),则为在银白的明月清晖里宫娥彩女的欢乐逗趣与天真烂漫。“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摹写的是行乐者的美好心情。“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桥伤别。”(《忆秦娥》)于秦楼月的追忆中发思古之幽情。“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子夜吴歌》)此乃想象当年西施采荷的可人画面的再现。而“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也以月色称誉妇女的美艳动人。总之,诗人笔下的月辉确是人间最为光明的世界,活动于此间的各色主人公都有如皓月一样明亮净洁的心灵,给读者以无限幽思与遐想,令人把玩不已。
此外,李白咏月诗赋月亮以无穷丰富的蕴含,拓展了以月喻人,托月传情,因月表意,以月喻政的广阔空间。月亮成为诗人最为忠实可靠的代言人。《蟾蜍薄太清》以月蚀喻朝政之昏庸,对山雨欲来之势将酿成的隐忧,以详前述;《古朗月行》也是此意,兹不赘述。而以月喻人,则将日本晁衡之渡海遇难咏之为“明月不归沉碧海”,是其显例。《峨眉山月歌》“思君不见下渝州”中之“君”也是以月拟人之佳喻。(参见《唐诗别裁》)至于托月传情之典范无过于“我寄愁心与明月”的名句了。“月色不可扫,客愁不可道”(《拟古四首》其二)亦是。以月喻人的“贤甥即明月,声价动天门”,“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其月下境界汗漫夐远;“万里舒霜合,一条江练横。出时山眼白,高后海心明”(《雨后望月》),那是诗人在雨后转晴观察月亮的独特的感受,亦即“四郊阴霭散,开户半蟾生”。云开霭散,月辉迷人,当此之际,诗人不忍心遽然离去:“为惜如团月,长吟到五更。”
要之,李白诗歌中的月形象,是诗人对美好事物的称颂,对人生理想的寄托,对美景前程的期待,也是其思念亲人、怀念故土、劝慰友情的载体,孤独寂寞时与之相伴的对象……是值得深入研究,认真发掘的艺术瑰宝。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