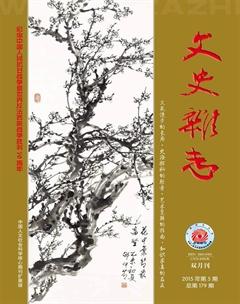白玉蟾行藏考
冯广宏
摘 要:白玉蟾是道教南宗第五祖,南宋嘉定间曾赴阙主持国醮,以后不知所在,著作颇丰,生平神异。关于他的生卒年历来颇具争议,其中生于绍兴四年说比较引人注目,但不能成立,当以绍熙五年(1194年)说可靠。其卒年似可延至元代中期,世寿或在百年以上。
关键词:神异;宁宗知遇;绍熙五年说;绍兴四年说;世寿百年
厘清事迹
白玉蟾是道教南宗第五祖,学识赡博,诗文并妙,且精于书画,著作又非常丰富,不过他的事迹有些说法不一,如生卒年岁就存在争论。[1]笔者拟就当时三亲材料及本人笔墨,进行深入稽考。
玉蟾家世,以亲传弟子彭耜(1185~?)嘉熙元年(1237)所撰《海琼玉蟾先生事实》(简称《事实》)为最可靠:“先生姓葛,讳长庚,字白叟。先世福之闽清人。”他原名葛长庚,字“白叟”是因长庚为太白星,又有长寿之意,并非怀念白家。祖籍是福建闽清,“时大父有兴董教琼琅,是生于琼,盖绍熙甲寅三月十五日也。”因其祖父葛有兴在海南主管教育,故出生于琼州(今海南琼山),生年是绍熙五年甲寅(1194年)春季,这是离他最近的权威性说法,不可任意否定。
《事实》指出,他幼时家庭发生了特殊变故:“七岁能诗赋,背诵九经。父亡,母氏改适。”葛长庚从小受他祖父培养,7岁(1200年)就能吟诗作赋,但大约9岁时其父葛振业去世,母亲改嫁,肯定祖父也不在了。笔者推测这一灾祸的起因是文字狱,《资治通鉴》记嘉泰二年(1202年)林采、施康年上疏禁程朱“伪学”,刮起“学禁”、“党禁”之风,于是反对宋金和议的道学一派受到沉重打击,可能牵连到管理教育的葛家,导致家破人亡,今人认为母嫁白家便改姓白,实属误解。此时葛长庚只有采取出逃一策,《事实》说他被本乡道士陈楠(号翠虚子、陈泥丸)收留,成为道童,“从师游海上”,随后来到雷州(今属广东湛江)投靠白家,更名“白玉蟾”,字“以阅众甫”。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只隔一条海峡,这应是陈楠为他解祸的策略。陈振孙(1183~1262?)《直斋书录解题》评论“玉蟾者,葛其姓,福之闽清人,尝得罪亡命,盖奸妄流也。”明代桑乔《庐山纪事》卷十亦称:“玉蟾,琼州人,姓葛。尝因任侠杀人,亡命武夷,事陈泥丸为道士。”臆测他因“任侠杀人”而亡命,不了解那时还是个孩子。
玉蟾在《必竟恁地歌》里叙述拜师时间:“开禧元年中秋夜,焚香跪地口相传”;而在《日用记》中说“予年十有二,即知有方外之学,已而学之,偶得其说。” 开禧元年(1205年)他正是12岁。后来他白家也呆不住了,陈楠命他出去访道,只好带上300文钱到处云游,所写《云游歌》叙述一路所受熬煎:
初别家山辞骨肉,腰下有钱三百足。思量寻师访道难,今夜不知何处宿。不觉行行三两程,人言此地是漳城。身上衣裳典卖尽,路上何曾见一人。初到江村宿孤馆,鸟啼花落千林晚。明朝早膳又起行,只有随身一柄伞。
他走到兴化,囊中只剩两三文钱,挨饿走到罗源兴福寺,要求担任童仆混口饭吃,结果干了半个月便离开寺庙。途中遇到暴雨,想在村民茅屋檐下过夜,结果也受到驱赶。听说建宁好善人多,便到那里去讨饭,仍然得不到任何怜悯。一路上“行得艰辛脚无力,满身瘙痒都生虱”;“火云飞上支提峰,路上石头如火热”;“记得武林天大雪,衣衫破碎风刮骨”;接着走到江西龙虎山,想在上清宫挂单,知堂道人嫌他褴褛肮脏,给他一碗馊饭和凉水,批评他丢了道教的人。在外流浪8年之久,到达武夷山又遇见陈楠,才正式成为南宗传人,“偶然一日天开眼,陈泥丸公知我懒。癸酉中秋野外晴,独坐松阴说长短。”癸酉是嘉定六年(1213年),玉蟾20岁,开始得到钟吕派丹道和神霄派雷法的传授。
苏辙后裔苏森嘉定九年(1216年)写的《修仙辩惑论》跋语云:“先生姓白,名玉蟾,自号海南翁,或号武夷翁,未详何处人也。人问之,则言十岁时师事陈泥丸;九年,学炼金液神丹,九还七返之道,虚坎实离之术。”表明白玉蟾10岁开始跟随陈楠,至20岁时才正式授法。苏森对玉蟾的印象是“蓬头赤足,其右耳聋,一衲百结,辟谷断荤,经年不浴,终日握拳闭目,或狂走,或兀坐,或整日酣睡,或长夜独立,或哭或笑,状如疯颠,性喜饮酒,落魄不羁”,是个邋遢而神异的道人,与传说中的铁拐李形迹相近。
今人据玉蟾诗文,得知他嘉定五年(1212年)在罗浮山(广东),八年(1215年)云游至武夷山(福建),九年(1216年)到江西龙虎山,受到当地道士的尊重。彭耜《事实》说“先生始而蓬头跣足,辟谷断荤;晚而章甫缝掖,日益放旷;不知先生者,往往以是而窃议之”,说明他开始不修边幅,实是迫不得已,但随后已经衣冠楚楚。他接着到了浙江天台,复至福建武夷;嘉定十一年(1218年)往江西鄱阳而至庐山(西山),曾受邀“为国升座”主持国醮。《事实》称:“戊寅春,游西山,适降御香建醮于玉隆宫,先生避之,使者督宫门力挽先生回,为国升座,观者如堵。又邀先生诣九宫山瑞庆宫主国醮,神龙见于天,具奏以闻,有旨召见,先生遁而去。”随后又到广西武城。宋宁宗时期政局相对稳定,重视道教,遂欲召见玉蟾。十二年(1219年)玉蟾从江西入浙,到达国都临安。那里的僧人孤云见他博极群书、贯通三教,劝说他当和尚以光大佛门,连衣钵都准备好了,而他却加以婉拒:“夷夏之道有所不同,道不同不相为侔也。”他接着游福建鼓山、江西皂山、江苏平江虎丘、福建三山,后来或因感激宁宗知遇,加上看到政治上的隐患,《事实》记玉蟾嘉定十五年(1222年)至临安上书言事:“壬午孟夏,伏阙言天下事,沮不得达。因醉执逮京尹,一宿乃释。既而臣僚上言:先生左道惑众,群常数百人,叔监丞坐是得祠。”此时玉蟾29岁。
从这些记载来看,玉蟾完全是个性情中人,挚爱师父,挚爱道教,挚爱宋廷,虽然身在方外,却要议论天下大政,可是腐败的官僚怎能把道人的意见上达朝廷?他只得仗醉批判京官,以致被拘留了一夜。其所以没有对他作更大的侵害,大概顾虑到随同他行道的有庞大团队。他对宁宗的感情,表现在1224年《嘉定甲申闰月五日闻皇帝升遐》诗中,宁宗驾崩使他“无任冰肝玉胆摧”,那时他31岁,正游历江西麻山。
陈楠以雷法授徒,玉蟾得到师传,并传授给弟子彭耜和留元长等人。留在《海琼白真人语录》卷首云:玉蟾对他说“向者,天真遣狼牙猛吏雷部判官辛汉臣授之先师陈翠虚,翠虚以授于我,今以付子,子宜秘之。”神霄派一般建有祀神的靖室,并建立小型教团。《鹤林法语》谓玉蟾让彭耜“亟命建靖治,立玉堂,置玉匮司,仍置黄箓所”。道徒彭耜、留元长、赵汝会、林时、林伯谦、吴景安、邓道宁、陈弥隆、谢显道、赵收夫、潘常吉、周希清、胡士简、罗致大、陈守默、庄致柔等人各有法职。彭耜对林伯谦提到过靖室名称:“度师(指彭耜)谓伯谦曰:尔祖师(指白玉蟾)所治碧芝靖;予今所治鹤林靖;尔今所治紫光靖。大凡奉法之士,其所以立香火之地,不可不奏请靖额也。”这种微型宫观,是经过官府认可的,也是合法的。
《事实》记有嘉定十五年(1222年)初冬,玉蟾在临江军(今江西樟树)落水,当时就有“水解”的传说,但后来有人在融州(今广西融水)见到他,宝庆三年(1227年)他34岁时在广东罗浮山,而“绍定己丑冬,或传先生解化于盱江”。《事实》根据玉蟾《呼唤体自述》诗云:“只贪饮酒与吟诗,炼得丹成身欲飞。曩劫曾为观大士,前生又是派禅师。蓬莱旧路今寻著,兜率陀天始觉非。料我年当三十六,青云白鹤是归期。”好像是说寿限,绍定二年(1229年)传说他水解于盱江(江西赣江支流),正是36岁。可是“逾年,人皆见于陇蜀,又未尝死,竟莫知所终”。认为他最后到了西蜀,但究竟有没有死,彭耜也弄不清楚。
《道法会元》载赵宜真(?~1382)《原阳子法语》称:“尝闻紫清白真人云游九年,辛苦万状,方遇真师。”说他20岁时(1213年)陈楠传授丹道和雷法。“又二十年,方得寄食洪都金宰相府,潜修十年,功成仙去。”“紫清真人闻金液大还之道,又云游行法,济世度人,方依金丞相府修炼成功,是先修福、后证道。” 所谓“洪都金宰相”,应指豫章(今南昌)人京镗(1138 ~1200)。记载表明“水解”后的玉蟾,40岁时隐居于南昌京家,京镗后人资助他十年,约在50岁时成道,证明他这30年中遁迹南昌,不再云游。此后来到蜀地留下诗句,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说,成都青羊宫还有他“字径半尺”的手书碑石,这是他最后的事迹记载。
生卒疑年
玉蟾生于绍熙五年(1194年),活动频繁期是20来岁。留元长《海琼问道集序》言其师“时又蓬发赤足以入廛市,时又青巾野服以游宫观,浮湛俗间,人莫识也,自云二十有一矣”。此外,苏森自号懒翁,玉蟾作于“嘉定丙子(1216年)初夏十有五日” 的《懒翁斋赋》,言“翁今已过‘从心’之一年”,所谓“从心所欲”是指70岁,则此年苏森已是71岁的老人;玉蟾又有《赋诗二首呈懒翁》:“懒翁老白结忘年,秋入淡烟疏雨天”,表明二人年龄相差很大,属于忘年之交,则此年玉蟾23岁为可信。
关于玉蟾卒年,《事实》明记其绍定二年(1229年)36岁时“水解”。与玉蟾同时代的刘克庄(1187~1269)虽和修道者交往,但对丹家甚为轻蔑,其《后村集》卷八《王隐君六学九书序》说:“近世丹家如邹子益、曾景建、黄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识,然知其为闽清葛氏子。邹不登七十,黄、曾仅六十,蟾尤夭死,时皆无他异,反不及常人。”他说“蟾尤夭死”基本属于传闻。《后山诗话》卷二说:“黄天谷,名春伯;白玉蟾,姓葛名长庚;皆自言得道,后死,乃无他异。”今人根据刘克庄得知玉蟾死讯,认为玉蟾即使不如此短命,也不能活过刘的卒年(咸淳五年,1269年),故其寿不能超过75岁。其实,刘所得讯息就是36岁的“夭死”,并无其他,故玉蟾寿命的上限与刘之卒年并无关系。
厦门大学尤玉兵在《全宋文》和《续修四库全书》发现有《宋白玉蟾尺牍》的新材料,此函是“玉蟾顿首再拜上覆判县宝谟郎中”的,说“玉蟾常敬足下性无尘俗,学有源流”,表示仰慕。笔者据其“兹勤军将之远来,下谕长生之密旨;文缄别幅,道莫妄传”之语,得知这个“郎中”不是带兵的军将,而是神霄派的法职。关键是下文“三十三年之蹭蹬,且过壬寅;七返九还之大丹,成于乙已。此去斗牛星里,利磨匣内之宝刀;他日熊虎幕中,环听明公之号令。几多珍重,未尽毫端。风云手段,屏除天下之鬼群;霖雨心胸,行简日边之帝听。”壬寅应是淳祐二年(1242年),乙巳则为淳祐五年(1245年),其时玉蟾为49和52岁。所谓“三十三年之蹭蹬”,是自谦这33年里碌碌无为,上推33年玉蟾是19岁,始得雷法之传,如今才成正果。据此,则其年寿超过五旬,可得一确证。
《重刻海琼玉蟾先生文集》有“南极遐龄老人臞仙”写的《原序》,言“余自乙亥于江浦遇纯阳,明年于乐安与先生邂逅一遇,两载之间,两遇天真,倏尔四十七年矣。”说明作者丙子年(即嘉定九年,1216年)在江西见过玉蟾;又说:“去岁夏,忽又遇先生于豫章,自称‘王詹’,乃知即‘玉蟾’之隐名也,与余相对謦欬一笑,人莫知识。自是别后,莫知所往。”原刻作序时间是“正统壬戌孟秋”有误,正统是明代年号,应作“中统”,壬戌为蒙古中统三年,即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自前次相遇至作序时间正是47年。所言“去岁”即1261年,此时玉蟾68岁,犹在南昌,这是见诸文献的确切年岁。
有些研究者在《文集》里寻找证据,推测其世寿可到六旬以上,可惜所举书证皆不可靠。因为集子里大量诗文都是彭耜所集,而彭白交往又限于他们年轻时代,只有晚于彭耜所集的散落作品才有老人口气,所以不少确证,基本上皆属误会。如经常被举用的《大道歌》“年来多被红尘缚,六十四年都是错”,似乎玉蟾自称64岁,其实原诗是“云谷道人仙中人,骨气秀茂真磊落;年来多被红尘缚,六十四年都是错。” 汪登伟君业已指出,64岁的是云谷道人,而不是他,玉蟾有《赠云谷孔全道》诗,故道人名为孔全道。[2]另一经常被举用的是《水调歌头·自述十首》:“虽是蓬头垢面,今已九旬来地,尚且是童颜。”好像写词时玉蟾竟近于90岁,这一点汪君也觉不解,不过将原词全文品味一下,就明白了其中的误解。
这首词是自述的第三首,前两首说幼时苦难,此词专述求道经过。上阕讲他为求道不怕千辛万苦,“吃尽风僝雨僽,那见霜凝雪冻,饥了又添寒”;而下阕“好因缘,传口诀,炼金丹。街头巷尾,无言暗地自生欢。虽是蓬头垢面,今已九旬来地,尚且是童颜。未下飞升诏,且受这清闲。”则说他遇见真师,准备传授他丹道口诀,暗暗高兴。下文形容那不修边幅的九旬老人是其师陈楠,并非玉蟾。诗词作品不像文章那么直白,有时无须主语,须仔细咀嚼才知原意。后面几首全讲丹道内容,再没有提老师的事。
不过,笔者相信白玉蟾年寿仍然不短,《文集》中后来所辑作品便有许多痕迹。如《览镜》“一回览镜一回老,天已安排欲我翁”,开始有了老的感觉,这是大量其他作品中所绝无。《菊花新》词:“看看皓首,瞒不过镜台儿”;《沁园春》词:“念镜中勋业,韶光冉冉,尊前今古,银发星星”;《岁晚书怀》“朱颜日已改,华发渐复稀”;《冬夕酌月》“二毛可惜雪霜侵,日有清都绛阙心”;《杜鹃行》“一声一声复一声,不管世间银发生”;都提到生出白发,《杜鹃行》应是成都所写,因有“滴破浣花溪上诗”之句。另一首《闻子规》“如今老眼应无泪,一任声声到月残”,亦为在蜀所作。《醉中赋别》“行色已如天色好,道情不与世情同。如今老眼浑无泪,醉颈当筵似玉虹”;同样提到“老眼”,这决不是中年人的口气。
《道法会元》卷一百八载元人虞集(1272~1348)《景霄雷书后序》,认为玉蟾年寿很长:“琼琯白玉蟾先生,系接紫阳,隐显莫测,今百数十年,八九十岁人多曾见,江右遗墨尤多。”白玉蟾到处写字题诗,来求者一概不拒,因此荆蜀收藏他的墨宝者甚多。正德《琼台志·仙释》:“玉蟾吾乡人,少闻诸父兄云:元末父老犹及见其还乡者,道其事甚详。”元末海南还有人看到他,恐非空穴来风。
现今学术界对于玉蟾生年,除绍熙五年甲寅(1194年)说外,还有绍兴四年甲寅(1134年)一说,两说研究者旗鼓相当。[3]绍兴说的依据,是弘治年间(1495年前后)裘仲孺《武夷山志》称玉蟾生日“绍兴甲寅三月十五日也”;以及何乔远(1558~1631)所编《闽书》卷五《方域志·闽清县·芹山》,言玉蟾“是生于琼,盖绍兴甲寅三月之十五日”,未见其他宋元旧说。康熙庚辰(1700年)所刊《神仙通鉴》云:“玉蟾本姓葛,大父有兴,福州闽清县人,董教琼州。父振业,于绍兴甲寅岁三月十五,梦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产子,母即‘玉蟾’名之以应梦。” 清彭翥(字竹林)《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即引用其文,这一晚期资料最不可信。不过有些研究者对现有文献的可靠性,常常不加甄别,盲目信从;对于文献原文也不愿仔细消化,往往曲解或误读。
绍兴说的最大漏洞,正如曾召南君所指出:历经高宗、孝宗、光宗的60年间,按此说应是玉蟾从青年、壮年而至老年的阶段,他的情况却不见有一点记载,而在他70岁以上的宁宗嘉定年间,几乎年年皆见于记载,活动非常频繁,实有悖于常理。原先不做云游的白玉蟾,高龄时期却突然到处云游,据其《云游歌》所言,到处挨饿受冻、蒙羞受辱,遭遇常人未有的艰苦,有这个可能吗?[4]
持绍兴说者引“从事郎新南剑州州学教授”汤于写的《琼山番阳事迹》:“白先生以二月五日到番阳旅邸,与一举公蔡元德剧谈”,蔡元德见他佯狂的样子,未加理会,次日黎明玉蟾留了一首诗,交给旅馆老板说“候蔡解元起,以此呈之”,蔡才大为怅惜。汤于将此事 “亦禀谯提刑,或可遣人往庐山物色之”,此文署“戊寅二月十一日”。绍兴说者据陈亮《龙川集》卷二十七《蔡元德墓碣铭》“君(蔡元德)卒于乾道九年(1173年)十二月之朔”,推论所署“戊寅”为1158年,认为玉蟾生于绍兴年间才说得通。可是按《墓碣铭》原文“君讳弥邵,元德其字也”,此人“进不得志于科举,退必有以自见于其乡”,没有考中,显然不是这位“蔡解元”,仅是其字相同而已。文中提到的“谯提刑”即谯令宪(1155~1222),眞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四《谯殿撰墓志铭》谓其嘉定八年(1215年),“提点江东刑狱”,谯令宪《松风集序》谈到与玉蟾的交往:“余持节宪江东之日,尝相契于庐山。”因此这个“戊寅”实际上是1218年,所以绍兴说者此证不能成立。
绍兴说者又举出许多书证,多属误解。
玉蟾有《别李仁甫》一诗,绍兴说者认为李仁甫就是史学家李焘(1115~1184),此人淳熙改元(1174年)之际曾任江西转运副使,有机会与玉蟾交往,因其卒年是淳熙十一年(1184年),表明玉蟾不可能在此后出生。近日汪登伟君细查李焘事迹,再据原诗“君向星江结草庐,我来抵掌笑相于”,认为很难找到他在星江(江西星子县)结草庐的理由,因此李仁甫与李焘决非一人,此证也无法成立。
据裘仲孺《武夷山志》玉蟾10岁(一说12岁)时曾到广州参加“童子科”考试,考官以“织机”为题,玉蟾写出“日月双梭天外飞”的佳句。《武夷集》录有此诗,题注考官为“韩郡王”,即抗金名将韩世忠(1089~1151),故玉蟾生于绍兴年间方能合理。按《通鉴》绍兴十二年(1142年)岳飞被害以前,韩世忠作为守边将军,不可能主考;岳飞被害后退居闲职,受封咸安郡王就杜门谢客,平时将佐亦罕见其面,故这一传闻纯属捕风捉影,不足为证。
诸葛琰《跋鹤林紫元问道集》说玉蟾“近日携梦蟾图一卷惠予”,图上写明孔毅甫元祐初年(约1086年)梦见月光斜照高岩,“有物如蛤蟆雪色,旁立二道士手各持文书”,梦醒后画了这张图。淳熙年间(1174~1189)“周益翁尝刻以遗临江简寿玉,石湖居士赋诗以记灵。余得此图始悟先生‘玉蟾’之号似非偶然者”。绍兴说者以为玉蟾淳熙年间即已现身人世,否则为何有人赋诗记灵呢?按这一书证全属误会,图画并非玉蟾作品,范石湖赋诗是针对图画内容而言,与玉蟾毫无关系。“玉蟾”名号的来历是诸葛琰在猜想,又与玉蟾何干?
相传玉蟾曾与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庐山有过交往。明代都穆《都公谭纂》卷下:“朱晦翁居白鹿洞,与白玉蟾善。”据此断定玉蟾生于绍兴甲寅为可信。按朱熹在庐山任南康军知军兼内劝农使,是淳熙六年(1179年),至八年(1181年)离任;而玉蟾至庐山又记有明确时间的《翠麓夜饮记》:“戊寅之春,清明后三日,有客白玉蟾来自琼山,游于庐阜之下。”依绍兴说“戊寅”当为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距朱熹知南康军早20多年,二人根本不可能在庐山相见,故都穆所记仅属无从稽考的传闻而已。至于玉蟾提到朱熹的文章,皆属纪念性质,更不能作为证据。
杨万里(1127~1206)的长子杨长孺《华文杨郎中札子》言:“初以为仙侣(指白玉蟾)不为今人也,徐而问之,乃知其为今人,而似仙非凡者也。”此信写于壬午年(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二月。绍兴说者认为,连当时人都以为玉蟾不是“今人”,说明他由前古一直生活到“现在”,只有绍兴说才解释得通。按这一逻辑更不能成立,误认为很早的人,怎能证明就是很早的人呢?
玉蟾《与彭鹤林书》注明丁丑年(嘉定十年,1217年),却称“琼山老人白某谨书”;又有一函写“十月二十一日,琼山老叟白某致书”;如果他当时只有24岁,怎么会自称老叟呢?故按绍兴说定为84岁,才合乎道理。这一点,须按道家习惯称老称寿来解释,道人弱冠就开始留须,苏森说玉蟾20来岁即“自号海南翁,或号武夷翁”;在弟子面前称翁称叟,表示是长辈;弟子尽管比师父年长,也习惯称其师为翁为叟。所以此信的称谓并不能支持绍兴说。
绍兴说举出的铁证,是《谢仙师寄书词》:“玉蟾素志未回,初诚宿恪,自嗟蒲柳之质,几近桑榆之年;老颊犹红,如有神仙之分;嫩须再黑,始归道德之源。叹古人六十四岁将谓休,得先圣八十一章来受用。”末署 “大宋丙子闰七月二十四日”。曾君查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和《续通鉴》,只有嘉定丙子(1216年)是闰七月,那时玉蟾只有23岁。绍兴说者指出,如果那么年轻,怎会自称桑榆之年老颊,又提到64岁数字?故此时应是83岁。按此驳也显得软弱无力,八旬以上并不是“几近桑榆之年”,而是深入桑榆之年了,再提64岁有何意义?所以绍兴说也难自圆其说。化解这一矛盾,仍然可用道家习惯称老、表示亟亟求师之情来剖解,玉蟾称“几近桑榆”,是觉得转眼就老,希望陈楠仙师传授秘诀,以却老防衰。“老颊犹红”与“嫩须再黑”是骈文里的对仗句,借以描写修道的成效,并非实指。至于谈到古人64岁休致,仍属虚指,仅与下文《道德经》第八十一章相对仗,并无与年岁相关的含义。
总之,绍兴说不能成立,或前或后稍加修正亦无任何意义。玉蟾生年在《事实》中是唯一的记述,定于绍熙五年(1194年)最为可靠。其卒年文献无征,似可延伸至元代中期,世寿或在百年以上。
注释:
[1]今人研究文章很多,如何敦铧《关于道教金丹派南宗第五祖白玉蟾几个问题的探索》,《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盖建民《白玉蟾生卒年考辨》,《上海道教》2000年第l期;李远国《白玉蟾生平系年考略》,《道韵》第七辑2000年8月;曾召南《白玉蟾生卒及事迹考略》,《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3期;谢金良《白玉蟾的生卒年月及其有关问题考辨》,《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4期;王尊旺、方宝璋《也谈白玉蟾生卒年代及其有关问题——兼谈近年来有关白玉蟾问题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3期;朱逸辉《琼籍文化宗师白玉蟾》,《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符颖、符和积《白玉蟾生卒年岁疑》,《中国道教》2005年第3期;兰宗荣《白玉蟾与懒翁关系述考》,《武夷学院学报》 2008年第4期;冯焕珍《白玉蟾生卒年新说》,《现代哲学》2011年第5期;黄永锋、方宝璋《白玉蟾活动区域考》,《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刘亮《白玉蟾生卒年新证》,《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刘守政《宋白玉蟾尺牍考》,《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等。
[2]参见汪登伟:《白玉蟾生年考疑——兼說其訪道、行道》,《新浪博客》2014-04-20 。
[3]参见陈撄宁、任继愈、朱越利、胡孚琛、方宝璋、王尊旺、曾召南、宫川尚志、周伟民等支持玉蟾生于绍熙甲寅(1194年)说;柳存仁、李远国、冯焕珍、盖建民、兰宗荣、郭武、何敦铧、王万福、谢金良、朱逸辉、刘亮等则支持玉蟾生于绍兴甲寅年(1134年)说或稍加修正。
[4]参见曾召南:《白玉蟾生卒及事迹考略》,《宗教学研究》2001年03期。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