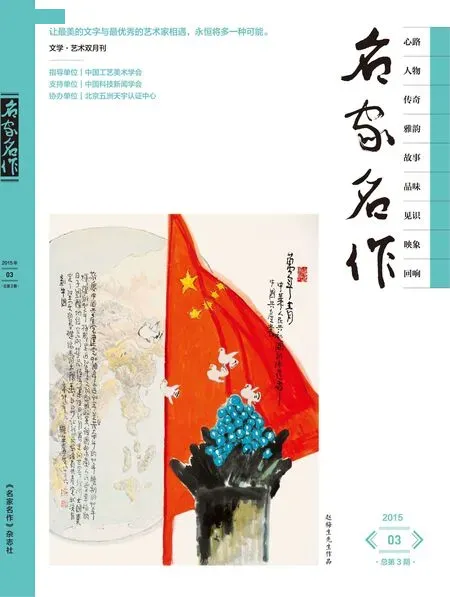又见姚元之
高洪波
又见姚元之
高洪波

《无欲乃积寿 有福方读书》姚元之/作高洪波/藏
四十岁以后,或曰:90年代以来,我突然萌生出一种怀古幽情。这种情绪的典型表现是大量搜集历代笔记小说、野史大观,继而津津有味地阅读,生吞活剥地解析,总之,这种情绪于今愈烈,根源在一个人,一个叫姚元之的清代官员、学者兼画家。
我曾在一篇叫做《寻找姚元之》的散文中记录了与他的精神邂逅,盖缘于姚元之遗落在世间的一方印章,印文仅一个字:“元”。深蓝色的印匣内注着另外二行漂亮的行书:“姚元之嘉庆进士左都御史”。印章有一边款,笔力不凡,上写:“伯昂仁兄属刻”,署名爽泉。
“爽泉”在我最初文章中误为“奕泉”,后来考订出来,此刻印者仍是我的同宗,叫高恺,字爽泉,清代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姚元之的朋友。
寻找姚元之的过程很艰辛,也很愉快。我被这一符号吸引,如破译密码般向清代典籍中寻求解释和帮助,最后终于弄明白了姚元之的大概情况,知道他善绘画、工隶书,名列清代十六画人之十一;也了解到他有专著《竹叶亭杂记》;姚还干过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兵部左待郎、工部右待郎及刑部、户部等重要部门的“副部长”,我认定姚先生为“万金油”干部,不敬,却是事实。
姚元之的面貌就这样渐趋清晰。然而我一直没有见过他的画与字的真迹,也无缘读到《竹叶亭杂记》这本在我看来极有趣的书。
无缘即是时机不到。
时机一到,相拥相抱。
我先是看到了姚元之的隶书对联:“无欲乃积寿有福方读书。”洒金纸的底上,还绘有飞蝠的暗纹,姚的隶书一笔不苟,勾如浮鹅,顿如蚕头,点如垂露,撇则若铁镰,从内容到外在形式,都给人一种沉静的气韵,大家的风度。
继而又看到了姚元之的画,一幅题为《梦梅图》的设色纸本卷,这幅画是姚为他的一位前辈建卿先生所画,建卿先生梦中得一名句:“盘空硬语如梅花”,命题作画,姚元之欣然从命。这幅画的构图清幽静远,朦胧的远山,淡云、高树,茅屋的有机组合,居画面之中的是一树高耸的红梅,树干直挑半空,切出的是“盘空硬语如梅花”题,画面的左上角晕染出一轮明月,以此月印证一个“梦”字,亦巧极雅甚。
此画有张廷济题迎首,梁章矩等十三位名人题跋,显得古色古香、脱尽火气。这正如清人邵梅臣在《画耕偶录》中谈及的:昔人论作书作画,以脱火气为上乘。夫人处世,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即所谓脱火气,非学问不能。
“非学问不能”,姚元之的《梦梅图》静穆、丰韵、润泽、名贵,可谓四善皆备。此画为北京瀚海艺术品拍卖公司1995年秋季拍卖品,标价三万多元。据说最后以三万元价格卖掉,我真羡慕这位有眼力的买家,他拥有了姚元之的一幅杰作,以三万元的巨款作物质保障,由此可见再纯粹的精神也离不开物质。
姚元之的字与画一一目睹,剩下的是寻找他的《竹叶亭杂记》。为这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的书,我曾多次造访北京书市,探询琉璃厂海王村的中国书店,可惜均告无书。
两年前走河北定州,在一位友人李君家小憩,李君曾任解放军某团政治处主任,现任定州市财政税务部门负责人,一位文学受好者。李君家中颇宽敞,引人注意的是客厅内极气派有一溜书柜,书柜内气宇轩昂地排着经史典籍,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尤众,再定睛看,赵翼与姚元之分著合版的《曝杂记》《竹叶亭杂记》赫然在目。
匆忙中不及细读,只记下了此书的印数:18500册,定价:1元。李君告之此书购于天津,时为1984年秋,正在军旅服役之时。
初次相识,不便掠美,怅然而返。但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姚元之这本小书,待到数月前再赴定州,一回生二回熟,厚起脸皮向李君借阅,同时赠一册自己的散文集《醉界》,内中有《寻找姚元之》一文,似可作为借条借据。孰料李君颇慷慨,允我将书带回北京长期阅读,就这样,开始了我对姚元之精神怪面的又一次了解。
公允地说,姚的这本《竹叶亭杂记》水平一般,文采学识虽有,但不如赵翼的《曝杂记》,赵文以阅历取胜,文笔生动;姚文以杂博见长,略嫌拘谨。八卷笔记,记风光物产、人情习俗,谈当朝掌故、礼仪制度,直至读书记、考辨杂纂,虽内容丰富,但总有一种官场气息。或许姚元之为人为文,就是这种原生态罢。
卷六有一记,可见姚元之另一性情:他在小绒线胡同某家发现旧书两架急欲出售,就匆匆前往购买,“以钱五十千得《管子》、《庄子》,初印《韵府》及《类函》、《事文类聚》、《六臣注文选》、元刻《楚辞》、《北堂书钞》、《四库总目》等书。”姚元之因为手头钱紧,向表弟张相如借,表弟把自己的一袭裘衣典当了之后换成现金,帮姚元之买下这批旧书。买书时姚元之问主人何故卖书,主人回答道:“赎当耳。”姚元之一听乐了,写道:“卖书赎当,借当买书,亦可留为异日佳话。”
这则笔记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姚元之爱书如命,其二他生活并不富裕,否则不至于让表弟把裘皮衣裳拿去典当。阮囊羞涩同时又嗜古成癖,古今文人命运相似。
姚元之还有一则有趣的笔记,现全文摘录如下:
“山东李鼎和曾得屏贼盗咒语羁旅路宿颇可预防。咒曰:‘七七四十九,贼盗满处走。伽蓝把住门,处处不著书。童七童七,奈若何。’学此咒,清晨日出时向东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鸡犬妇人见之。”
咒如童谣,又如幽默小品,但姚元之一本正经地写出来,且不能让鸡犬妇人见到,光这条禁忌就足以让人解颐喷饭。
再往深处一想,姚元之所处的嘉道年间社会治安想必不佳,否则何以有这般好玩的“防贼盗咒语”?姚的生年为1773年,逝世年为1852年,他逝世前一年,洪秀全先生已开始造大清朝的反。太平军将士,不仅仅是一般毛贼、车匪路霸,念叨一万遍“童七童七,奈若何”怕也不成喽。
不过这一切姚元之已不再关心,他活了七十九岁,尽享天年,也尽享了太平。剩下的事让曾国藩和左宗棠们料理好了,湘军注定要借洪秀全之势而崛起,直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为止,惟楚有材,於斯为盛,这也是天意。
姚元之辞世101年后,本文作者诞生。再40年后,开始寻找姚元之,直至又见姚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