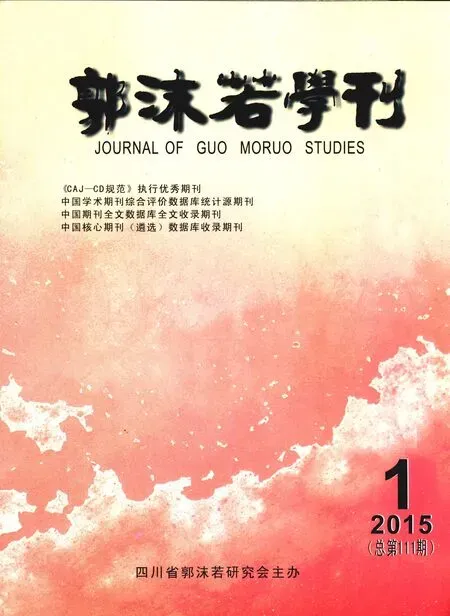鲁迅 郭沫若 茅盾论罗曼·罗兰
编者辑
鲁迅郭沫若茅盾论罗曼·罗兰
编者辑
鲁迅论罗曼·罗兰
我所见的外国名伶美人的照相并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没有见过,别的名人的照相见过几十张。托尔斯泰,伊孛生,罗丹都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勖本华尔一脸苦相,淮尔特穿上他那审美的衣装的时候,已经有点呆相了,而罗曼·罗兰似乎带点怪气,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虽说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来罢,但总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
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Frans.Masereel),是欧洲大战的时候,像罗曼·罗兰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本(Bei Kurt Wolff,Wünchen)。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
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写信,已经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今人作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来不及出版。王尔德的自述,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发表,这在我们中国恐怕办不到。
注:孔另境,浙江桐乡人。他所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后来改名《现代作家书简》,于1936年5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内收58位作者的书信219篇。牍(dú读),古人写字的木简。古人用尺把长的木简写信,故称书信为尺牍。
1926年6月,罗兰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瑞士的所记的《战时日记》原稿(分订29册,最后一册记于巴黎)交瑞士巴塞尔大学图书馆保存,又将3份打印字稿分交苏联列宁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要求各保管者到1955年1月1日才可以启封,并译成该国文字出版。
1927年为她的60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给她书简写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则说:“凯绥·阿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然而她在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儿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儿子像那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医生。
原书以1922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在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冲突。
……
但是,十二年前,作者却早借谟尔却的嘴给过解释了。另外,再抄一段法国的《世界》周刊的记事,在这里——
许多工人政党领袖都受着类似的严刑酷法。在哥伦,社会民主党员沙罗曼所受的真是更其超人想象了!最初,沙罗曼被人轮流殴击了好几个钟头。随后,人家竟用火把烧他的脚。同时又以冷水淋他的身,晕去则停刑,醒来又遭殃。流血的面孔上又受他们许多次数的便溺。最后,人家以为他已死了,把他抛弃在一个地窑里。他的朋友才把他救出偷偷运过法国来,现在还在一个医院里。这个社会民主党右派沙罗曼对于德文《民声报》编辑主任的探问,曾有这样的声明:“三月九日,我了解法西主义比读什么书都透彻。谁以为可以在知识言论上制胜法西主义,那必定是痴人说梦。我们现在已到了英勇的战斗的社会主义时代了。”
这也就是这部书的极透彻的解释,极确切的实证,比罗曼·罗兰和爱因斯坦因的转向,更加晓畅,并且显示了作者的描写反革命的凶残,实在并非夸大,倒是还未淋漓尽致的了。是的,反革命者的野兽性,革命者倒是会很难推想的。
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十场戏剧,卢那察尔斯基作,易嘉(瞿秋白)译,为《文艺连丛》丛书之一。剧本借用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的形象,将他放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进行描写,对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批判,也批驳了当时一些人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中伤和非议。剧中人物除了吉诃德和他的侍从山嘉外,还有革命党人德里戈、巴勒塔萨和封建专制统治者国公、伯爵谟尔却、侍医巴坡的帕波等。
林语堂先生只佩服《论语》,不崇拜孟子,所以他要让娘儿们来干一下。其实,孟夫子说过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唯送死可以当大事”。娘儿们只会“养生”,不会“送死”,如何可以叫她们来治天下!
“养生”得太多了,就有人满之患,于是你抢我夺,天下大乱。非得有人来实行送死政策,叫大家一批批去送死。只剩下他们自己不可。这只有男子汉干得出来。所以文官武将都由男子包办,是并非无功受禄的。自然不是男子全体,例如林语堂先生举出的罗曼·罗兰等等就不在内。
懂得这层道理,才明白军缩会议,世界经济会议,废止内战同盟等等,都只是一些男子汉骗骗娘儿们的玩意儿;他们自己心里是雪亮的:只有“送死”可以治国而平天下,——送死者,送别人去为着自己死之谓也。
就说大多数“别人”不愿意去死,因而请慈母性的娘儿们来治理罢,那也是不行的。林黛玉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女界的“内战”也是永远不息的意思。
注: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8月21日《申报·自由谈》,署名虞明。
本文从林语堂说的“让娘儿们干一下吧”这个话题入手,含蓄地把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嘲讽为“以妾妇之道治天下”,揭露了他们内部纵横捭阖、互相倾轧,以及对人民实行“送死政策”的腐朽反动本性。
这是《近代思想十六讲》的末一篇,1915年出版,所以于欧战以来的作品都不提及。但因为叙述很简明,就将它译出了。

注释:
①《论照相之类》,《鲁迅全集》一卷,186页。
②《〈连环图画〉辩护》,《鲁迅全集》第四卷,447页。
③《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四卷,263-462页。
④《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鲁迅全集》第六卷,414页。
⑤《〈凯绥·阿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鲁迅全集》第六卷,470页。
⑥博心译,见《中外书报新闻》第三号。
⑦《〈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鲁迅全集》第七卷,400-402页。
⑧《娘儿们也不行》,《鲁迅全集》第八卷,357页。
⑨《〈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十卷,424页。注:真勇主义,又译为英雄主义。

郭沫若论罗曼·罗兰
《阿Q正传》是鲁迅的有名杰作。世界介绍的开始是起自1926年罗曼·罗兰主编的《欧罗巴》杂志上的译载。这是谁都知道的事。然而最先拿介绍的笔的人是谁呢?这人就是创造社同人之一的我的同乡四川人敬隐渔。隐渔是天主教会养育出来的,精通法文和拉丁文。1924年在上海住着,一面把我的小说译成法文,一面自己也提过创作的笔,是在创造社的刊物上登载过的。此后,他因翻译《若望·克里斯妥夫》得到罗曼·罗兰的相识,1925年末应罗曼·罗兰的招请便往法国去了。
《阿Q正传》的介绍,自然,是隐渔在法国的主要的工作,鲁迅以这次的介绍为机缘在生前便博得了世界的高名,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隐渔的名字完全为世间所隐蔽。而且外面还有一种谣传,说是罗曼·罗兰有信给鲁迅,极力称赞《阿Q正传》,信是托创造社转交的,而被创造社的人们把它没收了。这种无根无蒂的飞簧,真正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
宏大的一只轮船停泊到了安全的海港。
这是当我从报上读到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在我心灵上所引起的第一个波动。
罗曼·罗兰的一生似乎是一部受难史,在人类这个海洋还没有达到风平浪静的一天,作为一位精神的领港者,要过着受难的生活是应分的事。
在今天,我并不怎么悲痛罗曼·罗兰之死。因为罗曼·罗兰已经尽了他的领港者或舵手的责任,他是应该休息的时候了。
罗曼·罗兰,他的身体虽然休息了,他的精神作用,毫无疑问,在人类史上是要永远存在的。他是法兰西的夸耀,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夸耀。人类中总有这样崇高善洁的灵魂,生死都为人们所景仰,超越国界,超越时间,这便预兆着人类必得有光明的未来。一切失掉人性的法西斯野兽们,尽管怎样地凶毒傲狠,总也掩盖不住在这个现实之前的它们的心惊胆战。它们假如不怕,为什么要回避或甚至摧毁这个现实?
世界规模的兽性大叛逆,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不知道摧毁了多少善洁的灵魂,有的肉体被毁灭,有的更把整个灵魂出卖了。象那些为法西斯服役的文化亡魂们,不是最可鄙夷的悲惨吗?
罗曼·罗兰傲岸地控诉了来,战斗了来。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及其它,还要继续着控诉起去,战斗起去。让那抵御兽性泛滥的伟大的防波堤,广泛地发挥它的威力吧!让善良的儿女们在这儿得到慰安,让凶残的野兽们在这儿发出战栗吧!
罗曼·罗兰安息了,安息在法兰西人民经过光辉的战斗、从纳粹兽蹄下获得了解放后的今天。先生,你安息吧,我祝福你。你停泊下的轮船,我们知道,在招呼着新的舵手。
有稀微的希望底晨光,破露在那天上,
斜射着还在波涛汹涌的血底海洋,
狂暴的雷雨渐渐地快要镇定的时候,
一只宏大的战船停泊到了安全的海港。
多么长远的、艰苦的,但可又磊落的战斗呵,
你伟大的法兰西的儿子,真理底领港,
你为法兰西底再生,人类底再生,和平底再生,
慷慨地、沉着地,输出了你最后的一珠血浆。
看呵,你的旗帜永远在塔桅顶上飞扬,
你伟大的人类爱底使徒,你请安息吧,
战船,就象嘶风的骏马,和你生前一样,
早又奔腾上消灭法西斯野兽的世界战场。
啊,你听,《马赛曲》底歌声是多么的嘹亮!
人类在庆祝着新的胜利,新的诞生,新的成长。
你伟大的民主的战士,罗曼·罗兰,你永生了!
你永远是法兰西之光,人类之光,和平之光!
罗曼·罗兰先生,你是一位人生的成功者,你现在虽然休息了,可你是永远存在着的。你不仅是法兰西民族的夸耀,欧罗巴的夸耀,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夸耀。你的一生,在精神生产上的多方面的努力,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宏大,人类是会永远纪念着你的。你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像太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
罗曼·罗兰先生,在20年前你的杰作《约翰·克里斯朵夫》初次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你曾经向我们中国作家说过这样的话:“我不认识欧洲和亚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民族——一种是上升,一种是下降。上升的民族是忍耐、热烈、恒久而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趋向一切的光明:学问、美、人类爱、公众进步;而在另一方面的下降的民族是压迫的势力,是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你说,只有上升的民族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弟兄。你说,你的祖国是自由的人类。这些话对于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是给予了多么正确的指示,多么有力的鼓励呀!
在今天的世界,正是这两种民族斗争着生死存亡的时候。你所说的上升的民族就是我们代表正义、人道的民主阵线,你所说的下降的民族就是构成轴心势力的法西斯蒂。一边是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解救人类的困厄;另一边是奴役,饥饿,活埋,杀人工场,毒气车,庞大的集中营,一个鬼哭神号的活地狱。但今天,上升的不断地上升,下降的不断地下降,光明终竟快要把黑暗征服了。我们要使全人类都不断地上升,全世界成为自由人类的共同祖国。
罗曼·罗兰先生,你伟大的法兰西民族的儿子,当你看到法兰西民族又恢复了她的光荣的自由,而你自己在这时候终结了你79年的人生旅程,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微笑的吧?但当你想到你的朋友,你的同志,你的兄弟的好些民族,依然还呻吟在法西斯蒂的控制下边没有得到自由,在和死亡、饥饿、奴役、恐怖作决死的斗争,在你那肃穆的容颜上,怕也必然表露出了一抹更加肃穆的悲愤的吧?
但是,罗曼·罗兰先生,伟大的人类爱的使徒,你请安息吧。上升的要不断地自求上升,下降的要不断地使它下降,我们要以一切为了人类解放而英勇地战斗着的民族为模范,我们要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趋向一切的光明。不避任何的艰险,尽力和黑暗、愚昧、残忍、凶暴的压迫势力、法西斯蒂、现世界的魔鬼,搏斗!我们中国是绝对不会灭亡的,人类是必然要得到解放的,法西斯魔鬼们是必然要消灭的!
罗曼·罗兰先生,你请安息吧。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象你一样,把“背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要象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我们一定要依照你的宝贵指示:“每天早上,我们都得把新的工作担当起来,把前一天开始的斗争继续下去。……对于错误,对于不公正,对于死,我们必须不断地力争,为着更大的更大的胜利。”
1945年3月21日
不足十年的工夫,四位伟大的文化战士,先后逝世了。高尔基、鲁迅、巴比塞、罗曼·罗兰,你们都请安息吧。你们都已经尽了你们领港者的责任,完成了你们的战斗的任务。
关于罗曼·罗兰先生之死,前两年曾经传播过一次,不久便打消了。这次又传播了出来,至今已半月,未见打消,但我毫不怀疑,就和前次一样,他依然是没有死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死。
罗兰先生是以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到世界文坛的,他同情人类,崇拜天才,歌颂音乐,以他的博大的人类爱,要像音乐一样,包含一切,融化一切,鼓励一切。也要象音乐天才贝多芬那样,傲昂地、崇高的、坚忍地、和人类的黑暗面战斗。亢扬文化的力量,鼓励创造的精神,促进进化的速度。他的足迹的步调是一种英雄进行曲。
他的这种精神受过赞扬,但也受过深剧的创伤。欧洲第一次大战时,他以他人道主义者的立场,采取了反战的态度,遭受了他祖国的主持帝国主义战争者的反对,以致不能容于本国,而向瑞士自行追放。这是世界周知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纯全是帝国主义者间争取霸权之战,受难者是人民无产大众,操纵者只是少数隐形在金山银山里的神仙,真真是“神人打仗,凡人遭殃”。罗兰先生虽然并不是具有这种明确的阶级意识,但他靠他的聪慧透悟了战争的本质,竟敢于向着以“国家”为面具的神仙挑战,他的勇气确是把他的贝多芬主义实践了。
出发点虽然不同,而归趣却是同一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的舵手列宁的领导,他在宏涛恶浪当中,把一只破褴的大船,驶向了宏阔的海港。在这种领导下,高尔基先生是分有着光荣的。这光辉照破了当前的浑沌,照彻了人类的前途,使好些可崇敬的人道主义者们更显豁地放开了他们的智慧的眼睛。鲁迅先生是这样,巴比塞先生是这样,罗曼·罗兰先生也是这样。巴比塞和罗曼·罗兰先生都曾以巡礼者的态度,先后访问过新兴的苏联,而成为了叡哲的光明的宣传使。虽然高尔基先生是由黑土层钻出,而其它三先生是由表层钻入黑土,但他们从黑土中又迸出了苗条,在我们一样是值得追随的领导者。大抵的文艺工作者都出身于表层,我们能随着领导者向黑土钻入,又由黑土钻出,倒是值得夸耀的。
晚年的罗兰先生,尤其在目前的第二次大战发生以后,他的消息和我们隔绝了。听说他又有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成一部分,可惜我还未见到。但我们可以揣想,罗兰先生一定是以反法西斯的立场吹奏着民主胜利的军号的。第一次大战时,先生反对战争,而在这第二次大战便不再有那样的号召了,是这位叡哲者立在反法西斯立场的极明显的保证。
伟大的战士,以79岁的高龄,得到安息了。而且安息在得到了光荣的解放的祖国的国土,这应该是我们对于这位不朽的战士申致庆祝的事。我们固然是受着损失,但我们应该跟踪上去,由自己的努力来补偿这个损失。
附带着我在这儿想追致悼念的是罗兰先生的介绍者敬隐渔先生。敬先生往年在上海天主教的学堂念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创造社的组织。罗兰先生的巨制《若望·克里斯妥夫》(按:现通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他着手翻译出来的。他因而与罗兰先生直接通信,并受着先生的邀请,在北伐期间他到了欧洲。还有值得我们记起的,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去的,也就是敬隐渔先生的功绩。
敬先生是四川人,本是一位弃儿,无名无姓。他被天主堂养育成了人,他的拉丁文和法文,都能自由写作。人很矮小而瘦削,到上海时,我住在民厚南里,每逢星期,他必来我家谈到夜深始去。他的眼神颇凝集而有异样的光辉,我们当时用日本话呼之为“鹃落里”(kyiorori)。他自己说,他懂催眠术,但我们也不曾让他施术过一次。
他到欧洲以后,深受罗兰的诱掖,但不久便因精神失常,被送回了中国。这是北伐以后的事,我当时亡命在日本,也曾经看见他写过一些文章,但后来便渺无下落了。有人说他因失恋而蹈海,我也不知道他的详细的情形。
就这样,当我默祷罗兰先生安息之余,我却由衷地哀悼着我们这位多才的青年作家敬隐渔先生的毁灭。
(一月十八日)
今天展读《人世间》第六号许寿裳先生所写的《亡友鲁迅印象记》,有这样一节:
他又告诉我:罗曼·罗兰读到敬隐渔的法译《阿Q正传》说道,这部讽刺的写实作品是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过阿Q,我永远忘记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因之罗氏写了一封给我的信托创造社转致,而我并没收到。因为那时创造社对我笔战方酣,任意攻击,便把这封信抹煞了。……鲁迅说罢一笑,我听了为之怃然。
许先生叙述得很娓婉,而于措辞之中却严正地寓有春秋褒贬的笔法。鲁迅的“一笑”自然表尽鲁迅的宽大与不念旧恶,而寿裳先生的“怃然”则既悲文物之堙灭,复悯人性之卑劣,真是慨乎其难言了。
不过这个问题却是值得追究的一个问题。
……
我那时候又朝日本去呆了半年回来,敬隐渔落魄在上海,是我劝他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翻译了,并由我介绍到商务出版。因此他和罗兰通信,并得到了罗兰的劝掖与资助而游学法国。
注释:
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0月22日鲁迅逝世后第四天,北鸥译的《东京帝大新闻》。本文原经作者亲自修改,载1936年11月15日出版的《观世界》第一卷第七期。
②《宏大的轮船停泊到了安全的海港》1945年1月8日,最初发表于1945年1月重庆《文学新报》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后收入《郭沫若全集》第19卷,512-513页。
③《和平之光——罗曼·罗兰挽歌》初载1945年3月25日《新华日报》,注为1945年3月3日作。后《民主与科学》等刊物转载,文字上略变动。收《郭沫若全集》第2卷,70-71页。
④语见《若望·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载1926年《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
⑤最初发表于1945年3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原题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悼念罗曼·罗兰》。收入《郭沫若全集》第19卷,531-532页,改为《罗曼·罗兰悼词》。
⑥《伟大的战士,安息吧!——悼念罗曼·罗兰》,《文艺杂志》第1期,1945年5月25日。
⑦《一封信的问题》,1947年10月上海《人世间》月刊复刊号第二卷第一期,《郭沫若全集》第20卷,2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8月。
茅盾论罗曼·罗兰
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发聋振聩”。……所谓大勇主义是罗曼·罗兰先说起,罗曼·罗兰也是个文豪。
从冷酷的客观主义解放到冷烈的主观主义,实是文学的一步前进,新浪漫主义想综合的表现人生的企图虽然在戏曲没有得到大成绩,在小说一面已经大放光明。这是罗兰(Romain Rolland)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
罗兰的大著“Jean Christophe”(即《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的新浪漫主义的代表,罗兰自称他这部书中的英雄的思想和生活好比是一条河,一切的人生观都依次在他生平中经过。英国文学家Gilbert Cannan称他这本书好比一条大桥,驾通19世纪的思想到20世纪的思想。一切19世纪的思想都集合拢来以为书中英雄(Jean Christophe)跳到将来的出发点。书中的英雄是个极好真理的人。不问环境如何,不问自身以及一己的性命,所知的只是真理。他书中打破了德法的疆界,既然德法的疆界可以打破,自然一切疆界都可打破。书中说的真理都是普遍的真理,书中Jean Christophe灵魂的冒险便是一切人类灵魂的冒险,欲摆脱过去的专制,服务于将来。
罗兰在他原书第七卷的序上说:“我要空气,我要对不卫生的文明反抗。”他这部书正和尼采的Zarathustra一样,“道着一切人却不曾道着一个人”,他这部新浪漫主义的大著作表现过去,表现现在,并开示将来给我们看。正如Eucken(倭铿,德国哲学家)重新说明人类历史上的生活,告诉我们人类生活的真价值,我们从了他可以得到灵魂安适的门。
新浪漫主义现在主要的趋势光景可以拿罗兰做个代表了,不过到底难说一定是如此的形色。我们要晓得浪漫的精神常是革命的解放的创新的。19世纪初文学上浪漫主义的兴起,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示。这种精神,无论在思想界在文学界都是得之则有进步有生气,中国实在连真真的浪漫文学都不曾有过,一向跼躅于好古主义的下面,浪漫精神缺乏得很。
法国大文豪罗兰在战后的著作有一本剧本唤做“Lilut”的,出版已久;这篇是讽刺剧,多讽刺欧洲各国的外交政策,而且也高唱非战的论调。这是已有英译的了。另有一本论文集,是紧接《超于战争》(Adove the Battle)那本中的论文之后的几篇论文,唤做《前驱》的,也有英译本了。
现在所要讲的,却是罗兰所作的诗体小说,唤做“Pierre to Lucie”这本小册子里,讲巴黎的两个儿童虽在不断的死的迫脅底下生活着,而到底能够发挥他们的浪漫理想,达到爱情的结合。罗兰自从做了“Jean Christophe”以后,虽争做了好几种别的有力动人的小说和剧本,但总要算这一佳篇是可以继续“Jean Christophe”,充着同一理想,有同一的面目。
他的那部“Iilut”自然很有人称赞他,但法国人诋毁他的,也很不少,理由是:这种讽刺的格调把罗兰描写美好天真的本领抹倒,徒见其粗直了。
罗兰(Romain Rolland)的小说比较的近出的,在“Pierreet Luee”之后,有一部小说,名“Clerambault”(或全 名是 Clevambault:Histoire D'une Conscience Libre Pendantia Cluerre战前之思想自由史),这也是一部鼓吹式的小说,倒有点和Liluli相近,只是艺术上比Liluli更完备罢了。书中的主人翁——Clerambault——初迷于宗教的爱国的偏说,自告奋勇去投军队,战场上的目睹惨状——其子之死——觉悟而回。罗兰在这本书中,虽然一面鼓吹非战主文,一面也很用心艺术上的完美。除开主人翁外,女角如Roeime——其女——及其妻,都创造得极有神采。本来一本小说中要同时保留“艺术的美”与“主义的鼓吹”两不同之点是很难的,罗兰在这本书中总算把难关通过一半。
罗兰所著大本小说不很多,除“Jean-Christophe”——原本七卷,英译四本——早在20世纪初出版外,有Colas Breugnon-Burgundian一本,剧本有The Fourteeth of July及Danton等数篇:有一本在《战争之上》乃是他在大战后所做的短篇论文以及公开的书札全集,不是小说。我在本栏第五条已说明。
新近出版的关于罗曼·罗兰的书,有两种,一是法人J.J.Touve的Romain Rolland,Virant;一本是奥人刺外西(Stefan Zwoig)所著“Roimain Rollang,dermann und das werk”,前书没有看见,也没有听人说起,不敢乱介绍;后书却已见过英报上介绍的话,现在写些大意吧。他这部书是罗兰精神发展的“一幅地图”,并且评述他的著作直到最近出的Cleram-bauit可算是罗兰研究的最有价值的著作。此书本用德文写的,然近据张崧年君给我的信,说这部书已有英译了,便是那Clerambauit(请务看本栏之十五条的介绍)也已有英译。
刺外西是奥国著名文学家。1917年做了一篇北战剧本Jeremias,极受罗曼·罗兰倾倒。做了一篇极长的批评登在Caemobium评论上。这篇评论极长,并且把刺外西原著抄上不少,可作一本缩节的Jeremais看,这篇评论后来又收入他的《前驱》内。
19世纪后半,因着自然主义的兴起,无产阶级生活乃始成为多数作者汲取题材的泉源。自然主义的创始者,法国的左拉(Zola),作了一巨册的《劳动者》,分明就是无产阶级生活描写的“圣书”。可是此时尚没有人将这种显然异于往者的文艺题一个名——一个便于号召的口号。据我所知,那是法国的批评家罗曼·罗兰(R.Rolland)首先题了一个名字叫做“民众艺术”。他批评法国画家弥爱(Millet)的田家风物的作品,就说这是民众艺术——艺术上的新运动。
然而实际上,在19世纪后半,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真正杰作——就是能够表现无产阶级的灵魂,确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喊声的,究竟并不多见。最值得我们称赞的,大概只有俄国的小说家高尔基(Gorky)罢。这位小说家,这位曾在伏尔加河轮船上做过侍役,曾在各处做过苦工的小说家,是第一个把无产阶级所受的痛苦真切地写出来,第一个把无产阶级灵魂的伟大无伪饰无夸张地表现出来,第一个把无产阶级所负的巨大的使命明白地指出来给全世界人看!我们仔细地无误会地考察过高尔基的作品之后,总该觉得像高尔基那样的无产阶级生活描写的文学,其理论,其目的,都有些不同于罗兰所呼号的“民众艺术”。原来罗曼·罗兰的民众艺术,究其极不过是有产阶级知识界的一种乌托邦思想而已。他空洞的说“为民众的,是民众的”,才是民众艺术,岂不是刚和民治主义者所欣欣乐道的For the people,of the people(英语。意即为了民众,属于民众。)的政治为同一徒有美名么?在我们这世界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我们如果承认过去及现在的世界是由所谓资产阶级支配统治的,我们如果没有方法否认过去及现在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独尊的社会里的孵化品,是为了拥护他们治者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我们如果也承认那一向被骗着而认为尊严神圣自由独立的艺术,实际上也不过是治者阶级保持其权威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该也想到所谓艺术上的新运动——如罗曼·罗兰所称道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性质了!我们不能不说“民众艺术”这个名词是欠妥的,是不明瞭的,是乌托邦式的。我们要为高尔基一派的文艺起一个名儿,我们要明白指出这一派文艺的特性,倾向,乃至其使命,我们便不能不抛弃了温和性的“民众艺术”这名儿,而换了一个头角峥嵘,须眉毕露的名儿,——这便是所谓“无产阶级艺术”。
和平主义的反战争的作品可以举罗曼·罗兰的《克莱郎鲍尔》(又译为《格荣昂波》1920年出版)为例。罗兰先生自称爱说“良心话”的,这小说不妨称为反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的良心话。此外属于第二类第三类的“和平主义”的战争文学,则连罗兰的“良心话”都够不上,只是嗜血的屠伯们的半个笑脸。
我以为现今应当表演的,是罗曼·罗兰的暴露帝国主义战争内幕的剧本“Liluli”(《里吕里》,发表于1919年的反战剧。作者采取喜笑怒骂与漫画的手法,鞭挞一切战争——引者注),不过“女青年会四楼的万国艺术剧院”之类大概不会喜欢这辛辣的现代名剧的。
自来的文学作品,粗粗可分为历史的,当代现实的,和幻想的(灵怪变异)三类。……
至于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我所爱读的范围就很大了:……但是同时代人的作品如果意图歪曲现实,或只是供个人消遣,那就不是我所愿意聆教的了。
同样,我也抱了这见解去读当代外国人的作品:高尔基和其他苏联有名的作家,巴比塞、萧伯纳、德莱塞——也曾醉心于罗曼·罗兰。
报载罗曼·罗兰逝世,这是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法兰西人民的一个莫可补救的损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曼·罗兰对于那些屠杀人类,毁灭文明的战争的罪犯者的控诉,曾是所有这一切正义呼声中之最响亮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西欧各民族的文化界人士都为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宣传所蒙蔽,“各为其国”地做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帮凶的时候,第一个看清了那战争的本质的,清醒地发出良心的呼声的,是罗曼·罗兰!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在全世界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创人类新历史的伟绩充满了偏见、成见,怀疑与恶意的时候,罗曼·罗兰又是西欧文化界权威的发出正义的呼声的第一人!
他的如椽的巨笔曾经暴露了一切在伪装之下的丑恶和罪行,曾经鞭策了在历史重荷下的人民的惰性和良心的麻木,也曾经预言了人的世纪的光明灿烂的生活,他给与怯弱者以勇气,悲观者以希望,他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精神上的鼓励和指导是不可限量的。
从法西斯铁蹄下刚解放出来的新生的法兰西民族,正需要它民族的最伟大的老战士继续作引路的灯塔;在斗争的烈火中前仆后继的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人民,也正需要这位人类所共宝的老战士继续给予力量;然而,79岁高龄的文化权威竟在这时候离开了我们了。全世界人民对于这一巨大损失的哀悼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可是,我相信,所有反法西斯的人民一定都明白:哀悼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战士不能以眼泪。这一定要以战斗!从地球上杜绝法西斯细菌,实现全世界的新的民主主义,这才是所以哀悼之道,而这也是我们这位逝世的伟大的思想导师所诏示的!

1944年最后那一天将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反法西斯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罗曼·罗兰,是在12月30日逝世的。
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者群,罗曼·罗兰不是一个生疏的名氏,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的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著名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转辗借得一读为荣幸。
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我们这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由敬隐渔君译为法文而在法国出版时,罗曼·罗兰读了以后曾是如何感叹而惊喜的;当《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兄弟们宣言》的寥寥数语中,给我们以多么大的鼓励。那时我们正在大革命的前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淤血堆中挖个窟窿透口空气的千千万万争民主,求光明的青年们,看到罗曼·罗兰对我们的号召:“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蒙、懒惰、迷信和野蛮。我是附顺前者的。无论他们是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争民主,求光明的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坚强了信心了。
我们也还记得:当“五四”初期,思想界还没有个中心的时候,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求启示,曾因探索“新浪漫主义”的内容而在若干文化工作者群中涌起了研究罗曼·罗兰的热心:在话剧运动的初期,罗曼·罗兰的“民众剧”的理想也曾被提出而讨论,田汉先生曾经热心地介绍过这一理论。
我们现在不但有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还有《革命戏剧》的大部分的译本,(罗曼·罗兰自称其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曰革命戏剧),有《葛莱郎波》的译本(?)也还有兹怀格的《罗曼·罗兰传》的译本。在当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中,我们可以说,除了高尔基以及若干苏联作家而外,罗曼·罗兰是和萧伯纳,德莱塞,纪德,等等同为我们热心研究的对象。而我们对于罗曼·罗兰的热心研究更有其特殊的理由,即因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他那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发表的《精神独立宣言》,是他的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写的反战论文的结集《超于混战以上》。而也因为在1932、1933年顷,法西斯的毒焰在全世界高扬的时候,罗曼·罗兰是国际文化界中的反法西斯与保卫世界文化的立在阵头的战士。
现在,正当法兰西获得解放而法西斯强盗的末日即将到来时,罗曼·罗兰——这位反法西斯的巨人和老战士却以79的高龄谢世了。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人民的胜利于今是确定的了,然而艰巨的工作还在前面。从军事上、政治上消灭了法西斯以后,还得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扫荡法西斯以及法西斯的毒瘤,这一工作不见得比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轻便些。我们在这时期特别需要罗曼·罗兰。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全世界,不但法兰西——的损失之大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争的第八年,在向前奋斗以求民主政治真正实现的今天,对于这一位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的逝世,不仅是哀悼就算完了事的。我们的处境也许比西欧的同志更为严重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也许比西欧的同志们所面对的,更为艰巨些,而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必讳言),比起西欧的同志来,也还觉得薄弱些的。然而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从“五四”以来的思想斗争的经验来的,是从鲁迅先生的光荣的业绩里来的,而也是从世界的反法西斯文化前辈的努力与其辉煌的事业而来的。
在今天,我们文化人,正经历着思想上的绝大的苦闷,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绝大的考验。今天,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正在展开,但也是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代。今天,相同于罗曼·罗兰在上次大战以后的“摸索和徬徨”的情绪,在我们文化人中,恐怕也还是相当普遍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哀悼和纪念之心,来追踪罗曼·罗兰一生所经过的思想历程,将能激发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的信心。
罗曼·罗兰所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当他70岁时,他感谢苏联人民对他70大寿的庆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70岁。这好像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经过苦痛而后快乐。’经过了70年来的战斗与劳苦互相更迭的长途旅程,我才到达了你们所建造着的‘快乐’,这世界人类的新社会。……”(用戈宝权的译文)。而在另一时,他又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你可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年代的深处来的?我是从消灭了的巴黎公社,从1870年惨酷的普法战争的时期来的。……我的来处是在战争期以及在革命期两度被征服过的法兰西,是当我的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屈服过的法兰西。”(用戈宝权译文)但是,时代和“来处”,并不能把罗曼·罗兰压在怀疑和悲观的深渊,也不能把他驱入“象牙之塔”,——虽则他早年的环境和教养是很有这可能的。当他毕业于高等师范,游学罗马与德国之后,曾经深受托尔斯泰和华格纳的影响。托尔斯泰的充满了热情的呼声“我们怎么办呢?”曾经使他深受感动。他和托尔斯泰的通信在他那时期是他的生活史上一大事件。“托尔斯泰帮我找到了生活的道路”,他这样说:从此他立下了为人民——为人类服务的伟大决心。
然而,人民的道路,——人类的历史的道路,是向那一个方向去的?此去又该经过怎样必不可少的步骤呢?这些问题,当时的罗曼·罗兰是有他自己的见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可说是他的这见解的形象化,那么,后来的《精神独立宣言》便是详细的注脚,抽象的理论。《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创造就是消灭死亡》,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淋漓痛快地发挥了的。克利斯朵夫是从窒息的、毒害的、僭妄的优秀阶级文化中钻出头来的英雄,——以创造战胜一切丑恶与危害的大智大勇的英雄;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那时是孤独的。我在一个精神上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的毒害的思想,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有着相当高卓的灵魂以便有说话的权利,有着相当雄壮的声音以便令人听得真切,这个主人翁,我耐心地造成了。”(用戈宝权译文)
从《约翰·克利斯朵夫》(1912年完成)到《超于混战之上》,罗曼·罗兰是从“创造即欢乐”的说教者走到了实际斗争的战士的阵头了,但在基本思想上他还是始终一贯的,这就说明了后来他在“光明社”何以会跟巴比塞意见相左。
直到此时为止,罗曼·罗兰的基本思想是个人主义,——或者也可称为新英雄主义。他认为“自由而阔大,坚毅的个人主义,便是人的最高价值,人的前锋”,而《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这理想的化身。罗曼·罗兰在《精神独立宣言》中表示:此种精神的个人主义是独立的,不附属于任何民族,不隶属于任何党派,保持着超利害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的观象台,以清明的眼光照耀着人类的前途。他更进一步说,这样的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可与人民的战士携手而且为其引路。
这样的“理想”,也许是“美丽”的,不幸面对着现实之时,却碰了钉子。1920——1927年间,正是罗曼·罗兰的“摸索和徬徨的年代”。他回到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又向甘地主义伸出乞援的手。但是,大智大勇大仁的罗曼·罗兰终于突过云阵,“向过去告别”,“从巴黎走到了莫斯科”。精神的个人主义的罗曼·罗兰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士。
1927年以后,罗曼·罗兰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他的几部著作来表示。这几部著作正可视为他的思想历程的里程碑。
《向过去告别》论文集出版于1931年,在这里他批判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宣告他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用他自己的话,这是“已经毁了身后的桥梁了,不管我后面有桥还是没有桥,我永不再回头了。”
《保卫新世界》论文集出版于1932年。
《动人的灵魂》(长篇小说)第五、六两卷《诞生》完成于1933年。这一部共六卷的巨著,开始写于1922年,初成第一卷《安娜德与西维尔》,及第二卷《夏天》,中经间歇,1926年完成第三卷《母与子》,又隔五年,那是1932年了,成第四卷《一个世界的死亡》,翌年完成最后两卷(五与六),均题为《诞生》。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同,这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前后亦跨十年,——1922到1933年。然而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作的十年间所不同者,这后十年正是罗曼·罗兰所自称为“苦斗十五年”的重要阶段,如果前十年可称为罗曼·罗兰前期思想形成的阶段。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其总结,那么,后十年便可说是罗曼·罗兰后期思想发展的阶段。而《动人的灵魂》最后三卷便是他“摸索”而合于大道的宣告。
安娜德最初还是“克利斯朵夫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了幻灭以后,她渐渐改变了,终于在她的儿子马尔克因为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谋杀以后,她坚决地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而踏上儿子所走的路——人民大众的历史的道路。她说:“没有力量的白旗染上了红血,已经成为红旗了;这旗帜将为千百万人所有,安娜德将拿起这旗帜与千百万人一起继续去战斗!”而罗曼·罗兰是和千百万人一起去战斗了,他在1932年以后成为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这样,我们在长篇小说《动人的灵魂》中看到了罗曼·罗兰早期思想的继续,也看到了《摸索与徬徨》,最后,又看到了自我批判的《向过去告别》,大踏步走向新的《诞生》。
怎样从一个个人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足足走了70年的长途。光是这一点坚韧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经值得我们万分景仰了。他这长途不是没有痛苦的,在他写给他夫人的信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我的累累的创伤,这就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明着前进的一步。”这就是罗曼·罗兰之所以伟大。
在某些点上说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自称的“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有些相仿么?50年来的中国,当然和1870——1920年的法兰西不同,但五十年来的世界不就是罗曼·罗兰所“摸索”的时期那一个世界么?而时代逼迫着我们回答“我们该怎么办”,不更紧急于罗曼·罗兰的1922——1927年的当时么?
让我们来认真思索这一切,这该是时候了!
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争取民主。而争取民主的首要条件,即是挥起我们的笔杆,反对法西斯的侵略。罗曼·罗兰一生的艰巨的行程给我们榜样,也给我们勇气和信心。为了哀悼和纪念这一位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我们的“摸索和徬徨”——如果还有,不该从此结束了么?《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该读《动人的灵魂》了。
我们相信: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伟大的罗曼·罗兰的逝世,将有无穷的悲哀,对于产生这位巨人的光荣的法兰西民族将永志其敬爱与感谢,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大众的损失;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将以善于学习罗曼·罗兰作为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向过去告别!”
让我们把这一句话作为座右铭罢!

大概说来,欧洲反法西文学可说是近十年来欧洲文坛的主流。最优秀的作家都贡献了他们的心力。一代的大师,如罗曼·罗兰、纪德、托马斯· 曼·亨利·曼(两人皆德国流亡作家)以及曾在西班牙内战时期参加“国际纵队”流过血的青年作家,保持了欧洲文学的元气。
……
在此次大战以前,巴黎曾经是反法西文学的一个活动中心。国际反法西保卫世界文化的大会,是在巴黎开的,“德国流亡作家协会”也在巴黎。巴比塞、罗曼·罗兰、纪德,这些光荣的名字,在法西斯黑潮正向全世界弥漫的年头,曾经怎样地给人以光明,希望和勇气!

我个人有这样的感想:如果把鲁迅和罗曼·罗兰相比较,很有相同之处。罗曼·罗兰70岁时,曾经为了答谢苏联人民对他的庆祝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70岁,这好像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罗曼·罗兰在解释他“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曾经沉痛地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度过的。同样地,鲁迅也经验过“寂寞和空虚”的重压,而鲁迅的“旅程”好像比罗曼·罗兰的更为艰苦,因为他不但背负着三千年封建古国的“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而且还得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的社会所形成的“买办文化”作斗争。

“现代派”和五十多年前曾一度使用的“新浪漫主义”,稍稍有点区别,当时使用“新浪漫主义”这个术语的人们把初期象征派和罗曼·罗兰早期作品都作为“新浪漫主义”来看待的。

注释:
①《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1920年1月10日《东方杂志》17卷1号,《茅盾全集》第18卷,8页。
②《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1920年9月15日《改造》3卷1号,《茅盾全集》第18卷,42页。
③《罗兰(Romain Rolland)的近作》,1921年《小说月报》12卷1期《海外文坛消息》。
④《罗兰的最近著作》,1921年《小说月报》12卷4期《海外文坛消息》。
⑤《两本研究罗曼·罗兰的书》,1921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7期《海外文坛消息》。
⑥《论无产阶级艺术》,1925年5月2日、17日、31日,10月24日《文学周报》172、173、175、176期,《茅盾全集》第18卷,500-501页。
⑦《战争小说论》,1931年7月26日《文艺新闻》19号,《茅盾全集》第19卷,228页。
⑧《非战的戏剧》,1935年12月26日《立报·言林》,《茅盾全集》第20卷,584页。
⑨《“爱读的书”》,1943年10月收入《茅盾全集》,第22卷,448页。





(责任编辑:王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