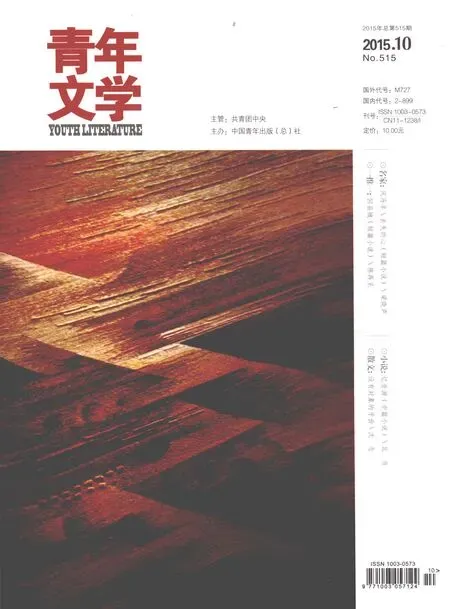我要去四川
⊙ 文 / 张 敦
我要去四川
⊙ 文 / 张 敦
在我老家那边,每村都有几个来自四川的女人。我娘就是其中之一。她们被人贩子骗到此地,以几千元的价格“卖”给光棍汉。我们那里的人都很善良,对待这些女人十分友好,尤其是像我爹那样的老光棍,简直如获至宝,指望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男耕女织,生儿育女,平平淡淡地老死一生。问题在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女人“并不安分”,总有人出其不意地逃走。
也难怪,光棍之所以会成为光棍,无外乎三点:一是早些年家里阶级成分高,无人敢嫁,等阶级成分不足为惧,早已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龄青年;二是家里穷,没钱盖房子,一大家人挤在风雨飘摇的老屋里,随时有可能房倒屋塌,同归于尽;三是长得太丑,甚至身有残疾,总是遭人嘲弄,天长日久,精神也变得不太正常,与傻子疯子归为一类;至于真正的傻子疯子,更不用提了。
我爹的情况属于第二种。
被拐卖来的四川女人嫁给这些老光棍,自然是不满意的。但村里人认为,她们应该知足。据说,她们的老家山穷水恶,更加贫苦,吃饭穿衣都是问题。命运安排,她们嫁到这里,虽然丈夫不尽如人意,但至少不愁吃喝。有馒头吃,有小米粥喝,这就很不错了。她们舍弃这样的生活,义无反顾地逃走,简直是昏了头。
每有四川女人逃走,村子的气氛就一下子紧张起来,犹如战争来临。大喇叭轰然响起,号召所有青年劳力统统放下锄头或铁锹,赶紧骑车子追。一时间,人们闻风而动,纷纷跑到村外的公路上。青壮的男人们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绝尘而去。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衡水市的火车站。路途遥远,真正骑到目的地的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中途掉队,摸着生疼的屁股站在路边休息,然后慢慢地骑回家来。只有当事人,也就是丢了媳妇的男人,一马当先,勇往直前,本族兄弟紧随其后。留在村里的人翘首以盼,等逃走的女人被带回来。通常是后半夜,男人的号叫和女人的哭喊骤然响起,大家纷纷起身,走出家门看个究竟。逃走的女人又回到村里,这是最好的结果。当着村人的面,丈夫不能显得太窝囊,狠狠地踹她几脚。女人哭得厉害。
丈夫边打边问:“以后还敢不敢跑了?”
女人回答:“不跑了,再也不跑了。”
女人浓重的四川口音让村人哈哈大笑,大家心满意足,回家睡觉。
那时我是小孩子,很爱看这样的热闹,还不知道自己的娘也是个四川女人。
不是所有逃走的女人都能被抓回来,也有逃跑成功的,但极少。究其原因,无非是她们人地两生,尤其对周边地理情况一无所知;另外,她们的智商也令人担忧,好容易跑出村子,只知道一鼓作气地奔往衡水市火车站,不懂得改变路线,另辟蹊径。如此一根筋的结果,只能是被风风火火赶到的丈夫一举抓获。那成功的几个,也不是因为聪明,恰恰是因为笨过了头,走错了路,南辕北辙,稀里糊涂地逃过了追捕。既然人家远走高飞,那我们又如何得知她们的逃跑方式呢?这就要说到我那些乡亲们的执着精神,真比得上夸父逐日。他们追到衡水市火车站,没找到人,毅然踏上火车,一直追,追到女人的老家——四川。
有一对哥俩就是这么干的。女人是弟弟的媳妇。哥俩很聪明,下火车后理发刮脸,又买了两身西服,打扮得光彩照人,拎着两大包礼物,来到女人家。追捕变成了相亲。弟弟那从未谋面的岳父岳母收下礼物,又要了礼金,就让女人跟他们回来了。这一回来,女人再也没跑过。有人问她:“当初你是怎么跑的,那么多人都没追上?”
“瞎跑呗,先跑到公路上,运气好,拦下一辆车,没想到搞反了方向,辗转去了山东德州。”
大家听完快乐地大笑。
还有一些逃走的女人去而复返。她们回到家乡,父母并不疼爱,相反无比憎恶,不给好脸色看,嫁人找不到好人家,只能嫁给当地穷凶极恶的老光棍,条件还不如原来的丈夫,权衡利弊,只好原路逃回河北。
可惜,这样美好的事情少之又少,大多数逃走的四川女人一去不回,就像我娘那样。
我娘经人贩子介绍认识了我爹。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河北人,能走到一起,也算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爹人不丑,身体也算强壮,他成为光棍的原因只有一个,穷。穷归穷,媳妇还是要娶的。我爷爷很有魄力,举债买下两个四川女人,分别许配给我爹和我大爷。媳妇有了,但房子还是泡影,一大家人挤在祖辈留下的屋子里,凑合着过日子。一年后,两个女人各自生下一个男孩,又过了一年,她们结伴而逃。
我大娘是个有心计的人,逃走之前,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她顾忌到自己人单势孤,拉我娘入伙。她二人虽是同乡,但此前并不认识,成了妯娌后,常因生活琐事吵架拌嘴,貌似势同水火。这是假象,她们知道,如果她俩表现得亲如姐妹,难免让人有所防备。密谋妥当后,俩人行动起来,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二百多块)。此举非常高明,以至于爹和大爷赶到衡水市火车站后根本没钱买票,只得望火车而叹。
两个媳妇跑掉了,可谓损失惨重。两个娃娃嗷嗷待哺,只能由我奶奶抚养。前年借的债尚未还清,债主纷纷上门,希望爷爷不要因为媳妇跑了就停止还钱。因为没钱,爹和大爷放弃了前往四川的想法,踏踏实实地干活儿,老老实实地还债。那些钱,就当买了两个孩子,也挺好,虽然家庭并不完整,但传宗接代的目的已经达到。
两年之后,我大娘奇迹般出现在院子里。她跑回四川后又嫁了人,那人家穷得更厉害,她考虑再三,只好跑了回来。对于一个失而复得的女人,全家没有责骂,欣然欢迎她的回归。我大爷高兴得几乎疯掉。只有我爹愁眉不展,他问大娘:“嫂子,我媳妇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
“她回去后就嫁人了,男人岁数大,也穷。”
“那她怎么不跑回来?”
“我找她的时候,她肚子里有了孩子,实在不方便往外跑。”
“就算她大着肚子回来,我也不会计较。”
“你们男人我还不清楚,孩子生下来,你能当亲生的看待?”
爹沉默了一会儿,问:“嫂子,你嫁人后没怀孕吧?”

⊙ 朱 个·猫王与栀子花
“怀了,我是生完后才跑回来的,男孩,长得像我。”
我大娘是个诚实的人,她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远在四川,她还有一个儿子,她必须每年回去一趟,看看儿子,要不没法安心生活。我大爷非常大度,答应了妻子的要求。即使不答应,也毫无办法,总不能拿铁链将她拴起来吧。大家都能感受到,有过两次逃跑的经验后,这个女人变得成熟而练达,简直成了精,如果她想再一次逃走,是死活也追不回来的。一年之后,全家拿出所有的积蓄买了车票,她以走亲戚的名义回了四川。大家提心吊胆,担心她会一去不回。过了一个月,她如约归来,带回不少四川土特产,全家皆大欢喜。
大娘回四川前,我爹提出一个要求:“嫂子,你回去后问问我媳妇,什么时候能回河北。”
大娘回来后,给我爹的答复是这样的:“你媳妇生了孩子后又怀了孕,她生了个闺女,希望这次是个男孩。”
我爹十分伤心,不再问任何问题,从此酒量大增,成了全村最能喝的人。
多年之后,我长大成人,常陪爹喝酒。我们坐在大炕上,围着一张小木桌。这小木桌十分古朴,并不常见。爹对此颇为得意,说:“从前你爷爷的爷爷就是在这桌子上喝酒的。”
每人面前放一口大碗,倒满明晃晃的老白干。爹三口干完,全然不顾我的节奏(我得十口干完)。这样的酒,爹能喝三碗。喝到醉意朦胧,他向后倒去,靠在被窝堆上,呼呼大睡。冷不丁地,他醒转过来,放声大哭。吓得我差点把嘴里的酒喷他一脸。他指着我,含混不清地骂:“我操你妈。”
我对娘的印象只有一个镜头——大雨倾盆,院子里一片汪洋,娘发脾气,将一个红色的脸盆扔了出去,溅起一片水花。脸盆在灰黄的背景中那么显眼,雨敲在上面,摇摇晃晃。娘不解气,一把捞起我的身体,扔了出去。我飞行的距离很短,降落在屋檐下,吃了一嘴泥。我哭着爬行,爬向那个脸盆。娘面目模糊,只残存一双冰冷的手。那双手,夹住我的身体,不带一丝温柔。
一岁的孩子,有记忆吗?这段画面莫非是我梦境中的神来之笔?如果是梦,我也应该做得清晰一些,记下娘的样子。当我念到“娘”这个词的时候,脑子里准确地出现她的脸。
我一岁多的时候,奶奶五十五岁,身体还算不错,带两个孩子,也能吃得消。我大娘回归家庭后,自然将自己的孩子从奶奶膝下收回,于是我成了奶奶唯一的孩子,十分受宠。家里的食物简单而匮乏,窝头、小米粥和玉米粥是主食,鸡蛋是最有营养的副食。我的牙齿尚未长全,吃起窝头来多有不便。奶奶代为咀嚼,嚼烂后示意我张嘴。我是个机灵的孩子,赶紧张大嘴巴。奶奶将嚼烂的食物吐入我的嘴里。我稍加搅拌,即可吞咽。这样的情景来自奶奶的讲述,我已经长大,她老得牙齿掉光,什么也嚼不动。
为保证我的营养,奶奶决定每天喂我一个鸡蛋。蛋由几只瘦弱的母鸡生产。每天下午,它们跳出鸡窝,咯咯哒地叫着。奶奶去捡鸡蛋,却发现鸡窝内空空荡荡。多次观察,才发现鸡蛋让我的大娘拿走了。奶奶找她问:“你拿鸡蛋干什么?”
“吃啊!”
“谁吃?”
“你孙子。”
“一天吃一个就够了,你不要都拿走。”
“你孙子吃了,我不吃?你儿子不吃?”
奶奶和我的大娘干了一仗,为我争取来一个鸡蛋。所幸娘走后,我自动断奶,奶奶无须为奶粉发愁。她坚信小米粥可以代替奶水,督促我多喝,喝得肚子老大,一敲嘣嘣地响。
在我成年后的身体上,依然能看到营养不良的童年印迹。我个头中等,尖嘴猴腮。瘦是我的身体永恒的主题。这都无所谓,关键是我相貌丑陋。站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半天也看不到比我更丑的人。我的爹并不丑,也就是说,我的丑来自娘。
奶奶死的时候,我身在石家庄。家里人打来电话,让我回去参加葬礼。开往老家的火车,要到下午五点才能出发。我在上午接到电话,尚有大半天的时间消化这个痛苦的消息。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事。奶奶的死,简直要了我的命,让我痛不欲生。我给最好的朋友打去电话,什么也没说,只是号啕大哭。对方心平气和地等我的哭泣停止。时间过了很久,我还在哭。他只好打断我,让我歇息一下。他一说,我的哭声更加汹涌澎湃。
火车上,我不敢哭得过于放肆,眼泪总是悄无声息地流下来。堂哥在火车站接我,骑摩托车带我回家。乡村路上,我眼泪又流下来。行进的速度很快,眼泪向后飘散。接近胡同,看见高悬的白布,我放声大哭,声音嘶哑。
堂哥说:“还没到家,你等会儿再哭。”
我不听他的,继续哭,跳下摩托车,往家里跑。院子里一片白,戴孝的人都无所事事。我奔进灵堂,扑在奶奶的尸体上,一直哭到半夜。
所有人都来劝我,让我停止哭泣。我十分固执,哭得更加执着。最后,我爹走过来,拎起我的脖领子,在我脸上扇了两巴掌。我终于平静下来,开始询问奶奶临终前的一些情况。他们讲,奶奶在咽气之前提到了我,让我去找娘。奶奶说:“既然有娘,就要找,毕竟是娘。”
这时我的爹在院子里高喊:“找个屁!”
葬礼结束后,我觉得应该跟爹好好谈谈。我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两瓶老白干,和两包花生米。爹洗了两个大碗,家里没有酒杯。我们先干了一碗。如果不喝酒,我和他根本无话可说。就像我们的喉咙里堵着一摊烂泥,只有酒能将其溶化。
爹老了。头发几乎掉光,皱纹纵横,让他的脸四分五裂,嘴唇漆黑,牙不知何时掉了几颗,好在还能嚼花生米。他盯着我,问:“你是不是想去找你娘?”
我点点头。
“想去就去吧。”
“前天你还说去个屁。”
“哈哈,那是说给别人听的。”
“你当初为什么不去找?”
“她跟别人结婚了。”
“你们毕竟是夫妻啊。”
“当年连结婚证都没办,算什么夫妻?”
“那如此说来,我是非法所生?”
“是啊,你就是个黑孩子。”
“你给我点钱,当作路费。”
“钱你自己去挣,我的钱要用来建房子,你看咱家这破房子,要全部拆掉,建新的。”
我和爹住在奶奶留下的老房子里。我爷爷早就死了,他是个老酒鬼,谁也说不清他这辈子总共喝了多少酒。每天清晨,他翻身溜下炕头,在院子里吐几口痰,喝两碗粥,下地干活儿,中午回家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午睡,睡醒了又下地干活儿,晚上再喝顿大的。他这辈子,除了喝酒与干活儿,没有别的事情。严格来说,他算个勤劳的酒鬼,但世人看重结果,对一个庄稼汉来说,为儿子建一座院子就是最大的成功。从这点来讲,爷爷非常失败。我爹没有自己的院子,我大爷本来也没有,但他很争气,在大娘的督促下奋发图强,成了一个优秀的泥瓦匠,为自己建了一座院子。爹很像爷爷,在酒量上,他已经超越了爷爷。他也能当个泥瓦匠,但有一次习惯性地喝多了酒,从房上掉下来,摔断了腿。虽然走路一瘸一拐,但并不妨碍他继续喝酒。他已想通,我大爷确实需要一座院子,人家有媳妇有孩子。而他本人,没有媳妇,儿子远在石家庄,住老房子理所当然。
我爹有过一个机会,娶个媳妇,过上我大爷那样的生活。那女人是邻村的寡妇,年龄与我爹相当,有一个女儿,其年龄与我相当。我爹想和那女人结婚,人家提出一个条件:让你儿子退学,去城市里打工挣钱。
人家自有道理:“你本来没有钱,还要供孩子上学,孩子上完高中,要上大学,这几年光阴,要花多少钱?我女儿早已不上学,能挣钱养家。如此相比,一出一进,我能不计较?”
爹考虑再三,最终拒绝了寡妇的条件。他觉得我上学比他娶媳妇更重要。
当时我正上高中。在我们村,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高中,我的同龄人大多上到小学毕业。我上的是县里最好的高中,考上大学的希望非常大。这是我爹最大的骄傲。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一所很烂的大学。爹很高兴,因为那毕竟是大学啊。大学毕业后,我流落到河北省省会石家庄,过上了打工的生活,钱没挣到,女朋友也没有找到。我的时代与爹的时代大有不同,但我找不到女人的理由没有改变,第一是丑,第二是穷。多么简单干脆的理由,我占全了。
因为上学,我接触过的女孩不算少。我总是装出很开朗的样子,主动与她们打交道,避免被归入性格孤僻的那类人中。为改变自己土里土气的外貌,我想方设法为自己添置一些洋气点的衣服。但我深知,那种来自华北平原的土气已深入我的骨髓,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女孩子中,也有土里土气的人,她们与我合得来,渐渐成为好朋友。我挑选一个模样还过得去的,想发展成为女朋友,却总是“雪拥蓝关马不前”。经过一番思考,我意识到,责任在我。我太过随和,给她们一种憨厚、无害的印象,于是被当成了知心大哥哥,或者可以随便聊天的傻子。她们哪里知道,当我们在充满阳光的教室中谈天说地的时候,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与女孩性交的画面。可惜,直到大学毕业,我仍是处男之身。
我的工作是英语教辅书编辑,跟文化沾边,说起来好听,实际上挣得很少,月工资两千左右。所幸这是石家庄,能勉强养活自己。我在单位附近租房居住,两室一厅的房子,我住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住着一对情侣,经常在午夜时分制造做爱的呻吟声,让我整晚失眠。
奶奶死后,我做了去四川的打算。为了积攒路费,我戒了酒,一日三餐简单随意。在厨房里,我炒了一盘青菜,热了俩馒头。那对情侣中的女孩走过来,她也要准备晚餐。她看见我的青菜,说:“你就吃这个?”我点点头。她说:“来和我们一起吃吧。”于是,我们坐在一起吃饭。他们炒了两个菜,西红柿炒鸡蛋和杏鲍菇炒肉片,味道还可以。我们早晨和晚上各见一面,可谓朝夕相处。他们刚刚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希望我这个已经工作了几年的人传授点经验。
我说:“只要别要求太高,工作不难找。”
“你工资高不高?”
“不高,两千。”
“每月扣除五百块的房租,你还剩一千五,再扣除五百零花,还剩一千,刚够吃饭啊。”
“是啊,刚够吃饭,但我还要攒钱,每月五百。”
“你攒钱干什么?”
“去四川。”
“去旅游吗?”
我说,差不多吧,这是一个梦想。
他们不知道,我的计划是半年之后去四川,看看娘,然后去九寨沟玩一圈。从大娘那里,我拿到了娘的地址。通过查询地图,发现那地方离九寨沟不远。这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远行,意义重大,应该复杂一些,不可随随便便,仓促而回。通过计算,我至少需要三千块钱,才能完成这次旅行。半年,是我攒够三千块钱所需要的时间。我毫无积蓄,还欠着外债——工作总是变动,工资又那么低,不可能有积蓄。每当丢了工作,找到下一份工作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时就需要找朋友借点钱。当然,我没向他们讲这些,作为两个意气风发的毕业生,他们需要的是鼓励。
半年的时间,我没有吃肉,在单位也格外老实,做事小心翼翼,生怕被开除。有一天,在热闹的大街上,我找到一家银行的自动柜员机,把卡塞进去,查询余额,三千多。我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脑子里想着即将到来的行程。我突然想到,该不该给娘打个电话,电话号码我是有的,那不是娘家的电话,而是当地村长家的,我要打过去,拜托人家把娘找来。这个问题需要找人商量。我给爹打电话,他说:“你随便吧,想打就打,不想打就不打,不用问我。”
“你打过没有?”
“一开始想打,但最后忍住了,没打。”
“你不想她吗?”
“不想,我恨她,我打电话,除了骂她两句,没什么好说的。”
“爹,想了多年,我想明白了,这事不能怪娘,大家都有责任。”
“你放屁,老子有什么责任!”
想了几天,我决定给娘打个电话。那是个星期天的中午,吃过饭,我躺在床上无事可做。电话通了,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浓重的四川话。我说:“你好,我找李铁兰。”
这个坚硬的名字属于我娘。多年来,我首次对人说出娘的名字。一时间,这个名字陌生起来,仿佛是我凭空捏造。
她好像没听清,问:“你找谁?”
我只好重复说:“我找李铁兰。”
她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村里有这个人,你是谁?”
这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我想了想,说:“我是她亲戚。”
“那就过十分钟再打过来吧,我去找她。”
“好的,谢谢你。”
这十分钟无比漫长。我焦躁地翻身下床,来回踱步。我终于再次拨通电话,马上有人接听。我小心翼翼地说:“喂——”
那边传来女人的声音,问:“你是谁?”
“您是李铁兰吗?”
“是啊。”
我突然想到了死去的奶奶,眼泪不停滴落,声音颤抖。
“我是牛力。”
“啊,你是牛牛?”
牛牛是我的乳名,据说是她起的。
“嗯,我是牛牛。”
“你真是牛牛?”
“是的,我真的是牛牛。”
“嗯,嗯,好,好。”
“过几天我去看你。”
“嗯,嗯,好,好。“
我的喉咙渐渐干枯,只剩波澜不惊的只言片语。我问:“娘,你过得好吗?”娘的回答千篇一律:“嗯,嗯,好,好。”
话已说尽,最后是半分钟的沉默。我首先提出挂断电话,娘说好。她那标准的四川口音不同于任何一个女人,总让我想起倾盆的暴雨。雨点击打着红色的脸盆。
我的四川之行即将开始。我先在单位请好假,然后打点行装,回到老家。老家的院子,是我正式出发的地方。我要沿着当年娘逃走的路线前行。爹要重建老屋,买来砖瓦和水泥,将胡同堵得水泄不通。再过些日子,他会带领村里的建筑队拆掉老屋,再把这些砖瓦和水泥堆砌成新房。他一瘸一拐地带我房前屋后转了几圈。这几年,村里多了很多楼房,大多是二层建筑,也有的是三层(属于做生意的暴发户)。爹要建的是简单的平房,像大多数人家那样,只要建成,就淹没在这村庄丑陋的建筑群里。而此时,我发现,在左邻右舍新房的映衬下,老屋卓尔不群,苍凉而肃穆。
“咱家新房怎么建,你设计一下。”爹说。他在开玩笑,新房的样式村里有无数样本,家家都一个样,就连建楼房的人家也不会推陈出新,将两排平房垂直罗列,就是楼房了。爹对新房的预期十分乐观,但我的话将他拉回现实:“你别指望新房建得多么漂亮,只要结实就行了。”爹不爱听,抬起那条瘸腿,猛踢过来。
临走之前的晚上,爹为我饯行。下酒菜来自村里的超市,凉菜、香肠和烧鸡,没有热菜,爹懒得做,我亲自下厨,弄出一盘大葱炒鸡蛋。刚要开喝,爹说:“去把你大爷叫过来。”我只好起身,踏着暮色穿过胡同,来到大爷家。红砖瓦房随着夜色的降临暗淡下去,我仿佛看到了爹新房的大致模样。偏房亮着灯,大爷正在做饭。我喊他一声,他回过头来,手里握着菜刀。大爷也是酒鬼,无力拒绝我的邀请,但出门之前,他必须征得大娘的同意。他放下菜刀,从偏房出来,登上台阶,进入大娘所在的北房。不一会儿,大娘闪身站在门口,请我进屋说话。
“不进屋了,我爸请我大爷过去喝酒。”我从未进过这个四川女人的北房。
“这是喝的什么酒?”大娘问。
大爷的脑袋从她背后钻出来:“喝酒就是喝酒,你不用问!”
我说:“我明天去四川,找我娘,这顿酒是饯行酒。”
大娘说:“真要去了啊,车票买了吗?几点的火车?”
我说:“大娘,当年你们跑的时候,做的是哪列火车?”
没等大娘回答,大爷跃下台阶,扯动我的胳膊,将我带离他家的院子。他说:“亏你小子还上过学,问你大娘这个干什么?”
我说:“打听清楚了,我就去坐那列火车。”
大爷说:“你坐个屁!”
与爹相比,大爷的性情还算温和,如果不是被我戳中痛处,也不会口吐脏话。当年大娘的出逃,就是大爷的痛处。他满载一腔怨气,坐在老屋的炕上,嘴里不紧不慢地数落我,说我的书都白念了,三八赶集,四六不懂。我最烦俗语,每听一句,就被恶心出一身鸡皮疙瘩。为了让大爷闭嘴,我端起大碗,说:“大爷,你别说了,我敬你一碗。”大爷说:“好吧,喝一大口,先别干。”爹问怎么回事,大爷又说一番,没想到,爹对此事毫不介意,哈哈大笑,表现出一个老光棍应有的大度与豪迈。
“孩子没有恶意,你别往心里去。”
听到我爹的规劝,我大爷往日的温和重新附身,闷头又灌下一大口白酒。
爹问大爷:“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大爷说:“牛牛要去四川,为他饯行。”
“错,你错了,去四川不值得饯行,就当旅游,没什么大不了的。叫你来喝酒,是因为——这是咱们最后一次在这屋里喝酒了。”
听爹这么一说,我们不约而同抬头观看。黑乎乎的屋顶,一盏多年没有擦过、长满黑毛的电灯泡。墙壁漆黑,部分墙皮脱落,露出暗黄的土坯。一张古旧的饭橱,油漆剥落,由暗红色转变为灰色。墙角蹲着的煤炉,凭借一身土色,几乎隐形。地面的青砖坑坑洼洼,多日未扫,满是花生皮,凸出之处磨得锃亮,泛着暗光,像夜色中大雨过后的院子。
仨人沉默半晌,爹率先出声:“这破房子,早该拆。”大爷不置可否地点头,我却说:“说说从前的事吧。”
“从前的事有什么好说的。”爹很不耐烦。
“说说我娘,她是怎么跑的,你们是怎么追的?”
“骑车子跑百十里地,差点累死,没意思,说个有意思的——那时候你娘跟你大娘同时来到咱家,我跟你大爷该娶哪个,这是个问题。相比之下,你大娘好看点,我跟你大爷都想娶她。眼看我们哥俩要打架,你爷爷出来主持公道,说抓阄吧,让老天爷做主。结果你是知道的,你爹我的手气不好。”
爹和大爷快乐地笑起来,大爷感慨万千地表示,这就是命,我们必须心服口服。随后,兄弟俩的矛头对准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对象。
“这个问题我仔细考虑过,主要是因为我遗传了爹的穷和娘的丑。”
“去你妈的,老子好的地方你不遗传。”
“老二,听说邻村有买越南媳妇的,咱给牛牛买一个,行吧牛牛?咱娶个越南媳妇,生个混血儿。”
“嗯,如果牛牛同意,老子就给他买一个。”
还未等我做出否定的回答,外面传来脚步声,大娘从漆黑一团的夜色中钻了出来。爹连忙打招呼,请她入席。她摆手拒绝,倚着门框,向我发问:“你明天真要去四川?”我点点头。她又问:“真要去看你娘?”我再次点头。她突然哭了,说:“你最好不要去。”这来路不明的哭泣和话语让人迷惑。
没等我们询问,大娘说出了答案,她一口气说完,显然早已打好腹稿,更要命的是,她放弃了业已纯熟的河北口音,操练起四川话,很明显,这种方言让她的表达游刃有余,同时给我带来不小的听觉障碍,事后我想,让大家听不清,恐怕也是她讲四川话的目的之一。这件事,明白大概意思即可,没必要听得太清楚。
“牛牛的娘早就死了。死了有二十多年了吧。那年我要回河北,去找她,劝她一起回来,她正怀孕。第二年我回到四川,听说她已经死了,难产,大人孩子一起死的,很惨。怕你们伤心,这事我就瞒下了。我给牛牛的电话和地址是假的,那个李铁兰,是我表妹,我拜托她接牛牛的电话。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牛牛好,好让牛牛觉得,他还有个娘活在这世上。”
大娘说完,快速隐身于黑暗之中。爹盯着我,端起碗,默默喝下一碗白酒。他的手来到我的肩头,用力按住。我还在回味大娘的话,又想起打过的那个电话,然后学着爹的样子,默默喝起白酒,半碗下肚,喉咙像挨了一拳头,一口喷了出来。
炕上飘起一阵酒雨。
爹和大爷在雨中坐着,沉默无语。我的眼泪被呛了出来,赶紧擦去,以免他们误会。冷不丁地,我想到了奶奶,眼泪又理直气壮地滴落下来。
爹开始摇头,说:“不对,不对,我不相信你大娘这么好心。哥,你信吗?”
大爷的脑袋也摇起来,表示不信:“这娘们儿跟我过了二十多年,我是最了解她的人,如果她真有这么好心,我就去吃屎。”
爹说:“她之所以这么说,目的只有一个,她不希望牛牛见到娘,因为这些年来,牛牛的娘托她捎给牛牛的东西都被她昧下了。母子一见面,她就暴露了。”
大爷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事。”
我说:“你们说得都不对,其实是我娘让大娘这么说的,她不想见我。”
爹和大爷坚决否定了我的论断,认为这不可能,天下哪有不想见孩子的娘?
最后,兄弟俩得出结论,我的四川之行不能放弃,一定要去看个究竟。这顿酒就这样不欢而散。小桌子撤下,我和爹分别躺在炕的两头。黑暗中,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如果她真的死了,那就是报应。”
听爹这么说,我的心像被人打了一拳。
天刚放亮,我从炕上爬起来。昨晚的酒让我头痛欲裂。爹尚在梦中,我轻手轻脚,穿好衣服,拎起背包,偷偷走出大门。我来到马路上,等来一辆开往衡水市的大巴。一个小时后,大巴到达衡水火车站。当年,我爹和我大爷骑着自行车也来到过这里,但他们肯定没有这么快。
我取出到成都的火车票,还未到检票时间,坐下来等待。兜里有一张纸,是前几日所做的“攻略”,写着如何从成都坐车前往娘的村庄,我掏出来,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坐在冰凉的铁椅子上,我对自己说:到成都后,如果还能记得那个村庄的名字,如果还对乘车路线烂熟于心,那就去看看吧。
我还有一路的时间用来回忆,或者忘记。

⊙ 朱 个·大车与小车
张 敦:一九八二年出生于河北张吕卷村,已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作品若干,同时从事诗歌、影评等创作。现居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