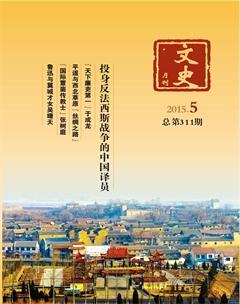魏晋北朝并州(晋阳)地区的各民族大融合(连载)
降大任
中国古代史上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并州(晋阳为中心)地区,是发生长期动乱和战争的区域,其时有匈奴、鲜卑、羯、氐、羌、契胡、丁零(高车)、柔然、乌丸、突厥、吐谷浑在此生存活动,他们或建立政权,或参与战事,或往来迁徙,或错杂聚居,形成了同中原汉族相冲突又相交流的民族大融合高潮,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发展历程。这是造就今天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魏晋北朝时期(220—581),是中国古代战乱频繁、生民涂炭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也是当时中国各兄弟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而其中以晋阳为中心的北方并州地区,成为各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从而对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晋阳与并州
晋阳是魏晋北朝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中心,是所谓乱世之强藩、治世之重镇。古晋阳城在今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一带。考古发现这里今尚有晋阳城墙、宫殿台基遗迹,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
晋阳城所在,从宏观地理角度看,处于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处,正如世界文明史所称的欧亚大陆桥,大致位于赤道以北的北回归线上。这里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秦汉以后,北部草原带曾经先后生活着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多个游牧民族,南部农业带则主要为经营农业为主的汉民族(先前称华夏、诸夏)占据。北方诸边族多以游牧业为主,游牧经济较之稳定的南方农业经济,更加依赖于大自然,一旦遇到严酷气候,畜牧的生存繁殖将深受影响。北方边族生计陷于困境,就不得不南下寻求活路。于是,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凭着刀枪铁骑杀向南部农业带,抢掠人口和粮草财物。这时并州地区便沦为各族厮杀的战场,而晋阳城则首当其冲。据考证,魏晋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曾经出现过两个大的冷谷:一次在290—350年(晋永熙元年至永和六年),一次在450—540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至东魏兴和二年、西魏大统六年)(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1期),据说其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2—4摄氏度。同时,并州地区水旱灾害频繁(见《魏书》记载)。遇上这样恶劣的气候,北方边境生活艰难,南下攻掠或入塞内附,便成为他们求生的唯一选择。
另一个原因是魏晋政权内部纷争,各边族与汉族以及边族之间战争不断,都极力争取利用彼此的力量,壮大自身,与政敌斗争,也招致边族的南下和攻掠。如东汉末袁绍援引乌桓兵马与曹操抗争,曹操征乌桓获胜,收编其骑兵为军事主力;又如曹操分匈奴为五部定居于晋阳一带;西晋八王之乱,各王均借重边族力量相互厮杀;又如刘琨守晋阳争得鲜卑拓跋部猗卢千余马牛羊的资助等。
第三个原因是魏晋北朝诸政权因战事频仍,人口减少,急需补充大量兵力和劳动力,往往引诱或强迫边族南迁落户或扩充军队,成为受人奴役的奴客、田客、勇力、吏兵等(参《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及同书《外戚王恂传》)。也有大批边族战俘留在并州,或为编户,或为兵士,为各政权服役效命(参《晋书·匈奴传》)。
还有一个原因是各边境入塞居于并州成立割据政权,均要在此区选择重镇要地,作为施政中心和军事根据地,依托该地进而图霸,争夺天下。如鲜卑拓跋氏先在繁峙建国,后建都于平城(今大同市),继于396年南并后燕,攻占晋阳,又全有并州。匈奴前赵刘渊初都离石,继迁蒲子(今隰县),又迁平阳(今临汾市),多次攻晋阳,终灭西晋。鲜卑西燕慕容永由长安入上党,建部长子(今长治市长子县);羌族后秦姚懿曾称帝于蒲坂(今山西永济市)等。由此可见,晋阳地区及并州所辖在魏晋北朝确实是当时举足轻重、进取天下的战略要地,各民族在这里的攻守征伐十分剧烈而频繁,是各族文化冲撞、交流、融合的热点地域。
晋阳文化政治军事战略地位之重要,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这里的地理形势决定的。晋阳,得名于所在位置的晋水之阳,依山傍水,宜于人居。从先秦至北朝,晋阳从来就是历代统治者的必争之地。《春秋》昭公元年(前541年)载:“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即太原)。”杜注:“大卤,太原晋阳。”《谷梁传》载:“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晋阳城至迟建于公元前497年之前。《春秋》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经文既称“入于晋阳”,显然先已有一座晋阳城在。联想到公元前790年有“晋人败北戎汾阳”(《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推测在西周末期(西周终止于前771年),该地已有城池之设亦有可能。晋阳城在春秋后期成为赵简子的军事堡垒,其时由赵简子家臣董安于进行大规模改建,成为赵氏保障之城,继由另一家臣尹铎任晋阳宰,治理有方,加强了军事防御功能。正是凭借这一坚固的城池,赵简子联合魏韩二氏于前453年消灭了权臣智氏的势力,在晋国形成三家执政的局面,最终“三家分晋”,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战国策·齐策三》云:“晋阳者,赵之柱国也。”
在战国时,晋阳一直是赵国西部北伐三胡、西抗强秦的前哨阵地。在秦朝,晋阳仍是秦廷屯兵以御匈奴的屏障。西汉文帝始封为代王,都晋阳。文帝在晋阳为代王十七年,治绩显著,积累了施政经验,后为诸功臣拥戴入长安,继帝位。东汉以后,晋阳隶太原郡,属并州刺史部,为郡部治所,是中原政权与匈奴、乌桓、鲜卑等边族斗争冲突的焦点。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评云,晋阳(太原)“东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岭,北扼东径、西径关,是以谓之四塞也”。可谓“控山带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诚古今必争之地”。史家亦多称其为“北门锁钥”“中原北门”。纵览中国历史,大凡西北边族南下夺取中原,改朝换代,无不是先据山西,以晋阳(太原)为依托,收河东,据上党而后顺势南攻,定鼎天下。足见晋阳(太原)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何等重要。
晋阳是并州的中心要地,但并州之区域十分广阔。在《尚书·禹贡》表述的远古行政区划中,并州为中国大九州中的冀州之地,与幽州合称幽并。并州之得名,《淮南子·地形训》认为“其州或并或没,故因以为名也。”是取兼并之意。《晋书·地理志》引纬书云,所谓并,“盖以其在两谷之间也”。所谓“两谷”,未见详指,而发语曰“盖”,当为推测之词,但并州多山川丘陵,或系指太行吕梁之间,亦未可知,但仍可备一说。《释名·释州图》云:“并之言并,阳合交并,其气勇壮,抱诚信也。”是阴阳家言,从民风同俗之释州名,此说可供参考。
并州之辖区,在传说时代为尧之唐侯封国,今太原南有尧城村,或系尧部落由河北唐县南迁入晋,定都平阳(今临汾市)之途经驻跸之地。春秋时,并州属晋,当是晋献公之前北扩于霍山之北后统治的区域。战国时,并州属赵,秦统一中国,置三十六郡,并州之地辖太原、上党、朔方上等郡(见《汉书·地理志》),包括今山西晋南、晋西南之外的大部分地区。西汉初并州之地设太原国,领51县,汉高祖时,治太原、上党等郡,不久以太原21县为韩国,封韩王信,都太原,后逐韩王信,封室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封皇子刘参为太原王,都晋阳。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始置十三州部,设刺史,并州为十三州之一,辖有太原、云中、上党、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东汉因之略有损益,并州由监管区域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域。此时,并州地域最大,除今山西大部外还领有今内蒙、陕西西北之一部分。直到魏晋北朝时期,并州辖区渐次缩小,基本上不出今山西地域。并州之郡县数由东汉9郡98县,减为西晋6郡45县,北魏5郡26县,北周2郡10县。辖区由塞内外缩为塞内,最后只占据晋阳附近,致使人们今简称太原乃至山西为并州。但这并不意味着并州的地位不重要,而是由于后世州郡设置日益频繁,与全国各地州郡设置皆日益缩小的大趋势是一致的,不足为怪。且魏晋北朝的并州各地边族政权彼此消长,势力或宽或窄,各自所辖范围均有限,统治力量均不能顾及全区。在这种分裂割据的条件下,并州的辖区自然只能是日益缩小。
晋阳(太原)既然是“四塞”之区,战略要地,以之为中心的并州自然也为历代兵家必争。《读史方舆纪要》称“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河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分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径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取于山西也。”(参《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九《山西方舆纪要序》)这已经把并州地区的险峻和重要地理形势讲得很透彻了,亦当是历代史家之共识,即后人所谓“得晋阳(并州)者得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
正是由于晋阳(并州)具有争夺天下的战略要地的独特地理条件,在魏晋北朝时期,汉族和各族政权在这里发起了长期不休的战乱争夺,从而客观上促进了中华各族的同化和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无法替代的重大作用。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