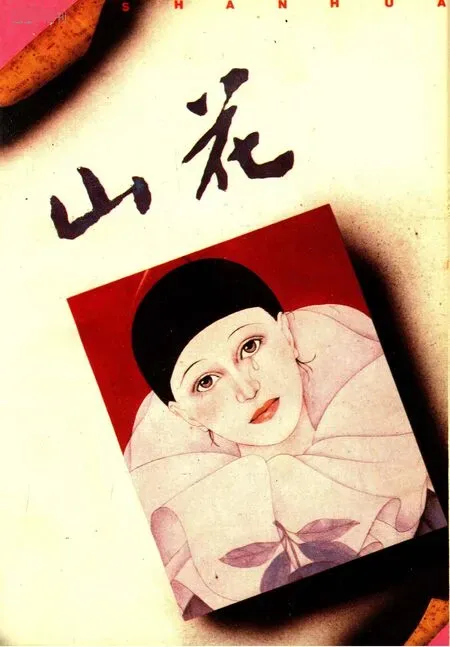石 英
徐汉平
石 英
徐汉平
鲶鱼婶家的黑猪是驼背叔变成的,我不相信,尽管那时我还不足五岁。这怎么可能呢?我天天看着,那只小黑猪是在我眼中长成大黑猪的。可大人说,驼背叔在村后天鹅山摔死后,就变成了黑猪。这事儿,不过是我们姚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那些破事儿相当纠结,也相当扯淡,在姚庄那方小天地勾连在了一起。现在回头看去,依旧扑朔迷离,让人想不明白。柳叔说,想不明白的事,最好学会忘记。
鲶鱼婶的猪圈在我家房前,也是她自家的房前。我们这座老屋子,在村子中央一棵老槐树下面,五间两伙厢,是姚庄最大的屋子。不过,那两伙厢只剩破架子了,楼板已掉光,屋檐上也开了一个个天窗,早已没人居住。可以说,这也是姚庄最破败的屋子。有段时间,夏天的傍晚,老屋里飞出许多白蚁。那白蚁见木头就咬,我家间底的板壁也让它们啃咬光了,换成了蔑篱。蔑篱那一边,就是鲶鱼婶家的间底。间底也就是卧室。太阳即将落山了,村子一派昏黄,那些白蚁就从栋柱脚、栋梁头或者别的隐秘处爬出来,源源不断地爬出来,然后结队成群地飞出黑洞洞的窗口,飞过屋前的石砌道坦、低矮的茅草猪圈,消失在了蓬蓬勃勃的老槐树里。
白蚁起飞时节,老槐树上的喇叭便唱起革命歌曲来。这是姚庄唯一的喇叭,它挨近我们五间两伙厢老屋,住户们就有点儿自豪。其实,住户除开我们两家,也只有五保户香梅老娘了。我哥看起来确实挺自豪的,他比我大一岁多,瘦猴样,个子跟我差不多。喇叭一响,他就爬上道坦前的照屏墙,吊起嗓子大声喊道,开唱啦——。那时节,村上好听的并不多,除了鸟的鸣叫,也就喇叭歌曲了。那些飞来飞去的鸟儿,啾啾、咕咕、嘀哩、叽叽喳喳的,的确好听。不过,相比之下还是歌曲更加动听,有女声,也有男声。对于女声,我已有点儿敏感,支楞着的两只小耳朵里头仿佛安了块磁铁,歌声不是灌进来,是吸进来,然后渗了下去;眼目里则出现了挂着两条长辫子的很好看的女子。也许我有些早熟,起码比我哥早熟多了。记得当时,看见鲶鱼婶在槐树下月影里擦身体时,我的目光闪烁几下,就粘腻起来。她左手撩着灰色无扣圆领短袖衫前摆,右手拿着湿毛巾伸上去,很大幅度地揉擦。擦了上身,又拉开花短裤皮筋带,擦下身。两个奶子虽然让灰色衣衫糊住了,却仍旧高耸着一颤一颤的,看起来特别巨大;那下面也相当广袤,有滩黑乎乎的地儿极其肥沃。那时节,村上好看的也不多,除了鲶鱼婶擦身子,也只有天上偶尔飞过的飞机、杀猪的场景、透明的石英以及村后天鹅山上的火烧云。那火烧云,有时变幻着色彩,变幻着形状,将村子渲染得酡红。那酡红有时又变幻着,让人有了虚幻的感觉,显出不真实来。
通常,鲶鱼婶是在歌曲声中喂黑猪的。她右手提着泔桶,左手挥打着面前的白蚁,屁股磨盘样一闪一闪地往猪圈走去。要是队长看见了,便喊,鲶鱼婶,给驼背送饭了啊。鲶鱼婶并不搭话,捷步走向猪圈,哗地一声将猪食倒在石凿猪槽里。队长是站在他自家道坦上喊的。我们姚庄的格局,由上坦、中坦、下坦组成。各坦排列着五六座房子,各各成了个半环儿。队长的房屋在上坦,屋前的道坦坎老高,视线擦过我们中坦老屋子的屋脊,可以看见屋前半个道坦,以及道坦上老槐树下的猪圈、照屏墙上的爬山虎。我们中坦老屋的道坦坎也老高,也可以看见下坦屋前半个道坦。鲶鱼婶提着空泔桶转过身时,队长就又喊,给驼背老公吃什么?鲶鱼婶依旧不予理睬,挥手打着白蚁走进了门洞。
起初就是队长说起的。鲶鱼婶的黑猪确实长得很快,别家的猪月长八九斤十来斤,鲶鱼婶的黑猪却每月长三十多斤。长这样快的猪,开天辟地以来都没有,队长说,肯定是驼背变成的,看他老婆忒辛苦,就变成猪,快快长膘子,好卖钱。后来,村里大人也都这样说,是驼背投胎的,长得这么快,自盘古开天以来都未曾有过。
我父母从不参与说这事,也从不提驼背叔。驼背叔不是我的亲叔,姚庄都姓姚,父辈的男人比父亲年少的,叫叔,年长的,叫伯。那天,驼背叔是在天鹅山挖石英时摔下来的。天鹅山矗立在村后,很陡峭,光秃秃的,一点也不像天鹅。驼背叔在山腰上摔倒后就滚下来,一直滚到天鹅湖左近,撞在了一块岩石上,脑壳裂开,就死了。那时,政府收购石英,工余时节大人都上山挖采,挖采那种柱形的透明石英,透明度越高越贵。那段时间,家家户户的道坦上,东一堆,西一堆,尽是石英,太阳光照耀着,就满村子闪闪发亮。面对闪闪发亮的石英,我就出现幻觉,幻觉里有驼背叔,也有我父亲,他俩扭在了一起,还嗅到浓浓的血腥味。这种幻觉是在老槐树下为驼背叔招魂时产生的,后来就常常出现。我至今尚未弄明白,当时鲶鱼婶有没有怀疑我父亲,尽管她后来说过,是一些亲戚非要那样弄。念佛先生显然是应了家属要求,才对一根竖立着毫无表情的竹枝发话的。他一脸肃穆地面对竹枝说,要是你自己摔下来的,就别动;要是被人家推下去的就晃三晃。这自己是指驼背叔,这人家肯定指我父亲了。那天,在天鹅山挖石英只有驼背叔和我父亲,没有第三人。幸亏那竹枝仍是毫无表情地丝纹不动,要是晃动了不知会发生什么大事情。尽管如此,我父母仍旧忌讳,从不提驼背叔,也从不提他变成了大黑猪。
大黑猪是越来越大了,差不多有生产队那头黑牯那么大。
姚庄就一个生产队,队里有三头耕牛,那黑牯处在两头黄牛之间,不大不小。晚上,猪圈里蚊子多了,鲶鱼婶便将大黑猪放出来。在老槐树下,大黑猪慢慢地走会儿,然后躺下来睡觉。也不是马上就睡,尾巴晃一下,又晃一下,有时脑袋也晃几下,还嗷嗷地叫一两声。也许让蚊子叮咬了,叮咬得它嗷嗷叫。鲶鱼婶便开始燃驱蚊草,每次她都要燃一堆驱蚊草的。那烟雾一起,蚊子在潮湿的空气里昏天黑地乱闯一会儿,便平静了下来。
我坐在一把小竹椅上,身后是老槐树的根疤和树洞。那树洞特大,白天待里头挺舒服的,晚上却有蚊子。队长曾说,驼背跟鲶鱼婶办事儿,没意思的,好比一根筷子在大水缸里搅乎。这话相当深奥,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回,待在老槐树的树洞里,便茅塞顿开。驼背叔不但驼背,且瘦小,而鲶鱼婶却硕大无比。有些难想的事儿,处在适宜的环境,点着了灵感也就不难了。
燃起了驱蚊草,鲶鱼婶就开始擦身子。那木桶里的泉水,是从下坦的水井里挑回的。姚庄一点也不好,小山窝而已,就那窝冷水好,冬天温暖夏天冰凉,挺宜人。也许有了那窝冷水,姚家祖先才就此结庐生息。男人可以在水井边擦身,女人则不可,这是约定俗成的。月影中,大黑猪是个庞然大物,鲶鱼婶也是个庞然大物。我看着她那巨乳肥臀,忽然想起队长那句话,目光顿时粘稠起来,竟有些脸红耳热。擦完身子,鲶鱼婶回屋子了,身上有水淌下来。
过会儿,我也搬起小椅子回屋了。起身时,视线透过老槐树的枝桠,远远的有一饼月亮贴在天际;树下的大黑猪则鼾声如雷了。通常,五保户香梅老娘最后一个回屋子。虽然她已相当苍老,脸色却依旧比一般人白。她从未在道坦上擦过身子,也从不只穿短袖、裤头,不知别处的肤色怎样。夏天晚上,她总喜欢坐在老槐树下,慢慢挥动一把褐黄色棕榈扇子,在月色里看起来非常安静非常古远的样子。
大黑猪大得邪乎起来,有些外地陌生人也来看稀罕了,都说没见过这样大的猪。队长说,这是鲶鱼婶的老公变成的。陌生人问,这怎么讲?队长就说道起来。我母亲是个羸弱女人,胆子极小,驼背叔摔死之后那段时间,她眼白多一些的左眼,时常翻动着惶恐。逢着这样的场合,她就远远地躲开了。队长说,鲶鱼婶也认为是她老公变成的,这样大了还舍不得杀掉呢。鲶鱼婶白了一眼队长说,它是你爹。陌生人就笑。
但猪终究是要杀的。
屠杀大黑猪前几天的傍晚,天鹅山上都出现了火烧云,一连数天都出现了火烧云。有时,彤红的一片,火烧着一样,熊熊烈火那样的气势;有时却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除彤红,也有橙、蓝、紫。随着火烧云色彩的变化,道坦上那些石英也变化着颜色,感觉上有些诡异。事后,我回想起驼背叔摔死前几天,那儿也都有火烧云。后来,发生大事之前,甚至死人之前,一连几天那儿都出现火烧云。柳叔说,也许是巧合吧,据说火烧云能够预测天气,至于是个凶兆,倒没听说过。
鲶鱼婶买来了香蜡纸。也许她真有那意思,以为大黑猪是她老公变成的了。杀猪时,主家是要举行送行仪式的,不过也只是烧些烧纸而已,并不点香烛。仪式极简单,屠工在白刀子进入之际,主家女人拿着一叠烧纸,从屋前道坦往外一路烧出去,嘴里说,啂,啂啂妮,去水南村头做相公。重来复去,就这一句。那啂,猪的昵称吧;至于为什么非要去水南村头做相公呢?香梅老娘说,那是大地方,猪也喜欢大地方的。水南,在我的感觉里很遥远,它是我们县的县城。那天,要不是发生了意外,鲶鱼婶笃定郑重其事地又点烛又点香,然后虔诚地送大黑猪去水南村头做相公。可意外的事一发生,就弄得鸡飞狗叫,整个局面全乱套了,哪里还能按计划行事呢。
杀猪是村里的大喜事儿,不但场面好看,全村每一个人还可以喝口猪血汤。这猪血汤,也不单是猪血,还有猪肺、大小肠子和槽头肉。有的主家还加上几片猪肝。都和在了一起,大锅里煮着,汤香味美之后,一碗碗盛好,分送出去,全村每户一碗。因此,逢着村里杀猪,孩子们就欢呼雀跃,好看之后还有好吃的。
我哥特别喜欢看杀猪,凡是村里杀猪,他都要去看的。杀大黑猪时,我哥原本爬上了道坦的照屏墙,是我母亲叫他下来的。我哥本性就喜欢爬高爬低,他攀爬确实厉害,爬上岩墙掏过鸟窝,有回竟然爬上人家的屋檐背偷梨吃,我母亲并不怎么管他,也管不住。可那天母亲却翻闪着左眼的眼白,叫他下来,而他居然也就跳了下来。要是我哥蹲在照屏墙上看杀猪,就不会让大黑猪拱下道坦坎。也有人说,也不是拱下去的。当时,大黑猪都差点上了杀猪案,不料垂死一挣扎就又落了下来,然后就往道坦外面逃跑。我哥慌里慌张地往后退,一脚踩空,就掉了下去。
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些人就愈加相信大黑猪是驼背叔变成了。不过除了队长,其他人要么放在心里想想,要么私下里嘀咕,但不会当着我父母的面来说。这事儿又与驼背叔的死关联起来。迄今我也弄不明白,驼背叔的死跟我父亲到底有无关系。有说他们争一窝石英,彼此推搡起来了。要是推搡起来,失手了不是没有可能的。我哥摔死后,队长说,驼背变成大黑猪,是来复仇的。
也许大黑猪确实并非寻常之物。几天后,它居然走掉了。
以前,大黑猪是驼背叔变成之说,村上总有人不大相信,以为不过是开玩笑而已;大黑猪走掉后他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大黑猪懂事儿呢,知道人们要屠杀它,就走掉,就神不知鬼0不觉地溜走了。一般的畜生怎么会懂得只有人才懂得的事情呢?
大黑猪是深夜偷偷溜走的。次日早晨,鲶鱼婶发现猪圈里没了大黑猪。那石凿的猪槽被猪舌子舔过了,舔得干干净净,露出黄黦黦的本色。鲶鱼婶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并没有意识到大黑猪就找不着了,以为它因为饥饿而自找食去了。这些天它惹下人命攸关的大祸,给供食确实少了。因此,鲶鱼婶并不担心大黑猪走失,担心它出去糟蹋生产队的庄稼。
鲶鱼婶开始寻找。她并不嚷嚷,独自寻找。可村里找过了,村子周边的田地上也找过,未见大黑猪的踪影。她急了,就哭了起来。得知原委,村上有人就帮忙寻找了。就像寻找马航失联的飞机一样,扩大寻找范围,扩大到周遭的山野。队长说,这个驼背跑天鹅山去了吧,他在那儿摔死的,可能跑那儿去了。就差人去天鹅山寻找——寻了天鹅山的阳面,又去阴面的树林里寻,寻遍了整座天鹅山,均不见大黑猪影子。
大黑猪就这样人间蒸发了。
可没过几天村里有人却发现了大黑猪。那人是在村子左边一座叫鬼剑下的山上发现的。那人说,大黑猪比以前瘦了,它跑得很快,一下子就消失在了松树林里。人们不大相信。那人在村上口碑不好,原本就喜好捕风捉影,蒙骗造谣。队长也不肯信,说你看见的是鬼怪,不是驼背。队长这样说,是因了鬼剑下有个恐怖传说。老辈人说,鬼剑下那个山洞里经常有白衣裳晾出来,里头有妖魔鬼怪。可是,一个礼拜后有个老实敦厚的男人也发现了大黑猪。他是在天鹅山阴面的树林里看见大黑猪的。他说,大黑猪确实瘦多了,还长出了锐利的獠牙。这老实人担心别人说他造谣,就别出心裁地以树叶包回了猪粪。他将树叶翻开来让人们看,嘴上说,大黑猪在那儿睡过,这猪粪就在那儿包回来的。大伙看这猪粪像砂糖一样的,就说这不是猪粪,是牛粪。老实人红头涨脑地说,大黑猪吃的是草,拉出来的自然就像牛粪了。
看见大黑猪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有说在那儿看见,有说在这儿看见,也跟寻找马航失联的飞机一样,消息有些混乱。没有看见过的人,就有些相信,也有些不相信。不论去下坦跳水还是在田地上干活,疑疑惑惑地多了个心眼。
这下可不得不信了。
有人在驼背叔的坟地发现了猪脚印,在我哥的坟包上也留有猪脚印。许多人都去看过,确实有不少猪脚印,千真万确的事儿。村子就惶恐起来。大黑猪确实仍然健在,仍然在村子周遭活动着。香梅老娘说,真成精了,不知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大黑猪的叫声是香梅老娘最先听见的。她在三更半夜听见从对面山传过来的大黑猪的嚎叫声。后来我母亲也听见了。再后来,村里许多人都听见了大黑猪的嚎叫声。这嚎叫声,有时是从村子后面天鹅山传过来,有时从村子对面山传过来的,还有从村子左边或者右边的山上传过来。看起来,大黑猪神出鬼没的,或前或后,或东或西,行踪不定,变幻莫测,弄得整个村子惶惶然起来。
我母亲也看见了大黑猪。看见大黑猪不久,她就发疯了。
她是在道坦那堆石英上看见大黑猪的。政府只收购两年多石英就叫停了,几乎每个道坦上都有许多废弃的不怎么透明的石英。应该说,我母亲是幻觉。在幻觉里她不仅看见大黑猪,还看见了驼背叔。那天太阳光相当好,道坦上那堆石英光芒四射,很有些虚晃。她望着光芒四射且很有些虚晃的石英,就叫喊起来。先是喊大黑猪,接着喊驼背,尔后就大黑猪——驼背——大黑猪——驼背地哭喊起来。她的哭是被惊吓的,她肯定相当恐慌,那眼白多一些的左眼里除了惊惶,还闪烁着紫色。那种乌紫烂色,让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这时候,我父亲还不以为他妻子疯了,直至次日,我母亲在头发里插上一簇野花,然后跟着喇叭里的歌曲且歌且舞起来,才断定是发疯了。
对那堆不怎么透明的石英,我好生奇怪。母亲怎么会在那儿看见大黑猪和驼背叔呢?我呆呆地前去就近瞧瞧,太阳光照耀着,那些石英就活起来,各自泛着不同色彩。我掏了掏,居然发现一根上好的石英,它通体透明,晶莹剔透。这些石英都是政府不要而废弃的,怎么还有这样好的石英呢?我慌忙拾起来,放袖管里头带回屋子藏在一个小竹筒里。
在我母亲发疯的日子里,大黑猪仍旧在村子周边活动,仍旧有人看见它的影子或者听见它的嚎叫声。特别是我母亲,她常常惊叫起来,大黑猪、驼背或者驼背、大黑猪地惊叫起来。好像大黑猪和驼背像幽灵一样跟随着她。香梅老娘满脸忧愁地说,许是让鬼魂迷住了,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自己的妻子变成疯子是相当羞辱的事情,让我父亲感到极其羞辱的是我母亲袒露着上身坐在道坦上玩石英。父亲不在场时,有人说我母亲的奶子算不得奶子,还不如鲶鱼婶的五分之一大。也有人撺掇我母亲把裤头也脱了,这样更凉快。好在那样一丝不挂的难堪,母亲从未有过,直至在天鹅湖淹死也不曾有过。
天鹅湖就在天鹅山麓。湖子中央的水域很深,四周却浅浅的,长满水草。湖里有小鲫鱼,也有田螺。那天,我母亲去天鹅湖不是摸田螺,但也不知为了什么。据说她是被大黑猪引着去的,一路上嘴里“啂、啂啂妮”地哼哼着,村里的人说得很邪乎。我哭着赶到天鹅湖,我父亲恰好把他的妻子从湖里背上岸,放在天鹅湖旁边的草地上。我母亲仍穿着衣裤的,在天鹅山上面火烧云的映照下,她的脸庞竟泛起一些虚红。我父亲将自己的白汗衣盖在了他妻子的脸上。这些我历历在目。若干年后,我给生产队放牛了,就是那头黑牯。有一天,我想我母亲,就把黑牯赶到天鹅湖边吃青草,下去摸田螺。田螺很稀少,但个儿极大,比水田里的田螺要大几倍。那天,我摸着了六只大田螺。
我母亲淹死后大黑猪依旧嚎叫。夕阳下山了而火烧云尚未褪去,就传来嚎叫声。有人循声赶过去,却无声无息了。可不一会就又传来嚎叫声,只是传来的声音变了方向,从村子左边鬼剑山下那儿传过来了。火烧云消失后,村子一派清明,那嚎叫声就显得凄厉。一些归宿的鸟儿,似乎慌乱起来,从老槐树飞到屋檐背,又从屋檐背飞到老槐树去了。香梅老娘说,可能要去坟头说故说故。我不知什么意思,鲶鱼婶却心领神会,备好了香烛纸,在一个黄昏跟同香梅老娘一起去驼背叔坟头说故了。我远远地望着,不知她们说故些什么——只见苍苍茫茫的残阳里烛光闪烁,香烟缭绕,很古老很久远的样子。
说故过后,大黑猪的嚎叫声居然消弭了。
村子就安静下来。
这种安静写在鲶鱼婶的脸上,写在我父亲的脸上,写在香梅老娘的脸上,也写在全村人的脸上。白天,我父亲要出工,鲶鱼婶也要出工。她的女儿小丫比我还小,也跟她一起下地,以前是坐在她后背的竹筐里去,后来牵着手走。我们五间两伙厢的老屋里就只有我和香梅老娘了。香梅老娘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脸白,还有一把棕榈扇子、一只铜火笼。队长来了,她就适时地将扇子或者火笼递过去。她不大言语,要是开口了,说出的话却很有些吓人。说故说故什么的,就似乎跟鬼神联系在了一起。于是,我也跟父亲一起出工了。大人在田野上干活,我和小丫则玩耍。
这样,白天的五间两伙厢老屋只有香梅老娘待着。我父亲和我,鲶鱼婶和小丫,我们四个人就出工、收工,又出工、收工地按部就班起来。
有一回,我从地上回来,发觉裤裆里的小鸡鸡凭空胀大起来。鲶鱼婶看了一眼说,让蚯蚓吹的。她去田坎上拔来一把草,捣烂后要给我糊上。她已蹲下来了,我却不让她糊,被我父亲吆喝了一声,才犹犹豫豫地拉下裤子。她的女儿小丫在一旁嘁嘁嘁发笑,我催她糊快点。她却慢吞吞的,伸出食指在我的小鸡鸡上敲一下,我白她一眼说你做什么吶,她却又敲一下,敲了三四下,然后说,没用了——才开始糊:先将草药敷上,黑布包好了,蓝绒线扎住。裤裆里安了个包裹,我觉得极不舒服。鲶鱼婶说,明天就好了。
当天晚上,一觉醒来我忘了裤裆里的包裹,只觉得那儿黏糊糊的有物事,继而又听着一种奇里古怪的声音,有点像大黑猪的嗷嗷声,却似乎又不是,便伸手一摸,床上空空的,摸不着父亲,我就哭喊起来。好一会儿,床前忽然亮起来,父亲擦了一根火柴,说,怎么啦?我已记起是草药了,说,草药掉下来了。父亲也不点油灯,丢了火柴摸索着伸过一只手来,在那儿摸了摸,然后说,燥了,先拿掉,明天再糊上去。拿干净后,我就又睡着了。
消肿之后,鲶鱼婶说,大鸡鸡又变成了小鸡鸡。以前,鲶鱼婶不会跟我开玩笑的;我父亲也不会跟她的女儿小丫开玩笑。那天,天上轰轰轰的响,开始是闷响,接着越来越响,有一架飞机像老鹰一样飞过来。我们小孩都喜欢看飞机,甚至连大人都喜欢看。那时,村里确实没什么好看的,除了杀猪的场面、天鹅山上的火烧云,似乎只有天上的飞机。村上有一些传说,飞机上会丢下面包、饼干什么的,甚至还有钞票,哪哪村里的人都拾到了,传说得活灵活现。我父亲望着抬脸看飞机的小丫大声说道,不好,丢下炸弹了,快逃。唬得小丫撒腿就跑,跑进老槐树的树洞里去了。我知道父亲是开玩笑的,仍旧看着飞机。可村子的天空窄窄的,不一会儿飞机就消失在了天鹅山巅的火烧云里。
火烧云虽然好看,但经历了那些事儿,我不喜欢看了。我有个发现,火烧云今天出现,明天出现,一连好多天都出现,就会出事儿,甚至死人。一看见那儿生成了火烧云,我心里就发慌起来,就如同听见大黑猪的嚎叫声。
又一连数天出现火烧云。一块一块的,一片一片的,一团一团的。有像人的,也有像大黑猪的,还有奇形怪状的,鬼魅似的说不出像什么。也不是在同一高度,有的远,有的近,很有立体感。在一些空隙里,似乎有物事出没。我心里慌慌的,好像又要发生什么事儿。
一个傍晚,鲶鱼婶望着一块火烧云说,那个是仙女,你妈变成的,你妈变成仙女上天了。我狠狠地说,那是你老公,他上天了,变成了仙男。我父亲说,吵,吵吵吵,听喇叭。坐一旁听喇叭的还有香梅老娘。她手上的棕榈扇子,挥一下,过了好一会儿,又挥一下。她不是扇凉,是赶蚊子。喇叭里不是唱歌,是讲话,是当地的土话,大约是说新闻吧。
真是见鬼了,果真又出事了。
出事的是我父亲。给鲶鱼婶家翻瓦片出事的。也不单是翻瓦片,先弄掉屋檐背那些槐树枯叶子再翻翻瓦片。要是没有那棵老槐树,队长不可能将村子唯一的喇叭挂在我们五间两伙厢老屋子跟前,可有了这棵老槐树,我父亲每年都要上屋檐背弄枯叶、翻瓦片。父亲翻好了自家的瓦片,跨过去,翻鲶鱼婶家的瓦片时便掉了下来。他是跟四条腐烂的椽子一起掉下来的,先掉在楼上——楼板早被白蚁吃光了而换上一张破篾簟——钻过破篾簟,就掉在鲶鱼婶的木床上。这么一掉,队长就说,我父亲老是想着鲶鱼婶的床,结果就掉在她的床上了;而我父亲则成了瘸子——成了瘸子不久,在生产队割稻时,让一只打谷的稻桶砸死了。
我父亲踩上腐烂椽子,据说跟大黑猪的影子有关。他起身从自家屋檐背跨向鲶鱼婶家屋檐背的当儿,忽然发现道坦那堆石英的光芒里晃动着大黑猪的影子,心里一悚,就一脚踩在了腐烂的椽子上。不知是我父亲自己说的,还是村人胡编出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自从我父亲掉在鲶鱼瘪的床上之后,大黑猪就又出现了。不但出现了,它的活动范围似乎也向村子逐渐挨近。不但来过驼背叔的坟地,还拱了生产队地上的许多番薯,我家自留地上的白菜也被糟蹋了不少。晚上,它的嚎叫声也更加嘹亮更加迫近。香梅老娘说,昨晚上大黑猪可能走进道坦了,那叫声好像就在屋前传过来的。
我父亲让稻桶砸死似乎也跟大黑猪有关。这些破事儿说不清楚,却仿佛勾连在了一起。以前生产队割稻,父亲是打谷的,成了瘸子后,队长不让打谷,让他割稻。父亲在田后坎割稻时,忽然就掉下一只稻桶。稻桶是在后一丘田四米多高的田埂上掉下来的。田埂上有若干半透明的石英,扛着稻桶的队长走近石英时忽然听见大黑猪的嚎叫声,便一脚踩上石英跌倒了,稻桶就离开他的肩膀掉了下来,恰好砸在我父亲的头上。那天,生产队许多人不但听见了大黑猪的嚎叫声,还看见了它的踪影,在对面山树林里有一团黑影掠了过去。柳叔说,许多事情在冥冥之中注定的。柳叔在我的人生中极为重要,姚庄这些破事儿也只能跟他说说。
父亲去世不久,我给生产队放牛了,就是那头跟大黑猪差不多大的黑牯。
大黑猪好像又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村上没人说看见大黑猪,也没有人说听见大黑猪的叫声。队长说,邻村有个人以狩猎夹夹住了一头大黑猪,獠牙五六寸长,不知是大野猪还是鲶鱼婶家逃走的大黑猪。不过,一个来自邻村的骟猪人说,没听说过有这么回事儿。但又说,当时,鲶鱼婶那口大黑猪还是小黑猪的时候,骟出来的睾丸儿好像不是猪的睾丸。
我所放牧的这黑牯是三头牛中最难侍候的,队长让我来看管,一天打两个工分。有时,我看着这黑牯恍惚起来,它便变成了大黑猪,心里惶惶然,可队长非要我看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队长相当威武,对我爱理不理,我有些怕他。有一天,队长提来一麻袋白色药粉,自己动手,给鲶鱼婶家撒上,给香梅老娘家撒上,又给两边的伙厢撒上,然后将剩下的摔在我的脚下说,自己来,柱头、地桁那些地方都撒些上去。这是杀白蚁的药粉。我撒到卧室蔑篱那儿,发现蔑篱破了,有几个小孔儿,视线穿过去,就看见了鲶鱼婶。她赤条条躺在床上,在昏暗的光线中,就像煺白的大黑猪。我的目光立刻滞住了,滞在她白白的肚子下面那摊郁郁葱葱的地段,足有十多秒钟才匆忙闪开。此后,一进卧室我就忐忑不安,想往那儿看又怕看但还是忍不住往那儿看了。可再也没有看见一丝不挂的鲶鱼婶。不久,那几个小孔让报纸糊住了。
不知是谁说起的,说下一个就是我了。也许是队长。我哥走了,母亲走了,父亲也走了。当时,我以为肯定是队长说的,他说下一个就是我了。我很害怕,整天心神不宁,战战兢兢,特别是晚上——到了傍晚,一看见天鹅山上的火烧云,我就害怕得浑身发抖。黑洞洞的门口好像有个大黑猪晃了一下,屋檐背上似乎唦的响了一声。我坐在老槐树下小竹椅上,害怕了就将身子缩起来,将脖颈也缩起来,像鹁鸪一样,然后视线透过枝桠,望着贴在天际上的那饼月亮。就这时候,我才稍稍有点安全感,似乎老槐树张着巨大的臂膀,保护着我。就这时候,我才产生一些美好的梦想,要是我待在那树洞里,老槐树像飞机一样飞起来,将我带到月亮里去多好哇。
这自然不可能的,可没多久我却真真实实地离开了姚庄。
我是跟一个陌生人走的,就是我在天鹅湖放牛摸来六只大田螺那天跟他走的。那个陌生人说,他去寻找钱,他有个朋友拾到一捆钱,是飞机上投下来的。那段时间,队长也说过,邻村一个人,在山上拾到很多钞票,是台湾的飞机上投下来的,运气好的话,就可以遇上了,不单是钞票,还有压缩饼干,真是妈妈的天上掉馅饼啦。我离开姚庄时随身带着藏在小竹筒里的那根石英,没跟谁打招呼就走了。走出那座五间两伙厢时,香梅老娘意味深长地冲我笑一下。香梅老娘除了脸白,让我记住的还有她说的一些话,比如说故说故那些话,又比如猪也喜欢大地方的那些话。
那个陌生人,我后来叫他柳叔。
都四十多年了,从姚庄带出的那根石英仍在,它柱状,拇指大,八厘米长,透明亮丽,很有光泽。看着它,可以看见火烧云、大黑猪,看见鲶鱼婶白白的身体,还有那些很扯淡很八卦的破事儿了。我想待柳叔过辈后,带着这根透明的石英去姚庄走一趟或者两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