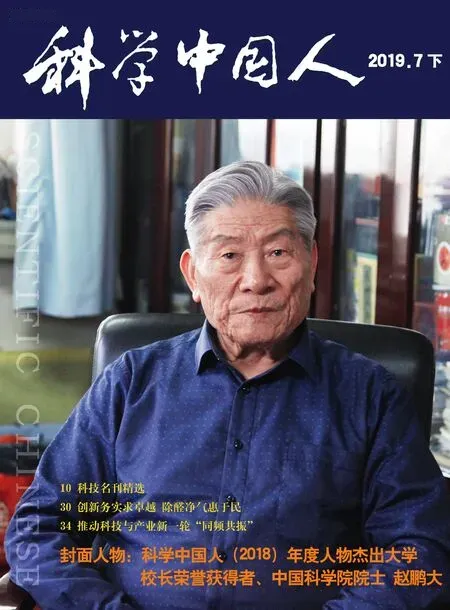执念如怨鬼
——先锋话剧话剧《恋爱的犀牛》赏析
金钰涵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执念如怨鬼
——先锋话剧话剧《恋爱的犀牛》赏析
金钰涵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孟京辉导演的先锋话剧《恋爱的犀牛》凭借着一种诗意的偏执,交织起一幕幕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借助独白和歌曲拼贴的形式,弱化情节安排,突出主人公对爱情近乎偏执的追求,对社会执拗的反叛,对于自由、理想、信仰的坚持。
先锋话剧;恋爱的犀牛;孟京辉;廖一梅;马路;明明;偏执
《恋爱的犀牛》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靠情节取胜的话剧,和孟京辉导演的其他作品相比,这部话剧的情节可以说是简单至极,全剧借爱情的外壳,讲述的是两个患有强迫症一般“非她不娶∕嫁”的为爱痴狂的疯子,固执地追求着不属于自己的爱情的故事。
马路是动物园的饲养员,养着一头名叫“图拉”的黑犀牛。某一天,在楼梯的拐角,他爱上了一个有着复印机味道的、名叫明明的女孩。可是明明执着的单恋着一个名叫陈飞的艺术家,对马路的一切殷勤视而不见,将他的真心弃如敝履。后来陈飞抛弃明明远走非洲,明明在绝望里背起行囊,不顾一切地、固执地想要追随陈飞而去。更加绝望的马路陷入了一种“我不会离开你,更不会让你离开我”的偏执里,他将明明绑架回来,用图拉的心,完成了自己对明明、对所谓爱情的献祭。
全剧没有瑰异稀奇的情节,只有男女主人公两人热烈得几乎要燃烧起来的激情。《恋爱的犀牛》凭借着一种诗意的偏执,交织起一幕幕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在冷淡与热烈,眼泪与欢笑的交叉转换中,为观众带来了艺术上的绝美享受。
话剧中意识流般滚动的大段大段的独白和歌曲的拼贴组合体现出一种语言的美感,更像是情感的一种诗意化表达——在音节的吞吐中,疏离个化的本我,在节奏的韵律里,召唤观众内心深处共同的情感记忆。
“我是说‘爱’!那感觉是从哪来的?从心脏、肝脾、血管,哪一处内脏里来的?也许那一天月亮靠近了地球,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季风送来海洋的湿气使你皮肤润滑,蒙古形成的低气压让你心跳加快。或者只是你来自你心里的渴望,月经周期带来的骚动,他房间里刚换的灯泡,他刚吃过的橙子留在手指上的清香,他忘了刮的胡子刺痛了你的脸……这一切作用下神经末梢麻酥酥的感觉,就是所说的爱情……”
编剧廖一梅的台词总是能捕获爱情中最微小的事物和最微妙的感觉,像一把微小却锋利的刀,在观众的心上轻柔地画上一道,留下细微而尖锐的疼痛。比喻和排比手法的大量运用,仿佛给与了所谓的爱情最真实、最可感的外形。观众似乎能够从台词里切切实实地听到爱人扑通扑通的心跳、闻到行动间弥漫的烟草微香、看到阳光下爱人背影镶上暖融融的金边、触摸到他胡子拉碴的初醒的脸。
当演员把台词或轻柔或激烈地吟咏出来,当一个个音节回响出异样的韵律,伴随着一首首干净动人的歌曲,舞台上呈现出一种或安静诗意、或戏谑荒唐的意境,观众在移情的同时无意识地陷入迷狂的境地。当一切声音消散之后,空气中仿佛还留有爱情来过的痕迹,这是一种恍惚的遥远的美感,像冬日下午的阳光。观众在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台词的反复渲染中,情绪达到最大化的饱和,诗化显然已超出原有的语言风格的象征,晋升成为一种生存的态度和方式。
主人公马路是一个勇敢坚强而又多情的理想主义者,面对一份求而不可得的爱情,他选择的是一种诗意的固执,“忘掉是一般人唯一能做的事,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她”。可他在正常人的眼里,不过是一个要美人不要奖金的、为爱癫狂的疯子,一个被定义为“就为了一个复印机味儿的女人”的失败者,一个行凶的绑架犯。
在这个“物质过剩的时代”、“情感过剩的时代”、“知识过剩的时代”,物质化社会的总是给美好的事物以恶狠狠的嘲弄。马路的朋友不断地对执着的马路进行打击,试图让马路“顺化”为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现实与理想总是反转,人们对“异类”本能的持有排斥的态度,马路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决绝抗争,甚至被看作是精神疾病的体现。
“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了输,我低头奔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马路的偏执,不仅体现在对明明的感情的执着追求上,还体现在对社会、对“正常人”的反叛上。他不会开车、不会英语、不会电脑、甚至不会恋爱。他始终处在时代的边缘,游离在浮华的社会之外。他与一头犀牛相依相伴,就连巨额奖金也不过是他追求爱情的道具,对马路而言,金钱并无意义。这些特征汇聚成马路对社会执拗的反叛,对于自由、爱情、理想、信仰的坚持。
马路这个角色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异类、是一种精神绝对自由的象征,是一个普通人隐藏在内心深处、抛去社会属性后仅存的理想与信仰。也许每个人都是马路,或者潜意识里都想要成为马路那样的人,抛弃一切世俗的纷扰,对一个事物酣畅淋漓的追寻,轰轰烈烈的投入全部的激情。然而在如今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值得坚持的信念或者盲目追寻的东西了,这或许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在《恋爱的犀牛》里,人不再是自由的,一切的存在均被套上固定的模式。“恋爱培训班”操控着人类的情感,恋爱教授传授着标准化、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爱情观,以避免情感滥用所引发的弊端和浪费。生活里不再有梦想,人类在审视自我的过程中陷入迷失。爱情变得不堪一击,人对于情感的诗意表达逐渐被规范化、一体化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荒诞不经的情节带来在笑声之余,也使得观众开始反思马路与明明之间寓言般的爱情究竟是“偏执”还是诗意的坚持。
早期的荒诞情绪在话剧情节的逐步推进中转化为对人自身精神困境的思考,人的内心世界与社会现状无法调和的矛盾使人陷入质疑人对自由的追求、对生活的反抗是否有意义的困境。在《恋爱的犀牛》的结尾,马路以“图拉的心”献祭,完成“偏执”于美好事物的坚持,形成史诗般的壮美效果的同时,升华了话剧的主题,由一个普通的爱情困境上升为对生命的思考,更具有永恒的时代意义。
金钰涵(1993-),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从事戏剧影视文学研究,现居河北省保定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