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我儿子
李长菊
午放学后,程家斌说去小学对面吃拉面吧,放上油辣子,好吃极了。
其实,以前我很少和他们一起出去吃东西。但这段时间,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简单一点说,就是自从爸爸去世后,我喜欢热闹,喜欢和别人在一起,喜欢没心没肺地大声笑。
小学对面,是店面很小的一家拉面铺子,老板娘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很和善,总是面带微笑,好像她的幸福多得心里装不了。
挤在里面吃拉面的学生很多。一人一碗,放进很多油辣子,稀里哗啦,吃得热气腾腾。我碗里的面似乎比别人的多,因为我感觉总是吃不完,并且吃着吃着,我会一下子想到爸爸,然后胃就撑胀起来。等他们吃完了,我们几个走了出去。程家斌说反正时间还早,我们去小学里面玩玩吧。就这样,我们三个走进了小学。程家斌在这里上过学,所以,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他领着我们一边走,一边介绍他在这里时发生的很多事,我只是随着他走,不过,有一会儿工夫,我感觉自己好像来此视察的领导。在拐过教学楼后面时,眼前的一幕让我们愣住了。一个胖胖的男生正在欺负一个女生,恶狠狠地说:“让你以后再说我,还敢不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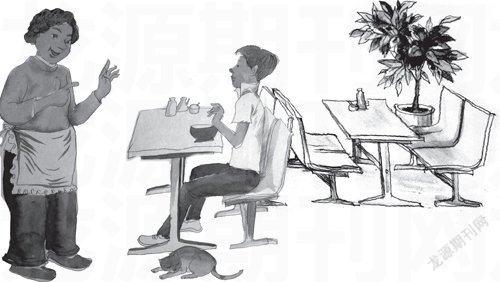
女孩什么也不说,只是怒视着他,但是她的脸红彤彤的,估计是被男生打了。
“住手!”我大喝一声,走过去,照那个胖子的屁股就是一脚。
我还想踢一脚时,程家斌走过来拉住了我,“算了,还是少管闲事吧。”
“以后老实一点,再欺负女生,让我碰见,把你的屁股踢扁。”
就像在路上随便踢了一块石子,我们都没有把这当一回事。
正上着课,我们三个被级部主任喊了出去。
“说,你们午饭后干什么去了?”
“没干什么。”程家斌很镇定。张政也很镇定。难道是……我心里一惊,感觉有些慌。但转念一想,不就是一脚嘛,再说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想到这里,我也表现得很镇定。
“不说是吗?人家都找来了。一会儿工夫,家长就来。你们到处溜达,还打小孩,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
我低着头,老老实实地说:“那个男生欺负女生,我过去踢了他一脚,就一脚。”
“还就一脚,你还想踢几脚?他妈妈这就来找你。你和那个女生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管闲事?”
“没关系。”
“没关系你干吗帮她?”
“她被打了。”
“你是侠客吗?别以为你什么事都能摆平,你能摆得平吗?现在,他妈妈这就来找你。”
“是他先打的人,你不信可以问他们。”我看着程家斌和张政。但是他们都低着头,好像这事是天方夜谭。
就在这时,校长走了过来。他很威严。他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就是一个神。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正干着坏事的时候,他会悄无声息地从某个角落里出来,把我们给逮个正着,这么说吧,他就像是《西游记》里面的土地神。因为这,我们私下里都喊他神。此时,我相信神一定盯着我看,所以,我很想地上有道缝,我能一下子漏进去。爸爸去世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
“谁动的手?让他回家反省一个星期,改好啦,再回来。”
神说完,就走了。
“听明白了吗?走吧,先收拾书包去——”
我被那个很胖很胖的女人威胁了一顿。然后,被撵出学校。我不敢回家。妈妈在爸爸去世后,一下子变得有些神经质,经常半夜醒来盯着一个地方,说爸爸回家了,弄得我和妹妹浑身挤满了鸡皮疙瘩。每当那个时候,我就会冷冷地看着她。然后极力控制着我狂跳的心,故作大胆地喊:“爸爸,是你吗?你真的回来了?你还会和我去河边钓鱼吗?你喜欢的仙人掌死了,是不是你把它带走啦?”黑暗像具木乃伊,冰冷僵硬地沉默着。远处,偶尔有几声狗吠,像一把把明晃晃的匕首,刺入黑夜冰冷的肌肤里。
我站在山顶上,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透彻骨髓的冷。这种感觉一直跟着我,挥之不去。
“别喊了。”妈妈恐怖中带着一点点哀求。但是我不可怜她。我不觉得爸爸的死是对她最好的惩罚。不管怎么说,爸爸留给我的温暖要比她多得多。如果说爸爸是冬天的太阳,那么妈妈顶多算是一颗星,挂在遥远的天幕的那一边。从一定意义上说,也许没有她,我会得到更多温暖。但是,在我的生活里,没有也许。她从睡眠中一次次惊醒,然后折腾半天,才会睡着。每当天亮了,我要去上学的时候,她总是浮肿着眼圈,迷迷瞪瞪地说:“你们两个好好学习,谁惹了祸,我也去死。”
我看着妹妹,她也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数不清的恐惧。这令我害怕。
“不用怕,哥再活一万年也不想死。”我对妹妹甜甜地笑。我不希望她天天哭丧着脸。说实话,我希望妹妹还像以前一样,和我争东西,和我吵架,为了一丁点小事大哭大闹。但现在,她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像离家流浪的一只小猫咪。有时候我回家开门的声音都会吓得她发抖。
我干吗要想这么多?想这些东西对我有用吗?我捡起一块石子,狠狠地往对面不远处的小河扔去。但是我的力气太小了,石子落在岸边的草丛里,没了踪迹。
周围没有什么人。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高坡上,散落着几个坟头,它们隐藏在荒草里,像一个个随便堆砌的小土堆。爸爸也被埋在了土里。如果人被埋进土里也能像种子一样发芽该有多好啊,爸爸会长成什么样子呢?他的躯体会像树干一样健壮吗?他的头发会像柳枝一样柔顺吗?他的眼神会像溪水一样清澈吗?他用什么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些事,在学校里,我从来不想。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我不想去想。可此时,我的周围再也没有引起我兴趣的事,好像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想爸爸的死,好像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为了让我有时候有空间好好想想爸爸的死。这些埋在心里的东西像火热的岩浆,找到了一个突发口,奔涌着往外挤。
我应该找那个男人算账,对,我应该找他算账。否则,我还算一个男子汉吗?我应该对爸爸的死视而不见吗?不能。我攥紧拳头,使劲砸在泥土里。松软的土一下子就被我砸出来一个深深的坑。那个隐约听来的村庄不是很远。那天我一个人悄悄地走在离家不远的一条小路上,听到几个女人正在窃窃私语:
“孩子都这么大了,还——听说是萧家庄的……”
“就是。”
“这个赵米香。”
看到我,她们还和我打招呼,好像她们嘴里的赵米香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赵米香就是我妈妈。我多么希望我的妈妈不是赵米香啊。有时候我甚至想我的妈妈如果也像陈乐的妈妈那样该多好,腿有点残疾,哪里也去不了,就天天在家里,等着陈乐回家,等着陈乐的爸爸回家。
骑了半个小时,就到了我要找的那个村子。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子,和我见过的其他任何一个村子没有什么差别。如果真的找到一点差别,那就是房子似乎都很低矮,丑陋。在村外,有几个老人,正在晒着太阳聊天。我走向他们,询问那个名字,那个被妈妈藏在手机里的汉字。
“你找哪个?一个年龄大的,一个年轻的。”一位老人很是热情地问我。
“大约四十来岁的那一个。”我猜想他也就是这个年纪,和我爸爸差不多。
“昨天刚刚走。你怎么不早来?”
“年纪大的呢?”其实这个人和我真是没有一点关系,但是为了填补我心里的失落,我像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抓住了这个问题。
“死了。”他们哄笑起来。好像死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年轻的那个,他家里还有其他人吗?”
“其他人?没有。”一个老人慢腾腾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卷上烟丝,慢腾腾地说,“就他一个人。他爹娘都死了。连个老婆也没有。”
“怎么没有?听说有一个。”一直靠在墙上的一个老人说。
“有一个?家里老鼠倒是有好几窝。”又是一阵大笑。他们的笑声听起来很豪放,但是在我听起来却很刺耳。我的脸腾一下子热了。我很羞愧。我有足够的理由羞愧。我不想再听他们笑。于是就骑上车子,朝村里走去。我还是想看看他的家。
大门紧锁。一棵很大很大的梧桐树,从墙里面伸出巨大的枝杈。我趴在门缝里往里瞧,院子里有很多野草,也许里面藏着很多野兔吧。除了那棵大梧桐树,里面还有一棵枣树,叶子早就落光了。这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家。房子很旧,院子很荒凉。坐落在一圈新房中间,像一个落魄的乞丐。我拿出手机,对着房子拍了几张照片。毕竟隔着门,效果不是很好。这很令人遗憾。我四处打量着,最终,我发现墙角有一棵杨树。我走过去,搂住它,噌噌几下就超过了墙的高度。啪啪啪,我又拍了几张。哼,这么荒凉的地方,也许只有鬼才感兴趣呢。就这样回去?这似乎不是我来的目的。看着那扇冰冷的门,我拿起一块石头,使劲朝门砸过去。我又拿起一块砖头,朝着锁使劲敲了几下。但是,那锁似乎想要证明自己的性能,没有一点变化。如果我能砸开它,我一定要撬开他的房门,一把火烧个精光,如果有兴趣,我还会再拍几张照片。但是不管我怎么使劲,那锁还是没有一点松动的意思。上面的铁锈被我敲成了粉末,被风一吹,有的就进入了我的眼睛里。我使劲用手揉了几下。
“嘿,你在干什么?”
我回头,一个中年人正狐疑警惕地看着我。那眼神,好像我是从荒野里窜出来的一只野狼。
“快点走开。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不好好在学校里念书在这里乱逛什么?小心我给警察打电话。”
他声音不高,但是透出不容质疑和抗拒的力量。阳光透过树杈,照着他有些花白的头发,很扎眼。我悻悻地走向我的自行车。
我的口袋里还有三块钱,够吃一碗拉面。我想去吃拉面。以前我都是和他们急匆匆地吃,这次,我要一根一根地吃,吃完了,连汤也喝掉。然后坐在那里好好想想,明天我干什么。
拉面铺子里很清静。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那里收拾碗筷。她总是笑眯眯的,似乎天天有什么高兴的事。有时候我们吃着吃着就要打起来,她也总是笑着说:“拉面凉了,再不吃,我可要端给我们家巧巧吃啦。”巧巧是她喂的一只狗,毛黑,体壮,耳朵总是支楞着。在我们挤满屋子的时候,它就趴到门口的太阳里,懒懒得看着我们吃面。我总疑心老板娘不洗碗,会把我们吃剩的碗直接给它舔。否则,它怎么能长得那么壮?倒是那只叫果果的小猫,更讨我们的喜欢。在拉面的香味里,她总是安静地趴在屋外的一朵阳光里,像一团柔软的绒布。同样是猫,经常碰到的那只瘸了一条腿的流浪猫,就没有它幸福。
“我要一碗拉面。”我对笑眯眯的老板娘说。
“等一会吧。我把碗洗干净。再也没有干净的碗了。”她的眼睛没有离开手里的碗。好像我吃不吃拉面对她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她脸上的微笑,不容我有任何猜疑。
忽然,砰的一声响,好像什么东西砸在了楼板上。我吓了一跳,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老板娘扔下手里的碗,就朝楼上跑去。确定那声巨大的响声不会带来任何危险后,我重新坐下来,等待着那碗不知何时才能出现的拉面。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小伙子,来帮帮忙!”
我疑惑地抬起头来,“喊我吗?”
“对。来帮帮忙啊。”
我疑惑地朝上走。
老板娘正吃力地拖着一个人的上半身,他的两条腿像被水泡久了的面条,无力地垂在地上。
“帮我把他抬上去。”
我走过去,拽住那个人的两条腿,使劲往床上放。他神情呆滞,目光迟钝,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猜不出他的年龄。老板娘把他的头放好,掖好被子说:“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你先去别处吃吧,哪天你来了,我请你吃拉面。”她很真诚,完全是为我着想。
“不用,我还是在下面等你吧,你什么时候忙完了什么时候做。我不急。”
“有时间等?”
“有时间。”
我朝楼下走去,重新在我一开始就坐着的那个位子上坐好。我现在有的是时间,时间多得像冬天里的风,不,像风里的冷,想要多少就有多少。那些碗,散落在洗碗盆边,等着那个面带微笑的女人。想到她的笑容,我不禁又猜测起床上的那个人来。她儿子?她会有那样的儿子?看她的笑容,不像。
我就在那里等着。足足等了半个钟头。老板娘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数到二百二十辆车了。在我等待的时间里,路上经过了二百二十辆车。其中轿车八十八辆,卡车六十七辆,电动车六十辆,三轮车三辆,自行车一辆,警车一辆。只是看到警车时,我眼前不由自主地闪过那张陌生而又威严的脸。
“还在这里等着?饿了吧。我这就给你做面吃。”一团面就像小时候妈妈绕在手腕上的毛线团,一甩一甩,无数线条就绕在她的手腕上,好像变了一个魔术。很快,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就端到了我面前。
“赶紧吃吧。”她给我放了好多油辣子,红油上面漂浮着绿油油的香菜末,颜色艳丽得像一幅油画。
我吃得很慢。我尽量不让她感到我像一匹饿狼。
“如果你是我儿子该多好。”她看着我忽然说。
碗里的热气升腾着,缭绕着,她的脸像雾中的一枚柿子,被时光打磨着,遗忘着,干瘪的红灿灿中有无法掩饰的沧桑,于是,那红润就有了一份虚幻。
“您真这么想?”
“真这么想。你看到了,楼上的那个是我儿子。为了给他治病,我开拉面馆,他爸爸去外地打工。如果他能好起来,我们做什么都不觉得累。他小时候和你一样,能跑能跳,上学放学。后来结了婚,生了孩子。可有一天,他突然就跌倒了——孩子被他妈妈带走了。好好的日子被什么东西咔嚓一下拧断了,明明知道接不上了,但却不能停下来。如果你是我儿子,就坐在我面前吃面,那所有的日子就像一个个花骨朵了……”她的神色黯然。脸上常见的笑容不见了。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把拉面吃得稀里哗啦。里面的油辣子可能真的是太多了,吃着吃着,我觉得眼睛里火辣辣的,有液体要流出来。一股巨大的暖流从心里四散开来,冲击着我的每一寸肌肤。寒风不再刺骨,而是有一种舒服的凉爽。
我赶紧端起碗,哧溜哧溜把汤喝进肚子里。
装着擤鼻涕,我擦了一下眼睛。我掏出口袋里的钱。但是老板娘说:“这顿饭我请了。不是你,我真不知道如何把我儿子弄到床上去。”
“我并没有帮多少忙。”
“这就够啦。”她还是不接我的钱。
我只好把钱放进口袋里。一时间我很想和她聊聊,但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很想告诉她我爸爸死了。就因为妈妈经常和他吵架。他不为有我这样的儿子感到幸福,否则,他怎么会选择去死?我妈妈也不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儿子而高兴,她总是板着脸,说我们家比别人家少了什么什么。在她愤怒到怪异的声音里,爸爸常常是低着头,一言不发。
“你怎么没有去上学?我记得你以前总是和他们一起来啊。”她的脸上又浮现出我熟悉的微笑。
“我,被学校停课了。我打架。”我不想瞒着她。
“男孩子,打架是难免的。可得有节制。回家吧,你妈妈会牵挂你的。”
门口有片红绸缎一样的阳光,那只叫果果的灰猫蜷着身子,懒洋洋地眯着。如果我是一只猫,那该有多好啊,我可以不去面对那些我不得不面对的生命碎片。我会找一棵最高的树,爬上去,雪再大,风再狂,我都不会害怕。谁都知道,短暂的寒冷只会冻坏皮肤。很多被冻死的人死在内心的寒冷里。
老板娘看着我,那是母亲看儿子的眼光,温柔,慈祥,满足,欣赏……
我低了头。一时间,我像被火烘烤着的飞蛾,想靠近,又想逃离。
我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溜达了好几圈。然后躲进一家小书店,看了一晚上书,口袋里的那三块钱,我摸了好几次,也舍不得去送给那个笑眯眯的网吧老板,这钱似乎有了别样的意味。快到晚自习放学的时间了,我才敢踏上回家的路。
读三年级的妹妹正在写作业。“哥哥,你再不回来,我就要跑了。”她笑着,但眼睛里分明有什么东西在闪。
“妈呢?”
“不知道。我回来的时候她好像要出门,她拿了一个包。说让我好好等你回家。”
“就这些?”
“嗯。”
她会去哪里?我拿出手机,翻看着我上午拍的那些照片,本来,我是想让她看到这些照片的。我想让她知道,那个地方,让我恶心。
妹妹看着我。她的嘴角紧紧抿着,好像在极力抗拒着什么。
“哥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几个人一起都打不过我。看,我的肌肉。”我脱下上衣,让妹妹看我胳膊上仅有的一点肌肉。
妹妹笑了起来。她一笑眼睛就眯起来,额头上还生硬地挤出一道很浅的皱纹,好像法术拙劣的一个小女巫。
各家各户的灯熄了,妈妈没有回来;整个世界静寂得像一口深井了,妈妈没有回来;鸡叫了,妈妈还是没有回来。我不止一次想锁定那个熟悉的号码,但是又都放弃了。虽然我早已经习惯了她的离开,但这在爸爸死后还是第一次。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妈去了外地。你好好照顾妹妹。我会按时给你汇钱去。厨房油罐底下的袋子里,有四百块钱,那是你和妹妹两个月的费用,你要是提前花光了,就等着挨饿吧。
每个角落里似乎都躲着黑乎乎的鬼魅,一时间,心里空荡荡的,我又置身荒原。冷。
“如果你是我儿子——”
这句话像荒原上的篝火,忽然在我身边燃烧起来。我拥抱着它,烘烤着厚厚的冰冷,直至让自己融化。我躲进被子里抽泣着,泪水滂沱,但心里却是秋水般的清澈和平静。
早晨的阳光洒满了院子。我起床煮了面条,让妹妹吃了,然后把书包递给她。妹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怯怯地说:“哥——”
“别担心,有我呢。你好好学习就是了。”
我想我应该学着做饭了。当然,我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送走妹妹,我就开始整理鸡圈。爸爸活着的时候曾经说他想买四只鸡,两只留着下蛋,两只留着过年吃。修好鸡圈,我就去买。
在鸡圈门口的空地上,也有一片丝绸一样的阳光,我的目光一下子被粘在上面,一时竟无法挪动。
我或许可以收养那只瘸了一条腿的流浪猫,让它也像拉面老板娘的果果那样,幸福地缩在阳光里。
插图/常德强
发稿/沙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