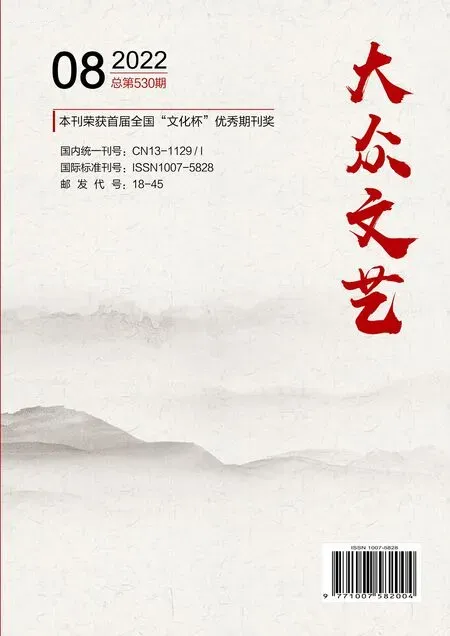影片《推拿》的身体叙事
诸亦曦 (浙江师范大学 321000)
电影《推拿》(2014)是由娄烨导演,马英力担任编剧,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郭晓冬、秦昊、张磊、梅婷领衔主演。《推拿》彰显了娄烨电影一贯的核心题旨:欲望、浪漫、对自由的追求,讲述的是关于一个渴望进入主流,更渴望真切生活的盲人群体。这是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片子,摇晃的镜头虚化了现实的本来面目,阐释了人物迷离的内心,用手持的长镜头与演员保持适当的距离,营造出纪录片的氛围,带领观众走进盲人社会的最深处。
《推拿》是一部关注身体的影片,片中的人物大多是盲人,盲人和推拿的结合使身体成为该片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符号,承担着影片叙事的主要意义。一方面,推拿这项技能使得盲人和主流社会的人群有了接触;另一方面,失明使得盲人对外界环境的感知更多的来源于触觉、嗅觉、听觉和味觉。影片通过三对人物线索勾勒了推拿馆这个与主流社会相对的边缘化存在。
一、沙复明和都红
沙复明是浪漫、诗意、渴望融入主流社会的有形化身,他的性格张扬,喜欢舞蹈和诗歌。又一次相亲的失败让他清晰地意识到,仅仅是因为失明使他和主流社会之间架起了一条不可逾越地鸿沟。都红在沙宗琪推拿中心工作时,常常会被顾客夸赞其身材和美貌,话语的调侃间显露了对身体的关注,她的存在更像是一个美的符号。美,对于盲人来说,是最沉痛的缺憾。沙复明在摸到都红的美貌后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都红,笔者认为这是沙复明在企图融入主流社会失败后,退而求其次地选择一份靠近主流社会的感情,依然失败。
小马以为休息室无人,独自悲伤,都红冷不丁地开口:“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但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就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了,那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而人和人总是让。”小马离场,都红表白被拒。沙老板不小心碰响了风铃,都红感知到这个空间场中第三人的存在。这一场戏细腻到咋舌,“看不见”使有限的室内空间变得无限大,同一场景,两个空间的三个盲人,彼此都在追求幸福,却在同一时刻,追求幸福的道路均告失败。这场戏以清脆的风铃声打破宁静,并在久久的尴尬中结束。
沙复明渴望融入主流社会却一直失败,喜欢跳舞却跳不出自己的人生,喜欢诗歌也只能独自在窗前低吟。影片中人物身体的每一次或被动或主动的伤害都会给其自身带来转机,沙复明吐血被送进医院,吐血不止。在严重的身体问题面前,他因看不见而不自知,或是自欺。都红的手指受伤后,不想拖累其他同事而选择默默离开。这些同化了盲人和明眼人之间人际关系的纯善与不安,使人性的复杂在盲人和明眼人身上做到了混淆和平等。
二、王大夫和小孔
王大夫带着恋人小孔私奔到南京投靠沙老板。工作安顿后,王大夫带小孔回家。临睡前,王母叮嘱“明天你们就搬到宿舍去咯,今天晚上你把她睡了,看她明天早上还敢往哪里跑。”身体的沦陷在王母看来更多的不是指向爱情,而是身份确认的投射。小孔在王大夫的怀抱里问道:“我们是几个人?”“我们是一个人,你要记住,永远记住”,小孔意图通过身体的缠绵用以证明爱情的存在,用朴素的话语,表达最坚固的安全感。
休息室里,窗外滂沱大雨,小孔在为金嫣按摩肚子,玩笑打闹,畅聊未来。那双手,那笑声和窗外的大雨,伴随着小孔自抑的哭声营造出悲凉的气氛,她们因为看不见而更想要握紧爱情,更需要安全感,她们唯有通过身体的拥抱给彼此温暖和力量。
王大夫自尊、自强、有责任心,是与主流社会接触最多的人。当亲人遭遇逼债,他想拿出准备结婚的积蓄为健全的弟弟还债,小孔知道后勃然大怒,“我都这样了,谁还要我啊?我跟你千里迢迢到南京来,你还说不说人话了”短暂的肉体交欢丝毫无法掩盖小孔内心的恐惧,同时表现了小孔对身体的巨大焦虑。为了践行对小孔的承诺,王大夫选择面对黑社会以刀割胸的做法,用这种对自己最残忍的做法逼退了追债人,保护家人,也保住了爱情,盲人获得幸福比普通人更加困难。于盲人而言,身体是他们对抗生活的唯一盟友,这种追求幸福的方式决绝、悲伤、血腥。盲人获得幸福比普通人更加困难,一切身体上的疼痛与血腥都是他们到达幸福的垫脚石。
三、小马和小蛮
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小马失去视力前看到世界的最后一眼,转动的车轮从此带走了他的母亲和他的眼睛。在得知眼睛再也没有复明的可能时,小马用自杀反抗父亲善意的欺骗。自杀未遂,这次小马对自己身体施加暴力的结果是他对黑暗世界的接受,从此他进入了盲校,接受了盲人的生活秩序,学习推拿作为谋生技能。嫂子小孔身上的女性气息点燃了小马的欲望,他开始莽撞地去追寻爱情。
小马与小孔的关系是出于最原始的动物本能,如同张一光理解的,如果矿难,一旦爆发,摧毁一切,张一光带小马去洗头房,把他的欲望引流到了妓女小蛮的身上。长久的陪伴,让两个人之间产生了感情。推拿与按摩都是肌肤的揉捏,通过小马的欲望和爱情而连接在了一起。小马去找小蛮,小蛮正在接客,妓女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身份的交换来建构的。“妓女的身体就其定义而言是一个具有多重性的身体,当他穿越社会经济,他自身扮演着并且也创造着激情、欲念和贪婪的叙述。”1在这个意义上,妓女作为城市中的边缘人群,通过身体同男人构造了短暂的但却是尖锐的社会关系。以小蛮的身体为中介,小马和一名主流社会的嫖客间形成了一种模糊的社会联系,小马和嫖客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正是这次暴力冲突使小马意外复明。
小马从地上爬起来,兴奋地一头扎进了街道,摇晃的镜头,模糊被放大的环境声,小马的狂笑,不停地变焦,摇晃的手持镜头,这些带来震撼的同时也营造了一种混乱感。这段独角戏,在画面和声音的围攻下,我们感觉小马能看见东西了,感觉到了盲人对于幸福生活的那种渴望。小马的复明如同一种眷顾,张一光吹笛子为小马和小马送行,营造的悲凉感如同小马离开盲人社会的仪式。小马推拿馆如希望一般在延续,爱情的激情燃烧之后,回归到最真实的生活,影片结尾,他痴痴望着在走廊上洗头的她。
盲人的异性间的吸引是通过气息、触觉、声音来完成的。都红与小马的身体碰撞后而产生了爱情;沙老板用手摸到了都红的美而爱上都红;小马通过嗅到了嫂子身上的女性气息而产生了欲望,触摸到小蛮的身体后而爱上了小蛮;泰和用“红烧肉”来比拟金嫣的美貌。身体叙事在影片《推拿》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按摩中心和洗头房是两个主要的叙事空间,都不可避免地跟揉捏身体相关。影片中身体本身,身体的欲望,是被接受与认可的,并没有带有批判色彩。
注释:
1.[美]彼得·布鲁克斯,朱生坚译.《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新星出版社,200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