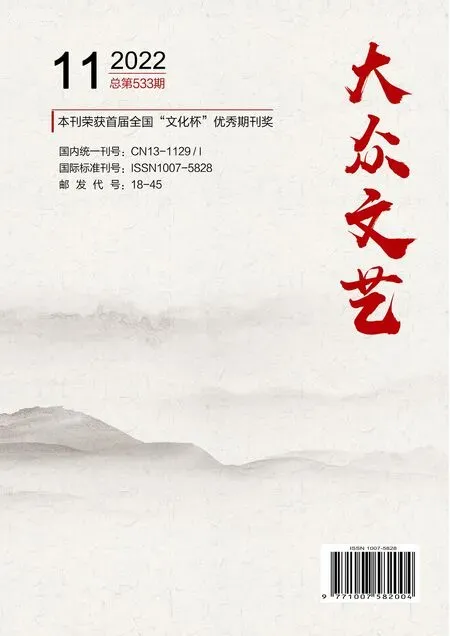让爱和自由发声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杨 珕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15000)
让爱和自由发声
——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杨 珕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15000)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一部充满哭泣、叹息、渴望、挫折、不幸和欢乐的爱情教科书”。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剖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解读马尔克斯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霍乱时期的爱情;女性形象
《霍乱时期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晚期回归现实主义的一部长篇小说。费尔明娜·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爱情纠葛为小说主线:年轻的电报员弗洛伦蒂诺和费尔明娜一见钟情并沉入爱河,但遭到女主人公父亲洛伦索·达萨的反对;弗洛伦蒂诺求爱失败,费尔明娜嫁给出身高贵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历经半个世纪,乌尔比诺医生死去,费尔明娜和弗洛伦蒂诺在古稀之年觅得爱情的核心。
在漫长的等待中,除了保留对费尔明娜忠心但虚无缥缈的爱,陌生人、妓女、黑人等622个女人在弗洛伦蒂诺的激情日记里一一登场。有人认为小说中的费尔明娜在父权社会中受到压迫和束缚,和那些成为男人激情发泄工具的女人一样是大男子主义下悲剧的存在。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她们一起为追寻爱和自由而存在发声。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角解读《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女性形象,探究女性的存在价值和马尔克斯的女性观。
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影响和渗入,是政治运动深入文化领域的结果。它主张从女性主义的全新视角对以往的文学作品重新解读,对男性文学作品中被歪曲的妇女形象进行批判,同时对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女性写作、女性语体等重新建构。
女性主义批评假定“所有的写作都打上性别的烙印”。基于作家自身的性别经验和心理因素,在写作过程中他/她往往会将性别观念一定程度上投射到文学文本上,而这些观点或固有形象则赋予文学文本不同的性别内涵。女性主义批评家明确地界定了以女性作家的创作及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其研究对象。这一批评视角以批判男性文本中的性别歧视作为研究基础,没有把研究只局限在女性的文本上,也不排斥对男性文本的探讨。
二、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分析《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学术视角首先关注的是性别差异,认为“生理性别不等于社会性别,人们习以为常的女性性别角色不是天生的,而是男权社会共谋的结果。”很多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往往被动地充当男性中心社会赋予的规定性角色,处于依从封闭孤独的境地,“被建构为贞节、物质性或精神性和非智力性等固定形象模式”。
马尔克斯在书中构造了19世纪生活在拉美地区不同命运的女性人物形象,这里以女性作为文本主要阅读点切入,可将教育背景、种族差异、社会地位等因素暂时搁置。
尽管生活在男权社会的大背景下,小说中的女性并不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而存在,她们追求性爱的愉悦体验、生活自由,这与以往男性或女性作家文本中所构建的保持沉默向命运屈服的典型拉美女性形象截然不同。虽然小说并不指向性别战争,但如果没有女性角色的串连,故事结构就不完整。书中女性与现实生活联系更为紧密,她们充满耐心与真诚;而男性虽然能做出疯狂而伟大的举措,但是他们缺乏耐心和信任,面对困境他们是弱者,需向女性寻求慰藉。
下面笔者将从单个人物出发对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作更为详尽的解读。
费尔明娜这一女性形象贯穿全书六个章节,作为女主人公她是弗洛伦蒂诺整整惦念了53年的爱慕对象。弗洛伦蒂诺在送电报时偶遇十三岁的费尔明娜,偶尔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个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书中第二章有这样一段描述“她走起路来有一种天生的高傲……就像一头小母鹿,仿佛完全不受重力束缚似的”这段描写第一次体现出年轻的费尔明娜的独特性。进入婚姻生活后,在她始终拥有自己的立场,她深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母亲、妻子、朋友、公众人物,因而她自信沉稳内心强大,敢于挑战贵族家庭的传统、辨别虚伪。她与乌尔比诺医生的婚姻生活虽然平静规律但充满矛盾:浴室里的肥皂、做饭、小便池的清洁都会引起争吵;然而暮年之时,她和医生却又能为对方灌肠、洗牙、拔火罐,这恰恰是爱情的保留,体现了马尔克斯对女性在回归家庭后付出的肯定。费尔明娜足够幸运,拥有温馨浪漫的恋爱、和谐稳定的家庭,最后重拾旧爱,老年依旧幸福。这里,马尔克斯对老年、死亡和爱情进行综合考量,将对幸福的思考杂糅在人物塑造中。
小说还塑造了其它自由独立的女性形象,比拿萨勒的寡妇、奥森西娅·桑坦德尔、莱昂娜·卡西尼亚、萨拉·诺列加、奥林皮娅·苏莱塔以及阿美利加·维库尼亚等。尽管她们没有好的背景条件,或是寡妇、妓女、黑人,但她们完全不需要颠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所谓的被压迫者成为一个压迫者,因为对于这些女性角色而言不存在任何的自卑或从属感。作为与弗洛伦蒂诺在不同时段享受床上颠鸾倒凤的情人,萨拉·诺列加甚至得出过“凡赤身裸体干的事都是爱。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以下”这样深刻的结论。
根据90年代“被伤害者女性主义”理论,所有的女人都处在被男人侵犯和攻击的危险中,女人永远是被害者因而要反驳和否认和父权扯上关系的价值观等。笔者认为小说中的这些女性角色并不是被伤害者,在她们身上并没有仇恨的身影。相反,从基本的追求经济和生活独立的女性主义原则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她们是被伤害者的对立面。弗洛伦蒂诺的母亲特兰西多·阿里萨和黑女人莱昂娜·卡西亚尼就是很好的佐证。作为单身母亲,她开了一家杂货铺,独自抚养弗洛伦蒂诺长大,甚至还会借钱给富人家。同时,她与儿子分享她对读书的感受,“尝试用自己的智慧之光为儿子引路”。
另一个成功的女性人物卡西亚尼——年轻漂亮的黑人女子。尽管被安排了最低等的职位,而她却抱着严肃认真、谦奉献的态度干了3年,她学英语、上夜校,最终付出得到回报。此外书里有这样的描述“她是他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尽管两人始终都不知道这一点,也从未做过爱。”当弗洛伦蒂诺试图向她表白并发生性关系时,遭到了卡西亚尼的拒绝。这一例子展现了女性自我觉醒的光辉,同时它说明了女性主义所强调的掌控性自由以及倾听女性声音这两个原则。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虽然被马尔克斯设定在父权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但是她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呐喊”,掌控自己的身体而不必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而生存,像费尔明娜、卡西亚尼、甚至是拿撒勒寡妇,最终都能冲破社会本身的桎梏而寻求充满爱的生活。
除了正面对女性人物进行塑造,马尔克斯将常人所解读的两性关系扭曲,改变了原本对暴力和性虐待的理解,从侧面树立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小说中第一次“强奸”发生在弗洛伦蒂诺身上,他被陌生的女人拖进房间夺去了“童贞”,尽管这样,他却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暴力的女性的真实身份,并且对这个未知身份的女性充满感激。在这里,男性成为了“受害者”,而女性则是“加害者”。小说中的第二次“强奸”发生在卡西尼亚身上,同样她也没有见到施暴者的脸,但事后卡西尼亚强调她永远记住了这个男人的体型和做爱的方式,她不但没有恨他反而爱他并渴望找到这个男人。在女性主义的观点下,强奸被视作是一种文化压迫,女性成为男性的性宣泄工具。而这里,马尔克斯在这里不仅将强奸的过程翻转同时颠覆了传统上对强奸的理解。过程翻转在于女人强奸男人,结果颠覆在于强奸带来爱和渴望而非原本会发生的仇恨。正如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1998)中所述,所有的压迫都会制造一个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二者的成长、自爱以及自尊。
三、总结
小说中,女性角色战胜了来自年龄、种族、社会会地位的偏见,获得了肉体和心灵上的自由与胜利,她们构成了故事暗含的发展线索,成为独立而不依附于男性的主体。尽管马尔克斯笔下仍然出现了对女性的暴力以及男权社会描的写,笔者认为这是社会历史背景的局限性所致。
有评论者认为费尔明娜的婚姻因女性固有的妥协性和男权社会的压迫是一场失败的婚姻,弗洛伦蒂诺那些情人的命运也是因其本身的妥协性而走向悲剧。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出发,马尔克斯在某些方面是凸显了男人在历史变动中的地位,但是笔者认为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女性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女性角色的塑造饱满而充满血肉感情,使小说的爱情的主题得到更广泛的延伸。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陈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爱情主题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3]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杨玲译). 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2.
[4]王军,侯天皓.论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范畴[J].求索,2008(10):161-163.
[5]王楠.性别剥离与标准重构—透视肖瓦尔特“女性批评学”的两个维度[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9(1):27-30.
[6]张翠梅.宽容与和谐——对《第一块石头》中女权思想的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10(3):138-140.
[7]张艳新.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林黛玉的生命意识[J].天中学刊,2014(3):85-87.
[8]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朱景冬.别具一格的爱情小说—评《霍乱时期的爱情》[J].国外文学,1990.(1):117-127.
杨珕 (1991-),女,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级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