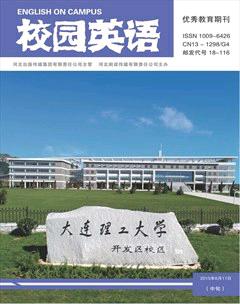浅析外训课堂中武术术语翻译的特点及原则
林燕妮
【摘要】在我国,武术术语研究一直乏善可陈,武术翻译研究类的文章或出版物不仅匮乏,其又多为琐碎技巧的探讨,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国传统武术,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笔者从外训的武术课堂翻译实践出发,系统性理论性针对性地探讨武术术语翻译的特点与原则。
【关键词】外训课堂 武术术语翻译 特点 原则
一、武术翻译研究现状
在查阅为数不多的武术翻译研究类文章时(知网主题搜索“武术 翻译”,共得到32篇文章),笔者发现绝大多数文章只是局限于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讨论,并没有从武术术语与众不同的特点出发,提出独特的视角来补充现有的武术翻译研究框架。总而言之,国内武术术语翻译研究的现状还是颇令人担忧的,整体乏力且重视不够。大多数专注于技巧方法的研究虽有个别闪光点,但还是缺乏理论的支撑,无法形成系统性地研究。另外,在规范化上,武术术语英译混乱,就连专业词典上给出的释义也相差甚远。例如,“太极拳”在《汉英武术词典》,《英汉汉英武术常用词汇》,《汉英词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和《新英汉词典》的译名就无法统一,有”traditional Chinese taiji”, “Taiji-quan”, “Taiji Boxing”, “tai chi chuan”, “shadow boxing”和“hexagram boxing”。理有恒存,却译无定法(李特夫,2006)。
二、武术术语的特点和翻译的方法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意识到,由于武术术语和其他术语特点不同,武术术语的翻译方法也应该实事求是,对症下药。诸如上面所提到的肖亚康的武术术语六特性和万军林概括的“精炼性、形象性和直观性”。但这样的分类还是系统性不足,前者过于累牍,如专业性和科学性之间就没有明显的界限,后者又过于简洁,不足以囊括武术术语的特点。因此,笔者通过总结自身在武术口译上的实践以及查阅文献所得,总结出以下四个特点:民族性、专业性、形象性以及简明性。
1.民族性。由于中国传统武术负载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天文、地理、医学、哲学、易学、军事、政治、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不能够透彻理解这些相关文化不妥善处理这些特殊的文化负载词, 就不能原汁原味地传播中国文化,不能真正地把中国传统武术推广到全世界。徐海亮提出的民族化原则就强调,武术术语的翻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不能片面追求达意而牺牲掉语言文化。
例如,在英国出版的“TAICHI for BEGINNERS”和在中国出版的《英汉汉英奥运词典》中,译者都把“手挥琵琶”翻译成“play guitar”。虽然琵琶和吉他同为弦乐器,但其抱握的姿势和弹奏手法大有不同,另外直接用吉他来替代琵琶,也抹失去琵琶作为中国传统乐器的价值,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武术术语的民族性不仅体现在术语背后的文化层面,也体现在其特有的语言风格上。另外,实践中也发现,保留中国语言特色,译语输出中尽量向原语靠拢,这样更有利于激发外国友人对中国武术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例如,在教授太极拳的时候,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把外国学员分为两个小组。当任课老师在讲解“白鹤亮翅”时,一个译员口译的版本为“raise hands and step up”,而另一个则译为“white crane spreads its wings”。虽然前者认为在口译中,为了让外国学员快速地领悟动作要领,传达最基本的动作信息,这样的译本是可取而且也是推崇的。但是实际教学中,从教学效果而言,后者更能活跃课堂气氛,提高他们的学习热情,更能激发他们学好每个动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术翻译研究中,也有人认为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某些民族文化特色不能对等翻译,例如,在翻译“手挥琵琶”时,万军林就赞同直接用“guita”来替代“pipa”,其原因莫不是因为“pipa琵琶”不为西方人所知,若直译无法达意,不被西方人接受。而这样的观点也不在少数。在《汉英武术词汇》中,甚至是网上甚为流行的武术词典里,“拳”所对应的译名为“boxing”。须知“boxing”源自于古罗马希腊格斗文化,在《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cdia Britannica)中定义为“Sport, both amateur and professional, involving attack and defense with the fists.Boxers usually wear padded gloves and generally observe the code set forth in the marquess of Queenberry rules…”而“拳”在中国传统武术中可不仅仅为用拳头的格斗技术。中国武术的拳法流派众多,有南拳,洪拳,咏春拳,少林拳,长拳等,其分类在外是形式的变化,在内却贯穿着阴阳五行、八卦太极等到家和儒家的文化思想,可谓“一阴一阳谓之道,而一阴一阳也谓之拳”(李特夫)。所以,把“拳”直译成“boxing”看则忠实,实则在文化意义上谬之千里。
因此,在术语翻译中,特别是在翻译武术术语这种载有深厚民族文化的文化负载词时,我们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的本位,保留中国传统武术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语言风格。
2.专业性。武术术语和其他术语一样,也有着其不同于其他领域或学科的独特词汇。如八极拳中的六大开动作术语,“顶”、“抱”、“单”、“提”、“挎”、“缠”等。就拿“抱”来说,抱乃八极拳中十字整劲的劲法,是精、气、神、溶为一体,刚柔相济,阴阳交错,内外合一的上乘功法。发力时上下相合,左右相合,阴阳相合皆为抱也。看了这解释还能像望文生义地把它翻成“hug”或者“embrace”了吗?
因此,武术术语的专业性要求译者必须通晓武术术语背后的概念,认真地学习和熟悉相关的专业知识,遇到难点困惑点切记自己胡翻,要虚心求教武术圈内的老师,这样在翻译武术术语的时候才能对动作通晓于心,口译的时候才能得心应手。
3.形象性。而不同于其他领域的专业术语,武术术语的最大特点就是“形象寓意”,追求美感。除了上面所提到的“白鹤亮翅”、“金鸡独立”等动作术语外,武术器械上也有“梅花桩”、“狼牙棒”、“流星锤”、“判官笔”,技法上也有“鸳鸯掌”、“剪刀指”,还有典故类形象化的术语,如“八仙过海”、“靳柯刺秦”等。如何处理这种“形象寓意”的武术术语确确实实是武术术语翻译的一大难题。笔者认为,既然是武术术语的一大语言特色,那么如果为了达意而造成的形象淡化和缺省势必会带来文化意义的缺失。
例如,试比较“鲤鱼打挺”的两种译法:“jump up from the lying position”和“take a carps leap”,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第一种译法更加直观达意,但在美感和文化韵味上,第二种翻译的形象移植更能保持“原汁原味”。而在实际运用中,笔者也发现,不少译者在教授这个动作时只把它翻译成“jump up from the lying position”,但我认为,即便是在课堂口授过程中,如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以形传形,以形象化译法为主,解释性的白描写实的译法为辅,更有利于课堂教学和传播中国文化。
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译者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处理这种形象性术语时能尽量“原汁原味”地移植,如“金鸡独立”翻译成“pose as golden pheasant on one leg”,而不是“stand on one foot”,月牙铲、流星锤、白蛇伏草、扑虎落地、金刚捣锥也翻译成“crescent shovel, meteoric hammer, white snakes hiding in grass, pounce on a tiger”。
毋容置疑,武术术语这种独特的形神兼备、以形传神的美感有利于武术的传播和接受。但要注意的是,译者在进行文化移植的时候也必须小心文化意象在两种文化中不同概念,若文化移植后的概念对等,则美不胜收,教授起来事半功倍;但若概念表述上含混不清,或缺乏理性逻辑,则啼笑皆非,事倍功半了。因此,在处理形象化武术术语时,我们必须处理好形象保留和译语接受之间的矛盾。
4.简明性。中国武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汉语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它的语言表达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李特夫(2006)就提出武术术语有“形趋简约”的特点。简洁精练,武术术语大多只寥寥数字。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尾注,习惯搭配为“名词+名词”、“形容词+名词”、“动词+名词”,如少林拳、武当剑、弹腿、虚步等。同时,语言简化也比较普遍,如“大悲陀罗尼拳”简化成“大悲拳”;“查米尔所传之拳术”简称“査拳”;而蔡家拳、李家拳、佛家拳更是简练成“蔡李佛拳”。不仅流派拳种上形趋简约,在技法表达上也短小精悍。如,“提膝独立双钩手”就描述了腿和掌的一系列动作。一腿提膝,一腿独立,双手如钩。类似的还有“马步推掌”、“歇步抓肩”等,都是把一系列动作概括成四字诀或七字口诀。
在翻译这种概括性的武术术语时要考虑到其简明性地特点,在完整表达意思的前提下力求翻译语言也能高度概括,在语言特色上达到统一。而在门派拳种的翻译方法上,笔者推荐先音译,再加释。例如,査拳和蔡李佛拳在武术词典上都已有约定俗成的译名,即“Zha quan”和“Choy Lee Fut quan”。
既然是术语,简明扼要、便于记忆交流就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尽管中西字词构成差异甚大,翻译时不能保证信息绝对对等,但至少要通过适宜译法使其相对一致又或将差异控制在最低限度。在现存的武术教材来看,部分术语翻译过于冗长复杂,其原意主要源于译者担心读者无法准确理解该术语的相关概念,所以译文更注重于注解,致使翻译变成解释。这样的注解无疑可以提高术语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但却不利于术语的传播和交流。故,控制和把握术语译文的信息密度也至关重要。
三、结语
武术术语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武术文化对外术语的重要媒介,故武术术语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翻译,就是通过“翻译容载或涵韵这文化信息的意义”(刘宓庆,1999)。这样,如何把武术术语中的文化信息给完整表达出来就成了武术术语翻译的一大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在武术翻译研究领域中,在传统的音译笔译、文化移植等翻译手法的分类说明中,音译或者说直译的地位日渐提高,学者往往愿意用大篇幅来讨论“零翻译”对武术术语的重要性,指出零翻译不是偷懒,而是在一切都可翻译的前提下的一种积极的翻译手法。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翻译武术术语的时候,必须立身于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下,充分考虑武术术语本身的特点,在“外尽其形、内尽其理”的原则下,适时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在忠实翻译武术术语的语言意义的同时,把武术内在的文化内涵准确地表述出来。只有坚持武术翻译的民族化和专业化原则,才能推广武术翻译的标准化和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1]杜亚芳.零翻译与武术术语翻译[J].搏击·武术科学,2010.
[2]何震亚.武术术语中常见的三种词汇类聚[J].学术交流,2008.
[3]李特夫.武术术语英译论析[J].体育学刊,2006.
[4]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159-172.
[5]万军林,汤昱.武术术语的特点及翻译[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05.
[6]肖亚康.武术术语的特性与标准化分析[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9.
[7] 徐海亮.武术翻译四项原则[J].中国武术,2005(1):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