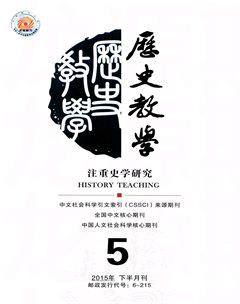唐修《晋书》使用骈语是非辨
摘 要 唐修《晋书》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史书,由唐初贞观年间房玄龄等二十余人修撰而成。由于受到唐初骈体文风盛行的影响,唐修《晋书》的部分内容采用骈体行文。从唐代开始,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评价,其中刘知几等学者对史文用骈持否定观点,而这多因他们对骈文的偏见所致,故打破个人的固囿,以历史和辨证的角度,重新对唐修《晋书》中部分内容的骈化问题及相关批评进行客观的再探讨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关键词 《晋书》,骈文,刘知几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5)10-0039-04
一
《晋书》的主体,也就是其叙述的部分,总体上都是散体行文。唐代史臣用爽朗之笔,把晋代的人与事诉诸笔端,其中不乏精彩生动之处,比如:《晋书》列传中多处可见关于伐蜀、伐吴的记叙,其事的前因后果、双方准备,以及战斗的复杂过程、激烈场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体现了唐代史臣对复杂叙事的驾驭能力和深厚的文学素养。
《晋书》中的骈体部分,主要集中在其序、论、赞中,比如:
夫文以化成,惟圣之高义,行而不远,前史之格言,是以温洛祯图,绿字符其丕业;苑山灵篆,金简成其帝载。既而书契之道聿兴,钟石之文逾广,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
——《晋书·文苑传序》①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晋书·王羲之传论》②
重义轻生,亡躯殉节。劲松方操,严霜比烈。白刃可陵,贞心难折。道光振古,芳流来哲。
——《晋书·忠义传赞》③
对于这些骈体行文,历来有很多评论。持否定观点的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是刘知几。他在《史通·论赞》中说:
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④
还有刘主持修著的《旧唐书》,在《房玄龄传》中批评道:
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由是颇为学者所讥。⑤
这些论述都着眼于《晋书》中的骈体行文,并对此提出批评。
持肯定观点的的学者,比如清代的李慈铭在其读《晋书》的笔记中说:
至其论赞则区区类别,尽当情理,诉斥奸佞,无微不著;又多责备贤者,殊上足正班史之忠佞混淆,下不同宋祁之刻而无当。行文尤抑扬反复,求得其平,往往如人意中所欲言,典切秀炼,而不以词累意。盖其书多出太宗御定,当贞观右文、儒学极盛之时,固足以集艺林之大成也。①
事实上,要正确认识和全面评价《晋书》骈体行文这一问题,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和分析。
二
骈文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体,刘师培曾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说:“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②天然骈语自古有之,《易》《书》《诗》中均可觅其踪迹,其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古代阴阳对举思维在文章中的反映,另一个方面也是中国汉字象形表意特点的一种审美体现。故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道: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③
当然这些天然骈语和作为文体的骈文还相距甚远。时至魏晋时代,人们的思想从汉代传统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文学得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骈文形成于这一时期,此时的史书也开始有骈化的倾向,比如《三国志·魏武帝纪评》言: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④
虽然这些文字还不能算作骈文,但已经比较注重文章偶对行文的外在形式了。
到了六朝时期,骈文发展到了通体完备的全盛时代,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所说: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⑤
此时骈文的鼎盛一方面体现在六朝文人对偶对、用典、声韵等骈文创作技巧的成熟运用;另一方面也体现在骈体深刻影响了六朝文化,上到诰、敕、章、奏等庙堂之文,下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书信往来,都采用骈文,故而骈文渗透到史书中成为了一种必然。在今传的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中,骈体行文随处可见,足证六朝骈文之盛,以及骈文对史书的影响。
唐代初年,骈体文风依旧盛行。因李渊和李世民及建鼎之文臣多是隋朝旧人,所以庙堂日常往来应用之文仍然沿袭旧日骈体。对此《新唐书·文艺列传》载:
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⑥
唐太宗李世民本人也十分爱好文学。《旧唐书·文苑列传》载:
爰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⑦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了皇帝的大力倡导,臣子文士自然也就闻风而起。但是,毕竟唐代的气象和隋代以及六朝时代大不相同,战乱不再,南北统一,版图大扩,国家初定。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文人的创作开始有了新的变化,虽然不乏虞世南、上官仪等文人,沿袭六朝辞藻华丽而体格卑弱的诗文创作,更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南北文风的差异和各自优劣。比如魏征在《隋书·文学列传》中就指出: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⑧
所谓“各去所短,合其两长”,正是对时代和文学进行深入思考之后进行的历史总结,魏征的《道观内柏树赋》描绘了“玄坛内之柏树”,文章自然朴素、通俗易懂,已经和六朝文风迥然不同。总之,唐初骈文既表现为沿袭了六朝骈文的一些风格,同时又有新的变化。
《晋书》的成书正处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所以《晋书》中的部分内容虽用骈体,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康健爽直。可见,《晋书》中的骈语既是唐初骈文文风在史书中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对前代修史惯例的一种继承,正如李慈铭所说:
晋书世多诋之,以其芜而尚排偶也。然骈俪行文,自六朝至五代,诏策诰诫,无不出此,是当时所尚,即为史体矣,安见论赞之必须为散文乎?①
可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唐修《晋书》的骈化行文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
为了更好地分析唐修《晋书》中骈化行文的是非问题,有必要从批评《晋书》的始作俑者刘知几开始论起。在刘知几《史通》一书中,《论赞》一章重点探讨史书中论、赞的发展、功能及其得失。
对于史论,刘知几在梳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之后,指出史论的基本特征是:“辨疑惑,释凝滞”,《文心雕龙·论说》载:“述经叙理曰论”,又指出论“辨史,则与赞评齐行”,②可以与刘知几之论相互参考。除此之外,刘知几还说:
史之有论也,盖欲事无重出,文省可知。③
也就是说史论也有补充材料的作用。不过,刘知几对史书中的史论整体上持否定的态度。他说:
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夫拟《春秋》成史,持论尤宜阔略。其有本无疑事,辄设论以裁之,此皆私徇笔端,苟 文采,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④(《论赞》)
既然论的作用是“辨疑惑,释凝滞”,那么史书本来没有费解之处,修史者为了议论而议论就是画蛇添足了。这种倾向从司马迁《史记》就已经开始,后人“苟 文采,嘉辞美句”而变本加厉就更不可取了。
接下来刘知几对历来史书加以评价,认为除了班固《汉书》史论“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⑤之外,对司马迁、范晔、裴子野、沈约等人都进行了批评,当论及《晋书》之时,便有了前文所引之文,指责《晋书》没有继承《史记》和《汉书》的传统,而受到徐陵、庾信骈文的影响,“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
对于史书中的赞,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说: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曰赞。⑥
刘知几指出赞是范晔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演化而来。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中曾说道:
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⑦
其所论和刘知几大体相当,可互相佐证。不过刘知几进一步说道:
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⑧
刘知几认为班固《汉书·叙传》“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而“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⑨
范晔《后汉书》把集合为一体的评论拆分为“赞”,附在每卷之后,使得“篇目相离,断绝失次”,后来的萧子显《南齐书》、李百药《北齐书》、唐修《晋书》都沿袭此法。对这些赞,刘氏进一步指出:
赞语之作,多录纪传之言,其有所异,唯加文饰而已。⑩
同时又说:
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11}
本来每卷有一些本无必要的史论就已经显得繁琐了,现在又加上了赞,就更不可取了。
刘知几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和他崇尚“简要”的史学观密不可分,在《史通·论赞》中他就说道:“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12}
在《史通》中他还多次强调其“简要”的史学观,比如:
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13}(《叙事》)
故知文尚简要,语恶烦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①(《表历》)
刘氏从“简要”的史学观出发,对并不是史书主体的论、赞存在本身就比较反感,所以对六朝包括唐初史书中具有文饰色彩的骈体论、赞,加以严厉的批评就毫不奇怪了,《旧唐书》中批评唐修《晋书》的论述基本上也是承袭了刘知几的观点,所以才有“颇为学者所讥”的话。
从刘知几史学理论本身来看,这种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刘知几忽视了史书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史书受其所处时代社会文化的影响既有学术的合理,也是历史的必然。第二,刘知几仅立足于史书最主要的叙事功能,追求史体的独立性,其理论忽视了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文化传统,同时也忽视了史书叙事以外的其他价值。
骈文作为一种追求形式艺术的文体类别,固有其优势和劣势。骈文最长于描绘,所以自古骈文名篇佳句汗牛充栋。其次在议论,中国古代的学术理论并不以严密的逻辑取胜,所以文章形式对内容的影响有限,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文心雕龙》。
骈文的劣势在于叙事,叙事以内容为重,故而不适用于骈文,所以古代用骈体叙事之文不多,佳作则更少,这也是历来史书的主体,即叙事部分多用散行的原因。史书中的论、赞以及小序,则偏重议论,所以这些部分用骈体行文并无不可。
唐修《晋书》中的序、论、赞或是太宗御制,或是史臣修撰,总体上工整而不失流畅,虽雕琢却并不失之于糜繁,所以才有了前文所引清代李慈铭“典切秀炼”和“集艺林之大成”的赞语。
不过从唐代开始反对骈文的声音兴起,并逐渐形成了对骈文的偏见和歧视,刘知几就是这个浪潮中的先驱,因为刘知几在史学领域有着重要影响,故而他的批评使得唐修《晋书》的骈化行文成了后来学者不时提到的一个学术问题。今天,骈散之争的学术背景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应该用历史和辨证的视角看待唐修《晋书》的骈体行文,用更为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简介】王荣林,男,1985生,辽宁铁岭人,辽宁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骈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