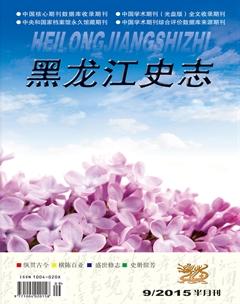1946年“制宪国大”的区域代表选举述论
杜云燕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1946年“制宪国大”的区域代表选举述论
杜云燕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1946年“制宪国大”的代表历经十年,终在1946年完成代表选举。该选举分为区域选举、职业选举、特种选举和国民政府指定等。其中以区域选举人数最多,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此文述论,以期为我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贡献锦薄之力。
“制宪国大”;区域代表;选举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依照《建国大纲》规定:“全国有过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1]鉴于国内要求民主、结束训政、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呼声愈加高涨,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议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应于十月十日前办竣”。[2]因这次国民大会的任务是制定宪法,故称“制宪国大”。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历经十年选举才于1946年11月15日走进“制宪国大”的殿堂。此期间,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与产生几经周折、变化,选举闹剧层出不穷,迄今为止,关于此问题只在少量著作中点到为止,尚未有专著论述,本文拟从“制宪国大”的区域代表选举为论点,从其法律法规、选举实况及评价三方面展开,对“制宪国大”区域代表的选举问题加以梳理分析,从而使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内容更加深入和丰富。
一、“国大”代表选举的有关法律规定
1936年5月5日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第廿八条规定:“国民代表之选举,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3]同年5月14日,国民政府又相继颁布《国民大会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7月1日公布《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4](以下简称《细则》)。此后,南京政府成立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事务筹备委员会和各级选举机构,曾一度积极办理国民大会的选举。
有关法律文件的颁布,规定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和产生的原则、程序和办法。首先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方面,《五五宪草》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依法律选举代表权,年满二十五岁者,有依法律被选举代表权。”[5]并规定国民代表任期六年。《选举法》的规定与此无大异,即“中华民国人民,年满二十岁,经公民宣誓者,有选举国民大会代表之权”,“年满二十五岁”,“现为该选区内之人民”可作为该区候选人,即有被选举权。[6]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较民国初期的议员选举,此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没有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范围大大拓宽,只要达到年龄,进行宣誓,就可获得选举权,尤其候选人只要为本区达到年龄者即可。
其次是选举方法的规定。《五五宪草》规定:“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且“每县、市及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一人。但其人口逾三十万者,每增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人。”“县、市同等区域以法律定之”。[7]而《选举法》中的规定与之稍有出入,“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记法行之。其选举票应载明候选人全体姓名,由选举人就中圈选一人。”“以得票比较多数者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票数相同须决定何人当选时,以抽签定之。”[8]区域代表由该区各县之乡长、镇长联合推选候选人,其名额为该区应出国民大会代表名额的十倍。
第三,各代表种类人数名额分配。除由国民政府指定24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260人为国民大会当然代表外,由人民选出者共1200名。依区域选举代表665名,“各省市应出区域代表名额依人口比例,每省人口未满百万者出代表9名,百万以上每增80万增代表1名,但以44名为限;每市人口未满20万者,出代表2名,20万以上每增30万人增代表1名,但以8名为限;至于各省选举区代表名额的计算,以全省所辖县市数除以该省应出代表的名额,为每县应出代表率,再以所得代表率乘以每个选举区所辖县数,为该区代表的名额。”[9]
尽管法律条文中展现的是“普通、平等、直接”的民主选举图景,但国民党实行的威权统制,牢牢掌控立法权,“制宪国大”的代表选举亦受于鼓掌之中,使“制宪国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大打折扣,成为名副其实的披着羊皮的狼,有人戏称“所谓的国民大会,无论如何,不能叫做国民大会,只能叫国民党大会”。[10]
二、捉襟见肘:区域选举的实际操作
相关法律程序公布后,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设立了选举总事务所,各省市也建立了选举事务所,选举工作在各区域陆续展开。区域选举需要经过初选和复选两个过程。
首先进行初选。确定选民,接着公布由各乡、镇长推选的候选人名单,召开选民大会,投票选举,开启代表的初选工作。
选举的前期工作是确定选民,“西方在20世纪之前大多已有了人口普查,根据普查,便可确定人民的选举权。”[11]然而,中国直到1953年才有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前这次国大选举权则是通过市府令公安局呈报全市户口实数统计来确定的。因国民政府在地方上实行的是保甲制度,曾下令编查过户口,遂编查竣事后,“将户口根据最近编查保甲之户口实数,”在接到电报一个月内,“报由贵府汇齐报部,其未举办保甲地方,务于三月十日以前,编查完竣,并将户口数目分别列报,”以备复查。[12]从编查户口中筛选,合格者才有望成为选民,继而由乡镇坊公所“将该管区域内曾经宣誓领有公民证之男女公民,造具选民册,于投票一月前,逐级汇报呈省事务所审核,并公布之”。[13]据无锡县1936年选民统计情况,“本县各区公民宣誓登记人数,经县府于八月二十二日呈报江苏二区代表选举事务所在案,兹各区长继报补行公民宣誓登记人数,为十三万四千零三人,前后共计五十二万三千五百十四人,昨由陇县长转报二区备查。”[14]临城于1937年6月基本完成选民登记,“全县各项选举人工为二万四千零七十人,已电省核辨。”[15]总之,由区公所令各保造报选民名册,再由区报市政府审核复查,而后发回各区列榜公布,以此产生选民。但在实践过程中,伪造名册之事屡见不鲜。
确定选民后,即可在各区开展竞选活动。官本位意识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小小区域代表即可令人激动不已,纷纷跃跃欲试,想品尝这一顿迟到的“民主大餐”。依照实行欧美式的民主,竞选人应在选区内争抢发表竞选演说,宣传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张,为民众谋利益等口号,借以争取选民。以四川为例,竞选手法大致有:①与报馆有关系的,便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我若当选,便将如何如何的发挥自己的抱负;②散发宣传品,标榜过去自己的经历及自己的竞选纲领;③通过家庭主妇及学校学生“走内线”,或者以送打防疫针为号召(这年成都市曾发生霍乱,死人甚多);④在住家附近茶馆发表竞选演说,由保甲长动员群众来听。[16]以上方式,可谓洋洋大观,但终究有了民主的样子。
接下来的选举投票大会,由县镇长主持,公民持公民证到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即可,投票完毕,由各选举事务所清点票数,按票数多少依次列出候选人名单,得票多者当选。并将初选候选人名单履历等详细资料造册呈报选举总事务所,总事务所根据所报名单,仔细审核无误,交国民政府裁示,备案准批。
复选相对于初选来说,程序更加简化。即再次审查身份,核实候选人资料,从初选人名单中,正式选定国民大会大表当选人,以使所选之人务必符合《选举法》所规定的代表条件。
然而即便如此,实践起来还是偏了轨,手续看似严密公正,实际却大大走了样。县、区长暗箱操作指定候选人之非法特权,又为他们增添了隐形魅力。国大北平区域代表60个初级候选人皆由16个区长偷偷摸摸地指定,“现在又定于日内开始所谓正式选举,办法是由政府从60名初级候选人中再指定正式候选人,然后命令被所谓‘公民宣誓’严格限制了的公民,在这些指定的候选人名单上划几个圈,就算选出了一批所谓国大代表。”[17]此外,四川还有土豪劣绅捐班出任国代,势力更大的则有可能直接获得国民党提名,难免会有民众大惑不解,“喂!代表先生们,你们是代表谁?我们并没有选举你们,你们是从那里来的呢?”[18]更有甚者,为拉选票,“大肆夸大捏造自己履历,如吹嘘自己是大学生,学士渊博,创办晴川中学,热心教育,主持抗日救国会,抵制仇货”等,[19]在竞选中,竞选人勾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拉关系,讲人情,金钱贿赂,毫无民意可言。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实施民主,原是天经地义之事,可实际付诸施行之际,却令人大跌眼镜,《选举法》成了一纸空文,民主形式下的选举俨然变成了少数人操控的政治游戏。
三、评价
区域选举制原则上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一实行普选的创始之举,亦是实现孙中山“直接民权”这一伟大构想的必要步骤,即在地方的县一级实现直接民权;在中央一级由各县选举一人组织国民大会行使简接的“直接民权”,并将此愿望在《五五宪草》中明确规定下来。
进步机构和人士在选举之前所做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以云南为例,针对“多数选民既未受过教育,亦未经训练”的情况,他们提议采取一种临时的补救办法,灌输给选民一些关于选举的基本知识,并由选举事务所来办理此项宣传工作,“最好由中央编印若干小册,层转各地仿印,务须传遍各乡各村,由小学教师、保长、及其他知识分子,分别用抄贴和演说的方式,转告人民周知,办理投票时,并且应该随时摘要登报端,并贴于公共场所,让选民在这次大选前多所接触,一面可以提高人民对选举的兴趣,俾能踊跃参加,一面可以减少选举的错误、弊病和纠纷,以期结果良好。”[20]但是临时采用注入式的宣传,其效果毕竟有限,一般选民仍然很难无师自通,必须进一步由适当的人才出来负责领导,然而由于境遇悬殊、利害各异、流品不齐,遂不能让自命高民一等的士大夫之流包办选举,因此,他们“主张由知识分子中的平民,(即平民中的知识分子)自动的组织起来,担负领导平民从事的政治改革责任”。[21]初衷和设想总是好的,但实践起来却是困难重重,捉襟见肘。
首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无限扩大,使达到一定年龄的国民都可能获得选举权,或成为候选人,表面上看起来是扩大了民主范围,实际上在区域范围内却为舞弊提供了方便。就选举权来讲,没有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文盲选民占很大比重,甚至连圈写选票的能力都没有,很容易被人一手包办。即使是有知识的人,往往也是漠不关心,自命清高,有的看到过去选举不能尽满人意,不但不积极参加,甚至还要冷饥热讽,便有了“无知无识的不能参加,有知有识的不肯参加”的尴尬局面。如南京市“昨日开票统计,公民有放弃选举,亦有全区公民半数之投票,如养虎巷有公民证公民11 042人,投票达5 442人,小胶巷有公民证公民9 412人,投票达4 579人;其最少者,通贤桥公民4 810人,投票只269人,则投票公民竟不到十分之一。”[22]竞选人方面,如各地新旧权贵、贪官、奸商、豪门、巨室等都想跃跃欲试,也不免大施长袖多财的通神技俩来诱买县、镇长和民众。“他们不但有钱有势,而且有党羽走狗,在平民尚未普遍觉醒的时候,其力量相当顽强而且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保身独善明哲,往往畏之如虎,不撄其凶锋,”[23]选民往往受其左右,从而使选举变成为虎添翼的“妙法”。
其次,中国人自古以来讲人际关系,寻找关系来达成目的快捷方式在中国官场职场上更是普遍,这与中国历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有很大内在联系,尤其在大变革时代。张朋园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中论述贿选、腐化在北洋时期何以会那么严重,其中一点用在这里颇为适用,“长远以来,科第功名和中下层官吏都可以因捐纳而获得。议员或国大代表虽不是官吏,但视之为官吏者,大有人在,一官半职的心态,贿选买票并不偶然。”[24]以区域为单位的普选方式,很容易使得乡绅在争取有限的乡镇长和选民方面发生矛盾。以苏州为例:一个浙赣路局的局长,他回到苏州去竞选,结果还是给一位地头的乡绅打败了落选了。这一件竞选,还引起了苏州新闻界的大分裂;那位乡绅,居然有力量封闭了一家报馆,不让他们有复刊的机会。那家报馆的记者,愤而投向民主同盟,又成为反政府的潜伏力量。“国大代表”的竞选,颇似群狗争骨,造成了地方上的空前大混乱[25]。
再次,区域代表分配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虽然规定每县、市,其人口逾三十万者,每增加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人。但中国区域辽阔,各选区大小、人口差异仍然很大,名额比例难以均衡。且近代中国处于巨大转型期,战争与自然环境的恶化,近代化的加速前进等因素,加速了区域间的人口流动,不仅选民难以确定,更加影响了区域代表名额的分配。同时,由于时局的关系,给选举造成极大困难,一些地方无法依法有序地进行。
第四,可能强化一党专政。国民党根据自己利益指定候选人,任命国大代表,不管是抗战初期还是内战初期,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处于弱势地位,共产党还曾一度处于地下状态,这也就使他们因为“非法”丧失了选举资格,无法成为国大代表。此外,经过民国十六年的清党,国民党县党部,早已成为地方绅士的变相俱乐部。“国大代表”,很多便是通过那些俱乐部产生出来的;国民代表大会,就其代表身份来说,可以说是全国乡绅的总结集;下与老百姓无关,上与政府无干,国民党就把自己的政权,建筑在他们的基层之上。实行区域选举,无疑使国民党的代表最多,高达80%。因此区域选举制的不完善和战后特备遴选更加强化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从而也引起其他政党的不满,国民党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民心逐渐丧失。
总而言之,1946年“制宪国大”代表的选举采取区域选举、职业选举、特种选举等选举方式,因为初创,现实环境又比较恶劣,实践过程中有所出入也在所难免。通过对1946年“制宪国大”代表区域选举的法规制定、选举结果以及对此选举的评价,我们可以对中国历史上这一普选有个较详细的了解,并通过对选举中各种问题的阐述,以期为我国当代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良好的借鉴。
[1]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下)[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567).
[2]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384).
[3][5][7]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6年5月5日)[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M].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1(277).
[4]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 [N].内政公报. 1936-9-7(46).
[6][8]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1937年5月21日)[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M].南京:南京古籍出版社,1991(260).
[9]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印.国民大会实录[Z],1946(74).
[10]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7).
[11][24]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论述[M].上海:三联书店,2013(212)(162).
[12]市府令公安局呈报全市户口实数统计[N].申报,1936-1-13.
[13]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施行细则[N].益世报(天津),1936-6-25.
[14]无锡区域开始选举[N].申报,1936-8-31.
[15]临城登记选民[N].大公报(天津版),1937-6-20.
[16]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C].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189).
[17]河北省广播电视厅史志编委会编.河北省解放区广播史料之二: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Z],(136).
[18]舒泽.“国大”普选的大丑剧[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2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361).
[19]刘钦珊.我竞选“国大”代表的回忆[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2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349).
[21][22][23]方国定.民意论集[M].出版社不详,1947(74)(75)(73).
[25]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总事务所三日刊[Z].1936-8-18,转引自刘会军.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与产生述论[J].民国档案,2008.2(83).
杜云燕(1992-),女,山东菏泽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区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