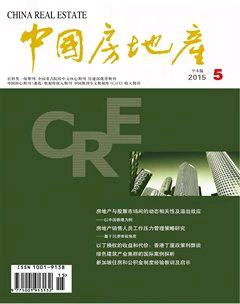以丁换权的收益和代价:香港丁屋政策利弊谈
摘要:丁屋(Small House)是香港新界的特殊房屋形态。尽管丁屋的屋宇属于私人,但政府仍然保留了土地所有权,即凡转让给非原住民的丁屋,都需在对外转让的时候按照市场价向政府补足地价。政府的这种置换安排有一定积极意义,即在保留政府很大一部分土地权利的同时,有效降低了管治成本,而同时丁屋的发展仍处在可控范围,即在今后涉及到城市更新时,政府仍可以以较低成本重新买回这些屋宇。当然,有得必有失,丁屋政策也不是全无代价,由于政府严格限制了这些屋宇的尺寸,使得丁屋容积率偏低,在香港寸土寸金的大环境下,这些屋宇在占地方面就显得超额,而这样的资源搭配就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福利损耗。同时,丁屋政策转移给原住民一定的租值,这使得很多原住民选择不再工作,成为食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香港本就稀缺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村民子子孙孙都享有这种丁权,这种约定使得政府不得不保留大片土地用于应付未来的丁权行使,这使得可供政府自由发展的土地过少,从而导致市区过于拥挤。讨论香港以丁换权的收益和代价,尝试分析丁屋的历史权利界定对香港地政民生所产生的深远利弊,并以史论今,通过对比香港丁屋和内地城中村发展的差异来为内地制定相应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香港土地史,权利置换,产权和制度,土地政策,法律与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9138-(2015)05-0018-24 收稿日期:2015-04-16
1 丁屋缘起
1841年,清政府战败,被迫和英国签订了《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政府。同年,英国军队占领了香港岛,作为远东英军的驻扎基地。清政府最初以琦善无权割地为由,拒绝承认《穿鼻草约》。不过割地一事在第二年清政府再次战败之后成为事实。1842年,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战败,于是重蹈覆辙,被迫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割让给了英国。而英国人获取九龙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建立战术缓冲地带,以维护香港岛上驻军的安全。
与割让港岛和九龙不同,英国人获取新界的方式是通过租借。1898年,英国政府以香港的防卫需要加强为由,逼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到新界深圳河以南地区(除九龙城寨),以及附近200多离岛一并租给英国,为期99年。
因为新界并非割让,英军占领了新界之后,发现无法像从前一样简单地宣布所有土地属于英国女王。而当时在新界散布的原住民手中所持的,乃清政府颁发的永久地契,明确规定了土地的私有性质,并且没有限制土地用途,因此殖民地政府若强行占地则会面临舆论和实际操作两个难题。1905年殖民政府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将新界土地产权变为承租官契,即土地甲方为英国皇室,而原居民变为承租乙方,必须每年缴纳地税。这种方式的实质还是剥夺了原业主的土地所有权,但这名义上的权利变化并不影响当时村民对土地的实际使用。新界当时还是农村,村民所需的只是耕种以及本户居住的权利,而转让和开发在当时并不普遍,因此这种承租契约虽然侵犯了原住民的产权,但在操作中并未产生太大的问题。
1972年,当港英政府决定开发新界的时候,土地权利的矛盾冲突就到了必须解决的关头。即便之前签订了承租条约,村民仍然有抗拒征地的理由,因为他们原本拥有的就是永久地权。因此若要获得村民的支持,殖民政府必须给予村民一定的权利置换,使得抗拒征地的净收益低过承认承租条约的净收益。1972年12月,政府出台了《新界乡村小型屋宇政策》,规定凡当年参与签约的新界居民,年满18岁的男丁,一生都可获取一次特权,修建1栋属于自己的小型屋宇。这样的屋宇被严格控制在每层700尺大小,一共3层不超过25英尺高。因为限于男丁,这种屋宇被称之为丁屋。丁屋政策给予村民的好处是世袭的和可扩展的,可扩展性源自对于丁权数目的不限定性,即子孙中男丁越多,则可获取更多的丁权。远大于村民抗拒征地的好处,因而获得了推广,下面会详细讨论这一政策的具体内容。
2 以丁换权的权利界定
在英国政府参与前,新界的地权是永久的私人地权,持有地契的权利人可以自由使用其所拥有的土地。而在英国政府参与后,新界土地变为承租性质,即殖民政府为甲方,拥有处置权,而村民变为乙方,获得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利,并且有用途限制。丁屋所处的土地,也受到该承租契约的限制,即村民获准修建总面积2100平方尺,不高于25英尺的3层小楼。
丁屋政策是政府为减小地权转变过程中的执法成本而做出的妥协。作为对于强制村民让出永久地权的补偿,政府给予了一定优惠政策,即丁屋在村民自己居住期间可豁免差饷,而差饷原本是任何私有土地都需承担的费用。更重要的是,丁权属于世袭和可扩展权利,即如果该原住民家庭生育了多个男丁,那么就可以拿到更多的丁屋土地,这等于是将村民现有的固定大小的永久地权拿走,但置换成对将来更多土地的丁权,即便这些只是使用权,但毕竟权利所辖面积可随人口增长而扩大,政府也必须预留大片丁权土地以应付将来的人口增长。因此这些权利置换使得丁屋政策在当时更容易推行。
除尺寸限制外,丁屋的转让受到严格控制,在转让时,新业主必须按照市价向政府缴纳一定的土地费用,俗称补地价。这一措施排除了非原住民染指丁权的可能性。当然,如果村民并不出让其丁屋,只是永久用来收租,那么政府的补地价部分就拿不到,也会一并被村民收走。
丁屋政策以未来的丁权置换新界原住民现有的私有土地,因此获得了成功推广。这一政策的权利界定基本是明晰的,政府给予每个新界男丁的只是三层小楼的使用权利,这权利包括自己住和出租的收益,并且通过补地价政策(即丁屋在对外转让的时候按照市场价向政府补足地价)排除了非原住民染指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丁屋引起的纠纷有限。但丁屋的一个悖论在于丁权的世袭性和扩展性,即子子孙孙都有这样的权利,那么随着人口的增长,所需土地无穷无尽,而政府将来并无这么多土地用于行使丁权。
合理的解释在于这一权利安排在港英政府期间是可行的,因为考虑到99年的新界租期,港英政府的此项置换安排实际上是将便利留给了自己,问题则留给了将来香港回归后的中国香港政府,因为在港英执政期间,考虑到人口繁殖所需时间,行使丁权所需的土地并无可能在99年内发展到无法想象的地步。
事实上,这一权利安排引起的问题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已经开始凸显。据新界乡议局2003年的估计,香港有24万新界男丁拥有丁权(刘敏莉,2013),即便以0.5的建筑覆盖率计算,不考虑人口增长,都需要超过3700公顷的土地来安置。而根据最新统计,预留的政府乡村发展土地只有3147公顷(香港规划署,2012),远远不够。一方面是土地的紧缺,另一方面政府则必须预留大量土地以供未来村民的子孙行使丁权。政府也在考虑修改丁屋政策,考虑将丁权中的三层小楼改变成高层建筑中的一定面积,但修改政策成本很高,在政治上并不讨好,因为新界居民必然反对。
3 丁屋政策利弊谈
丁屋政策对香港的地政民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影响源自于特定的合约安排对经济结果可能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这符合真实世界中经济学的一般结论,即在非生产性成本大于零的时候,经济结果只可能是收入转移,福利损耗,或二者兼备。
对当前权利的索求和对未来权利的放弃为港英政府的丁屋政策的实行带来了便利,这减小了丁屋政策的早期执行成本,即早期的社会成本,为港英政府发展新界带来了契机。当然这一便利的背后则是未来的无穷无尽的丁权问题。
就收入分配而言,丁屋政策以期权换权利,减小了当时的执法成本,丁屋的发展在政府可控范围,因此对当时的香港经济有利。但从长远来说,则有一系列的问题。第一,该权利的置换是否是等价?从短期来看,一部分权利及其附属收入是从村民手中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因为政府是获取了新界原住民手中永久地权的一部分。但从长期看,政府是用无穷尽的期权去换取当时的权利,因此最终仍然是村民及其子孙获取了更多权利,当然,在1997年之后契约甲方改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因此最后负担损失的并非是英国政府。这一权利置换尽管无法计算具体数额,仍可以简单描述为土地权利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转移到村民手中,然后从村民手中转移到了港英政府手中。或者用权利相欠来描述更为清楚,即港英政府借取村民土地权利,而还债人需要用超额权利去偿还,这个还债人却变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假如现在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当时亦可参与政策制定,那么这政策必然不能通过,但因为当时并不存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而中国政府当时亦未参与政策讨论,因此这一权利转移是在权利最终移出方并未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对于参与政策的港英政府以及新界居民来说则是皆大欢喜,因此政策获得了成功推行。
从对地政民生的影响而言,丁屋政策并非一定会导致社会福利损耗,其实际产生的损耗则源于城市垂直发展的需求,即当新界城市化进度加快之后,三层小楼的尺寸安排损耗的是本可以修建的超过三层部分的租值。根据统计(刘敏莉,2013),自1972年到2011年,政府批出的位于乡村发展区内的丁屋数量总计为36912个,按照香港市场此类住房每层每月租值为1万元港币计算,若以最高可建33层为标准,则每月损耗社会福利最高可达110.7亿元。这一损耗并非是政策之过,而源于时间变化带来的预测误差,其损耗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将来政府可以考虑征收丁屋并重建为高层住宅。而将村屋控制为三层小楼可能也包含了政府这一重建考虑,即这会使得重建的补偿问题较为简单。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实施起来会有重重阻碍,所以,即便丁屋政策的权利界定清晰,要维护三层以上空间的政府所属权利仍然不容易(名义权利和实际控制权分离,并且变动合约的成本高企),而实际损耗难以避免。
除尺寸过时导致的损耗之外,为应付未来丁权而预留的大片土地,则损耗当期福利。参考前段的计算,以预留的3147公顷土地可供修建20万栋丁屋为标准,这些损耗最高每月可高达600多亿元港币(按前文提到的如建非丁屋平均可建33层为标准计算)。当大量香港市民挤在狭小空间里蜗居之时,新界的大量可建设用地却一直闲置,无法用于建设,村民未来的子孙还未出生,政府无法同村民未来的子孙谈判达成任何合作,谈判成本无穷大。这种权利约定对于土地资源紧缺的香港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亦解释了香港市区规划得极其拥挤,而郊区土地却大片闲置这一畸形城市规划的形成原因(这种畸形城市发展从很长时间段看都难找到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新界原住民享受的这一特权,亦导致食禄阶层的产生,这也浪费了香港本来就稀缺的劳动力资源。
当然,除此之外,丁屋政策并未赋予妇女丁权,因此在历次女权运动中备受诟病,这引起的社会冲突,也可计算为福利耗损的一部分。
4 和内地城中村的对比
不同的产权厘定,使得香港丁屋的发展有别于内地城中村。换言之,为减小执行成本所作出的权利置换安排,其导致的收入转移和福利损耗本身就是政策的一部分,是政策的主动安排。而内地城中村的不明晰产权,则导致了城中村发展的失控,即城中村的发展偏离了权利设定的初衷,造成了事实上的权利转移和损耗。
在聂致钢和黄国俊(Nie and Wong,2012)的文章中谈及,内地城中村不完整和不明晰的产权导致宅基地上着建筑的密度失控,形成了握手村,即城中村的超建,并导致了社会福利损耗。这一结果建立在城中村和非城中村小区的租值对比之上,也证实了城中村中缺失的城市规划管制对于非城中村经济效率而言有正面效果。超建导致的损耗加上政府的部分地权以及较小的协商成本,则给城中村建筑带来了较短的寿命(相比正规产权建筑的超过20年的经济寿命,城中村建筑的经济寿命大约10来年左右)。
这些现象在丁屋中都没有出现。丁屋是受到政府严格管控的产物,因此违建虽有,却并不普遍。很多时候,所谓的违建只是村民在楼顶搭了一个简易的雨棚而已。相比内地城中村,丁屋的执法成本更低,这源于事先的明晰产权。村民因为对未来的丁权很满意,所以对于承租契约的认可度很高,他们也担心若不执行契约会损失掉未来的丁权,因此违法成本高企,这也减小了政府的执法成本。而相比于三层村屋,政府执法的动力也来源于保护自己的更多的可收回的租值,即执法能给政府带来更高的租值回报,远超过执法成本。试想,拆掉一栋三层小楼而代之以55层的高层建筑可能获取的租值,怎不会远超过执法的成本?即使政府未必有拆迁计划,但潜在的高租值也可能是支撑政府执法的动力。不仅如此,香港有相比内地更充足和高效的常备警力,人口约700万的香港的常备警力有36535人(香港警务处警方统计数字,2012),占人口比例约千分之五,而人口过千万的深圳的常备警力则只有1万余人(Nie,2014),只占人口比例的约千分之一,而且深圳关外警力尤其薄弱,警员占总人口比例只有约万分之五。这也有效降低了额外的执法成本。
而反观内地城中村的发展,由于事先权利界定不清楚,政府能对村民施加的法律成本有限,执法有困难,因此城中村的高度和建筑密度都不容易控制,这形成恶性循环,即越不容易控制则违建越多,则可回收的可能租值更少,则更难控制。这在警力不足,而租值也不够高的深圳郊区尤为明显,即十几层的违法建筑在深圳郊区比比皆是,而政府则无能为力。
5 结论和启示
综合上面的讨论,香港的丁屋政策起源于1898年新界租让给英国政府之后租权与原住民的永久地权的权利冲突。而作为一种解决冲突的合约安排,港英政府以未来的丁权置换当时的地权,即所谓的“以丁换权”,减小了当时的执法成本,这对于港英政府推行香港新界的城市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别于内地城中村的例子,其影响机制较为简单,即权利的转移是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到村民,再到当时的殖民地政府。 机制虽然简单,但其影响却很深远,整个香港的地政民生都因之而改变,按照上文中的估算,每月的影响总值可达将近1000亿元港币。这只是影响总额,并非是净损耗,估算后者会更复杂,因为还需减去居住现状所能挽回的残值。除执法成本和社会冲突所产生的社会损耗外,这些影响主要来源于三个途径:一是丁屋尺寸过小带来的丁屋上部空间的浪费,损耗社会福利;二是为保障未来丁权而荒废大量新界土地,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三是形成了食禄阶层,造成了劳动力闲置。这些都是其政策本身能预料到的产物。而内地城中村的发展,则偏离了权利设定的初衷,政府的一部分租值被强行转移到了村民手中,而政府在特定条件下挽回租值的办法则仅仅限于对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而伴随着改造的则是浪费,比如十年的新建筑也被推倒。因此,内地城中村的社会损耗则主要源自超建和拆迁,而其经济结果往往更为激烈,其对内地地政民生的长期影响虽然还未完全浮出水面,但可以预期到同样会很深远。
香港丁屋政策的发展历史以及同内地城中村的比较带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几点。
第一,权利在法律意义上的清晰界定是经济效率的保障,因此当权利界定不清晰或者两种权利起冲突的时候,经济结果就可能偏离最优。丁屋政策作为解决港英政府租权和原住民地权冲突的产物,其最终结果仍然带来了权利转移和社会损耗,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政策带来的麻烦仍将深刻影响香港的城市规划、土地政策以及土地市场。当然,这并非是说清晰的权利界定一定不会带来收入转移或社会损耗,而只是说清晰的产权对经济效率有一定的正面效果。
第二,执法成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香港新界的租权和地权的冲突,带来了丁屋政策,这是一种新的产权安排,同时也是对于执法成本这一非生产性成本的一种适应(比如港英政府为了减小执法成本而牺牲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权益)。而其经济结果也同样受到各种非生产性成本的影响(比如名义权利和实际控制权分离导致丁屋三层以上空间无法有效利用)。同样,内地城中村的发展,也反映了高额执法成本对于经济结果的影响,即政府对城中村的超建违建的放任本质上源自高额的执法成本,这里有产权不清晰的作用,也有警力配比的影响(比如前段所述的深圳郊区警力配比失衡导致大量违建的例子)。当然,其他类型的非生产成本也必然对经济结果产生影响,而对于其中之一的执法成本的强调并不否认其他成本的作用,也不否认产权明晰的重要性。因此,香港丁屋政策以及和内地城中村发展的对比带来的启示延伸了科斯定理(Coase, 1960)的具体涵义,即产权和交易成本都适用于成本分析,都对经济过程和结果产生影响。而从一般意义而言,对丁屋政策的成本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香港城市拥挤,郊区土地浪费背后的苦衷,也可给内地正在进行的保障房安居房建设提供决策分析参考,这启发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谨慎。不仅如此,这些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才能制定合适的法律以降低执法成本,达到现实约束条件下的社会最优。
第三,以丁换权有利有弊,这提醒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审慎。当年港英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因为代价无需自己承担,因此更多的是考虑到当期收益,这给香港回归后的土地政策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内地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的时候,收益和代价的承担方都是自己,因此制定政策时更加应该审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前期的详细利弊分析就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1.Coase,R.H.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
2.刘敏莉.小型屋宇政策II:最新发展,思汇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2013.http://www.civic-exchange.org/wp/wp-content/uploads/2013/04/SHP_cn.pdf
3.Nie,Z.A and Wong,K.C,Why Build More to Earn Less:Property Rights Implications of Urban Village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2012.12
4.香港警务处统计数字.http://www.police.gov.hk/info/doc/2012_police_in_fig.pdf.2012
5.香港规划署.审核2012-13年度开支预算,答复编号DEVB(PL)223.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press/exam12/pdf_c/223-3491.pdf.2012
作者简介:
聂致钢,香港大学房地产与建设系博士,现为南京财经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房地产经济、价格理论、土地产权以及制度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