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上塘书》(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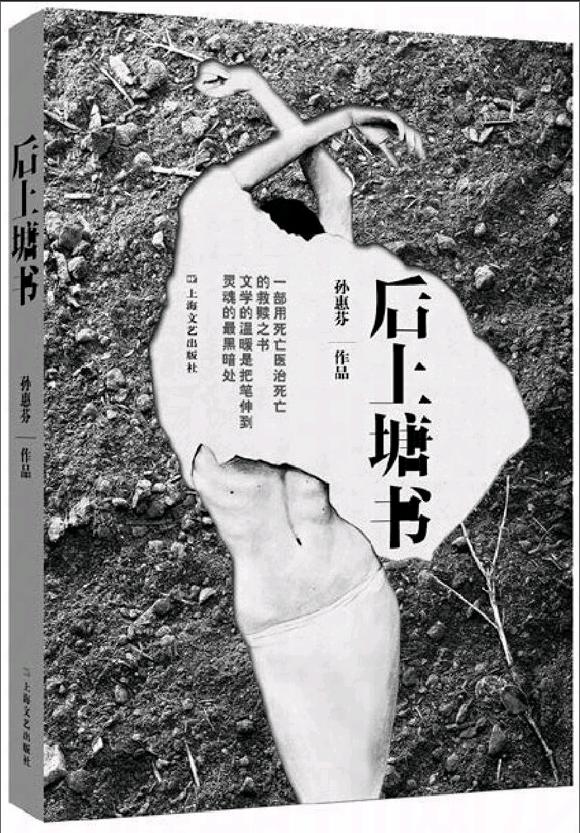

叫声在空中回响时,上塘的村庄、草垛、街道以及街道外面的山野统统染了一层红,像血。这是傍晚时分,大地的红分明来自天空的红,是霞光,可是因为叫声里有着撕裂人心的疼痛,疼痛里又夹杂着诉说不清的冤屈,霞光从西天喷涌而出时,一程程改变了颜色,由混沌的黄一点点变成惨烈的红。
当然,人们觉得惨烈,是因为一年前同样有过这样的惨叫,也是在黄昏时分,也是疼痛里夹杂着冤屈,听见的人们无不毛骨悚然。当人们惊恐中慌里慌张循声追去,就有人在上塘新挖的方塘里发现一袋白花花的人骨。
上塘新挖的方塘,在上塘村的北边。上塘之所以叫上塘,是因为村庄南边有一个自古就有的水塘。上塘地势北高南低,如果以水塘取名,本应该叫下塘,却不知为什么叫了上塘。把下塘叫成上塘,也许仅仅是图个吉利,可是到2011年,从上塘走出去的刘杰夫,回来承包了上塘以及原来歇马山庄村大面积土地,他不但以新掘的方塘还上塘作为地名的准确,还当上了村长,还把拥有五十多年历史的歇马山庄村改成上塘村。也就是说,在行政管理上,上塘一直在歇马山庄属下,歇马山庄是爹,上塘是儿,问上塘是哪个村的,你得说是歇马山庄村的,可他当上村长之后,颠倒了过来,上塘是爹,歇马山庄是儿,不但如此,上塘一夜之间有了好多儿,徐家炉,小王屯,唐庄,八里庄,下河口,甘甸子,住在那里的人们走出来,问是哪个村的,都得说上塘村的,为什么?刘杰夫是上塘人!
刘杰夫原名刘立功,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他辞掉歇马山庄村长,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冬天,不间断的大雪动不动就封了上塘前街和后街的土道,可有关他的消息从未被封住过:他跟歇马镇一个叫方永和的铁哥们干工程去了,方永和的舅哥在城里当大官,跟他干的人没一个不赚大钱。至于他怎么就和方永和成了铁哥们,说法很多,有的说赌博时,他即使借钱也一定要有意输给对方;有的说他以村长之便,把村里好几个漂亮闺女拉出去送给方永和。但不管怎样,后来他确实向人们证明他真的有了钱,这并不是说他像上塘后来另一些人,刚有点钱,回来过年就穿皮夹克在上塘的街上耀武扬威,他从不上街,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方式,是一夜之间把家搬出上塘,就像当年一夜之间辞掉村长。在中东、伊拉克、富士康的消息不断地通过电视传到上塘的时候,刘杰夫在远方的消息也不断地在人们嘴里发酵。他在翁古城开起了夜总会;他和一个叫大下巴的黑社会合伙打人蹲了拘留;他改掉原来名字,不叫刘立功叫了刘杰夫;他到福建和南蛮子合伙开矿,当了矿老板;他不但在福建有公司,在翁古城还有一个豪华大酒店;他在好几个城市里都有房子,家里保姆佣人三四个,来回出行,身边还有保镖……刘立功虽然改名刘杰夫,上塘人们茶余饭后,从没有忘记过,就像一首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有关他的一切,人们每次说起都仿佛就在眼前,可是一个铁的事实是,不管他如何在上塘“发酵”,他仅仅是一个传说,没人觉得这个叫了刘杰夫的人还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离上塘越来越远了,就像上塘山谷里的布谷鸟,每年春天都能听到它布谷布谷地叫,却根本看不见它的踪影。可有一天,这个在传说中叫来叫去的人突然就回来了,他不但回来了,还挨家挨户流转了土地,还在上边领导亲自主持召开的村民会上当选了村长,更改了村名。在那个村民选举会上,一个差不多一面墙的规划图展现在人们眼前,什么蔬菜园区,葡萄园区,蓝莓园区,温泉区,把十几个村庄的农业土地重新规划。上塘七十多岁的鞠长德,会场上皱着眉望着天,一副木呆呆的表情,领导让他代表大伙儿说句话,他迟疑半天,最后说:“咱老祖宗留下的历史,就这么说改就改啦?你刘立功的本事也太大了!”鞠长德话里明显有着忧虑和不满,然而没有任何人在乎他的不满,因为任何不满都无法改变这已经改变了的历史。只是,就在刘杰夫回到上塘,改变了上塘历史的那个夏天,一声惨叫让上塘陷入一场泥泞。
那惨叫不是一声,是一声声从不间断。一开始,人们并没特别在意,还以为是疯小环的喊叫。上塘前街赵瘸子的闺女疯了,动不动就在大街上发出一声喊叫,可疯小环的喊叫尖细、短促,像吃地瓜噎了后的打嗝,不像这个叫声那么粗壮、悠长,带着一个九曲十八弯的尾巴,这很像鞠长德家的老狗。半年前,鞠长德的小儿子从城里拣回一只双目失明的老狗,它每到黄昏时分就大声嚎哭,在此之前,上塘人看到过狗流眼泪,但从没听见过狗嚎哭,并且是这么撕心裂肺地哭。那粗放的哭声不但带了尾巴,那尾巴里还藏了一把钩子,钩得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疼。可是谁都知道,那老狗两个月前就断了最后一口气……不是疯小环又不是老狗,人们于是按捺不住脚步。可循着声音的源头一颠一颠来到方塘,那喊叫却小孩捉迷藏似的一程程躲远了,躲到方塘西北角的山谷里。当人们觑着眼,侧愣着耳朵静静去听,有人突然发现,方塘的水面上,有一个鼓胀胀的物体在上下漂浮,因为沐浴了霞光,那漂浮的物体像沾了血迹,不,是沾了血迹的人的尸体,因为一眼望去,那刺楞在外面的部分很像人的胳膊。于是,就有人扑通一声跳进去,又有人扑通一声跳进去,当两人合力把那物体拽上岸来,打开袋子,才知道根本不是人,而是装在塑料编织袋子里白花花的人骨。上塘当晚就驻进了警察,刘杰夫的影响力,一个电话就惊动了翁古城公安局。破案非常迅速,警察在上塘十几个村庄摸底两天,就摸出徐家炉小队徐庆中老婆两个月前失踪。邻居说她和徐庆中一起到盖县做小买卖去了,找到她在中学读书的女儿,让她给母亲打电话,她突然就哭了。据她的同学和老师反映,她两个月来一直是独自行动,每天眼睛都是哭肿的样子。警察嗅到其中不妙,当即把警车开到盖县,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一个卖小首饰的摊位找到徐庆中。见面后警察什么也没问,只说是翁古城公安局的,他的腿就颤抖了。他杀死老婆的原因非常简单。大半年没回家,想回家和老婆亲热亲热,两人长期分居,老婆从来都是如饥似渴,这一次却护着身体坚决不让动,怀疑老婆生了外心骂了几句难听话,结果,激怒了老婆。从不会发火的老婆居然扇了他响亮耳光,结果,压抑中的他一个狠劲儿,就把老婆掐死在炕上。最初的瞬间曾想去自首,可是想到还在念高中的女儿,只有把老婆大卸八块埋到自家房后果树底下,并告诉了女儿真相。蹊跷的是,徐庆中带警察到果树下挖出尸体的当天,上塘黄昏时分的那声惨叫突然消失,仿佛喊冤叫屈的正是这个不幸的女人,可令人不解的是,那袋人骨并不是徐庆中老婆的尸骨。
当这声惨叫在一年以后再度响起,人们不由得就想到那袋人骨,不由得就头皮发麻浑身发抖:莫非又有冤魂在喊冤?莫非是那袋白骨的魂灵在继续向世人叫屈?虽然它被刘杰夫手下的人埋到了徐家炉小队的土门沟里,离方塘很远,可是当闻声聚到方塘,人们不由得就朝水面看去,仿佛那个可怕的物体会在水面重现……
然而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汪闪着波光的血淋淋的红。水面本是平的,纹丝不动,可是因为霞光中的云是动的,并且是一团一团一簇一簇地动,霞光又因为在日头掉进西山之后突然变暗,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便在深不可测的变幻中弥漫开来。
上塘人太有理由感到不安了。那个徐庆中,是个多么厚道老实的男人啊。在人们记忆里,他从就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厚厚的习惯上翘的嘴唇,总像露馅的饺子皮似的漏出憨憨的笑,在上塘外出民工只知道往家甩钱的年月,戴在他老婆耳朵上脖子上手上的金银首饰,不知让多少女人在暗中跟男人叫劲,“看人徐庆中多会疼女人”。上塘的男人后来也会买些小东小西哄女人,但给你和你要,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谁也想不到,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做出了如此丧心病狂的事。破案后在果园挖出女人尸体,上塘女人像遭了严霜的地瓜叶,一夜之间面容衰败。执行枪决那天,她们没一个走出家门,没一个生火做饭,她们串联好了似的,统统坐在炕头,和老天一起哭泣——那天,上塘下了一天一夜大雨……她们不知道自己哭谁,是哭那个不幸的女人,还是那个倒霉的男人,还是那个又苦又累的自己——虽然刘杰夫回来后,她们当中大部分男人都回来了,承包了刘杰夫已经为大家建好的大棚,或者在葡萄园银杏林里为刘杰夫打工,可是毕竟还有男人没回来,毕竟,她们的儿女在外面打工没回来,她们的儿女找对象结婚,也在经历夫妻分离……
责任编辑 晓 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