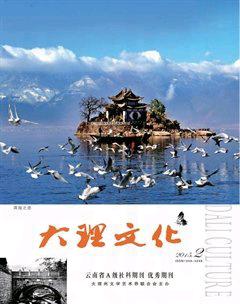夜殇
张淼
1
我喜欢种花,从小到大,我住的地方必有花,特别是桃花。
奶奶说,人生讲运程,人运即花运。
奶奶又说,我命犯桃花。
奶奶跟我说话的时候,长长的青丝和玄色的衣衫映衬下的白净的面庞在油灯的黄晕中仿佛一朵盛开的牡丹。
牡丹?从没见过奶奶养花,可她说她的牡丹每年都开得极好,满园的五彩缤纷让她如飞天临世。她说,那一年牡丹正盛时,一夜霜雪让所有的花朵萎败,从此再没有发芽。她的神情黯淡而忧伤。那年秋天,在中学教书的爷爷就被镇压了,说是现行反革命。保释的文书已经来了,可被狗剩的爷爷压下了,直到行刑后才拿出来——狗剩就和我家一墙之隔,那时我和他整日在田野山林厮混,就是不串门——狗剩的爷爷那时是革委会的头头,一年以后以同样的罪名被枪毙。奶奶恨恨地咬咬牙。
她说,我的母亲也爱养花。母亲长大后,在奶奶荒芜的牡丹园中种上了雏菊,每年都很繁茂。可是有一年,春天来了,却不见发芽,到了初夏,才零零星星发了几枝,也没开花,后来就全死了。那年冬天,我父亲在水利上被哑炮炸死了。不久,母亲得了产后风,我还不到半岁,她就死了。
我是奶奶养大的,是个乖孩子,可就是不爱读书。
我总是温顺地听着奶奶的教训,心底却萌生了无端的厌恶与逆反。
你看你这成绩,怎么只考了这么几分啊!奶奶哭了。
我害怕看到奶奶哭,她一哭我就手足无措跟着哭。可这一次我却一反常态,定定地从她手里抢过试卷,撕得粉碎。
奶奶惊愕半晌,一扬手,啪,一声脆响,我的左脸热辣辣的。我愣愣地捂着脸,一转身,嗖,纵身越过矮墙,消失在夏日的阳光下。
当我在第二天午夜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时,看见奶奶背靠着檐柱坐在黑暗中。灯光昏黄,我看到了她斑白的头发和苍老的皱纹。
那一刻,我满眼泪花。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已经将你的花园打理过了……奶奶颤颤巍巍走进了她的房间。
我就这样结束了白己的学生时代,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那一年,我十四岁。
2
我终日无言,只是专心地侍弄着田间地头的庄稼。
这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情,对我充满了诱惑。
从播种发芽到拔节抽穗再到开花结果,这难道不是花的生命过程吗?饱满的籽粒,嫩绿的新芽,肥硕的枝叶,形态大小香味各异的花朵,丰收时沉甸甸的果实,我还有什么奢求?人们耕种的是农田,我耕种的却是花园啊!
几年的劳作,不仅使我的生活逐渐滋润,而且使我长成壮实的小伙。瓜子脸,大眼睛,古铜色的肌肤,挺拔的身材,让许多姑娘钦慕不已。
他还嫩呢,过几年再说吧。奶奶一边吆喝着满院的鸡仔,一边回绝了所有提亲的人。
我想起了她那句话:我命犯桃花!
3
我喜欢黑夜。
我喜欢在黑夜里点一支廉价的香烟蹲在花园里,静静地聆听桃枝上花瓣舞蹈的音乐,或是脚下花草喧嚣嘈杂的话语;没有人听懂,包括我,可这种热闹却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欣喜若狂地跪在麦田深处,吹起嘹亮的短笛,直到把高亢昂扬吹成低沉哀婉悲戚,最后,成了无声的哭泣,在空旷的黑夜中久久回荡……
二楞就在这时找到了我。
二楞是我的同学,多年不见,当年拖着鼻涕糊的邋遢小子已经西装革履人模狗样了。
“跟我出国吧,包你赚钱!”他很神气地说。
我摇摇头,一脸的茫然。一个文盲,还出国,还赚钱?
“你知道,最有钱的是谁?是腊狗!洋楼就几幢!你知道他哪里发的财?是外国!跟着我没错!你看我,”他咧开满是金牙的嘴巴,用缠满金手链的双手扯了扯脖颈上拇指粗细的金项链,“我才去了两年!”
我就这样跟着二楞走了。
临行前,奶奶佝偻着背,把我送到村口:
“你命中总有这一劫的……去吧,什么时候长大了就会回来的……但愿奶奶能等到那一天……”
4
整个一直往西的行程就像游击战。
白天在车上睡觉,晚上出发,说停就停,说走就走,像是躲避着一张无形的网;每个人都看似极庄重神秘而又兴奋不已,却都是一脸的惶恐和无奈。
经过了半个月的颠簸,由客车换成货车,再换成拖拉机,再换成小三轮,最后步行了三天,终于到达缅甸一个叫坎龙的小镇。
老橡树,芭蕉林,鸡蛋花,睡莲,赤裸的臂膀,人字拖,映入眼帘的已经是别样的风景。
我们的工作就是淘金。金船靠在坎龙江西岸,旁边是一溜T棚;对岸就是坎龙镇。
一连几天,除了大声叫嚷谩骂的男人汗流浃背的裸体和隆隆的轰鸣中显得格外沉寂机器,什么都没有。
我欠了二楞三百。蛇头每人收三百,二楞垫付的。
三百,是我和奶奶一年的生活费。
“没事,这是小钱,等你发了饷再还吧。”二楞大大咧咧的,“不还也没关系,兄弟嘛……”
我习惯了没日没夜的轰鸣声。摇曳的灯火把江面映照成无边的绚烂,我就在沙地上吹响了悠扬的短笛,极陶醉地。
“习惯吗?”麻子一身酒气,拍拍我的肩膀,坐下。
“还行吧……”我笑笑。
“过两天就发饷了,到时候带你到镇上乐呵乐呵……”麻子说,“这里啊,虽然平日清苦一些,可一是来钱快,二是女人有味……男人的天堂啊……”麻子是头,已经驻扎了五六年了。
“不过,你得离二楞远点,有些事情可是要掉脑袋的啊……”
在我惊愕间,麻子已经甩着酒瓶走远了。
5
发饷了。
“好好干,不要乱花钱,”大腹便便的老板递给我几张老人头,“不要让麻子带坏了啊!”
“什么带坏了啊,”麻子嚷嚷着,“不就玩几个女人嘛……你总不能让小伙子进洞房了还不知道干啥吧……哈……照规矩,憨豆来了,总该表示表示吧……”
“就知道瞎起哄……”大肚腩笑着提高了嗓门,“好吧,今晚放假休息,弟兄们放松一下,具体由麻子安排……”
一伙人欢呼了起来……
“好啊,就让麻子给你找个雏……”
“麻子,让你的狄娜亲自教教憨豆……”
“憨豆,别打了软泡啊……”
6
太阳落山,一伙人穿过吊桥到了对岸的小镇。
路旁的芭蕉树下站着几个涂脂抹粉的女人,麻子走近,她们就围了上来。他摸了摸绿坎肩的脸,顺手在她的胸前捏了一把:绿坎肩笑骂着掏向麻子的裤裆,麻子闪身跑开,甩手之间又捏了一把筒裙的大腿……
身后,是那一群女子哇啦的声音。
“麻子,她说了,今晚你不去睡她,她就劁了你……”
“那平板玻璃还想勾引我?……学着点,要先验货,不然撞了红你还以为破处了呢……”
“你教教憨豆就行了……”
一伙人哄笑着,我低着头跟上……
小镇很小。两三百米的街道。白天除了几家百货店饭馆发廊,半条街关门歇业;街上没有人,只有几条狗伸长了舌头耷拉着脑袋横卧在树荫里,几个艳丽的发廊妹叼着烟打着扑克,嬉笑着,谩骂着,声音敲击着空寂的街道传到很远很远……这是几天前跟傣婆买菜时见到的小镇,可现在却是喧嚣热闹的河流:满街的烧烤摊杂货摊灯火辉煌,两边的歌厅赌城发廊霓虹闪烁光怪陆离。熙熙攘攘的人潮、喧闹震耳欲聋的音乐、食客猜拳行令的吆喝、搔首弄姿的发廊妹很甜腻的打情骂俏,使每一个男人都激情飞扬……
真是不醉不归啊。我在众人的热情中一杯一杯猛灌,恍惚间,席间飘来一群妖艳的女子,麻子他们又搂又抱的,可不知何时,他们似乎就都人间蒸发了,只留下我一人守着杯盘狼藉的残局,朦胧中被老板娘叫醒,恍恍惚惚地被人架着回到宿舍
第二天早晨,当我忍着剧烈的头痛和傣婆做好了早饭,才陆陆续续地看见麻子他们从吊桥那边摇晃着走来……
7
我是最年轻的的伙计,照例,做完白己的要工作后,要协助傣婆做饭。
半年后,我不仅学会了烹调各种傣味美食,而且已经能和傣婆用傣语白如地交谈了。
傣婆是麻子找来的炊事员,丰腴却不失风姿,特别是丰满的臀部在筒裙的包裹下散发着成熟女人无尽的诱惑。
“把我的姑娘嫁给你吧,”她总是说,“我有两个女儿,都很漂亮、温柔、贤惠,”她凑到我耳边,“都还是雏呢!”
我腼腆地笑笑,没有说话。
“你要是回国,就只能娶一个,要是留下来,都是你的……”她热辣辣的眼光盯着我。
后来,偶然见到了她的女儿,都亭亭玉立,标致极了。
“怎么样,看上哪个了?”她问。
我想告诉她,我全要。正想开口,却听到奶奶的呼喊:
“你命犯桃花!”
我的神情迅速黯淡下去……
那天晚上,我醉醺醺地走向了三十五岁的傣婆的房间…
8
当我推开了傣婆的房门,她猛然掀开了薄薄的被单,把我紧紧地搂在她丰满的胸前……
那一夜,我成了真正的男人……
她说,我留在坎龙,三个女人都是我的。我说,我愿意。可就在一刹那,我看到了奶奶玄色衣衫包裹下的苍白的脸,心一颤,于是,我听到我说,我会考虑的……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在轰鸣的雷雨中走向了她的房间。我无法抵挡她丰腴的肉体对一个男人的引诱。
可是,走近了,却听到黑暗的房间里男人和女人畅快的呻吟和喘息……
我一咕噜灌了半瓶酒,一个猛子扎进了咆哮的坎龙江……
我湿淋淋回到宿舍,二楞正躺在床上快乐地哼着小调。
“傣婆晚上怎么不回家?”我问。她家就在对岸的小镇,十多分钟的路程。
“她是麻子请来的,”二楞神秘地说,“是麻子的女人……”他突然瞪大了眼睛,“二十元就可以上一次,你不知道?”
我转身出门,闯进了傣婆的房间,一言不发地把正在镜子前梳妆的肉体抛到床上,撕开了她的筒裙……末了,我把一摞钞票狠狠地摔到了她的脸上……
几天以后,傣婆离开了我们的工棚。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9
新来的炊事员莎莎是傣婆的女儿。高挑的身材,长长的黑发垂到腰下,网脸,大眼睛,水红色的筒裙,吸引了每一个饥渴的男人的眼球。
“我妈病了,我来换她……”她微微笑着,浅浅的酒窝调皮地律动着。
“哇,漂亮,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雏啊……”
“晚上在这儿陪我们吗?……”
“谁先上呢?……”
“白然是麻子啊……”
“太不公平了啊,这样的鲜花就被麻子糟践了……”
“竞价吧,这公平啊,谁出得多谁先上……哈哈……”
莎莎听不懂男人们嘻嘻哈哈的玩笑,扭动着摇曳的身姿忙碌着大伙的早饭。
黄昏来临,我依旧坐在离工棚不远的沙地上,吹起了悠扬的短笛。我总会在夜里梦见奶奶,而黄昏的笛声里我会听见她遥远的唠叨:
“不要贪玩啊……”
“做好白己的事情啊……”
“不要和漂亮的女人纠缠啊……”
“你花园里的桃花开了,很漂亮的啊……”
我突然想起,自己已经来到这里两年多了啊,可除了傣婆,我没碰过任何一个女人。虽然每个月都会和麻子他们到镇上逛一两次夜市,每次都会有许多衣着艳丽的发廊女舞厅妹热辣的挑逗甚至拉扯,可我还是每次都在麻子他们消失在街巷深处后一个人回到宿舍:虽然这时同宿舍的二楞不时会带一两个傣妹回来过夜,有时还叫我和他们一起玩,可我依然会灌下半瓶老白干找一张空床倒头便睡……只有这支父亲留给我的短笛,在每一个寂寞的夜晚陪伴着我……
莎莎静静地坐在我旁边听我不停地吹奏一支又一支曲子。她的眼睛总是在平静江面寻找一个又一个漩涡,目送它们走远……
“你妈妈的病好了吗?”我问,“她怎么还不回来?”
“她找了一个男人,在家种香料呢……”她开始往江中丢石子,不停地丢。
“你晚上怎么不回家?”我看着她的脸。
“我妈说,你是个好男人……我想听你吹笛子……”她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那个男人很讨厌,老盯着我的胸脯看……”
我诧异地盯着她的眼睛,她乌亮的眸子在黑暗中闪着晶莹的光。
“那个男人有钱……她睡了我妹妹……我妹妹只好去了帕拉塔……”她恨恨地说。
“去做什么?”我问。帕拉塔是一个县级城镇。
“一个女人,还能做什么?”她把一个鹅卵石甩得远远的,突然定定地看着我:“你能娶我么?”
半晌,我站起身,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她滚烫的泪珠洇湿了我的胸膛……
她呻吟着撩起了短裙,我知道,她要把白己全部交给我。
我吻着她的脸:“我要娶你,可我要使你在洞房做一个完整的新娘……”
她愣愣地看了看我,猛然挣脱了我的怀抱,捂着脸跑了……她低沉的呜咽声消失在无边的黑暗由……
几天以后的早晨,我听到麻子郑重地吩咐陀陀:“从今天起,你来维持伙食……这些娘们!”
后来,我问二楞,他神秘兮兮的:“麻子把莎莎睡了,人家不依不饶,他就把人家撵走了……”
难怪这两天莎莎都躲着我呢。我操起一根铁棍就冲向了麻子的宿舍。
“我知道你喜欢她,可你们结婚了吗?她是你的什么人呢?再说,讨个老外回家,不合适啊……”工友把我死死拖住,麻子一脸的痞相,“兄弟,你还嫩呢,没见大街小巷都是婊子?漂亮姑娘遍地都是,有钱才是硬道理啊……”
那一夜,我酩酊大醉睡在了二楞找来的女人的怀里……
10
不久,我们就回家了。
二楞死了,是在小镇上被乱枪打死的。工友们把他扛回到T地的时候,还没有断气。
“我冷……”他说,“我想回家……”
他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麻子说,需要输血,可是我们离最近的医院还有几个小时的路。他无论如何也撑不住的。
看着二愣绝望的眼神一点点黯淡直到岑寂,我感到一丝刺骨的痛,冰冰地穿刺了我的脊梁。
大肚腩的老板来了,召集大伙在河岸上把他草草掩埋。
“都是白粉惹的祸!”大肚腩有几分沉重,“活人回去也很麻烦,何况是死人……就说他被警察处决了!”
他的床板下几个纸箱里全是钞票。
麻子说,二楞一直在走货。
麻子又说,这是丧尽天良的事情啊,害人终害己。
后来,麻子把二楞的钱全部寄回给她的媳妇,说二楞被警察枪毙了,好在警察没有查到他的积蓄。
不久,奶奶捎信来,说我花园的桃花全枯死了,叫我回家,还说,再不回去,会没命的。我正犹豫的时候,大肚腩也死了,死在镇上一个叫妃雅的女人的床上。据说,是脑溢血猝死的。麻子却说,是药吃多了,可我不知道什么是药。
丰满的老板娘来料理后事。我找到她,说,我这几年的工钱都寄存在老板那里。
“我几百万的投资都还不知道他寄存在哪个烂人的骚洞里呢!”她清理着账本,头也没抬。
“我要要回我的工钱!”我执拗地站着。
她抬起头端详了我半天,语气缓和了许多:“先回国吧,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命!如果警察追查起来,所有的都会被查抄!那样,你找谁都没用了……”
一个月后,我们回到了县城,我找到了她的家。
她正在暗淡的灯光下白斟自饮,披散着头发,眼神里有几分疲惫的妖媚。
“给你吧,两年半,十万……”她从坤包里摔出一沓大红牛,“不过,”她斜着眼勾勾地看着我,“今晚你得叫老娘舒服……”
她撩起长裙骑到了我的身上,我热血澎湃地迎接着她的癫狂……
随着长发的疯狂舞动,我听到了她声嘶力竭的叫喊:
“死胖子,你死去吧!老娘终于给你戴了绿帽子了……”
11
我在深夜敲开了家门。
奶奶颤颤巍巍地接过我递给她的几大串佛珠,老泪纵横:“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她说,花园的花全枯死了,这是不祥的征兆。看来,是躲不过这一劫了啊。
我说,没事的,都已经回来了啊。
可就在几天后一个阴雨的黄昏,当我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发现奶奶躺在了血泊中。
奶奶是被同村的癞头捅死的。癞头听说我带着一大笔钱回来,就起了歹心。当他看着我扛着锄头出了门,就翻墙进了我家,翻箱倒柜一无所获准备出门时,却被奶奶撞见。于是,慌乱之中他在奶奶的胸前捅了十几刀……
警察很快就带走了癞头。我把奶奶的棺材停在癞头家门口,哭得天昏地暗。可是,当看见他的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父母跪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毅然让人抬走了棺材。
安葬了奶奶,我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黑暗的院落中,看着空荡荡的花园,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袭来,使我在星星闪耀的黑夜惊悸不已。
12
奶奶出殡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隔壁瞎眼的李婶拄着拐杖敲响了我的大门。
“我家狗剩已经有了一个一岁多的孩子了,过几天就带着媳妇孩子回家了……”她浑浊的眼睛一闪一眨地泛出星星点点的神采,“这孩子也真是的,你去淘金后不久,他也就出门了,一直没有音信,前几天突然请人捎话,还给我买了个什么手机……”李婶抖抖索索地从衣衫的最里层掏出一个崭新的诺基亚,骄傲地扬了扬就立刻翻开层层衣衫藏了回去,“还说叫我看个日子,要给孩子办个风光的周岁宴……”
我倚着大门唯唯诺诺地答应着,心里却想着怎样撵开她。奶奶说,千万不能让狗剩家的人踏进来,否则会有祸端,何况,我正心乱如麻呢。
这时,远房的二表哥恰好出现,李婶便乐颠颠地走了开去。
二表哥是来找我的。
“老是憋在家也不是回事,一则睹物思人,伤心悲愤,伤口难愈,二则我想真心帮兄弟一把。你看,我们这么多年来往不多不是?来往不多,人情就淡了,往后还要彼此关照啊……”二表哥虽然年纪不大,但能说会道,据说已经是一个什么建筑公司的小头目了。
我跟着二表哥来到了建筑工地。出门前,我把一个红包给了李婶,虽然见不到狗剩,可这份人情却不能担待啊。
“先在这里干着吧,慢慢适应……”二表哥把我交给一个中年的豁豁,撂下一句话,走了。从此,我便再也没有在工地见到他。
“既然是老板的表弟,就要先学点手艺,不然以后怎么混呢?”这是豁豁交代给施工员的话。
从此,我成了基建队的苦力。
可我就是不服气他人别样的眼光,下狠心钻研所有的技术。除了两只手,我身无长物,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白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谋生。就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辗转了几个工地,我已经成为从拌料配料到做钢筋浇灌砌墙到粉刷油漆直至室内装修无所不会无所不精的技术工了。
可是,每个黄昏,我总是独白静静地坐在凌乱的工地一隅,看着漫天飞舞的彩霞在高缈的天际变幻着神奇的姿态来来往往,不禁黯然神伤。
或搓麻将斗地主,或猜拳喝酒,或看毛片嫖妓,这就是这些睡大通铺的工友晚饭后的娱乐。我是老板的亲戚,待遇自然好些,跟工长豁豁一样有个单身宿舍,可一块薄薄的木板挡不住他和女人激情的呻吟。豁豁是个好人,能够善待每一个工友,特别是我这个学徒。可我就是看不惯他裸露着的两颗大板牙,蜡黄蜡黄的,拉着粘稠的丝丝,让人作呕:再有就是他的夜生活,极大地刺激了我的每一根神经:他总是隔三差五地把形形色色的女人带到与我一板之隔的宿舍,毫不知耻地把一张木板床弄得吱呀作响……这时,我就会想起那个异国小镇,和小镇上的傣婆,莎莎,以及我葬身在那个异国小镇的儿时的伙伴二楞,还有大肚腩老板和他风骚的女人:我就会想起我的花园和花园里美丽妖娆的花枝,还有我的佝偻着背影的奶奶……他们的音容笑貌清晰而模糊,仿佛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隔壁的响动稍稍平静,一阵窸窸窣率率之后,在高跟鞋踢踏踢踏的节奏中,女人的声音有些幽怨:
“怂货……真没劲……只知道瞎折腾……”
高跟鞋走远,豁豁还在嘟囔:“这个婊子,老子有的是钱……”
我就在这样的无奈中煎熬着黑夜,直到豁豁的鼾声响起,我也就在麻木中渐渐进入梦乡,可梦中依然是奶奶鲜血淋漓的惨淡的笑……
工棚内肆无忌惮的哄笑无情地击打着我的耳鼓,我悻悻地走回宿舍,却遇到正准备出门的豁豁。
“晚上一块玩?”他的大板牙拉着粘稠的黄丝。我明白他的意思,扭过头。
“不了,你玩吧,”我推开门,想想又回过头,“要保重身体啊,不行就休息休息……”
“知道知道……”他呵呵笑着,走了。
“下一个工地别让我住你隔壁!”我冲着他喊道……
13
“我就说,你跟着我干一定会有出息的!”很长时间没在工地露面的二表哥开着小车找到了我。晚上,我们醉眼惺忪。
“收拾一下行李,跟我去开发区……”表哥在开发区有个很大的工程,要交给我。
“哈哈,你终于成才了啊……”豁豁嚼着鹅肉叼着烟卷拉着黄丝笑着。
“快过年了,我想回家看看……”我郁郁地说。
“不是还有几天的吗?”二表哥拍拍我的肩膀,“到时候我也要回去给大哥办喜事呢,急什么?等安顿好了,我们一块回家!”
我知道大表哥,很帅气,就是脑子不好使,三十老几还没找到媳妇。这是远房大伯的心病。
“哦,好事啊,找了哪家的姑娘啊?”我端起酒杯。
“什么哪家的姑娘,是老子用钱买来给他的……”二表哥愤愤地打断了我的话,“不说这个……”他愣了愣,斜着眼,“不过,那个妞很有味道,就是不会说汉语……正好你可以做翻译啊……”
“你小子注意啊,”豁豁斜着眼把筷子敲到我额头,“只是做翻译,别把人家翻上床……”
由于工地上的耽搁,我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年关,没赶上大表哥的婚礼。
出于礼节,我去看望了远房的大伯。
看到开门的人,我惊呆了,是莎莎!
错愕间,大伯颤颤巍巍地把我迎了进去。
我坐在老人的对面说话,莎莎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的身边,我清晰地闻到了她身上那种特异的香味。帅气的大表哥一直站在大伯的身旁,傻傻地笑着,不停地递烟。我看看老态龙钟的大伯,看看流着口水的大表哥,再看看青春靓丽的莎莎,心里很不是滋味,直到出门,我才想起二表哥的话:“什么哪家的姑娘,是老子用钱买来给他的……不过,那个妞很有味道……”我恨恨地将路边家家户户点在门口的香头踢得火星飞溅……
三天以后的早晨,我正在院中面对荒芜的花园黯然神伤时,莎莎敲响了大门。
“我是被骗了以后卖到这里的……我原来想着要报警,要回家,可是,回家又能有什么呢?再说,那老头找人把我看得紧紧的,根本没机会……现在看见你了,我就不想跑了,我要为你生一个孩子……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
褪去衣衫,她丰腴的裸体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眸,泪珠跌落,被揉碎在疯狂的喘息中,咸咸的
后来,我才知道,就在那个小镇,她是为了逃避他的继父的魔掌才来到我们的金船做了炊事员,可我以我的方式拒绝了她的真情,使她伤心欲绝;那个夜晚,麻子把她灌醉并强暴了;可是得到了麻子的好处的继父不仅没有为她讨还公道,还逼着她和他睡觉;无奈之中,她只好去找妹妹;结果,没找到妹妹,却落人蛇头的魔爪……几经周折和蹂躏,被卖到了这里,卖给了我的大表哥……
她的黑发拂过我的面颊,遮蔽了我的眼睛,我就在她特异的香气中煎熬着自己本来就该属于黑夜的魂灵,直到第二天的黎明……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大表哥身后一个屁颠屁颠的男孩眼神中不经意的一瞥,直直地穿透了我的灵魂深处那根最脆弱的弦……
过了年,我就回了工地。出门时,却遇到了李婶,她正牵着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你就要走了啊?”衣衫破烂的李婶的声音沙哑而苍老。
“是啊,工地忙啊……”我把一张百元钞票塞到小女孩手中,就急忙走了开去。狗剩在孩子周岁宴后不久上山捅蜂窝掉下了悬崖,他的媳妇不久也就外出打工去了,不知去了哪里,只是不时寄点生活费回来,现在家中只有奶孙二人。儿子的死是李婶最大的痛,使我不敢开口说话。走出好远,我还听到李婶的声音,幽幽的,穿透了清晨刺骨的寒气:
“要是狗剩活着的话,也该出门打工去了啊……”
14
工地的事很多,每天都要面对许许多多繁琐的事物,但好在有几个大小工头围着我转,我依然一副逍遥自在的样子。
这是一个偏安于西南地区的小城,那时正沉浸在对兰花的疯狂中,街头巷尾男女老少的话题无一例外的就是盛产于西南地区的莲瓣兰。于是,我也加入了疯狂的人潮,每天到花市淘宝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白然,那些大小的工头总是隔三差五地送给我几株当时看来价值不菲的兰草,并殷勤地为我作技术上的指导,于是,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成为了行内高手,不论什么样的名品真品单凭几片叶子就能一眼识别,不论怎样假冒的兰株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甚至有些很有名气的养殖户都邀请我去赏鉴:我也在宿舍旁边开辟出一间简易的兰室,把自己大部分积蓄全都押了上去:虽然只有不多的几盆,虽然不期望一夜暴富,可养兰赏兰却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快乐。
从开发区到商业区的兰市有一条小巷,据说是以前的干货市场,后来在城市改扩建中市场搬迁,住户就在小巷的两边盖起了许许多多的简易房出租,于是,就成了现在极狭窄的小巷。租住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女人,每天日上三竿,她们就开始端坐在街边,要么三五成群悄悄聊天要么独白一人默默刺绣要么半眯着眼睛慵懒晒太阳的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花花绿绿的女子,成为了这条街独特的风景。
“这是米线鸡一条街……”光头带着我穿过这条街的时候,目不斜视,一脸的不屑。光头是本地人,号称“百事通”。
“米线鸡就是淘汰鸡,一碗米线钱就可以崩一炮……”他翘了翘嘴角的烟卷,“都是大妈级的了……”突然凑到我耳边,“你可别小看,那些民工可经常光顾,哪天在这里遇到了我们的工人,你就当什么也没看见就行了……”
我没有说话,一甩头,却看见拐角处的房间里走出来一个抬着小板凳的年轻女人,披散着长长的卷发,丰乳肥臀在印着大红牡丹的连衣裙中呼之欲出……
那段时间,我经常路过这条小巷,原因很简单,一是捷径,我从工地到花市,不抄近路,至少得绕两倍的路程:二是眼馋,即便是多看几眼,也是男人的眼福,何况,红牡丹每次都会冲我勾勾地笑笑……
初春的早晨,和暖的风中洋溢着迷人的香味,我却分不清是花香还是女人的体香。红牡丹斜坐在爽朗的阳光里,直直地瞅着我走近,然后甩了甩漂亮的卷发,笑笑:“玩玩……”
我友好地笑笑,没有说话,径直走了过去,身后传来她磁性的声音:
“免费哟……交个朋友吧,帅哥……”随后,是一串放荡的笑声……
15
我依然穿梭在那条小巷。
光头成了最好的朋友。他不仅指点我养兰的技艺,而且帮助我在花市炒作中赚钱,低买高卖,不长的一段时间,我就已经赚了好几万了。
“现在已经是高峰了,别玩了,把钱揣好,观望观望吧……”光头把工地的材料清理了一遍,跑进我的办公室,很严肃地说。
我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就走了出去。我一直怀疑白已是不是花痴。从我的小花园一直到现在的兰室,我的痴迷似乎达到了癫狂。不仅每天的工作成了副业,就连半夜醒来我都要赤身裸体地到兰室看几分钟才回到床上继续睡觉,睡梦中看到的依然是兰花娇艳的姿容;更何况,我和那时许多的人一样,养兰的收益高出正常的收入好几十倍!
“我的材料全拉来了,你派人清点一下……有事情打我电话……”光头在我身后大声喊道。光头负责供应材料,材料足够了,他就不到我的工地了。去你的吧,老子不想再听你唠叨了,婆婆妈妈的!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光头,偶尔短缺的少量材料,他也只是派人送来。有时躺在床上想想,还挺想他的。可是,正当我准备打电话约他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从一个兰友家醉醺醺地出来时,已是深夜;走到那条小巷,黑魃魃的,只有红牡丹的房间里还亮着灯:走近拐角,房间里隐隐约约的哼哼唧唧的声音紧紧地拉住了我的脚步……
我把耳朵贴在了门上…-.
“给老子老实点,敢报警,老子宰了你……”男人恶狠狠的声音。
“你行行好吧……怎么整都随你,可那是我几年的积蓄啊……”是女人的哀求。
“你以为你这骚货稀奇?……老子是冲着它来的!”
“你行行好吧……救命啊……”女人哭了。
我掂了掂手中的半截钢管,一脚踹开了门
被胶带捆着的红牡丹斜靠在床上,裙子撩到前胸,丰满的下身赤裸地蜷曲着;同样赤裸着下身的男人站在床头,手里端着一盆名贵的兰花——是光头!
两人都呆住了!
我接过光头手中的兰花放在桌子上,拉下了女人的裙子冲着光头吼道:“滚……”
16
我依旧穿梭于那条小巷,可每次路过红牡丹的门口,她总是扭过了头去。
光头依旧给我运送各种材料,可是除了正常的业务往来,我们从不多说一句话。
一年以后,我的工程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