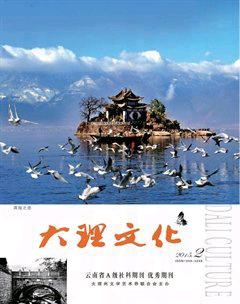伸展
冯秋子
来到剧场以后,人们忙着跟国内的家人通话。租住的公寓里没有电话,大家着急,到汉堡好几天了,还没给家人报平安。剧场的T作人员说,那个大化妆间里配置的电话,是专供演员使用的长途电话。我用在汉堡买的国际漫游卡,拨通了内蒙古家里。
问母亲情况怎样,她说都挺好。
她不会告诉我“不好”。真有不算好的事,也不搁现在说。问题是我回到北京,她也不会讲。一件事从发生,荡悠到不再算是事儿,比如等我过节回到内蒙古,她挑捡出一件两件拉呱给我听,曾经的大事已经波澜不惊。你看,过都过来了。是啊,还有什么比“过来”更好呢。
她愿意报喜不报忧。我在外面时,她没跟我说过除了好的情况,哪怕是指头肚那么一丁点儿的不合适。明知道她会这样,这么做的时候义无反顾,对我来说,确实又是需要的。比如现在,知道了这些“好”的消息,我能够站立在好的心境搭架的平台上,心神顺遂地从事眼前的事:我能够集中精力,不从正在做的事情里跳出来、掉下来。尤其是处在演出当中,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现代“舞蹈剧场”的艺术交流这件事,心里若有了麻烦,会出现干扰,也许是些微的,也许很严重。处境如是,心里的困扰与正在进行中的“舞蹈剧场”可能搅和在一起,滋生出抑滞,或者是虚幻、荒诞之感。这种情绪一旦涌现出来,人就俩惶、不可终日,不知不觉驳离了跟环境建立起来的和谐关系,而一下子变得浮游、干燥起来,身体和心灵会向着人的底线收缩:人和环境不再融洽,如同驾驭着马车的两匹马,本来安好地并相前行,突然间拒不合力,不安分、不配套、不合作了,一匹往东、一匹向西,背离了原本的轨道,遗漏了将要进行的事情。
在舞台上,身和心分离,身和心坠落,是最糟糕不过的情形,一只巨形魔掌触碰了似的,眨眼之间人被改变了形状,原来正常的那个人消逝不见了,徒有其表的人,对正相展开的所谓的艺术创作不再善尽其责。此类事故在中外舞台上屡见不鲜。
我一回又一回体会到,母亲所说的“都挺好”,对我的意义。也深知,长成大人,甚至人到中年,还是有脆弱的地方。内心深处,有一个角落里隐藏着一些虚弱,平时尽力遮蔽起来,修理维护着,也培养锻炼着,为了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至于不堪一击。我清楚地知道,只有至亲至爱能够安抚那个地方——那就是他们安然无恙。不论身处何方,我在内心祈祷亲人能够平安和顺。但是,当事实并非如此,我往往又能够镇定自若,面对现实。怕就怕正站在临界点上,犹如立身刀刃之上。不过,真的站在刀刃上的时候,倒没有恐惧,没有眼泪。以往听老人们描绘过此情此境,说那种时候“连哭都顾不上”。我描述不出,那种情境中,人是怎么啦,那么冷静、清醒,该做什么去做什么,而且还能够顾了这个又顾那个。唉,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只有裹紧疼痛的身躯,扛住艰难的时间,扛住担待的责任。
母亲说的“都挺好”一排子话,无非是身体挺好,吃的也好,穿的好着呢每天换,睡眠也有好转。贵贵妹妹叫她去集宁住一段时间,她呢,是想,快过阴历十月初一了,该给父亲扫一扫坟墓上的雪了,暂时不离开我们旗,过了十月初一再说。她没有讲其实那时候,她的双腿关节又发病了,支撑不动身体,她不能下地走路,不能做什么事情。过后,贵贵妹妹告诉我,进入深秋,因为腿病拖拽,她被修磨得有一段时间了,面色很不好看。
四十多年前,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八点多钟,街道两位女干部推一辆平板车把母亲送回来交给我们。女干部对我大哥和平交待:让你妈回来,是为了更好地反省白己的问题,过了年回去作交代。
过了年,再回到那儿?大哥问。什么时候回去?
听军管会的。
母亲全身的骨骼哪儿都不听使唤,身不由己似的,几个小孩合力抬起母亲,放到炕上,让她平躺下。见她龇牙,或许是感觉不适,再搬起她,放她侧身躺。
那时候,我们年岁小,意识不到母亲的身体因为“文革”的专政酷刑埋种下了什么麻烦。只看见她腿上、脚上布满冻疙瘩、血腱子,全身上下青黑滥紫。她听我们说话,反应缓慢;眼睛乌里巴涂,看不清楚东西;耳朵几近失聪。
大年三十,一清早,太阳起是起来了,还没进家。二十多岁一个男青年,腾地一下推开门,喊我母亲回去粉刷禁闭室,做大扫除。我们说,搬动我妈妈才能翻一个身,她起不来呀。男青年的眉毛马上立起,大声喊喝:“少他妈废话,必须刷房子做大扫除,这是任务,你这个……小心……只有老老实实……让你回家待几天是为了更好地接受改造、交代问题,不然跟我回去,在那儿待着,在那儿过年。”
事实清楚,理路确凿。
旁边院子早先做小买卖的石大爷有一辆推货出去叫卖的两轮平板车,我们叫着“石大爷”,说明原委。“借车?”他说,“用完照原样立起来。”久未使用的平板车,车底朝外,两只长辕臂膀伸举至高处,整驾平板车斜靠在柴草房的墙壁上。
我们用石大爷的平板车,推母亲返回监舍。
母亲围着白茬皮袄坐在平板车上,我挨着她。大哥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一、扶住母亲,二、护好摞在一搭儿的两个瓷盆、几把刷子和七八个白土块儿。两个哥哥,老大驾辕、老二在车辕的一侧助推。
母亲脱离监舍在家过了一夜,复又转回。她摇摇晃晃,想说话,一个字没说出来。离那排房子还有一段距离,她开始哆嗦,坐卧不宁,不一会儿就往一边倒下去。二哥见状,跳上平板车,大哥一边推车,一边指挥我们把母亲扶起来,用白茬皮袄围裹严实。
母亲浑身颤动。很快,我发现,我跟着她一块儿抖呢。那时候我很渺小,身体比一只枕头大不了多少,完全没有办法抱牢一个大人,使不出吃奶的劲气,除了跟她一块儿抖,基本没用。
母亲点头表示这样、表示那样,有一下没一下地指挥我们行动。我们把从家里带来的白土块儿捣成粉末,用温水搅拌和匀;把刷子浸湿、理顺……按部就班地投入了劳动。这项包含技术难度的营生,现今内蒙古城市中的主妇们已经基本弃之不做了,早已不像过去那样,无可选择、亲力亲为。今日内蒙古的大中小城市,腊月末了那几天,不少主妇们雇佣专人代劳粉刷房间,只需支付三百元左右,大半天、最多用一个白天,连擦擦洗洗的细碎工作也能做完,经过验收,交工了事。这也从侧面说明,粉刷房子是个重体力活儿。
那一年的年三十,这项重体力劳动历史性地落在谁头上,谁就像个大人似的,而且是一下子长成的大人那样,光荣而神圣地站立在高高的桌椅板凳上,举起枳棘草捆扎出来的刷子,一下接续一下地粉刷,样子庄重,表情专注,格外地有耐心,怎么看,都像一个小英雄。两个哥哥,加上我,三个半大的孩子,搬桌子、摞板凳,看谁合适,谁就爬上板凳,做“拿一把刷子的师傅”,负责刷顶棚、刷墙壁。
站在高处的人,一手端一个盛白土水的小盆:另一只手握紧一把沉重的大刷子,蘸上不稠也不稀的白土水——若蘸多了水,在盆檐儿上顺一顺刷子,多余的白土水即归人盆中,也省得白土水四处淋拉,不干不净——这时候,凭管是谁,像个准备好写毛笔字的人,只不过手里握的“笔”不是狼毫、羊毫毛笔,握的是一把枳棘草杆捆扎成的小腿粗细、超过一斤重的大刷子。这时,他正定自若地,从顶棚、墙壁,自右而左、或者自上而下、秩序井然地刷下来:而且一刷紧挨一刷,衔接处略微压住上一刷留下的湿印,一指头宽瘦的小边边儿。尽可能是一刷到底,不断开、不打嗑巴,这样,水分干了看不出断痕,就像书写毛笔字,不作补笔,粉刷顶棚和墙壁,也讲究刷子下去,一次性完成。
第一次粉刷房子,我们一是有母亲坐镇指拨,二呢,脑子里有她昔日从事此项劳作的过程做参照,顺利地上了路。
看见小盆里的白土水快用完了,地上的人接茬儿冲泡、搅拌出新的白土水。
我比较多的是被指派给哥哥们打下手,帮他们扶牢桌椅板凳,拿个东、递个西。听到他们的指令,迅速做出反应。
高处刷完了。我从老大或老二手里要过刷子,刷一截低处的墙壁,水缸啊、木棒铁棍的后面……此时此地,人小显出了优势,我能够到犄角旮旯里头,把白土水刷上去、涂进去,让黑糊糊的地方有了明净亮泽。刷完最后一截,母亲表扬我,说刷得横平竖直,有眉有眼。我欢喜不已。
这次受到的鼓励,使我把刷白土粉这项劳动热爱了好多年。以后,家境好转,而我已磨练成劳动人民之勤奋的一员,收都收不住那一双总想做活儿的手,尤其热衷于粉刷。家里原先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一年全面地清理粉刷一次房子。长大的我,决定大包大揽,等不及一年那么长的时间,刚到半年六个月,就把房子刷新一遍。一年粉刷三到四次,也有过。实在没得刷了,怎么办呢,开辟出新的劳动空间——先清扫干净房屋地面,然后绕着墙脚、衣柜、水缸、火炕……刷出四五寸等距离宽的白土地围,整个房屋确实显得洁净、清爽、分明。这件事,每天做,早晨、中午,甚至晚上,什么时候家里人少了,我就动手去刷新地围。只为每一天,家里的气象能够焕然一新,人人能够生气勃勃,活得有点劲儿。
母亲说,不用每天刷,过于干净了,下不去脚。
我是这么想,每天,总有人把干净的地围踩踏脏了,不刷,又脏又乱,没意境。于是,每天家里飘浮着白粉的土腥味。那些年月,有什么事情能比营造出一尘不染的明亮家境更好的感觉呢?没有什么陈设的家,那个一成不变的家,因为白土粉刷过而有了一些变化。我想让家有所改变。我想让母亲高兴。我想给家人带来一点舒缓的东西。也许还有我想给白己一点点鼓励,或是证明。
从早到晚,我望着白土墙,望着白土地围琢磨,哪个地方的弯道和弧线,刷子应该怎样表现。哪个地方需要抹泥取平,哪个地方潮湿阴暗,哪个地方容易沾染污渍。没人的时候,我紧贴墙壁,深深地吸一口气,闻一闻白土墙粉沁心人肺的香味,偶尔忍不住想舔食一口墙头上的白土。我哥哥回来,一眼辨认出,墙上多出来的那些舌头印儿是我留下的,承不承认,已是枉然,我的脸是苍白的,像那面白土墙。
我哥哥指出,我肚子里有蛔虫。蛔虫饿了我就会去吃墙壁上的白土粉,因为蛔虫爱吃白土粉。“蛔虫想吃,你是因为它才去吃的。”
我是想不清楚啊,到底是蛔虫想吃,还是我想吃。明明是我想吃,怎么是蛔虫呢?我肚子里头真有蛔虫?我天天夜里捂着饥肠辘辘的肚子睡觉,可着,我是捂蛔虫睡呢?这些问题揪扯着,使我的肠肠肚肚开始作痛、抽筋,肚子里面咕咕噜噜的叫声,让我睡不着觉,睡着就做噩梦。我真的饿啊,真的想闻、想吃墙上的白土粉。这样,一个疑惑了很多年不曾解开的谜就存在我心里:刷房子的白土粉是蛔虫的军粮?我该不该刷房子、刷地围?感觉上,把房子打扫干净,杂七杂八麻烦人的虫子就没地方存活了。这个道理有没有被改变,不知道。这是后话。
我们几个小东西通力合作,完成了通常是大人才有可能做好的比较涵盖技术指数的这件郑重的事:刷好了那个大房间。
后墙上开出一个低矮的小门洞,连接出一间凉房,那个男青年在一开始就交待“不用刷那个,不要进去”。
母亲也说给我们,“不要进去”。她费力抬一下手指,指那间凉房。
我们领会了,那边不在打扫范围。
干着活儿,突然发现母亲的脸色惨白。三个小孩围着母亲喊叫,她终于缓过一口气。
我们把母亲背后垫的羊皮袄整理好,让她半躺着看我们给那间监舍涂脂抹粉,装扮旧历年节的喜庆气象。
过了年,但愿母亲不再回到这个监舍。
不能想这件事,一想就心烦意乱。
一边清理,一边想这间房子,跟我母亲关系挺深,不能不上心去打扫。
母亲身体好不好,从她的脸色有时候能看出来,有时候看不出来,她总能忍耐住,不表现出疼痛。从母亲,我体会到女人的抵抗力、忍耐力和柔韧性,她们总是能够无限地发展和延伸白身的底限。什么时候是扛不住的边呢?我既好奇又恐惧。
巴顿四岁时跟着录音带学会唱罗大佑的《七十二变》《鹿港小镇》和《亚细亚的孤儿》。有一天,他唱累了、唱不动了,转过脸对他的父亲说:“一唱《亚细亚的孤儿》,妈妈就哭。
他父亲是作音乐的,音乐感觉、音准是天生的,没法讲,是一种什么样的好。我没有当他面唱过歌。
是唱到“黑色的眼睛里有白色的恐惧”那一句,眼泪止不住流出来。
不好意思呵。让一个小小子看见了。
说不清楚,很稀少、很稀少的时候,会忍不住哭泣,显出软弱无力,挺大的一个人,一下子蜕化变质为婴儿。巴顿揭出这件事,把我引逗得差点没忍住泪水。
不过,这时候的哭,不同于曾经有过的哭,那种痛是从腹腔深处,往出推,滚滚奔突吧,又不全是,一路上磕磕绊绊,不能不出来,又不能顺畅地往出走,有点像麦场上没有出路的毛驴拉着溜轴走,茫然而又不那么情愿地绕着木条一圈一圈地、硬搋搋地碾过麦秸。这种时候的哭,不出声,表情亦无,只是眼泪抑制不住地流出。真不想是这样。这个环境,跟人,两者之间有着诸多不情不愿的事儿,没有办法。我知道这一点。
我只是不愿意停在让我难过的地方。
不想流泪。
不过,眼泪不流出来,并不说明没有哭。经常看见哭不出来的人,有东西寄存在他们脸孔上。
软弱的大约不只这一个,或者是那两个。
母亲说,她还能劳动,用她的说法,是还能“做生活”。天哪,这看起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能“做生活”,想不出母亲怎样生活。从她妈妈那里她继承下来“做生活”这个词汇,也那么使用。我在别处还听过类似的说法,比如“做营生”。做这,做那,做活儿,除不开是为生活下些大力气,给出全副的心力。
我能想象出来,母亲怎么“做生活”。对于她,“做生活”不完全是通常说的干活儿。“做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就像是伸展运。在她那儿呢,比如去取点吃的东西,去做饭,去外面晒太阳,劈木柴,打碳、取碳,洗一把脸,浇一下花草,沏壶茶,倒掉废水,剪枝、抚顺叶片……不一而足。她理解的做生活,还包括思谋事情,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小事。也包括冥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形而上学那样式儿。还包括读书、看报一类。她眼睛还算好的时候,为我父亲念几页书,念几版或几段报,念几条小信息,解释一条或几条电视里演示的好事或麻烦事:还有小孩子们领来别的小孩子们,七八个、十来个,趴满她的一间、两间甚至三间平房写作业,在她铺了干净炕单儿的大炕上爬上翻下……“做生活”的内容是繁多的,超出想象地复杂。而且她双腿盘坐在那里唱内蒙古的老歌时,也是那种“做生活”的感觉。
我表扬她,妈妈活得挺努力的,赶明儿给你发个小奖状。
她说,有时候,一想点儿深刻的,到黑就睡不着了。
她用了“深刻”这个词。我笑了,没一会儿笑不出来了。
她静默地待着,有人推门进来——常有人说想她啦,过来看一眼——问她:大娘(或者是婶婶、姨姨、大姐、老郑),做什么呢?她只是笑,不答,因为“做生活”呢。能看见的,不用说。问的人,也不是就要问你做的是什么,他或是她,只是问好似的,进了门,走过来,和她打声招呼。后面只需默守时间,说多说少,意思互为通达,各白心里照旧网满、欢喜。
她拍拍身旁的空地儿,让进来的人坐下。情况好,能在地面来回走的话,她会慢慢挪动不方便的腿脚去取些好吃的,奶食,点心,糖,水果,杏仁、腰果、开心果一类干果,还有我们一回来就给父母剥出的瓜子仁,她想让来的人吃,就着热茶,慢慢品尝。到了开饭时间,她说:“不要走,在这儿吃饭。”
除了正餐,母亲平常喜欢吃奶制品和面包、点心,偶尔吃一点水果,想不起吃其他的了。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失明的父亲,喊叫她:“老郑同志,有什么吃的,搜集一点来。“她挑捡出糖分少的东西递给父亲。然后,就等有人进来,递给他们。她脸上的表情,跟劳动带给她的感觉没有差别,安生、简朴。她从这个房间进到那个房间,就是为了给人们找吃的。我见她如此感觉着的时候比较多,总想问问她,你动的时候、或者不动的时候,怎么,老是一副幸福的样子?但一次也没去询问这种话。这叫什么话呀。
央视的《妇女半边天》栏目主持人张越采访我的专辑(上、下集)于2003年“三·八”妇女节期间播出以后,有观众打电话问栏目组,那个谁,怎么会有幸福感,怎么会有那么多幸福感。不知道,就是感觉到幸福。我只说了意识到的东西。接到导演方卉的电话,以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而现在,仅仅过去了一年多,又经历了一些离难、变故,世事沧桑,繁复的,简化多了,但是度过了这些时间以后,和许多人类似,一时间竞不知从何说起。
凭心而论,幸福感仍是我经常能够感觉到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家人,也许并不那么如意,但幸福感的确比较多地涌进我心里。感觉幸福的渠道,一直存在着。过去,我一开口唱“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就抑制不住流泪,尽着克制,唱不下来一支完整的歌。现在.我能唱完一些歌了,比如《诺恩吉亚》和《小二郎》,虽然还是不喜欢唱歌,不想唱歌。
《亚细亚的孤儿》,没有再唱。其实,我在心里面唱过几次,往下念唱了两句,即有酸楚的东西涌起,唱不了。但我对幸福的理解没有改变。我体会到幸福,体会到幸福的刻骨铭心与宽博,体会到幸福的艰难、困苦与磨砺,体会到幸福埋藏在土地里,斗争、牺牲,终于顽强地努出、生长出,每一天上路,它消化和埋藏起苦难,而能向更多的人走近,和着人们的力气和心理节奏,发酵后,冒出烟气,蕴藏下新的热量。
有一年,我回旗里,从车站往家走,远远地,见回家的路边上,站着母亲往车站方向看。我说:“你知道我回来?”她说昨夜里梦见了。她高兴得直笑,笑着、笑着,眼泪要出来,嘴唇瘪瘪地抖动了两下,然后她说,咳,回都回来了。又变成全是笑。
我生了小孩,四个月大时,抱着小孩从北京回到旗里。时值四月初,我们旗刚下过一场大雪,我用棉被把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像棵加长了的大白菜。我斜抱着裹了孩子的大包袱,迈进院子,刚绕过院里堆的雪山,就见母亲向门外挪,她的身体撞到门框上,左边、右边,弹过来、弹回去,来回来去好几趟,终于迈出门,迎住我们娘儿俩,把孩子接下。
又一个春天。我们旗正刮特大黄毛风和沙尘暴。我费了很大力气才跨进家门,一边脱大衣抖沙土,一边说:“看看,这叫什么春天。”母亲说:“春天好。”我说:“好吗?净是沙子。”母亲说:“春天好是真的。因为春天总刮风沙就说它不好,可惜了的,白长了人不长心。春天就是春天,就得刮风起沙,翻出新底儿。”好吧,随你。挺好。
母亲这个人,有时候在常规里头,有时候在常规外边,不好把握她在哪种状况里待的时间多一些。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她突然地从这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
我从欧洲的艺术节回来,去内蒙古接她来北京住。跟我聊天时她说,从没有恨过一个人。
她说出这个话,我惊着了。
那天下班回来,我叙述了一点点在外面遇到的事情。现在想不起那天遇到的是件什么事情,跟谁有关。但忘不了,当时内心郁结,愤闷而悲伤。我们一起做了饭菜,吃过饭,放下筷子,之后,母亲对我说了这句话。
这句话把我打懵了,打成弯腰折背的塌秧形状,打回了老家。
缓过一口气,我说,不能吧,怎么会,老太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话虽说有些老旧、有些功用,是以外部和内部斗争为哲学基础建立的,可也是这么多年以来,中国革命依循的其中一条法则。
她大不以为然。
“没恨过。”她又说了这样的话。
她大概是这样理解:另一些爱、或者说更多的爱,是不需要缘故的——所以才这么讲。
她怎么说就怎么是吧。我不想争论。
“文革”前,她做过我们旗的劳动模范,那时候叫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参加的社会实践比我多,实践出真知,劳动长才干,她大概更清楚那句话的含义吧。而在我不算太长的生命历程中,清晰地看到,恨和爱,这两种真实的东西,死缠烂打,互为敌手,不分胜负,始终并存,也终将会共亡。
也许,母亲想表达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她是不满意我,生我气啦。她不认为我应该去恨。她不同意我恨,不同意我有恨。不同意我去恨什么,不同意我恨谁。
我同不同意她,我想保留、省略什么,她并不在意,她认为那是又一回事情。
我心里,有一些话不能说,不敢说,也觉得没必要说。
我不相信,“不恨”这种话。
要看这话怎么讲。即使它真的存在,我宁愿拉开距离看它。即使说这种话的是我母亲,我也不能不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些警惕。
我不相信,你懂。
在我心里,有一句话真实地存在着,就是不原谅。
不原谅,贪得无厌,腐败堕落。
不原谅,欺凌弱小。
不原谅,邪恶阴暗和无耻,永不停歇地见缝插针、谋算和陷害他人。
现在,我又增添了郁闷。
毕竟,老太太真实地生活在她的地方。那天,她捋清楚思绪,说出来的话,是要交待给我,想让我明白一些事理。
我呢,以后也不会问她:她有没有底线,比如……前面,我说的那些方面。
不过,有过重重的经历,能一辈子不恨一个人,还是感染了我。我动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