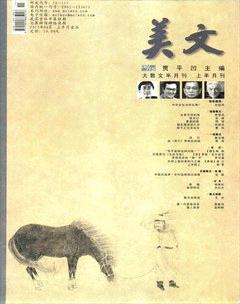“你不能再这样对我!”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诗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其研究领域以文学和思想史为主。顾彬也是中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已发表几百篇学术论文,出版由他撰写、编辑的五十多部学术著作、上百部译著和两种学术期刊,出版八本诗集、两本散文集,三本小说。
在中国,并没有举办公开朗诵会的传统,至少我一开始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也并非全无道理。中国古代人不朗诵,而是歌唱,并且不是在陌生人,而是在朋友面前歌唱,唱的还是自己的诗句。他们一边唱,一边吃喝,经常还有一些美人载歌载舞助兴。至于这类场合是煽情的诗歌、杯里的白酒还是女舞者害羞的神情重要,学者们直到今天还有争议。重要的是,此类源于2000年前古人为迎接春天而进行的清洗仪式的朗诵,只是家庭的游戏。这一点,在中国后来的朝代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明朝时,曾一度很流行2000人的比诗赛,但参加的都是些官场失意的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只好通过写诗来抒发心中的郁闷。当然,这种集体作诗、诗句不通者被罚酒的游戏,是可以控制的,特别是听者的人数,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对此,中世纪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只要有一两位志同道合的人来听我的诗歌,便够了。”
从这以后,中国人便笃信“能听懂我诗歌者,即为我友”。人一般不可能有很多知心朋友,故而严谨来讲,听诗歌的人也不会很多。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多年候选人的北岛(1949年生),最喜欢在公开朗诵会(最起码是在德国的朗诵会)上引用这句话,德国的听众(都多于一至两位)一般回之以一个淡淡的微笑,而我对此却不甚满意。因为作为翻译(口笔译),我花费了很多心血在德国推广中国文学,但获得的成功却屈指可数。这当中的曲折,不知情的人不要说去体会,就连猜也难猜。
我还是不要讲台北那在传统及西方文化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混合朗诵形式吧。比如说2003年秋天的国际诗歌节,在台北剧院登台朗诵的每一个人,上至市长,下至中学生,都心情愉悦地或吟或唱出自己心中或是口袋里装着的诗。我也不想说我那试图在香港举办中德诗人对话的尝试,因为结果让我很是灰心。经过我15年的努力,虽然歌德学院会零零散散举办一些朗诵会,但朗诵会的合作者香港大学和香港艺术中心几乎都不邀请大众参加,每次都是两位孤单的诗人坐在讲台上,他们面前的每张面孔无不是他们认识的,因为都是他们私下邀请的。虽然有粤语、中文、英语、德语四门语言,但我们只能将此称为家庭朗诵会,因为它与在莱茵河及鲁尔河之间的德国地区重又流行的私人朗诵会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情愿谈一谈这二十多年来,让我欢喜让我忧的那些朗诵会。
一 皮皮
2004年9月末柏林国际文学节,我被选作女作家冯丽(1963年生)朗诵会的主持人。当时她获得了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一个艺术家项目的奖学金,可以在有着施普雷河的柏林逗留一年。由于我是一个喜欢把准备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的人,所以在朗诵会前一天,我与冯丽(因酷爱皮皮长筒袜,她在中国将自己称为“皮皮”)在柏林市中心舍恩伯格区的一个咖啡厅见了面,以消除彼此的陌生感。经过两小时的准备,第二天晚上的朗诵会看起来已万事俱备,但仅仅只是“看起来”,因为面对着柏林克洛兹伯格区一个后院的聚光灯和坐满了的听众席时,冯丽突然在朗诵会开始前一分钟告诉我,她不想朗诵已选定的文章,虽然那篇文章是她自己选好的。我拿到的是中文稿,一篇关于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的小短文,而特意请来的女演员则将根据德文稿进行表演。当时冯丽临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说她改主意了。纸条上的内容当然是没有德文翻译的。她说我可以即兴口译。这当然可以,只是这口译的质量就达不到“文学”的标准了。还有,坐在观众席中、花了好几个星期将那短篇翻译成了非常棒的德语的那位译者,他会说什么呢?更别提那特意赶来表演的女演员了。这都是花了钱的!难道柏林有这么多钱,可以随意做无谓的投资吗?而为此特意买了门票的听众们,愿意从我口里听到临时的蹩脚翻译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吗?
听众们很快听到了我们的讨论。麦克风已经打开,朗诵活动早就应该开始了。“这里可不是马戏团耍猴,我们可都是职业的!”我对冯丽说道,“别像个不爱喝汤的小孩子一样闹脾气!”冯丽会德语,她将很多德语儿童读物翻译成了中文,而我用的德语词“Suppenkasper”(不爱喝汤的小孩)她应该是知道的。这个词拯救了那个晚上。小短文是冯丽自己选的,她不想出洋相,所以只能把汤乖乖喝光。她将自己对一对老夫妻的担心作为短文的主题,得到了听众的认可。而翻译的到位,加上女演员给力的表现,使得整个活动并没有变成一场灾难。作为主持人的我,也很开心,因为我没有失职。
二 梁秉钧
不是每个马戏团耍猴都能圆满结尾,有的甚至会十分糟糕,多年的友谊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良好的关系会受到破坏。2000年5月的维也纳,来自波恩和香港的两位朋友间的友谊将在这里接受考验。维也纳大学邀请了香港作家梁秉钧(1949年生)来其新校区开朗诵会。地点选得特别合适,是在原来维也纳综合医院(1796年由弗兰茨二世建立)的解剖室。虽然我们并不是解剖尸体,但同样也是件棘手的事。我习惯准备好朗诵会95%的内容,剩下的5%我让偶然去决定,因为这样不至于太无聊,但偶然则意味着风险。
我原本希望此次的朗诵会会有所惊喜,但PK(梁秉钧的简称,取自其名字粤语发音Ping kwan的头两个字母)却决定朗诵他自创的“聊斋志异”。我并不喜欢这类讲女鬼的东西,因为里面讲的都是些年轻有魅力的女人,讲她们原本都是花,当这些花凋谢时,它们便能变成人重新回归人生。因为我从未遇到过此类事,所以也就对此很不以为然。作为翻译,我并不是诗人,但我对诗人作诗的经历感兴趣,而从未碰到过狐妖的维也纳听众肯定也想知道,应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一个极度渴望爱的已逝灵魂的追扰。当然了,这个灵魂是个女性的灵魂。我认为PK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而我作为一个普鲁士人是没有的。
PK开始滔滔不绝地朗诵起女鬼在人世寻找替身的事,我一边翻译,一边任由着头顶的投影仪将解剖桌上的翻译稿投射到墙上。他说得越多,我就越感觉此刻正有一个狐仙在我们当中驻足。但作为一个欧洲人,应该如何识别一个中国的鬼,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中国的女鬼”呢?根据她无与伦比的美丽?但许多中国女人都很漂亮。还是根据她的残忍?中国只有一些女人残忍。我们还是问问熟知花神的诗人吧:“你碰到过狐妖吗?”诗人的脸在一刹那变得煞白,因为这个问题太过了。翻译把不现实的东西当作了具体的现实,而维也纳的听众也被这问题吓了一跳。那天晚上的结果便是:我和PK带着心里一道深深的裂痕回了家。而这道裂痕,直到很多年后才愈合。梁秉钧后来找了其他的翻译,而我则加深了对鬼怪主题的学习。
三 翟永明
解剖室的那次,女神级诗人翟永明(1955年生)也在场。我在此前的一天与她在综合医院的药房开了朗诵会,当时并没有狐妖来,因为狐妖都是在黑夜中出现。黑色原本是所有重生者的颜色,但这里面隔着的世界,从来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翟永明不想让我提问,但作为一个翻译,一个严肃的翻译,是需要他所翻译的诗人的帮助的,特别是当要翻译的诗歌黑暗晦涩的时候。而翟永明不仅黑暗,而且美丽。至于是黑暗多一点,还是美丽多一点,后人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这不是我所关注的。我关注的是要翻译的诗歌,以及诗歌中那些我求助了其他中国人但未得到解决的地方。这一开始便是一次非常艰难的问答,最后翟永明很清楚地告诉我,以后不会回答我所提出的任何问题。
当然,这可被称为3号马戏团的囧事是事出有因。翟永明不习惯朗诵,因为在她的家乡四川,人们不习惯公开朗诵。要朗诵的话,就得用当地方言四川话,但用方言朗诵,听起来很可笑,可用普通话朗诵,虽然翟永明普通话不错,但听起来总有点外国人的味道。
就这样,被邀请在远离家乡的北京开朗诵会的翟永明,在看到北大400名学生听众后,竟然想拍拍手走人,但往来于波恩和维也纳的我为所有的事都做好了准备,当然也包括朗诵者要落荒而逃。
记得在我和她的第一次朗诵会时,我就和她聊了所有我可能在朗诵会上提的问题。她在一位女性挚友的陪伴下,终于同意从柏林来波恩开朗诵会。而原定在波恩大学举办的朗诵会,原本是不会出什么意外的。波恩的语言文化屋将此次活动视作自己的活动,做了很好的宣传。
那是一个温和的五月下午,波恩大学的会厅里坐满了人,但我不知是怎么了,竟然自以为是地多次打断了她的朗诵,提起了问,而且还提了事先没有聊过的问题。虽然翟永明的回答非常巧妙,观众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媒体也没有白来,但我事后的惩罚很快来了:“你不能再这样对我!”这是翟永明给我的温柔警告。而我作为一个一辈子受女人调教的男人,当然会遵守这句话。她2000年回中国之前,柏林最后为她举办了一次朗诵会。那一次,我一个问题也不敢准备,更别说提了。我知道,她的心在哪里。
像所有美丽的女人一样,翟永明也很重视照片的效果,也想看起来光彩动人。“我看起来漂亮吗?”这是她那晚直到第二天日报出版所关心的唯一问题。而第二天日报上的她,看起来漂亮极了,这对于我这个翻译来说,已经够了。我于是心满意足地从波恩回到柏林。
四 再说翟永明
没有了我所钟爱的提问、回答环节,每一场朗诵会在我看来便失去了悬念,都是可以预料的。尽管这样,这种纯粹的按部就班的朗诵、翻译,开始、结束,中间解释、后面注释也可以在德语区碰到感兴趣而注意力集中的听众。不过,这并不能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成为前提。黑暗的诗人在中国与在德国一样黑暗,但他们在中国会被人以更批判的眼光看待。人们不一定愿意去细细思考那些陌生的名字及困难的篇章,“胡说八道”的评论很快会被得出,一场朗诵会则很容易变成一个多事之灶。人们来,人们走,人们吃,人们喝,人们聊,人们找着自己的乐趣,就像以前的中国人在戏院里听戏一样。
2001年的3月,我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邀请,参加在北京、上海举行的欢送会,卸任领导希望能有一场诗歌朗诵会。翟永明和我于是有了半小时时间,朗诵她的《咖啡馆之歌》。
首先是北大的400名听众,然后是同济大学的400名听众,大部分都是中国人,但都不愿意倾听,注意力不集中显而易见。虽然他们既没有学会如何与困难的文章打交道,也不懂得如何尊重诗人,就连朗诵会的咖啡自助也比当时所朗诵的任何一首《咖啡馆之歌》都更具吸引力,可你连气都不能生。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的朗诵会,翟永明都和她的诗人朋友们坐在一张小桌子上,而我却要与那些热情的中国日耳曼语言学家在一片嘈杂中讨论翟永明诗歌的含义。
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继续折磨着自己去翻译德语界无人敢翻译的翟永明的诗。遇到困难时,我找中国人和德国人帮忙,但不找翟永明。一般来说,我的妻子能猜到翟永明的意思。而诗人、翻译家约阿黑姆·萨托柳斯则让我在看到热情而流动的长诗时安静下来。他赞同翟永明的观点,爱情——这个词是我不愿翻译并在写作时刻意避免使用的词——是所有创造力的源泉,而诗歌源于生活,其魅力正在其平凡、不重要处。就这样,在很多人的帮助下,《咖啡馆之歌》德文版最终找到了出版社,也找到了清醒的读者。但直至今日,怀疑始终没有离开作为翻译的我,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将多少爱降温,并没有照亮多少黑暗。那翻译究竟是否被需要呢?他难道不首先是个仆人吗?美丽女人的仆人?优雅女诗人的赫尔墨斯?
一本书需要一个文学屋,而一个文学屋则需要一个女人的声音。就这样,女诗人翟永明2004年2月初开始去世界各处开朗诵会,巴士拉是其中的一站。我从北边出发,她从东边出发。我在位于德国这边的巴士拉巴德火车站接了她。一切都很顺利,只有我们的护照被认真查看了。当时,我们三年未见。那三年间,我只看到了很多她的照片,是她给《作家》杂志为一个自传系列提供的。我当然知道,只有男人会变老,也只有翻译能体会到翻译这一行业的苦恼。但美丽的女诗人不仅会越变越美,而且会越变越年轻,当时我是不知道的。特别是当女诗人突然转变成女模特时,这于我这个语文学家看来,是很值得怀疑的。但在看到那些青春美貌的照片时,我并没有怀疑,而只是尖锐地笑起来。对,这位女诗人从不应该离开T台,因为那样的话,我便会少几分忧郁了。
幸运的是,从巴士拉火车里下来的并不是一个稚嫩的女孩,而是一个作为酒吧所有者的成熟女人。我不敢马上和她谈起她兼具诗人和模特的双重天赋,所以就把T台照片的事留到了后面,因为我担心她会理解错我的意思。我宁愿跟她讲我翻译她的《咖啡馆之歌》碰到的困难以及其他人对我的巨大帮助。“你为什么不来问我?”我们在一家巴士拉咖啡厅喝咖啡、吃蛋糕时她问起。我一脸不解地看着她。在巴士拉教堂时,我终于敢问她那些模特照的事了。她笑着回答我:“我的读者喜欢我这样!”“可照片上的你那么年轻,太夸张了吧?”我答道。“哎,都是以前的照片,总有摄影师来找我,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很多都是熟人,而且拍照也蛮有意思的。”
这是我们第一次不像狗和猫一样,我们看来好像都成熟了,而在巴士拉的朗诵会则进行得完全不一样。翟永明一袭黑,我一身蓝。她很中国,我很中欧。她声音很小,我音量很大。她的诗行别具诱惑力,而我的翻译则带有寻找的意味。我敢于提出了一些问题,听众们也一起进行了讨论。最后,翟永明给不少书签了名。我的工作并非一文不值。但我难道不是在欺骗自己吗?听众听到的并不是翟永明在纸上念的,而且翟永明朗诵的时候,声音里一直夹带着一丝颤抖,而我则试图在翻译时显得格外自信,避免让听众察觉到她的紧张。
翻译完困难重重的《咖啡馆之歌》,我准备再开始翻译翟永明的其他诗歌,但她却一如既往的谦虚:“还是翻译其他人的作品吧,我的东西你翻译得够多了。”这种话也只有她能说出来,其他人比如PK或杨炼是不可能说这样的话的。他们的作品虽然已被多次翻译成德语,但他们还是不断要求我这个可怜的翻译继续翻译他们的其他作品。
五 王家新
北京的艺术家们习惯在北京城外的乡村扎根。虽然土地还是属于国家,不得买卖,但农民自从人民公社解体后,得到了土地的使用权,便会把那些他们不能种植的土地租赁出去。实际上,此类租赁也意味着转让,因为租赁的画家以及其他浪荡的艺术家们在租赁的地盘上开着大画廊以及各式其他店铺。除非是惹急了当地政府,否则政府是不会派房管或是其他执法人员来查禁,而且查禁归查禁,真正将房屋推倒是没有的。就这样,在北京的门户前,也就是北京郊区,便有了一些艺术家区。它们拥有一致的优势:好的空气、简单的生活、节约的花销,以及最重要的公共安全保护。
在德语区,人们对警察和诗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他们之间水火不容。这在1979年至1989年的中国也不很大相径庭。当时,第一批朦胧派诗人便是在老圆明园的废墟上见面,吟唱他们的新诗。对此,我们不需要再过多地回顾历史。但在绝对市场经济时期,维护公共安全的官员却经常是诗人们唯一,或者说最好的读者,因为他们怀疑这些诗人还在宣扬反抗,哪里料到沉迷于购物消费的大众早就将这些诗人淡忘了,更别说会认为他们还有反抗精神了。如果大家重又觉得诗人有反抗精神,那整个中国的呐喊将是一致而坚决的:世界各地的购买者们,联合起来吧,将诗人打倒。
如今从事公共安全工作的人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有教养的人。他们对于文学有些了解,所以诗人们也能与他们进行关于诗歌的对话。虽然会不欢而散,但大家也不会因此而成为敌人。曾多次来过德国的北京诗人王家新,便很明白应该如何将这里面的种种好处巧妙汇聚在一起,汇聚在他北京西北的诗歌林里,那里有一个很伟大的先行者:圣琼·佩斯(1887-1975)。佩斯曾经在20世纪初,在临近北京的一个杏村里写下了他那伟大的诗歌《阿纳巴斯》。
虽然传统的带花园的四合院对中国人来说很大,但它的面积不够容纳所有受邀参加2002年9月底王家新牵头举办的以“北京西北”为名的朗诵会的人。于是,我们便在他的邻居——一个成功的画家(这个画家都是有人预订才作画,完全依据市场导向创作)的画廊里见面。很多有名望的诗人从中国各地受邀来此参加朗诵会,但在进行激烈的讨论前,先得把肚子填满。王家新带我们去了当地唯一的酒馆。酒馆的陈设与《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们所处时代的陈设相差无几:四面白墙,几张桌子,几条凳子。我们是唯一的客人,故而把所有的地方都占据了。于是乎,酒馆前的平地和稍后冉冉升起的月亮也专属于我们。
饭桌上当然少不了白酒,但喝的人却不多。如果我记得没错,我当时是为数不多静静享用白酒的人,这里面的缘由,我很快就知道了。原来,此类诗歌朗诵会易起争执,经常出事。一旦喝酒,就得喝好久,直到有人感觉到“白酒的精神”,也就是喝吐了。有的故事说,有诗人的妻子最后喝多了,瘫坐在地上,开始擦起了地板,但更多的还是流血冲突。王家新作为此次朗诵的主人,不得不提前向公共安全部门提出申请。申请通过,但王家新对朗诵会的平安举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公共安全部门唯一的要求是:朗诵会在22点必须结束,到点会有迷你大巴来接我们回去。
画廊里的座位很有限,我们或坐或站在一个半圈里。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圈里读自己的诗。有两点比较引人注目:有一个人穿着疗养院的衣服出席了朗诵会,此人便是郭路生(1948年生)。他当时也不想隐瞒自己在疗养院养病的事实,而媒体对他的报道也是正面的。他朗诵了他在“文革”时地下传阅的所有诗歌,而他的病是“文革”结束后很久才出现的。朗诵会上,他说是因为我才来的。他的到来,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真正知道怎么朗诵的人。他不会声东击西,知道如何掌控听众,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们都怀有感激之情,不约而同地想起他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外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一小群青年人,他们给人的印象不是文人,而是一群无所事事的混混。他们一罐接一罐地喝着啤酒,喝完后百无聊赖地用脚将啤酒罐踩碎。他们是四川“非非诗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二十多年前,我曾热血沸腾地将他们的诗翻译成德语。
没过多久,画廊里凳子乱飞,诗人们没有像往常那样拿着破碎的酒瓶,而是擎着凳脚开战。大家好像也对此有所准备,有人甚至提前让公共安全局的人请了警察到场,否则那个晚上将作为一场中外厮杀而被载入历史。
很多到场的诗人已不再写作,而只是朗诵他们以前写的诗,比如芒克(1950年生),北岛曾经的战友。这次,他只带来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是他新写的诗,但实际却没有什么新意可言。我想起他也曾经作为新诗的代表,也曾经是中国相信诗歌力量的先行者。而我,没有什么作为诗人的过去,我的德国声音在这里很陌生,可王家新希望我能读我的诗。我于是先将我的诗用中文解释了一遍,然后才用德语朗诵。我选的是与中国有关的诗,韵律感很强,重复很多。但大家好像并不为我的努力而动容,我自己也习惯了这样,我的诗在德国的反应也一样。
我们不想指责任何人。如果我们能记起比月光下的平地更多的东西,那就够了。
六 郑愁予
朗诵需要翻译,有时一个翻译的演讲才能甚至能挽救一场朗诵会。可惜,这一点经常被轻视。人们觉得有了作者,就有了全部。但事实是,有了作者,经常就有了窘境。我们想一想许多名人蹩脚的朗诵会,就能证实这一点。我们还是不要去想那些拿了不错报酬、却无兴趣去准备、提供与报酬相当的朗诵质量的人。我们也想对有些作家轻便的行囊保持沉默,他们嫌沉,甚至不愿把自己要朗诵的书带上,因为他们觉得翻译会带,或者至少听众会带。我们还是想想那些为数不多的歌唱者,他们即兴发挥的才能很强,无需过多的准备,便能在台上发挥出色。
不少中国作家都声称,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下才能写作。既然这样,那为何不在朗诵会的讲台上放一瓶中国白酒呢?这对郑愁予(1933年生)是有用的,但对北岛却已经不再有用了。无论是在纽黑文还是台北,在波恩还是金门,这位因“美丽的错误”而被大家所熟知的诗人,总是随身带着酒。不过,他不是独饮者,也不是酒鬼,他只是想要找个喝酒的伴。但他像个典型的酒鬼,每次不是打开车的后备箱,就是打开一个塑料袋:“饮料随意选。”有些时候,大晚上酒瘾上来了,他会带我开车在台北的街头到处找还在开门营业的酒馆,那些愿意就着高浓度的酒,给我们上点小菜的酒馆。还有什么比在波恩的联邦艺术廊摆好一瓶茅台酒,在2003年12月邀请这位懂得唱诗的老诗人来开朗诵会更简单的事呢?我们以一杯酒开始了当晚的朗诵会,以一个空空的酒瓶结束。虽然度数有52度,但我们谁都没喝醉。那是德国听众第一次迷醉于一个中国诗人的嘴唇,仿佛不再需要我的翻译了。他在朗诵的时候,很多听众都不自觉地闭起了双眼。“他知道应该怎么握麦克风!”波恩的文学女皇在朗诵会结束后兴奋地评论道。“那酒都让我感觉要飘起来了!”郑愁予自己这样评论道。他在朗诵会上给我们展示了他五十年的人生,一个“美丽的错误”如何变成很多“美丽的错误”,一杯酒如何变为多杯,以及一段诗行如何变为许多歌。
朗诵会上,听众们不断要求郑愁予吟唱那些短歌,最后还播放了录音带。那个夜晚的波恩,夜变得很长。最后,连一同来的杨炼和张枣(1962年生)也被请上台。俄国革命歌曲取代了中国旋律,而波恩的文学女皇也唱了很多歌。
但这却不适用于北岛。他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都鼓动我重新喝酒,自己却在几个月后的2004年的12月拒绝在波恩的语言文化屋喝欢迎酒,而我当时没有准备牛奶。虽然当晚的朗诵会非常成功,但那两瓶摆在讲台上的56度的北京纯正二锅头却丝毫未动,宣告着诗人儒家一面的胜利。孔子真的曾经说过仁者要远离三样东西:女人、仆人以及酒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也知道,为何孔子没有成为诗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