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和一座城市不断较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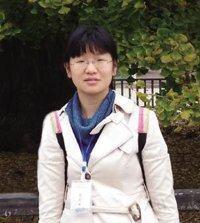
卢欢,80后,湖北某媒体文化记者。关注出版动态,遍访文化名家;喜好阅读,“为了让所有的善意颗粒归仓”;带着谦卑、耐心与好奇心,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丰富的过渡色彩。

“写作于我就是一种巨大的兴趣和创造的感觉。”作家邱华栋说。
少年成名,中文系科班出身,坚持写作二十多年,如今又身为文学杂志《人民文学》副主编,他在文学作品创作领域深耕细作,不仅自己留下了不少“和当下共时空的文字”,也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生态有着独特的观察。
有一阵子,一些文学座谈会时不时讨论“城市文学为什么写不过乡村文学”之类的话题。且不说城市文学在当今文坛是否真的颇显弱势,乡村叙事比城市叙事是否更高明,至少在包括邱华栋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城市文学是沉睡的资源,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或者说,未来能够成为汉语文学的增长点的,毫无疑问是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学。
城市题材是邱华栋写作所擅长的领域。在1990年代,他的六七十篇“社区人”系列中短篇小说密集发表,在国内文学杂志上犹如一轮地毯式的“轰炸”,并迅速地获得了评论界的关注。在媒体报道中,你会看到他被冠以“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圣手”的头衔,甚至,有评论说他是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的代言人。
那时候,他是一个“城市闯入者”,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北京闯荡,很快如愿成为了一名报社记者。早上奔跑于新闻现场,像博览群书一样博览生活,晚上就酝酿着如何把事件变形,升华为文学。所谓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出发的地方,他对此深有体会。
“在我的小说中,我塑造了一座越来越被国际都市流行色同化的北京。”自称“新北京人”的他将写作资源偏向了当代的城市共时性的生活。写得最多、也是最好的作品即是以北京为背景、以中产阶层为描述对象的城市小说。
从城市地理学入手,他看到了城市里的各种建筑符码,以及声光色电和纸醉金迷;而当转换到城市病理学的眼光时,他又发现了建筑符码所代表的城市物质力量和这物质压迫下人的异化,以及都市里一张张冷漠面孔下鲜活的心灵。
不过,时过境迁,他的心理状态也发生了变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写作这件事情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40岁之后,对于中产阶层他不像过去那么有兴趣了,而更愿意穿梭于古今世界,把目光投放在了一个个的生命个体身上,以悲悯之心去观察一个个具体的人生选择和命运。
实际上,除了城市题材之外,邱华栋的写作涉猎面一向很广,历史的,青春的,边疆的,科幻的……另一类写作中,他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历史,投向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无论是选取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历史事件作为背景,还是追踪丘处机、利玛窦等历史人物的足迹,他觉得,在大历史背景下,个人命运像镶嵌画一样,生动地呈现他们鲜亮的生命色彩,也使得我们回头去看那些刚性的历史事件时更多带有了一点柔和的目光。
不断地追问和质疑,竭力走进城市深处
卢欢:您在少年时期就发表了小说,18岁之前出了书,还因为文学特长被武汉大学录取,显然属于出道较早的那一类作家,可视为那个时代的韩寒、郭敬明。回过头看,当时的您与如今的文坛新秀有什么差别?
邱华栋:这要感谢武汉大学给了我这个机会。当时,1985年,我是看到武汉大学中文系特招了一个南京的校园诗人洪烛,就让我所在的中学推荐我,结果成功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二十多万字的作品。那时被保送到各个重点大学的文学特长生一共有一二十位呢,比如北京大学有田晓菲,南京大学有刘梦琳,南开大学有段华、邵文杰,复旦大学有景旭峰等。进入大学之后我们还互相写信联系。我感觉我们这些当年的校园文学才子们,和当代的韩寒、郭敬明们最大的区别还是现在是一个市场化的环境,文学的名利更多更大。而当时文学对于我们来说主要是一个爱好,没有太大的名利,因此,相对更为单纯一些。
卢欢:可以说您是在198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提起最初的写作环境,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邱华栋:我进入文坛没有那么早,少年时期的写作不算。我是1993年之后,因为写了一些与城市生活有关的小说,才被注意到的。当时我大学毕业刚刚来到北京,面对北京这样一座正在迅速变化的庞然大物,的确是感到惊奇,白天写新闻,晚上写小说。我觉得一个作家写作,应该首先要贡献一种符号价值,就是你和别的作家的区别在哪里。一开始就要确认自己的写作取向和风格,也就是去寻找自己写作的符号价值。
卢欢:当文艺青年、写诗在当时像是顺应一种潮流。您很早就在写诗了。
邱华栋:我从十来岁开始写诗,到今天都没有停止,最少的一年也写了5首。只是后来光写,不发表了。因为有的诗涉及到比较私人的生活和情感,就不发了。对于我来说,诗是语言的黄金,我自己每天都要读诗,每年都写,就是为了保持对语言的敏感。我收藏了三千部国内外诗集,我可能受到超现实主义以来的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比较大,以及当代很多诗人的影响。但写诗对于我更像是语言练习和玩儿,我就是写着玩儿呢。
卢欢:在小说方面,您早期的作品大多关乎“成长”的主题,比如20岁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讲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故事,与自己的成长背景有着关联。您把这些作品归入青春期写作一类么,现在如何看待它们?
邱华栋:大学毕业前后,也就是我二十二三岁那时候,写了三个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前面有什么》,都是练笔之作,后来也出版了,但都不成熟。不过,我倒是因此练习了长篇小说的结构和内部时间的把握。写长篇是需要体力和结构能力的,这几部小说对于我个人有着生命的记忆作用,但实在算是一种青春写作。
卢欢:早年在新疆生活,再到武汉求学,这两个地方在您心目中各是怎样的存在,给了您哪些经验和文学资源?
邱华栋:我30岁的时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共18篇,叫做《西北偏北》,是关于我在新疆生活的少年记忆的。2000年去阿勒泰住了一个月,写了一本散文《绝色喀纳斯》。去年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楼兰》。而且,在新疆的生活,目前正逐渐成为我下一步写作的重点。比如,当代新疆面临的严峻的恐怖威胁等等,它的根源在哪里?还有,中国经略西域的历史,也一直是我感兴趣的,我会写关于新疆的当代小说和关于西域的历史小说。
在武汉求学,包括后来我还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了在职文学博士,在昌切老师的指导下,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最终取得了学位。这当中,武汉大学对于我在不断地进行知识准备和学养、眼光的开阔上起到了决定作用。武汉这个九省通衢的大都市、大码头,开放和气魄都是很惊人的。不过,我可能写不出来关于武汉的小说,因为湖北的小说家太能写了。
卢欢:您被贴上了“都市小说作家”和“城市文学作家”的标签,是进入1990年代后的事情了,您写了《手上的星光》、《环境戏剧人》、《闯入者》等几十篇小说,迅速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与此同时您也从武大中文系毕业,去北京工作、定居。北京又给您带来了什么?这背后发生了什么让您如此持续地关注当代城市生活?
邱华栋: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在机关和报社都工作过。我觉得,文学史上有一类作家,是和一座城市不断较劲的,所以我选定了北京作为我观察的对象,写了很多北京在1990年代开始的都市化变化的细节。一直到今天,我仍旧在持续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希望我的写作和这座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要知道,一个作家只有和一座伟大的城市联系起来,才可以获得更久的生命力。
卢欢:对了,您对说您是继王朔之后都市文学新的代言人的评价怎么看?
邱华栋:王朔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对于当代城市文学来说,是开山者。这个人也非常有趣,只是最近一些年不大见到他了。有评论家说,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我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人。不过我们有区别:王朔生长于北京,他天然就是一个北京人;我则从湖北到北京,城市一开始对我有着强烈的震撼力。像我,是以异乡人的身份不断地面对北京,以小知识分子的方式在追问、质疑、拥抱、逃离北京。王朔对城市的书写,就是对他自己的大院经验和成长记忆的书写,北京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外在的空间,北京就是他贴身的服装。而对于我来说,北京永远是一个外在场所,一个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的“他者”和异在,不断地追问和质疑,使得我竭尽全力走进城市深处,也就使我成为全力书写城市的作家。
写“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揭“社区人”的隐疾与暗伤
卢欢:作家刘震云认为您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的生活,眼前发生的新事,放到小说里,要的就是浑浊和新生。这显然是针对您在城市文学方面的创作而言的。一直以来,您也看重“浑浊和新生”所带来的刺激和真实么?
邱华栋:是的,我有一部分的写作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比如,2000到2010年,我写了六十多个短篇小说,叫做“社区人”系列,后来以《来自生活的威胁》和《可供消费的人生》为题结集出版。2015年初至今,我在修改13篇短篇小说,写的是人到中年的情感状态的系列短篇,今年会陆续发表出来。因为生活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对眼前生活的新鲜感的感受和持续的观察,对于我十分有吸引力。
卢欢:我感觉您创作的系列小说较多,比如还有以“××人”为题目的城市“意象”小说,有关于城市的各种“闯入者”的故事。您似乎很喜欢将自己的小说分门别类。关于城市文学写作,您心中是否很早就有了一个谱系,或者说一个理想的目标?
邱华栋:是的,我希望我的写作要和一座城市联系起来。我就打算和北京联系起来。我发现了北京的生活多元、复杂、有趣、丰富。北京是世界性的都市,也是最中国的都市。我作为新北京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这座城市一起度过一段快速变革的时期,并成为这个时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但你发现没有,我写的都市小说,是没有老北京的那种地域特色的,是一种更为国际化和抽象化的城市。有些小说是变形的、夸张的、荒诞的,比较现代,也是小众的。这是我有意追求的目标。
卢欢:是的,现在看来,“时装人”系列短篇小说这类作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运用了那种超现实的、夸张变形的手法,颇有后现代小说味道。这让我联想到,您曾说过:“以城市作为背景的创作常常要直面剧烈的变动性,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往往是不足够的。”
邱华栋:这主要是受到了卡夫卡以来的现代派小说家的影响。我采取了意象、变形、夸张、荒诞、信息、搞怪的写法,来呈现都市人微妙的感觉。
卢欢:但我也注意到,您后来对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有个反省,认为那是属于那种爆炸式样的写作,风格强劲,文艺腔调很足。有时候在一种表面的浮光掠影中,没有深入到城市生活的深处,而是符号化地处理了自己所看到的城市的变化。所以,时过境迁后,您调整了写作方向?
邱华栋:的确,那一段时间的写作,文艺腔太重了,是学院派的路子。现在的写作,比如我刚刚完成的短篇小说系列《十三种情态》,每篇15000字,篇幅也长了,涉及的生活确实千人千面。我在写作的时候,如果说写一个飞行员,那一定要去找来飞行手册看,要了解飞行员的生活。同样,写到一个电脑工程师,我就要深入到他的专业中去学习。这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这个系列是我的最近最新的作品,很有意思的。
卢欢:您起初是关注城市地理学的,后又转到城市病理学上,为何有这种转变?
邱华栋:我到北京工作时,一开始为城市的外在所震动,城市建筑与建设的复杂和广大,城市欲望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扩展,都是我观察的方向。于是,我很关注城市在地理意义上的变化。但后来我发现,无论高楼大厦多么现代,无论一个人怎么修饰自己伪装自己,如果剥开了他们生活的外衣,就会发现,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烦恼事,每一个人甚至都有自己的情感痛点,这个痛点是他们的隐疾与暗伤。于是,我就开始研究城市人的病态。写“社区人”系列的小说,我抓住了当今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勃勃兴起的新阶层,把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与疼痛揭示出来,这是当代生活的真相,也表达了中产阶层的困境:他们一直试图寻找到理想的生活,并努力地承担着生活赋予他们的一切考验,但却不断地遭到各种挫折而无所适从。
卢欢:将目光聚焦到北京郊区的中产阶层的生活社区里,这种写作多大程度上是依据您的生活经验的?
邱华栋:观察、经验和想象是写作的三大法宝。很多小说的确都是来源于我的生活经验和我对生活的观察。比如,小说《流水席》的完成,就得益于一个叫黄柯的朋友,他的人生具有传奇色彩。据说,他是经历了一次车祸而生存下来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存在来自于某种神秘的关照。后来,他就在北京望京自己的房间里,开了一个很有名的流水席——整天接待朋友和朋友带来的任何人吃饭,成了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别人可以在他家白吃白喝的地方。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就此做了专题节目。比如某年过年,十多天里,他招待了三千人。我就去过好多次,曾经建议老黄把来过的各种艺术家按照门类,组织他们以流水席为题材创作不同门类的作品,一定好玩。我还答应自己也写一篇,于是,这样一篇小说就诞生了。但是,我从来没有问过老黄他当时是怎么遭遇车祸的,是在什么情况下遭遇车祸的,因此,那篇小说就完全是我本人的虚构和想象了。
再比如《威胁总来自黑夜》的写作,来自于两个触发点。一个是在我家附近,去年夏天的一天晚上,忽然有警察抓那些建筑工地上看黄片的民工。结果,有的民工逃跑的时候,掉到粪池子里淹死了几个。这使我想到了民工的性生活压抑的问题。还有就是一天晚上,在机场附近,我们的班车坏了,在冒雨步行穿越一片黑暗的空地时,一个黑影企图抢劫我,被我给打跑了,于是,我就写了《威胁总来自黑夜》。这个小说主要涉及到了现在贫富分化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还有些小说涉及到代孕、借种、激情杀人、婚姻危机、未婚早孕、师生恋等问题,都是我周围人的生活表现。
卢欢:“来自生活的威胁”、“威胁总来自黑夜”中的“威胁”具体指什么?您是在强调现代生活赋予社区人、中产阶级的考验,以及它对人的异化么?
邱华栋:那种威胁是无所不在的,类似达摩克里斯剑那样悬在我们的头顶。对于很多人来说,日常生活中的无常和突然的灾祸临头,是很容易发生的。破产、失去亲人、交通事故、刑事案件、各类意外事故和各类无法预测的灾祸,悬浮在一个个体生命的头顶,说不定哪天就是灭顶之灾。对于在生活中奋斗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很害怕自己努力奋斗得到的东西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因此,生活中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不光是人的异化,而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威压是从心理到生理的综合的压力,是无形的,但又是可能的。
卢欢:您的小说也提示了我们今天的处境之一,是城市的存在、发展以及城市人的生活与现在这个消费时代关系密切,中国日常生活的主导意识已彻底完成由“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对于“可供消费的人生”,您是怎样的态度?
邱华栋:对于很多人来说,人生就是一场消费的过程。人的生命正在被商品代码化,商业社会使一切都具有了价格,人的生命在投入社会中的时候,就具有了消费性,这是今天这个商业社会的特性。我对人的消费性是持批判态度的,人之所以为人,是人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要远大于人的消费特征。但现代社会里人的指向过于强烈地导引到消费的符号化里,这是可悲的、必须要批判的现象。
卢欢:还有,您的小说代表作《教授》在上世纪末就对当代知识分子做出了深刻观照,写出了教授的新面孔,称之为“叫兽”——“在课堂上、电视上、研讨会上,甚至是女人的身体上叫着”。当初看过小说的部分读者还觉得观点过于偏激,如今这个绰号越来越广为人知,他们又重新发现书里说得没错。您现在对这部作品有什么话说?
邱华栋:《教授》是2008年写的。我对于利益集团结盟的知识分子比较注意,就塑造了那些形象。不过,现在我觉得我更需要进入到我观察的人物的内心,而不是从外部以漫画的方式去讽刺。悲悯心是到40岁之后,在我心里才更多地涌现出的。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包括贪官,把他当一个丰富和复杂的人去写的时候,小说本身才有价值。
另外,现在中国的现实太庞大、复杂了。一个作家很难整体上去把握,需要慢慢来,拉开距离。如今我对于中产阶层,不像过去那么有兴趣了,我把目光投放在了一个个的生命个体身上,去观察一个个具体生命的人生选择和命运了。
左手写都市,右手写历史
卢欢:再来聊聊您的历史小说创作吧。这些年您在写完了一部当下现实题材的小说之后,就会写一部历史小说,这样的交替写作对您来说很有必要?
邱华栋:我平时喜欢读闲书,乱翻书。其中就读了不少历史书。二三十岁的时候,心态比较浮躁,写了不少当下都市题材的小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慢慢静下来了,读书也更加杂乱。在阅读历史著作的时候,我时常会萌发写些新历史小说的念头。我不喜欢重复自己,或者说,每次写个小说,总要稍微有些变化,或者题材,或者结构,或者叙述语调等等。可以说,我的左手写了不少当代题材的小说,右手,就又写了一些历史小说。
卢欢:说到您的历史小说,读者比较熟悉的大概是《中国屏风》系列,那四部描写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的长篇小说(包括《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贾奈达之城》《时间的囚徒》)了。但我注意到,您去年其实还完成了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叫《十一种想象》,这里面涉及的题材视野更广了。能谈谈创作时的灵感来源么?
邱华栋:《十一种想象》收录了我写的11篇历史小说,包括3个中篇和8个短篇。从题材上看,中外都有,不同历史时期都有,都是依据一些史实所展开的一点想象。
其中,《安克赫森阿蒙》是一篇关于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小说。图坦卡蒙的死因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十分神秘。我某年出国,在异乡的宾馆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了一部纪录片,讲的就是考古学家对图坦卡蒙的金字塔进行发掘的情况,后来我又读了几本关于埃及法老的书,有一天兴之所至,就写了这篇小说。
《瘸子帖木儿死前看到的中国》讲述了瘸子帖木儿险些对明朝中国发动战争的故事。据历史学家说,假如帖木儿不是碰巧死了的话,明朝将面临最大的一场危机。
《玄奘给唐太宗讲的四个故事》取材于《大唐西域记》,我挑选了几个对唐太宗应该有触动的故事,由玄奘亲口讲给了唐太宗听。
我一直很喜欢《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最终导致了《三幅关于韩熙载的画》的写作。在小说中,我想象了历史上失传的、关于韩熙载的另外两幅画的情况,以及韩熙载和李煜之间的关系。
《色诺芬的动员演说》取材于古希腊著名作家色诺芬的著作《长征记》。我一直对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著作有兴趣,这篇小说不过是随手一写。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座古城里醒来,而一个古代的人在我的耳边说:“这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和建造的城市,它是亚历山大城!”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很年轻就去世了,死之前他已经建立了很多亚历山大城,他的远征路线一直到了印度。我不知道我今后会不会写一部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长篇小说。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我对他的生平特别有兴趣。
《利玛窦的一封信》则是我有一天去北京市委党校,看到利玛窦的墓地之后,产生了写一篇小说的想法,写作主要取材于他的《中国札记》和史景迁的研究著作《利玛窦的记忆之宫》。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了丘处机的一些诗作,非常喜欢,就对这个人物发生了兴趣。何况他又是中国道教的著名人物。因此,才有了《长生》的中篇版和长篇版。小说写的是13世纪初期,丘处机道长收到正在成为人间新霸主的成吉思汗的召请,不远万里地前往如今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下与成吉思汗面见的故事。假如今后有时间,我还想再把《长生》的小长篇扩展成一部大一点的长篇,类似吴承恩的《西游记》那样,虚构出丘处机带着十八个弟子,一路上与妖魔鬼怪斗法的故事,这样是不是更有趣呢?
卢欢:尽情表达历史人物的内心声音,这是您写作时为自己设下的挑战?
邱华栋:一切历史小说也都是当代小说,正如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在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有意地、尽量去寻找一种历史的声音感和现场感,去绘制一些历史人物的声音和行动的肖像。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历史小说观念使然吧。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她所写的《哈德良回忆录》、《熔炼》对我影响很深。此外,我觉得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魔戒》是另外一路的历史小说,他把神话和欧洲人的历史以想象出一个全新谱系的方式来重构,其瑰丽和繁复的想象是我特别震惊的。
我不大喜欢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那些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与写法,都过于陈旧和传统,大都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外面打转,没有进入到历史的复杂情景和人物的复杂内心,也无法逼近历史的真实。主要是依赖习惯旧的审美趣味的大众在传播,在小说层面上,我觉得没有创造出历史小说的新境界。
至于我的那11篇历史小说,于我自己是一种题材的拓展和大脑的转换,假如能给读者带来一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和会心的微笑,我觉得就很好了。
卢欢:据说您今年计划写一部科幻小说集,叫做《十二种宇宙》。这是第一次写科幻题材?怎么想到跨越到未来向度的写作中去?
邱华栋:我最爱看科幻片电影了,总让我感觉人在宇宙中是那么渺小。我喜欢卡尔维诺的短篇集《宇宙奇趣》那样的科幻小说,也很想试试,写出那样有趣的小说。因为我的小说集《十一种想象》是历史小说,《十三种情态》是当代题材的情感小说,那么,《十二种宇宙》就是关于未来的科幻小说。这样,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这不是很好?所以,写作有时候一定要不断地突破自己,给自己提出新的任务和可能性,最终,你的写作才会有意思。
卢欢:在您看来,保持文学阅读的兴趣很重要,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作家,但文学修养则会内化于一个人的心灵和日常生活。您经常给人推荐阅读书目,这里面哪些是您自己常读常新,也会反复提到的书?又有哪些阅读习惯?
邱华栋:德国人喜欢阅读有难度的书、复杂的书、有思想的书。中国人的阅读层面还比较喜欢热闹、通俗和过于生活化。阅读是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很重要的过程。我每年要翻阅几百本书,也藏了两三万册书。我觉得,书很难死掉,纸书太完美了,不会死掉。经典,比如先秦散文、唐诗宋词、《红楼梦》,以及卡夫卡、普鲁斯特等很多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都是应该不断地阅读的。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书单,而且,这个书单要不断地变化。
说到阅读习惯,我习惯躺着读书。我有一个带滑轮的小书车,和床一样高,放在床头,一般这个滑轮车上有五十多本书,都是我最近要看的,我就东翻翻西看看,每晚如此。滑轮车不变,滑轮车上的书,隔一段就要换一换了。
责任编辑 向 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