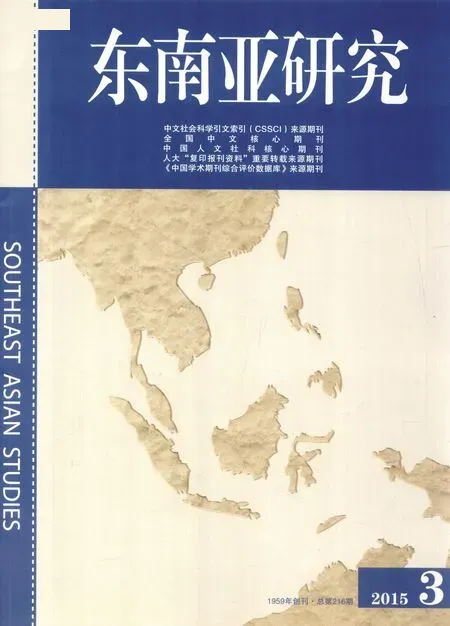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与局限性研究
李建勋
(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湖北黄冈438000)
南海极具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近几十年层出不穷的海盗与武装抢劫事件严重威胁中国的海洋安全,也严重影响南海各方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破解南海现实困境急迫性之认识,南海各方于2002年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该宣言表达了各方共同利益之诉求:“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有关各方可探讨或开展合作,可包括以下领域:海洋环保;海洋科学研究;海上航行和交通安全;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包括但不限于打击毒品走私、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以及军火走私。”①《南海各方行为宣言》,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9zt/2009 -03/17/content_ 1692028.htmZou Keyuan,“Seeking Effectiveness for the Crackdown of Piracy at Se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1,2005.上述合作涉及领土主权等高敏感领域以外的低敏感领域。为了因应上述低敏感领域问题,南海各方几十年来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达成了一系列规范各方行为的协议、决议、宣言与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海低敏感领域区域合作法律机制。该法律机制涵盖海洋环保合作法律机制、海洋科研合作法律机制、海上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法律机制等诸多领域。分析南海低敏感领域区域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以及探寻破解南海低敏感领域区域合作困境的路径选择,对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国海洋经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对促进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进行分析。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就南海航道安全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国内学者李金明就南海周边各国打击海盗与加强反恐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②李金明:《南海地区安全:打击海盗与反恐合作》,《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 期。;金永明从国际法视角分析了中国的海洋安全与南海问题的特质与政策回应③金永明:《南海问题的政策及国际法制度的演进》,《当代法学》2014年第3 期。;史春林探讨了影响南海航行安全的主要因素④史春林:《当前影响南海航行安全主要因素分析》,《新东方》2012年第2 期。;邹立刚剖析了南海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⑤邹立刚:《关于南海若干重大法律问题的探讨》,《法治研究》2013年第6 期。;张湘兰重点探讨了南海周边各国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⑥张湘兰:《南海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研究》,《法学论坛》2010年第5 期。;其他学者,如包广将、王历荣、文铂、钱忠礼、张丽娜、郭渊、葛红亮、刘阿明等等也就南海航道安全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国外学者Robert Beckman 回顾和分析了马六甲海峡沿岸各国打击海盗的合作机制⑦Robert Beckman,“Singapore Strives to Enhance Safety,Security,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Its Port 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Ocean and Coastal Law Journal,2008,p.167.;Noel M.Morada 探讨了区域合作应对南海航道安全等问题的路径机制⑧Noel M.Morada,“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ional order:between norms and balance of power”,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Asia Pacific Countries”Security Outlook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fense Sector workshop,January 21 -22,2010,p.33.;Mary George⑨Mary George,Legal Regime of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Lexis Nexis Malaysia,2008.,Rosenberg David⑩Rosenberg Davi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ir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Naval War College Review,Vol.62,No.3,2009.,Zou Keyuan⑪《南海各方行为宣言》,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2009zt/2009 -03/17/content_ 1692028.htmZou Keyuan,“Seeking Effectiveness for the Crackdown of Piracy at Sea”,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1,2005.,Ian Storey⑫Ian Storey,“Securing Southeast Asia's Sea Lanes:A Work in Progress”,Asia Policy,No.6,July 2008.,Mark G.Rolls⑬Mark G.Rolls,“ASEAN and the Non-Traditional Regional Security Agenda”,Track II India-NZ Dialogue,Wellington,New Zealand,13 -14 September 2010,http://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47737129_ ASEAN_ and_ the_ non-traditional_ regional_ security_ agenda,Robert Forster.⑭Robert Forster,“Trouble at Sea:Maritime Threats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tegration in Southeast Asia”,http://forster-photography.com/wp-content/uploads/2012/12/Forster-Robert-Trouble-at-Sea-October-2011.pdf、John Mo⑮John Mo,“Options to Combat Maritime Piracy in Southeast Asia”,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Vol.33,Issue 3 -4,2002.、H.E.Joseluis Jesus⑯H.E.Joseluis Jesus,“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 against Piracy and Terrorismat at Sea:Legal Aspect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Vol.18,No.3,2003.等就南海的海上航道安全保障等非传统区域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上述研究存在不足:缺乏对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与局限性及因应策略的深入探讨。
一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之有效性检视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是指南海各方为了维护南海航道安全,以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国际合作等方式建立的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具有实际后果的一系列规范、规则、原则等的总和,包括多边合作机制、双边合作机制与全球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开始于20 世纪70年代,形成于20 世纪90年代,发展于21 世纪初。首先,多边合作机制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协议、决议、宣言等形成的对合作方具有一定约束力或能产生一定实际后果的行为规范。其主要包括:20 世纪70年代由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倡导的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20 世纪90年代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形成的新—马—印三边海上与空中巡逻执法机制;肇始于20 世纪90年代的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形成于2004年的《打击海盗与武装抢劫船舶亚洲区域合作协议》 (ReCAAP)区域合作法律机制。其次,双边合作机制主要指东盟成员国之间为了打击海盗、武装抢劫等非法行为而形成的一系列规范、规则、原则等的总和。这些双边合作包括:印尼—新加坡联合巡逻机制;马来西亚—印尼协议机制,马来西亚—印尼协调巡逻机制(MICP),马来西亚—印尼操作协调巡逻机制(MIOCP);马来西亚—菲律宾巡逻机制;马来西亚—泰国联合巡逻机制;菲律宾—印尼巡逻机制等等[1]。最后,全球合作法律机制是指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与《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等全球性公约或协议为合作框架所形成的一系列规范、规则和原则等的总和。
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问题是国际治理与国际合作的核心,决定了国际治理与国际合作的成效。深入分析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可以更好地明晰南海各方在共同应对海上航道安全方面区域合作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对加强南海各方的进一步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的含义
“有效性”是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核心概念。“有效”意指“能实现预期目的”, “有效果”[2]。“有效性 (effectiveness)”意为“产生预期结果”[3]。学者Olav Schram Stokke 将“有效性”解读为“所建立的合作法律机制得以解决或缓解具体问题的程度”[4]。更多的学者则从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的视角界定“有效性”的含义。Marc A.Levy 等认为: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在于形成文本规范以解决机制创制者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5]。奥兰·R.扬却认为: “从最一般的层面来看,有效性是用以衡量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或影响国际行为的一种尺度。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与国内制度的有效性一样,是可以从能否成功地执行、得到服从并继续维持的角度来加以衡量的。”[6]他的这一定义在国际机制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但奥兰·R.扬的理解侧重于对国际法律机制的实然解读,忽视了对其应然层面的“伦理证成”。
笔者认为,应从实然与应然两个层面对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进行界定。一方面,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是指该机制在其运行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实际实施效果,即通过相关合作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行为或非国家行为,以及解决区域性与全球性问题的程度;另一方面,有效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应该是内在的体现公平、正义等价值追求目标的合作手段,此种内在价值追求应该反映当代及后代人类、区域与全球层面公众的正当需求。具有此种正当合理性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就能对各国及其民众的行为发挥影响和约束,因为其符合各国及其民众内在的道德要求。借鉴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将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界定为:南海各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为了实现南海航道安全保障的共同利益而采取的合作法律机制所能达成的实际效果及其应具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程度。
(二)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的评估标准选择
对国际合作法律机制有效性的研究必然引出对下述问题的思考:如何评估法律机制的有效性,评估机制有效性的标准与程序是什么[7]等等。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对此,学者们的观点可谓百家争鸣。奥兰·R.扬坚持评估国际合作机制有效性的三个标准,即“第一,机制对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改变程度;第二,机制对所涉及问题的解决;第三,机制对问题的解决以和平有效的方式进行”[8]。有学者则坚持,对国际合作机制进行有效性评估时,既需要确定对机制实际绩效的参照点,也需要给定评估标准[9];有学者建议,对国际合作机制进行有效性评估时,要对其所达到的目标进行区分[10];国际法学者则通过研究“遵约”以考察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11];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更是以遵约研究为基础,提出了评估国际机制有效性的三个标准:目标获得、问题解决与集体最优[12];也有学者将国家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履行相关国际合作机制作为评估机制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指标[13];国内学者认为,“国际制度有效性评估标准除了关注政治、经济、生态标准这些所谓的问题解决视角外,最近的研究也越来越关注过程管理,并作为问题解决视角的补充”[14]。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整套评估国际法律机制有效性的具有说服力的标准体系。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评估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标准分为内在标准(如表1 所示)与外在标准(如表2 所示)。
内在标准是指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所形成的规范体系在形式上是否符合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基本构成要素,即是否具有完善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与纠纷解决机制等。首先,南海航道安全保障领域的决策机制实质上就是立法机制,它往往以缔约方会议决议、部长会议决议、联合宣言等方式,不断补充、修改、解释该法律机制的内容。一般来说,决策机制越能够不断解释、形成、补充与修改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这种决策机制的有效性就越高。其次,合理的执行机制可以在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运行过程中,由缔约方通过具体规范设置相关的组织机构和遵约机制,以加强各缔约方的履约能力和确保该法律机制得到较好实施。再次,具有权威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化解缔约方矛盾和提高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作用。最后,资金机制是缔约方能够有效实施合作法律机制的保障。

表1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的内在标准

表2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的外在标准
外在标准是指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实践。缔约方数量、缔约方自愿遵约情况、缔约方履行情况、合作法律机制所能解决问题的程度等外在实践都可以成为衡量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的外在标准。首先,缔约方数量影响机制的有效性。按照美国学者奥尔森的观点,集团内成员数量的多寡影响集体行动的成功与否。小集团因为成员数量少,相应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因素就少,其促使国家之间的合作可能性较高,相应地小集团所形成的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程度也高。南海各方作为一个合作集体,符合奥尔森的小集团规模(10 多个成员),更易于采取集体行动。但如果这个小集团的一些成员拒绝参与合作,反过来也会影响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其次,遵约与合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有着密切联系。遵约指各国是否遵守国际协议条款以及是否遵从它们制定的执行措施[15]。遵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机制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影响和改变的程度[16]。再次,履行与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密切相关。David G.Victor 等认为:“履行对有效的公共政策至关重要,对那些引导国家行为的国际协议尤为如此。”[17]履行是缔约方将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以国内法的形式认可并让国民一体遵守的情形。履行对于衡量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没有履行,就无法实现有效的国际合作。最后,导致机制生成的问题得到解决的程度是衡量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因为“国际机制通常是对具体问题的回应——环境退化、关税高涨、边境冲突。归根结底,有效性是指机制对推动其创设的问题得以解决的程度”[18]。因此,导致机制生成的海上航道安全问题所能解决的程度,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该机制的有效性高低。
(三)评估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有效性
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仅仅具备了上述内在标准,不等于具备了有效性,因为机制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改变和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才具有实践意义。同样,机制具备了上述外在标准也不等于该机制的有效性就高,只有综合分析机制的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才能较为全面衡量该机制有效性的高低。对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的评估,如表3所示。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坡主导,其他使用国参与的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有效性程度很高,无论是机制的内在标准,还是参与国数量、遵约情况和履行情况等都基本达到了合作各方的要求;由新加坡、马来西亚与印尼形成的三边联合巡逻机制有效性程度也很高;东盟机制使得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海上航道安全保障合作更加深入,合作效力较高;中国与东盟在海上航道安全保障方面正在形成有效机制,合作水平不断提高,软法机制对于各方的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效性程度较高;有效性程度最高的则是东盟成员国相互之间形成的双边合作机制。
有效性程度最低的是全球合作机制与ReCAAP区域合作机制。首先,就全球合作机制而言,东盟成员国一些国家根本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以及《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①泰国和柬埔寨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印尼、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与泰国没有签署《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全球合作机制中执行机制、纠纷解决机制与资金机制根本无法在南海海域得到有效实施,更谈不上全球合作机制的遵约和履行。其次,就ReCAAP 区域合作机制而言,由于海峡沿岸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迄今为止都没有签署ReCAAP 协议,所以,根本无法在南海海域形成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

表3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评估(内在标准与外在标准)
此外,机制的问题解决程度也可以成为检验机制有效性的重要标准。多年来,海盗与武装抢劫等海上袭击一直威胁海上航道安全,南海各方通过集体行动对海盗与武装抢劫等海上袭击起到了一定威慑作用(如表4 所示)。

表4 2003—2013年南海及周边国家海域抢劫事件次数统计
从表4 可知,近十年来,整个南海海域的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事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事件的发生频率整体有所下降,从2003年的188 次下降到2013年的133 次。第二,2006—2009年期间,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次数最少,南海各方的合作处于较好时期。第三,印尼海域、马六甲海峡和马来西亚海域的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事件一直居高不下;越南海域和菲律宾海域的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事件虽有所减少,但一直困扰着两国当局;除南海各方近海海域外的南海海域,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前几年处于沉寂或低发态势,但近几年又死灰复燃。第四,只有柬埔寨海域没有发生过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事件;相关各方在新加坡海峡的努力效果较为明显,近几年很少发生海盗袭击事件;泰国海域和中国靠近港澳的海域,海盗袭击与武装抢劫也正在销声匿迹。
从问题解决的视角而言,以表4 的数据进行整体评估,南海各方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有效性程度不高,尤其是处于黄金水道的马六甲海峡,各方在该水域的合作基本上没有取得成效。但综合考量内在标准与外在标准的评估结果,南海各方形成的双边、多边与全球合作法律机制具备一定的有效性。首先,保障海上航道安全的共同利益诉求让南海各方协作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其次,有利于南海各方搁置传统领域的利益争端,实现共同应对新型海上安全问题的合作共赢。再次,合作发展是时代主题,南海各方在海上航道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有利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最终惠及各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局限性考量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有效性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其重要原因在于该机制存在局限性,使该机制的作用发挥受到限制。具体来说,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一)合作机制的软法性导致遵约和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
南海各方形成的多边合作机制主要表现为国际软法机制,这些机制对合作各方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如东盟八国、中国、日本等18 国签署的Re-CAAP 协议虽然规定了成员国应尽的义务和能够享有的权利,但权利义务不具有强制性,其对成员国是否应该将协议中的义务国内法律化,以及是否应该监督国内执法机构实施这些规定,都没有规定拘束性机制。成员国的遵约与履约完全基于政治意愿和道义责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为主导的海峡合作法律机制,虽然以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的形式规定了新加坡等三国对海峡享有的主权权利,也规定了海峡使用国应承担的责任,但义务的软法性导致成员国履约行为的非拘束性,最终导致“合作机制在促进海峡航道安全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19]。
(二)合作机制固有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损害其权威性
虽然法律机制都是利益相关方博弈的结果,其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妥协的产物,没有妥协就没有合作,但包括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在内的国际合作机制,合作相关方的妥协或者合作更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其上没有一个更具权威性的机构或机制进行约束,利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妥协或合作的纽带,如果利益发生变化或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妥协各方就会退出妥协,合作就会崩溃,维系其合作的法律机制就丧失其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因为该合作机制是国际软法机制,不具有惩罚国家行为体违约行为的机制,最多只能影响违约国家的国际声望或国际形象。该机制的弱惩戒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其权威性的最大发挥。
(三)合作机制的原则性影响权利义务的确定性
机制的软法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机制的原则性或抽象性,而机制的原则性影响了成员国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如虽然东盟成员国之间在反对海盗行为、维护航道安全方面有共同的愿景,但东盟并没有一个清楚明晰的计划去实现这一目标,东盟所采取的行动大多仅仅是“宣言”,缺乏成员国应采取的具体“联合行动”的义务,各国因此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所以,东盟在维护海上航道安全领域的进展不大[20]。虽然南海各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并没有明确合作各方在维护海上航道安全方面应该履行的具体义务等内容;虽然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机制没有拟定保障海峡海上安全的具体措施和成员国应尽的具体义务,最后导致“新的合作机制在促进海峡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21]。
(四)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受限于国际势力干预性
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是妥协的产物,机制的健康发展需要逐步摆脱域外大国的干涉,机制应该具备独立性。但南海各方在维护海上航道安全保障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欧盟、印度等域外大国和地区的不利影响。美国为了稳固其全球霸权地位,插足南海事务一直是其重要战略之一,如美国提出了专门针对马六甲海峡的《区域海事安全倡议》。该倡议是一个监测马六甲海峡的区域外倡议,涉及提高信息共享、改善决策结构、加强区域海岸警卫队,以及改善机构与部门合作以整合区域能力等内容[22]。由于除新加坡外的多数东盟国家都抵制美国在该区域强有力的军事存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海事安全倡议》没有得到实施,但美国一直通过双边或多边军事合作等加强在该区域的存在,影响了南海各方区域合作机制的独立性发展[23]。此外,欧盟和印度等域外势力进入该区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海各方的区域合作。
(五)合作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影响其实效性
国际合作法律机制通常表现出“相当高度的公共物品属性”[24]。南海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也具有这一属性。国家行为体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国家作为理性个体在进行国际合作之前会进行利益权衡,可能会基于特别的国家利益考量而选择不合作,也可能基于成本—效益考量而选择“搭便车”。因为机制的“公共物品属性”,国家行为体即使不合作也可以享受合作法律机制带来的惠益,但利益相关方的不合作肯定会影响合作法律机制的实施及其有效性的发挥。南海各方的合作就存在类似情形。南海各方为了应对航道安全问题,多数国家选择了双边与多边合作,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南海各方的区域合作与全球性合作法律机制成效不显著,其原因之一在于,作为海峡沿岸国家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基于国家利益的特别考量至今没有签署ReCAAP 区域合作协议,泰国等沿海国家没有签署打击海盗与武装抢劫事件的全球性公约,这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机制的有效实施。
三 因应南海航道安全保障困境之路径选择
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利益成为国家合作的联系纽带。如何平衡利益考量,完善南海航道安全保障合作法律机制,成为南海各方加强海上合作、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课题。
(一)建构软硬法有机联系的合作法律机制
国际软法机制因其灵活性、弱惩戒性等更易于促进国家行为体的合作,为合作者之间扩大合作领域、形成合作互信提供极大便利,但其欠稳定性、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等特性也可能使国家退出合作,不利于合作各方的长期、稳定合作,不利于南海各方长期、有效保障南海航道安全。因此,笔者建议,随着南海各方合作的深入发展,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由南海各方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航道安全保障区域合作法律协议,形成国际硬法机制;也可以在现有《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经过南海各方的磋商、合作,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以规范包括航道安全保障合作在内的一系列南海低敏感领域区域合作法律机制。
(二)完善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
合作机制的妥协性与弱惩戒性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权威性的发挥,南海各方可以通过完善机制的内在构成要素加以应对。首先,完善高效的决策机制。为了提高决策的高效性,缔约方会议可以在两种会议表决方式“全体一致”和“多数决定”之间作出选择,应该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选择不同的表决方式,以实现高效的决策。其次,强化执行机制的有效性。通过技术指导、资金援助、提供培训机会等强化合作机制在各国国内的遵守和执行。再次,建立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通过缔约方协商、调解与仲裁等方式解决各方存在的纠纷。最后,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因为航道安全直接影响各国海洋经济的持续发展,建立稳定、有效的资金供给机制应该成为南海各方的意愿和实际行动。
(三)协同努力确保合作法律机制的独立性
南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历史原因使其成为相关方关注的热点。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在南海的影响依然存在。美国依然以冷战思维对待东亚和南海区域,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美国曾经和正在加大对南海乃至整个东亚的影响和控制;日本、印度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将南海作为其战略关注点,有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南海各方应协同努力,共同构建不受域外势力影响的、真正独立的海上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其对南海各方海洋经济发展及地区和平稳定都极具战略意义。
(四)强化南海各方有效合作的“选择性诱因”机制
按照美国学者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如果理性个体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可以通过创建“选择性诱因”机制以诱使其采取集体行动,如通过物质性奖励、国际声誉等影响理性个体的行为选择。制度经济学的建构主义则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文化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因此,培育国家行为体在规范、规则、意识形态、文化等领域的共同价值追求有利于共同合作中的机制实施。为了破解南海航道安全保障的集体行动困境、促进南海各方有效实施航道安全保障法律机制,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创建激励机制、国际声誉影响机制、海上安全文化培育机制、意识形态领域交流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工具手段予以应对。
【注 释】
[1]Int'l Maritime Org.(IMO),“Jakarta Statement on Enhancement of Safety,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IMO Doc.IMO/JKT 1/2,Sept.8,2005;Ian Storey,“Securing Southeast Asia's Sea Lanes:A Work in Progress”,Asia Policy,No.6,July 2008.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390 页。
[3]《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缩印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45 页。
[4]Olav Schram Stokke,“Examining the Consequences of Arctic Regimes”,in Geir Hranneland & Olav Schram Stokke eds.,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rctic Governance:Regime Effectiveness and Northern Region Building,London:Routledge,2007,pp.15 -16.
[5][18]Marc A.Levy,Oran R.Young,Michael Zürn,“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o.1,1995,pp.267 -330.
[6]〈美〉奥兰·R.扬:《国际制度的有效性:棘手案例与关键因素》,载〈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7 -189 页。
[7][9]Arild Underdal,“The Concept of Regime Effectiveness”,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27,No.3,pp.227-240.
[8][24] Oran R.Young,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Building Regimes for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10]Arild Underdal,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in Arild Underdal & Oran R.Young eds.,Regime Consequences: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Strategies,Dordrecht:Kluwer,pp.27 -48.
[11][13]Edith B.Weiss,“Rethink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in Eyal Benvenisti & Moshe Hirsh eds.,The Impact of lnternationa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eoretical Perspectiv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40.
[12]Hovi,Jon,Detlef F.Sprinz & Arild Underdal,“Regime Effectiveness and the Oslo-Potsdam Solution:A Rejoinder to Oran Young”,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3,No.3,pp.105 -107.
[14]王明国:《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以国际环境保护制度为例》,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5]Edith B.Weiss,Harold K.Jacobson,Engaging Countries:Strengthening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cords,Cambridge:MIT Press,2000,p.4.
[16]H.K.Jac obson,Edith B.Weiss,“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Lessons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in Mats Rolen,Helen Sjoberg & U.Svedin eds.,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on Environmental Issues,Dordrecht,Boston,Lond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p.83.
[17]David G.Victor,Kal Raustiala & Eugene B.Skolnikoff eds.,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s: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MIT Press,1998,p.v.
[19] [21]Robert Beckman, “Singapore Strives to Enhance Safety,Security,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Its Port an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ingapore”,Ocean and Coastal Law Journal,2008,p.167.
[20]Frank Frost,“ASEAN Since 1967:Origins Evolution and Recent Developments”,in Alison Broinowski ed.,ASEAN into the 1990s,London:Macmillan,1990,p.1.
[22]Stryken,Christian-Marius,“The US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 and US grand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in Kwa Chong Guan &John K.Skogan eds.,Maritime Security in Southeast Asia,New York,NY:Routledge,2007,p.135.
[23]Sam Bateman,“Maritime Security:Regional concern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in William T.Tow ed.,Security Politics in the Asia-Pacific:A Regional-Global Nex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