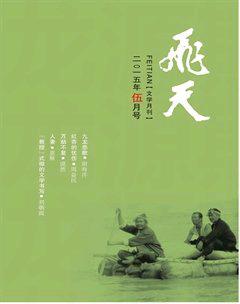人妻
惠雁雁
1
天还没有大亮,她就起来了,悄悄倚靠在窗台上望着天色。窗台上也是暖的,自然是因为有暖气的缘故。正是这寒冬里的一点暖,让她睡不安宁。
楼道里传来了别家孩子上学的脚步声,但这间房子里静悄悄的。
她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呆立了好长时间仍没有听见另一间卧室里有声音传来。她便拿出先前用过的餐巾纸,悄无声息地就着一丝微亮的天光擦拭厨房的窗玻璃。也许她是爱干净,更多的只是想让时间过去。
等到主人起床,她才开始做早餐。她是两个月前来这里做保姆的。
两个月,与主人渐渐熟悉了,有一天主人正在喝茶,突然问:“怎么称呼你呢?”
这一下把她问住了,她嗫嚅着答不上来,说:“我儿子叫……”
主人笑呵呵地说:“你的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名字,她是有的,可是已经有好多年没人叫了。
“张玉梅。”55岁的张玉梅说出自己的名字时,连自己也觉得恍若隔世,这还是在乡村小学作业本上写过的名字。
一年前,他和男人草草收拾了秋庄稼,背着两床铺盖和一些必备的炊具来到了北山市,他们这一生里的辛劳与经营也在那个秋天草草了结了。
七八十户人家的村庄,渐渐走得支离破散了,邻村的学校一撤,年轻人更是个个都带着孩子外出打工了,去种地甚至看不到同伴。张玉梅的境况更是支离破散,两个儿子成了家,带着媳妇孩子进城务工,甚至过年也不回来瞅一眼。他们老两口没有一丝抱怨,儿子们日子过得不容易,能顾好小家就行了,哪里还有余力顾着他们俩呢?这在做父母的看来,就像是秧苗缺了水,自然是先保住那还新绿的叶片,那黄了的叶子只好扯掉了。
他们的女儿三年前病故了,女婿带着小外孙很快再娶,自然就断了来往。世人常说为富不仁,其实贫穷之家的情义更是和他们的钱财一样短缺,其间的凄凉与无奈,世间都不肯留下一句话来说道,圣人们只肯高瞻远瞩地留下一句高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女儿活着时,还顾惜到老两口,穿穿戴戴常为二老添置。女儿治病时,老两口悄悄给凑了一些钱,儿子儿媳们知道了,虽没说什么,可明摆着一年四季连个电话也没了。
就这样,老两口商量也进城寻个活儿度日,那个静得叫人心慌的村庄里,种地没有多少收入,却总是叫他们想起一连串伤心的事。
他们独自来到北山,北山离老家近,总还容易碰到个熟人,听到熟悉的乡音,且也不必凑到儿子们跟前惹他们不快。他们在东郊租了一间二楼上的石棉瓦屋,临时性建筑,一楼的平房上刷着一个大大的拆字。房租每月300元,这是他们能承受的最高房租了。
两口子想尽一切办法拼了一年命,男人什么活儿都干,又脏又苦的重体力活儿,给人搬运货物。玉梅做了鞋垫,擀了杂面沿街去卖,可那收入实在太少了,不要说顾得着吃,就连水费都顾不过来。那些日子,玉梅看见穿黄色马甲扫大街的都觉得羡慕,怎么样才能寻得着这样的一个活儿?一个月挣1100块呢?快有她的男人挣得多了。
一年后,男人终于用攒下的钱买了一辆小三轮给人送货,有了三轮,手头一下又全空了。两人真怕有个头疼脑热的,况且,他们老了不能干活了怎么办呢?
玉梅就是在这时候提出自己出去找个活儿做的。能做什么呢?玉梅去想打扫卫生,给人家带孩子。把这想法在认识的老乡中一说,没想最先介绍来的活儿是给一个老头儿做饭,工资一个月1500元。
老头儿的老伴去世了。
玉梅一听,心里七上八下的无法回话。1500元,可真不少啊,除去付房租还有1200块。可是,老头儿的老伴去世了。
回头说给男人,男人也是半天没吭声。玉梅果断地说:“咱不去了,我另找个活儿,总能找着活儿的。”
过了几天,介绍人来催问,说人家只是要见见人,未必就是说定了。
再说与男人,男人说:“你看着办吧。”
30多年来,玉梅对这一句话并不陌生。这一句话里有她熟悉的冰凉。他的男人没本事,不是那处处能拿主意的男子汉,玉梅一次次地恨着这句话里的冰冷,也一次次原谅了男人的无奈。这就是她的男人:实诚,没本事,话语冰凉。
玉梅随着介绍人来到市中心的幸福小区,一套旧了的三居室里,一个胖胖的中等个儿的男人和气地招呼她们坐,倒茶递水地很是热情随和。
玉梅心里一格登,他年龄不大呀,也就和玉梅差不多的年龄。
中等个儿男人的话很快使玉梅明白了,他是给他的父亲雇保姆。父亲一个人住,他们不放心,虽是同在一个城里,但不便天天过来照顾,有个人住在家里,既可以照顾父亲的饮食,又可以陪父亲说说话。他那样随和地看着玉梅,说只要照顾得好,工资还可以再商量。
“周末两天你可以回去,我们过来照顾老人。”他再次微笑着说。
话说得这样委婉亲切,就像他们之前很熟悉,此时有事托她帮忙一样。玉梅一时间觉得城里人就是会说话,把一件百般坚硬难堪的事说得这样光滑软和,仿佛一块生铁也可以吞下去糊里糊涂消化了似的。
这一块生铁,玉梅是听出来的。不过此时玉梅喝了人家儿子递过来的两杯热茶,一时顾不得掂量那生铁的分量。
“爸,你过来一下,过来坐坐嘛!”
这时,玉梅突然坐直了身子,玉梅一直以为老人不在家,一直以为眼前这个男人在说着一件和自己关系并不大的事。
“不用,不用,我又不是老得不能动了,我能照顾自己,你放你的心!”随着一个果断的声音,一个身材削瘦的老人端着水杯走了出来。他满头白发,却身材笔直,气色红润,比着他那五十多岁的儿子,叫人很难相信他的年龄。
显然,他老大的不高兴,并且毫不掩饰这不高兴。
介绍人在打着圆场。
玉梅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有再喝茶。事实上玉梅是从头至尾一直没说话。
“那咱们走吧,来了好一阵子了。你们在啊!”玉梅站起来告辞,礼貌,但坚决,她头也不回地先于介绍人走出了房门。
2
老人姓李,天天手不离茶杯,多半时间茶叶在那一只透明的杯子里静静地沉着,茶杯盖紧紧拧着,直到茶水冷彻。玉梅来了之后不久,茶杯更多地闲置在角落里,他开始在茶壶里泡茶,然后分开在小茶杯里喝。老人似乎没有其他喜好,闲了就是喝茶。家里几乎没有人来上门,多半时间就他和玉梅两个。
“来,你来喝杯茶吧。”第一次,他随和地招呼她喝茶。
“我不渴。”玉梅怎么能和主人在一起喝茶呢?
“茶不是要渴了才喝。来坐吧,又没有多少活儿!”确实是,两个人的饮食以及房间整理对于玉梅来说真没多少可忙的。
“我就喝一杯。”
“不怕,茶还能喝醉吗?”喝完了一杯,主人又给她添茶。
“热乎乎的,倒是好味儿,可是怎么能让您老人家给我倒茶呢!”玉梅说。
“我老人家,我就老得连茶也倒不了了?你不念叨我老,我也知道我老了!”老人笑了,但那笑浅浅浮在脸上,明显是怨玉梅说他老了。
玉梅于是赔上了一个笑:“人不都得老嘛,谁能不老呢?”玉梅自15岁起,便生得这样细长身材白白脸,到55岁了,还是这样的细长身材白白脸。枯瘦的脸在这暖如春月的房子里捂了两个月,倒显得皱纹也少了些。而且来到老人家里,老人非常和气,说话也很有趣,一句话里表面听着是一层意思,里面似乎又裹着另一层意思。不似她的男人,说话就像石头块子撂在地上,就是那个形儿,就是那个质地儿,再没有想象的必要。
玉梅有些害怕主人对她和气,但茶还是这样喝上了。有了第一次,接下来就渐渐成了习惯,玉梅才洗完碗,还在拖地,老人就开始泡茶,并招呼她:“该喝茶了,快来!”喜悦的声调儿,一本正经的将一天的日子进入下一个程序,就像他们又回到了儿时,一起在玩过家家一样。
直角的沙发,玉梅坐那个小一点的角。玉梅渐渐习惯了不渴也一杯又一杯地喝个不停。老人往往会在喝茶的时候讲起一些往事,说起他50多岁的儿子小时候的言语举动,说起儿子非得给他找个保姆的事,句句嗔怨里都在表明,他有个孝顺的好儿子。说起两年前他老伴的死,虽是多年沉疴,想不到却是突然病发,孩子们都不在眼前,老伴就死在了他怀里。说着老人就唏嘘抹泪。玉梅也跟着掉下了眼泪,她想起了女儿临终前的种种情形。
玉梅就这样在老人的讲述里,一一回想着自己的往事,似乎也在和老人进行着无声的交谈。她发现,原来这个当过小领导的老人竟和她有着许多共同的话来拉谈: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孙子,胳膊腿儿酸困,头疼脑热,还有亲人的离散!
每每老人问她的家人时,她总是极平淡地笑笑,说家里就老伴和两个儿子,平平常常,没什么可说的。这平常在她的心里其实是一番难以平静的起伏跌宕,可玉梅是不会对任何人说道的。两个儿子,吸着她的乳汁长大,那吸饱了乳汁之后,在她怀里露出的笑眉笑眼如在她眼前;两个儿子,仿佛还在她的掌心里学站立,笑得口水流出来。那种种可爱神态、亲爱之情,在母亲的心里扎下根,永不能忘却。可是儿子转眼长大成家,与母亲完全地生分了,没有一碗米,甚至没有一句话来体量到她这个母亲的不易,体量到父亲的年老力衰。再一想,又想到儿子们眼下拉扯着孩子,日子过得艰难,她就完全地原谅了他们,恨不得自己再去帮帮他们。她心里唯一解释不了、平伏不了的是女儿的死,但她只是淡淡地对老人说:“还有一个女儿,前些年得病殁了。”
天寒日短,两人常常是午饭后坐着喝茶闲话,仿佛一下子就到了下午饭的时光。晚饭后,天色已经全暗下来了,老人执意要出去走一走,多半要叫上玉梅。他说:“走吧,你也出去走走,万一我滑倒了你还能扶我一把呢。现在这世道,还指望谁?”
玉梅自来到这里,白天很少出去,更不和老人一同出去,早晨多半是老人独自去买菜,若需要买许多,也是两人一前一后远远地走,不像是同行的样子。这其中的微妙,玉梅懂。
但夜晚就不一样了,老人领着他在人影稀少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在公园里转圈儿散步,还絮絮絮叨叨地和她说着这个城市的建筑和布局,很家常,很认真,像是她必须了解这个城市的面貌。还问她冷不冷,冷的话咱就回。
玉梅忍着颤抖说不冷,老人穿着半长的羽绒服,玉梅就穿一件半毛半化纤的薄外套,还是女儿生前给买的。
一天,老人带着玉梅来到商场,建议玉梅买一件羊毛棉袄。玉梅说不用买,不需要。其实玉梅也早想有这样一件合身的棉袄,平常穿着暖和,干活时又不受拘束,可一件就得240元。
老人动手挑起来,拿了一件暗红色底,黑色花朵的小圆立领棉袄要她试试。玉梅一试,果然合适,棉袄还有收腰,就是年轻媳妇穿着也很俏了。暗红的小棉袄配着玉梅的黑色长裤,玉梅一下子精神了许多。玉梅这个年龄还记着年轻时的小圆立领棉袄,一件红缎子棉袄,几乎就是那个年代至美至贵的装扮了。玉梅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暗暗下定决心就买了吧,再给老伴也买一件小圆领的羊毛袄,出外干活又暖和又不拘束。
这时,玉梅突然发现老人已经在柜台上付钱了,玉梅连忙赶过去:“我买,我拿着钱呢!”
老人沉着脸看了她一眼:“哎呀,还不一样么!”显然,老人是嫌她抢着付钱了。玉梅只好作罢,自去换衣服。老人却不再板着脸了:“不用换了,就穿着。咱把旧衣服提上。”
回家的路上,玉梅心里十分忐忑,顾不上其余几条条心思在七上八下翻腾,只想着不知什么缘故,她什么事都得听老人的,连同老人给她买衣服她都没有权利拒绝。
“回去,我就把钱给你!240元,我这几个月的钱还没花呢!”为了底气足一点,玉梅一连串地说,生怕有什么力量打断她的话。
“你这个小老太太,能不能不跟我这么生分!我给你买件衣服怎么了,谁能管得着我吗?”他的笑,从眼里流出来。
什么小老太太,连同玉梅自己,都觉得一件收腰的新棉袄,足足让她年轻了好几岁。这个老老头儿可真会说话,那话里的意思总叫人琢磨。
玉梅于是又无话可说,只剩下条条缕缕的心思在无声地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里,玉梅却有一种真实的快乐。整整三年了,玉梅没买过一件新衣服了。
3
东郊的出租房里,滴水成冰。一阵紧风吹过,玉梅担心石棉瓦的屋顶会给掀走了。
夫妻俩早早躺在被窝里以减少些寒冷,丈夫哆嗦着说冷冷冷,将玉梅完全地夹抱在怀里。两体合一,似乎真的就不那么冷了,玉梅舒适地蜷在丈夫怀里,淡淡地说着一些家事。
“给你买一件羊毛棉袄吧!儿子穿罢的那件旧袄你又穿了这几年了,不暖了?我去街上看了,240块。咱一人买一件。”玉梅回家来,还穿着那件半化纤的旧外套。
“不用,暖着呢。立马就打春了!你看下的话,给你买一件。”
“那咱换租一个房子吧,这房子会把你冻坏的!”
“这天寒地冻的,哪里就那么容易找个现成的房子?要换,也得等开春了再说。这会儿你还觉得冷哩,有我这么好的被子你还嫌冷?”
“别穷开心了,不嫌累!”
“穷人也得活啊,穷就不活了?”
“要不,我回来,不出去做活了,回来最起码你进门来还有一口热饭吃。”
“唉,别说了,别咯囔了,睡吧!过了今冬再说。”
玉梅回到家,总要蒸两笼馍,以备丈夫一个星期食用,但随着天气的转冷只好作罢。房子太冷,面粉根本无法发酵,只好买回一大袋馍来。玉梅清洗丈夫换下来的几件衣服,打扫房间,这一间小小的出租房里,可做的家务少得可怜,以至她坐下来仔细搜寻思量,还是找不到可料理的活儿。屋顶没法换,炉子没再买一个大些的,几块煤就堆在门角,再要多买些就没处放了。几件衣服就摞在床边的一个小几上,玉梅早就将它叠齐整。一个铝水壶、一个塑料大水桶、也擦净了。
玉梅回到幸福小区的那套三居室里,温暖扑面而来,一下包裹了全身。窗台上花依旧在开,屋里又亮堂又宽绰,衣食所用的东西一应俱全,无用的东西也摆得每间屋里都是。这里真如在天堂上一般,人与人的日子为什么是如此的不同!
在这间暖得可以开花散叶的房子里,玉梅念叨着丈夫在那间薄壁房子里的冷,心思迟重,手脚言语都慢了半拍。到第二天起来,才知是感冒了,浑身滚烫,眼里酸热。主人见了,立刻递药递水,要她躺下。
玉梅连说不要紧,挣扎着起来做了早、晚饭,又早早躺下。夜未全黑,玉梅烧退了些,心里懒懒地想着一些事,模模糊糊不知自己在想什么。虚虚浮浮,飘飘忽忽,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病了躺在这样一个温暖却陌生的地方,丈夫不知道,儿子们更不知道。
一只手再次抚在她额头上:“还是有些烫,你到大屋里来吧,大屋里暖和,这个屋里冷!”
“不!这怎么行呢!”
“怎么不行呢?你可不能再重感冒了,你也是这把年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较真呢?我们都没有多少年可活了,何苦呢!”
玉梅不动,很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怎么呆了三个多月,主人说话的那腔调,就像是两口子闹了别扭似的,他凭什么用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说话。一件棉袄240元,至于要为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玉梅这时要命地想起了那每月1500元,眉头皱得更加深了。
下雪了,雪在对面的楼顶上堆了厚厚一层,像是一层虚软的白面包。麻雀一会儿飞回树上,一会儿落到晾衣的铁丝上,落到窄窄的窗台上。这可怜的小东西,哪里是它们能容身觅食的地方呢?玉梅可真想拉开玻璃,让麻雀进屋来暖和暖和。
这冷寒的夜,是无处逃生的城市,这水泥楼群中,麻雀去哪里藏身呢?在乡下,麻雀可以躲在旧窑洞里,可以在猪食槽里捡点儿吃的。乡下,此时在玉梅的想象里,就是麻雀安生的天堂。
主人走进玉梅的屋子,将一床被子重盖在玉梅的被子上,说,“这化雪的天可真冷呢!”说着顺势就挤到床上来,就像一对暂时分居的夫妻再次合居一样理所当然。
玉梅一弹要起来,但被子外的寒冷,比寒冷更强大的一股力量让她无限止地虚弱了。
“你摸摸,你摸摸我,看我老了吗?”他拉她的手向下摸去,玉梅吓得紧紧缩着手。如果非得如此,玉梅也只想摸摸他的胸膛,摸摸一个男人的心。
一阵手忙脚乱,胳膊腿儿都僵硬得无处放置,如同一架机器乱了程序,每个零件都不再是地方;又好像有什么塌下来了,那横梁、铁架、石块、土渣混乱地砸了一地。玉梅闭眼忍耐,缩着一颗心逃生。
4
早市上,玉梅买菜时很快认识了两位同一个小区里的保姆,看那穿戴打扮,言语举动,甚至年龄,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同行。
玉梅小心翼翼地提到一些话题,回答是相似的:家里平时就只男主人一个,老伴去世了,孩子们平时不大往来。
“唉,这样住着,总是不大方便。”玉梅说。
“方便不方便,就那么回事,不过大家都装糊涂罢了!咱就是那过了春季的韭菜,自个儿倒是想整捆地总卖出去呢,可是人家买那么多回去没用啊,就一小把儿一小把地买,省得到时候用不了没地儿扔!”没想同伴说话倒是干脆。
玉梅苦笑道:“唉,话说得太扎实了,比事情扎实还叫人难受呢!这样一说,人立马就没法活了。”两个同病相怜的人都笑了。玉梅问对方家里的情况,说是男人去世了,玉梅宁愿相信这话是真的。玉梅也没敢说自己的男人就在郊区揽活儿。
粗粝的人生需要多少遮遮掩掩,才能这样虚虚浮浮地走过。活着活着,再不是原来的滋味;走着走着,再不是原来的路径。玉梅没有想过掌心里摩挲着长大、心里眼里宠爱着的儿子们真的会三年两载不给她一个电话;她更没有想过年纪轻轻的女儿会死,死在她的前头;她更想不到的是,男人活着,她却会住在另一个男人的家里。在玉梅心里,结发的男人,犹若生身之父,这一生里是不会再改变了,就像这一生里她不可能是别人的女儿,这一世里她不可能是别人的妻,她甚至从没有想过男人会先她而去,总以为一切都会是亘古不变,男人理所当然会陪着她直到满面皱纹,白发稀疏,直到死去。
但是,活到55岁的今天,一切都不再是想象的样子。
玉梅买完菜刚进门,就接到了男人的电话。她吃了一惊,男人从不曾打来电话的,有事只是发短信。在这个家里,没有他的声音,他的存在。进了这个房子,玉梅就仿佛是独身一人,男人明白这一点。
玉梅心跳火急地问:“咋了,啥事?”
“咱家那间老窑塌了,三叔托人捎来的话,里边的东西也全压进去了,门窗也烂了。”
“大冬天的怎么会塌呢?”
“这两天雪化的。”玉梅脑子里一下想起了那个夜晚,那个胳膊腿儿都不是地方的夜晚,那个横梁、铁架、石块、土渣都往身上掉的夜晚。
“啊,你听着呢吗?塌就塌了,也没啥!”
“听着哩!”
“这房子里冻得恶哩,昨天把那只大塑料水桶也冻裂了,这个星期天你不要回来了,回来再把你冻感冒了。等天气松和了再回来。”
“那,你不冻?”
“我冻惯了,能扛住。”
“蒸馍吃完了吗?”
“完了。我会买哩。”
玉梅听着男人挂断了电话,一时悲从中来,泪流满面。那间薄板房里没有暖气,做饭时一只小铁炉勉强有一点热气,呆在屋里都冻得人发抖,男人还得风里雪里拉货、送货,回来冰锅冷灶的自己生火做饭。
老家那间旧窑是婆婆纺线织布织出来的,玉梅就在那孔旧窑里成亲,在那孔旧窑里生下了三个儿女,这才积攒钱粮修了新窑洞。旧窑里存放着玉梅陪嫁的一对红木箱子,自然是旧得不能再旧了;还有婆婆用过的纺车、织布机,以及孩子们小时候睡过的柳编摇车。都是一些旧得不能再挪动了的东西,但玉梅一直没舍得扔,玉梅熟悉那旧物上面的每一道痕迹,甚至那上面蒙着的蛛丝网也是那样亲切。如今,这些旧物件都被压在了土堆里,玉梅感同身受地想象着那一件件熟悉的物件儿,好像她也是那被压在底下的一个物件儿。
从幸福小区到东郊出租房,坐公共汽车是一个小时。玉梅从摇摇晃晃的车子里漫看着窗外的景致,觉得像是在梦里一样,有好几次,玉梅坐过了站才想起下车。雪化净时,天气回转过来,玉梅是多么祈望寒冷真的就这样过去,这间薄板房会把她的男人冻坏的。
回到租住房里,丈夫并未在家。玉梅尽力地忙开了家务,炉子生起来,极大方地添煤。煤块,面粉,蔬菜,油盐酱醋样样添置齐备。做好了饭等着丈夫归来,又怕丈夫回来。
丈夫的脚步声上了一楼的台阶,丈夫进门来,无喜无悲,看不出任何表情,就像玉梅不存在似的。夫妻俩默默吃完了饭,然后是玉梅收拾家务,实在找不到活儿来做时,就是极难堪的沉默,夫妻之间无话可说,几平米的空间里无可回避。
好不容易夜色浓了,于是躺下歇息。屋子里黑乎乎的,只有别处的灯火偶尔照拂这黑暗。
“娃们来电话了没?”
“没。”
“没就好,没就是好着哩!”玉梅自言自语。
“真累死人了,快散架了一样。”
“我给你按按?”
“不用。”话冷得像沾霜的薄石片子一样,屋子又陷入了黑暗中。
“咱躲在这里,咱妈的坟上也没人去撇一张纸,今年寒衣都没送。窑塌了,我就想去给妈上一回坟!”玉梅说到这里突然哭了,伤心难抑的泪水汹涌而出,堵住了呼吸。
“哭啥呢,妈知道咱们的难处,你待妈好,妈还会怪你吗?要怪,也是怪我,怪我没本事!”
男人在玉梅的被子上按了按,玉梅哭得更厉害了,好像眼泪堵在体内会把人憋死。
流过泪,玉梅觉得松和些了,连房子里的空气也不那么冻得生硬了。
5
老李病了,一连几天心慌气短,却只说不要紧,在玉梅的催促下,不得已通知了他的儿子。老李住院十几天,他的儿女们轮流陪护送饭,仿佛生怕玉梅要前去照顾。玉梅突然害怕起来,怕老李有个三长两短,玉梅在房子里理理这,看看那,心神不宁地等着老李病愈归来,他真希望老李能多活几年呀!
一场小病,老李的身子仿佛一下就垮下来了,玉梅更是汤食衣衾精心伺候着,月余之后才渐渐康复。孩子们带来什么好吃的,老李总要玉梅也吃,孩子们不在时,老李总要坐在玉梅身边,两个人比先前更亲近了,玉梅也渐渐习惯了这一份亲近。
元旦前,老人的儿子前来探望,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吃过饭就走,见老人进了卧室休息,他儿子来厨房和玉梅说话。开头的话很委婉,问玉梅可住得惯;说他爸这几个月来看着身体好多了,感谢玉梅的照顾,家里能找到玉梅这样好的帮手真是幸运。玉梅听得顺耳,只是无话可回,只有赔着笑。但是接下来,他话锋一转,虽然同样还是带笑的面容,甚至更为客气的笑容,话却叫玉梅咽不下,咬不动。
“找个时间让你儿子来家里一下吧。有些话拉拉。”
“他们来做啥呢?”
“还是找个时间来一下吧,见个面,有些话我们晚辈之间应该说说!”
“有啥话,就和我说。我的孩子们还小呢。”玉梅已经听出一半的意味了,她突然沉了声音这样说。
“还是让你儿子来吧,我和你儿子说比较好!有些话先说清楚比较好,你说呢?”
“没什么要说的,有什么说的呢?”玉梅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但还是不好完全拒绝,面对一张客气的笑脸,玉梅心里再苦,也不好沉下脸来。
老人起来了,咳嗽声,接着是接水、添茶的声音。老人的儿子与父亲匆匆说了几句便走了。
玉梅察看老人的神色,看他与儿子说话的神情,他像是知道了儿子谈话的内容,又像是不知道。
几天里,玉梅一直在仔细观察,仿佛在老人的每一个神态、每一个举手投足间都潜藏着答案。玉梅全身每个细胞都长出喉咙来,想向老人讨一个答案,可是玉梅纵使长有十万个喉咙也出不了声。
玉梅这一辈子里没对一个人这样察颜观色过,只有女儿身染重病时,她一天天地察颜观色,惴惴不安地看女儿还能在人间呆几天。女儿的死深深印刻在她心里,比照得玉梅从此看人生的一切都是冷凉。
虚虚浮浮地捱了几天,玉梅终于在一次喝茶的时候说:“你儿子那天来时说,要我儿子来一趟,他有些话话要和我儿子说清楚。”
“来也好,不来也好,能有什么话说呢?”老人简淡地说,无喜无悲,说着给她添上一杯茶,然后去看电视。
玉梅听了,一颗心悬在半空里,落不是,升也不是。
那一杯茶的热气还在冬天的阳光里徐徐飘散,仿佛一支空有的香。
她的女儿临终前躺在床上瞅了她一天,叫了一声妈,轻得像是一声叹息一样,然后眼一合睡去了,永远地睡去了。玉梅瘫坐在女儿床边,哭都不会哭,握着女儿的手渐渐冰凉。
玉梅站起来,犹豫着,提了垃圾袋走出门,走下了楼梯。
天寒地冻。当电视里主持人以各种形象的语言、通俗亲切的话语谈着天气时,身在石棉瓦顶的出租屋里的人却在体会着砭肌刺骨的冷。天太冷,简直伸不出手去,出去也找不到活儿。他感冒了,鼻涕眼泪的,只好给自己放一天假。躺在被窝里,似乎愈觉得冷,愈觉得自己虚弱。
“你在哪里?今儿风可紧哩。”是玉梅发来的短信。
他看到这一条短信,眼里顿时酸了,心中无限的酸楚,什么时候夫妻之间就像偷人似的连个电话也不能打了。调好了呼吸,他拨通了电话。
“怎么了,你有事儿?”
“没啥事儿,今儿冷得厉害哩,要不你别出去了。”是玉梅怯弱的、轻柔的声音。
他听出了妻子声音里的胆怯与匆忙,大概那边屋里有人吧。
“没出去,出去也没啥活儿。好像感冒了,冷得缩不住。”
“冷哩,那是发烧哩,你觉得怎样?我回来!”那声音顿时着急起来。
“不用,能扛得住。”
“扛,你就知道扛!”那边屋里没人吗?妻子的声音里带着如常的嗔恨。
“我立马就回来!振刚,我不做了!咱回,回老家去吧,咱今儿就回,村里就咱两个人了, 咱也回!”
马振刚,这个50多岁的男人突然间沉默了,一股暖热的气流铺天盖地向他扑来,他感觉,妻子李玉梅正幻身一个巨大的、暖热的形体向他飞来,他干枯、冻结的心伸出强有力的臂膀来,抱住了这一个巨大的暖热的形体。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听见了。咱回!”
临近年根儿,在回乡大军拥挤的火车上,又多了一对50多岁的夫妇,他们背着铺盖,抱着铝合金锅,提着几大袋零碎的东西,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女的穿着深蓝底、孔雀蓝色小菊花的羊毛棉袄,男的穿着深蓝色立领羊毛棉袄。棉袄崭新,这传统的中式棉袄穿在他们身上,显得他们多了几分精气神。归置好了行李,他们紧紧地靠在一起,站立在拥挤的过道里,终于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