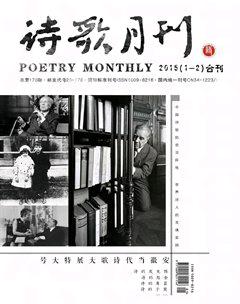那青春盛开的火焰(节选)
姜红伟+蓝角
姜红伟: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蓝角:对于热爱诗歌和诗歌写作的人来说,任何年代都属于诗歌。20世纪80年代是个不朽的年代,它,不仅仅属于诗歌,同样属于除旧布新、承前启后的中国社会。应该说80年代的中国诗歌正赶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候,它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密不可分。换个角度看,这个阶段的诗歌更多是全方位为曾经中断的中国诗歌史补课——诗歌原来不全是我们看到的样子,什么样子?而这时,中国大门被彻底推开了,我们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所谓黄金时代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纷至沓来、接二连三的各种惊喜。是的,我们和苏醒过来的中国一道惊喜,诗歌当然首当其冲、跃跃欲试。80年代成就了一批具备伟大品质的诗人,他们属于那个时代,同时也属于永远伟大的中国诗歌。需要提醒的是,中国诗歌一直是条绵延不绝的河流,它经过不同时代诗人的滴血煅打和生命创造,才不断形成新的更富生命力的潮流。我从来不把某个年代作为诗歌的终极点。历史不是从当代开始的,五千年文化是一面镜子,在五千年历史面前,每个人都是尘埃,每个年代的诗歌事件也同样是沧海一粟。
姜红伟: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革命生涯”。蓝角:1984年,我从一江边偏远小村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从跨入校门那天起,几乎毫无前奏地迎来各种新思潮的暴风骤雨。在老师的鼓动下,我和班级里的同学一起办起手写版的文学小刊物,并把加入校园文学社团当作无限荣光的事。在朱世英教授的指导和校园诗人俞凌(巫蓉)、章礼斌等影响下,开始尝试诗歌写作。那个时期,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蒋维扬,已是中国诗歌圣地《诗歌报》实际掌门人,俞凌、章礼斌的诗歌作品在《诗歌报》、《飞天》等文学刊物上频频露面。俞凌更是以惊人的版面被《诗歌报》隆重推出,这一切,极大刺激了尚对诗歌写作充满无限憧憬的我。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向位于宿州路九号的《诗歌报》编辑部送稿。在省文联大院二楼简陋但十分干净的编辑室里,我认识了著名编辑家、诗人蒋维扬。在其帮助下,一年级下学期我就在《诗歌报》发表了二首诗歌处女作《外乡人》,其后,又在当时极具影响的全国诗歌地方集片“安徽专版”等版面上,发表了《鱼的消息》、《我对你说》等组诗作品,在大学生诗人群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个时期,我开始在合肥接触一些诗人,并和南京林业大学、武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诸多校园诗人保持书信来往。时有南京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科技大学等合肥本土校园诗人频繁造访我所在的校园,在学生宿舍和校园里讨论诗歌、宗教和哲学。1987年,与当时已有一定诗名的经济系学生沈天鹰、佘文中、丁惠黎、无线电系学生戴自成五人在愚人节成立“唯唯诗社”,后因校方干涉,无果而终。大学期间所写的诗歌《这一年》被青年学者石晓林评论后,在《安徽大学报》上以半版篇幅予以推介,后该报又发表了钟仁勤对我的诗歌专论《静止的旅人》。在合肥等多家地方报纸数次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开始有部分作品选入全国大学生文学作品选集中。参加大学生诗歌比赛并获奖。在《飞天》等报刊上陆续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其间不间断向《飞天》“大学生诗苑”编辑张书绅、《安庆日报》编辑沈天鸿投稿,得到他们的帮助和肯定。
1986年,因所写通讯作品《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在《中国青年报》发表,经校系研究同意,转至新闻专业就读,成为文革后安徽大学因专业特长转专业第一人。
姜红伟:您参与创办过诗歌刊物吗?您参与创办过诗歌报纸吗?编印或出版过诗集吗?
蓝角:如果把参与《诗歌报》的经历,可以算作编辑诗歌报纸的话,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自己的编辑生涯。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后的很多年。那个时期的《诗歌报》可谓如日中天,名扬四海。作为里面的看稿编辑,不自觉中也被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我去外省某地参加一个活动,随意约见几位当地的诗人,后来有位在当时诗坛影响很大的先锋诗人,知道我去了他的城市却未与他见面表示极度吃惊。他的理由是,蓝角来这里不可能不和我见面,在他那个城市不和他见面,等于放弃了与中国顶级诗人切磋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事有很多,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张报纸当时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诗歌报》给了我很多的东西。在那个只考虑诗歌,而从不考虑其它非诗因素的地方,我学到、领悟到了太多做人、写诗的道理。其实,我对编辑这个行业一直保持着某种警惕。你是一个编辑,不见得你写得就比别人好,不同的是,你掌握着作品的生死权和不可争辩的话语权,你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获得一些真真假假的掌声。我认为,一个清醒的编辑是孤立的,他不应属于哪个人。这和做一个纯粹的诗人完全是两回事。编辑的苦衷在于,他代表着一个刊物,他代表着某个努力的方向,而他很多时候言不由衷。在兼任《诗歌报》选稿编辑期间,我主要负责四川、云南、甘肃、西藏、福建、内蒙古、贵州、青海等省的诗歌稿件。所编稿件中印象较深的诗人有:雷平阳、郑单衣、何小竹、宋渠宋炜、李亚伟、刘亮程等等。首发诗坛新人作品若干,他们中很多成为当代诗坛的中坚。书信接触骆一禾、杨克、邹静之、杨然等大批杰出诗人。几乎每星期,我收到全国各地的诗人、作者来信有近百封。记得当时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星期六下午,我骑着单车去编辑部,从那里取出几乎一麻袋来稿,然后一个人来到合肥稻香楼旁的雨花塘,在冬日暖阳下,拆开一封封来自远方的信。
多年之后,还有人问我,你做《诗歌报》编辑,发表稿件会不会比别人容易?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我那时写得还不足够好;我也没学会与其它刊物的编辑搞稿件交换。这,似乎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几乎每个月都给主持《飞天》“大学生诗苑”的张书绅老师投稿,直到大学毕业,他让我共露过二次面。一次是一首短诗,一次是个组诗。但张书绅老师每一次都在我的来稿上,用铅笔提出极得要点的修改意见,他的执着认真,他的责任心,以及他不同寻常的严谨细致,几乎影响了我的整个编辑生涯和后来的职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