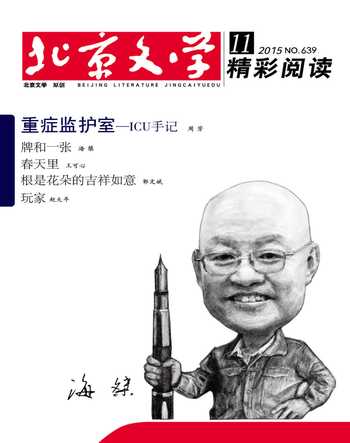村头树(散文)
愚石
我家村头的老榆树,是上了《宁阳明清县志》的。虽然没有在县志的正文里出现,只是在艺文篇中以一首佚名诗的方式留存,对我们村,对村头的这棵老榆树,已经是天大的荣耀了。在历史上浩如烟海的万千诗作之中,这位佚名作者的诗句之所以能够留存,在我看来不仅仅是大浪淘沙,更像是一种奇迹。诗里这样说,“山带流云水带沙,村头老榆是吾家。荒村篱落秋容淡,一架西风扁豆花。”这首诗并不是为了吟咏老榆树,只是在唱赞淡妆清绪中的田园风光。这种日常琐屑中的平凡诗意,对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诗作者和后世的读者来讲,都是一种澈阔心胸的享受。
在離家几十年之后,村头的老榆树仍然是我脑海中最坚实的记忆,扎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像儿时黏粥似的根。
老榆树之老,老到村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说出它的年代,共同的一句话,爷爷的爷爷说,这一说便有了千年。然后便有人推测,千年的王八都能成精,这老榆树早就该成仙了吧。老榆树之大,树冠覆盖20张八仙桌,再加上8个人才能搂抱过来的树身,整棵树占地要在100个平方以上。据村人讲,曾经有富户人家在儿子婚喜之日大摆宴席,摆了7天的流水席。只是后来,村里的富户遭天火烧了七进院落,便有人传言是冲撞了榆树大仙,此后再也没有人放肆造次了。三五村人搬个小桌酌几杯小酒,倒成了经常的事。但他们的第一杯酒、第一碗茶,必然是要先敬老榆树的。老榆树之神,据说能呼风唤雨,每逢大旱之后,村人们只要买好三牲,对着老榆树行祭祀之礼,三天内必然有雨。而村人们最直接的感受是,不管谁家的孩子吓着了,到树下喊一喊孩子的名字,不出两个时辰,孩子就会完全好起来……
更重要的是,老榆树是村人的救命树,这也让更多的乡邻,视之为生命神树。
三年自然灾害,让并不肥沃的土地,变得像人的命一样贫瘠,绝产绝收的事连续两年发生。村里人无米下锅,吃光了所有能吃的野菜、树皮,只有村头的老榆树没人敢动。到了后来,所有人都聚集在老榆树底下,看着树上的叶子口水直流。不知是何缘故,那年的老榆树似乎有些异样,枝叶变得稀疏寡落,如同在悲悯世人的苦难。大队书记明白众人的心思,招呼村里族里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好歹凑齐了三样祭品,带领全村老少向老榆树下跪。举行完简单而隆重的仪式,几个年轻人踩着板凳、梯子,小心翼翼地摘下榆树叶子,到集体食堂拌上点玉米 子,让村里人吃了一顿饱饭。连续几天下来,榆树上的叶子变得更加稀疏。
这几天的饭,“四类分子”家里的人是捞不着的。看着村人有些夸张地打着饱嗝离开,地主家的儿子愤愤不平,趁夜深人静之时,偷偷到老榆树下,报复似的摘了一筐榆树叶子回了家。此事正好被巡夜的人发现,报告给大队民兵连长,民兵连长第二天就召集全村人开批斗会,地主家的儿子以盗窃罪被送到人民公社,后来被判刑10年。地主婆想不开,在夜里吊死在老榆树上。眼看着这种不吉利的事发生在老榆树身上,有人提出要鞭尸解恨,让反动阶级死不瞑目,也有人提出要把地主一家全部消灭。族里的几位长者捻着胡须,说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话,此事便不了了之。大队里害怕老榆树再被人偷,便派了10个青壮年劳力,24小时不离窝地值班把守。摘榆树叶子的事变成了集体食堂伙夫的公差,天天摘几筐放进大锅,亦菜亦饭地为大队里出工的男女老少,聊以充饥度日。
周围村里有不少人饿死,而我们村甚至没有饿死一个老弱病残。老人们常常感慨的一句话便是,多亏了那棵老榆树啊!
在所有的传说和感叹之外,我想起村头的老榆树,总是和母亲联系在一起的。我初中时便离家求学,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趟,十几里的路完全要靠一双脚一步一步地丈量。每个星期天我要去学校的时候,母亲就送我到村头的老榆树下,千叮咛万嘱咐;回来的时候,又在老榆树下,和其他孩子的母亲们一起,左右张望着等,无论阴晴雨雪。
一个冬日,雪时大时小,从早晨一直飘到傍晚。按照惯例,此时我早该踏上回家的路了。可我感冒发烧,浑身没有任何力气,连回家的劲儿都没有。所有的同学都走了,宿舍里空空荡荡。眼见着天慢慢黑下来,只有13岁的我放声大哭,病痛、委屈、无助,再加上深深的恐惧。我知道我必须走,回家,家里有药,有炉火,有温暖,有母亲总是在我生病时擀好的面,葱花炝锅,热腾腾地下肚。十二万分的精神,二十万分的坚持,终于看到了村头的老榆树,隐隐约约,在厚厚的积雪覆盖下,变身成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向我招手。远远的,我寻找娘的身影,在她经常站着的位置。这样冷的天,我想娘一定不在。我哭着大喊一声娘,整个人就倒了下去,然后听到一个人喘着粗气飞奔过来,一声“儿啊”就拥紧了我。我看到冰冷的雪在娘的后背上堆成了山,简直比泰山极顶还要高耸。我感觉到母亲的身体僵硬,手比北极的冰山更凉一层。后来我才知道,娘已经感冒发烧三天了。她等我,从午后直到半夜。
前几天娘来电话说,县城新建了植物园,县里要把老榆树挪到植物园去,村干部正在做工作,娘问我她该不该签字。我想起了久未再见的老榆树,感觉到它身上散发出的千年香气,在我的骨血里,仍然温暖地飘荡。而它身上被时间刻下的黑色洞斑,像历史深邃的头颅,在不停地思考着人类的某个命题。
莒县浮来山下任家庄村头有一棵银杏树,后来被圈进了定林寺。据当地的人讲,此树经林业部的专家鉴定,为“全国银杏第一树”。
对这个“第一”,当地人这样传播它的神奇。2005年第9号台风“麦莎”,是影响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次台风。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经过时,海上阵风最高风力将达10~11级,内陆地区最高将达6~7级。可偏偏那一年,其他树都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独有这棵银杏树叶子长得奇小,树枝也都收拢着,如同患了重病一般。林业部门还专门请了病虫学专家,对银杏树进行诊治,却始终没有让它旺盛起来。台风过后人们才发现,那些高大魁梧的树,重的被拦腰折断,轻的被吹折了枝头,银杏树却一枝未损。以它27米的身高,台风对它的杀伤力可想而知。自然界的先知先觉,突然变成一种神的力量,让人不可捉摸。
而这种神力,似乎从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开始。
《春秋》这样记载,鲁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传说鲁莒会盟即在此树之下。春秋时期,鲁莒两国不睦。莒虽为子爵之国,但自恃有较强的军事、外交优势,经常与鲁国发生边界摩擦。战争造成了大量的兵士伤亡,边民逃离。《左传》记载:“鲁莒争郓久矣。”纪国娶鲁公长女伯姬,两国联姻,关系密切,伯姬希望丈夫出面调和鲁莒两国的关系。两国接受了纪君的建议,同意前往浮来山下的银杏树下。这里既不是鲁国的都城,又没有莒国的军事威胁,是两相宜的地方。据说,会盟时这棵银杏树已有千年树龄,早已声名远播。如果以此计算,这棵树已沐过近四千年的历史风烟。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揣测鲁莒两国的君主,如何把一酹清酒举过头顶,然后再缓缓落下,祭天祭地。但我们似乎还能听得到会盟时的豪迈柔情,看到两国国君比肩而立,意气浮来,在月色如水、树影摇曳之中,消弭了多少年的恩怨情仇。
银杏树是幸运的,它看到了两国一触即发的战争如何在它的荫翳下消弭,时空如何在它的轻声吟唱中绵绵流传。
而更幸运的是,曾经有那么一个人,在它的脚下,徘徊了那么久,仰望了那么久,然后以一部《文心雕龙》,汇集了时间和空间的智慧,诠释着生命与生存的宏阔意义。有人说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也有人这样提炼和概述:吸纳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安邦治国的政治思想、“重伐谋,轻交刃”的兵学思想、“质文并重”的文学思想、“秉笔直书、宁阙勿滥”的史学思想、“因显”和“托附”的社会生存理论。
这个人,就是刘勰。
刘勰,生于南北朝宋泰始元年,即公元465年,卒年则像他的《文心雕龙》一样,成为众多史学家研究不透的谜团。早年成孤,此后发愤图强,博闻强记,胸有成书。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娶妻结婚,和佛门僧人住在一起。这样的人生际遇,也决定了他生命道路的与众不同。天监初年,他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清正廉洁,政绩斐然,升任步兵校尉。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定林寺撰写、订正经文,请求出家,皇帝应允,改名慧地。定林寺由刘勰兴建、并葬于定林寺之说,由此而出,并一直争议不断。
我无意厘清历史的真相,却想通过刘勰一个人、一部书、一棵树、一座寺的生死情缘,猜想这位前无古人的文学大家最后的生命轨迹:禅房里的木鱼声是和银杏树上的鸟鸣一起醒来的,刘勰吹灭了油灯,信步来到银杏树下,抚摸着它粗粝的皮肤,感叹被时光冲洗的人生,甚至抵不过眼前这棵树的一枝一叶。他思考着人生的意义,探究文学及世间万物的生存法则,“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透过银杏树与自然风雨的纠缠表象,他似乎看到了先天地而生的“道”或“神”,以超自然、超社会的法力,决定着客观世界的一切变化,“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而他自己,多想通过久藏心中的这些理条,梳理好世间的一切杂象。他坐在银杏树下,一天、一个月、一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时光在他静坐沉思、倚树而究、沉醉入眠的安静中走过。禅旨近了,文心也更加真切,成了更深的孤独,成了厚厚的纸笺。那棵与自然灵性相通,有着挚爱情怀的银杏树,竟然在刘勰倚身而立的地方,悄悄留下他背部的整体轮廓,变成了他思考时遮风挡雨的温暖之洞,它会在刘勰高兴时起舞放歌,也会在刘勰悲怀时,落泪成雨。书终于长成了树,树也变成了书。在刘勰完成《文心雕龙》之后,他倒了下去,银杏树上的叶子瞬间全部掉光,此后3年不发芽、不结果,树枝上天天滴着苦雨……
3年后,梵音再起。定林寺的香火更加旺盛,有人专为祭奠而来……
3年后,银杏树再次茁壮。每天总有一片叶子,在树洞内飞旋,似乎在打扫时间的尘光;总有一片叶子,飘飞到离银杏树不远的刘勰墓碑前,诉说着不一样的前世今生…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流传于中国北方的民谣,是生存的记忆,更是历史的流觞。
2014年的某一个夏日,我坐上了前往山西的火车。走这条西行的路,并不是为了寻根,而更像是一种朝拜,为民族的根,我在心底一次次匍匐前行。
泪眼模糊之中,我似乎看到元末明初的民生凋敝之际,那些衣衫褴褛的“草芥”揭竿而起,他们豪情万丈,赤膊厮杀。20年的血流成河,尸骨遍地,整个山东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换来的也只是一个朝代的更替,和无情的流放与迁徙。
广济寺,这是一个让心灵归于沉静的地方,突然间就成了生离死别的伤心场;大槐树,曾经枝叶繁茂的休憩地,眼睁睁地目睹了锁链、罪枷,被无情地套在成千上万的脆弱脖颈之上。父子亲情被割断,家族血缘被撕裂,祖孙相送,兄妹互别,还有夫妻间的泪眼顾盼。挥不动离别的手,流血的眼记住了大槐树;想不起家里的土坯房,颤抖的心记住了老鸹窝。这天上的老鸹啊,为什么全身都是黑的,为何它的叫声,凄惨得如同地狱里的哭泣?而它们无助的飞翔,将三晋之地涂成了黑夜。我相信天下所有老鸹的叫声,在那次移民之前,一定美得像百灵。而此后,它再也没有了歌唱,只有悲伤欲绝中的哭泣和哀伤。
那棵大槐树,在寒冷冬日的凛冽撕扯中,不让任何一片叶子落下,它要努力保持某种永恒的姿势,让离乡的每一个人,都能记住家的模样。
历史有功过是非,可我们看得并不分明。让我们铭记更多的是苦难和悲情,因为我们只是草木之人、血肉之躯。
史料记载,明朝大移民最早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前后历时50多年,移民18次,涉及18个省500多个县、881个姓氏。我无法确切地计算出当时移民的总数量,但按照“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推算,400万人口的三晋,迁移人口应在260万人左右。在山东的140多个县市中,就有90多个县市,存在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村落。
怪不得,为什么北方的大部分村头,都植上了槐树,那是对故土的思念,亲情的寄托,“怀”成了“槐”,开了花,结了果,一代一代,绵延不绝。怪不得,每棵槐树的根总是扎得深些,再深些,那是它们记忆深处的沟壑,唯恐记不住离乡的岁月几何。怪不得,每棵槐树的皮都是那样粗粝,那是思乡的血泪浸泡而成,树皮变成了故土的盐碱滩。怪不得,村头槐树的根,最粗的一条总是朝向西北方向,那是家的呼喚和根的向往……
史学家吴晗曾经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在胁迫和威逼中上路的百万之众,到达迁徙地之后,以老槐树的韧性和坚毅,垦拓出新的生命空间。《明史》曾这样描述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时至今日,再探究和追问那次举国迁徙的意义和功过,已经不合时宜。但它却让我看到了历史经纬中一条神秘的丝线,像人的血管一样,遍布整个民族疆土的身躯之上,把一个个的家族串联起来,成为一张亲情的网,成为一张心形的地图。
而这张地图,是以山西洪洞县的域界为蓝本的,大槐树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坐标,它的根,扎在历史的最深处。
我曾经无数次注视山西洪洞县现在的地图,看着李家庄、张家楼、史家岭等等以姓氏命名的村落,揣测着它们是否北方相同姓氏的根之所在,那里的山山水水,是否还跃动着与大明风烟同样的韵律和节奏。还有那些或急或缓、汩汩而流的無数个泉流,它们依着乡民迁徙的路径,自明开始,流成了不同走向的河流,流向了下游的山东、河南以及再下游的长江南北。这些泉流的根又在何处?它们发源于何处的山涧,经过多少苦难之后,才有了各自的灵性和长相?我似乎看到了在明之前、或者更早之前,就有无数从全国各地流向山西的溪流,在洪洞县蓄积、汇流,然后又各自流去。
这些泉流,更像是遍布身体的血管,萦绕着心的节律,流去,再流回。
每次迁徙,都是家族生命的苦难史,也是每一个姓氏繁衍奋斗的命运抗争史。
881个姓氏,都把大槐树当成了亲人。
这也难怪,为什么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每年都要到山西洪洞参加祭祖大典。而每一个到此寻根的姓氏和游人,都要大哭一场。
突然间想起,恰是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打破了只有皇家才能建庙的禁忌,在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各个姓氏建造宗族祠堂,整顺礼制,依规祭祀。这些家庙,迅速塞满了背井离乡的游魂,和他们漂泊不定的乡愁。这到底,是延伸,还是阻断?
抚摸着宏大寺旁边大槐树的身躯,我竟然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据说,我眼前的这棵槐树,已是明代大槐树的第三代嫡孙了,它从一出生开始,脸上就刻满沧桑。大槐树一代一代坚贞繁盛地更替生衍,是为了记住什么,还是为了守望什么?
而我,又是为何而来?
母亲的电话从遥远的老家打来,“老榆树的事,我签不签字?”
我没有回答。我在想,如果没有了那棵老榆树,我是不是还能找到归家的路,还能在哪儿看到母亲高扬的手?
母亲顿了顿,“镇上的干部还说,整个村子很快要迁入社区了。那个社区离老家十好几里路呢。”
我捡起脚下一片干枯的槐树叶子,竟不知该放至何处。
天暗下来。我,只想回家……
责任编辑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