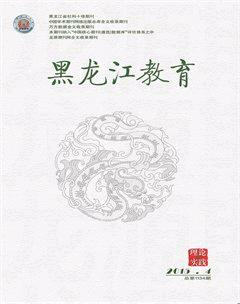《所罗门之歌》的文本图像叙事
摘要:文本图像是指语言艺术的图像化。本文在承认语言和图像叙述差异的基础上,结合两种叙述方式自身革命化的需求和趋势,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文本案例,力图说明语言叙述(即小说)是一种非分离性的符号体系;小说的结构,情节和人物塑造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从而使语言叙述具有了图像叙事的功能。
作者简介:包威(1978-),女,副教授,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身份与空间——当代美国小说空间叙事个案研究”,项目编号:11C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一、引言
当前文化领域中的图像转向引发了视觉文化的消费方式的相应转变,并引起人们对语言的视觉性问题的思考。文字作为言语之载体,其视觉性的存在以及可视性再现的功能也随之颇受关注。文字视觉再现的样式与文学原则指向一种思考:由文字构成的文本唤起、融合或替代视觉经验的动力是什么?本文在承认语言文字和图像叙述差异的基础上,结合两种叙述方式自身革命化的需求和趋势,以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文本案例,来说明文字语言叙事如何建构了一套非分离性的符号体系。换言之,文本中词句段落形成的结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由此语言叙述具有了图像叙事的功能,如托尼·莫里森在《记忆的场所》中提出的“文学考古学”的方法,记录“从形象……到文本的记忆”和“伴随那个画面而来的感觉”,也就是本文题目中文本图像的内涵。
二、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的差异性存在
米歇尔·福柯在阐释文字与图像的复杂关系时,明确指出“语言与绘画的关系是一种无限的关系。”(福柯:1973:86)W. J. T.米歇尔在分析图像理论时借用了福柯的观点,他分析了词语和视觉表现的形式不对称性,并且“再现这条错误路线与根本的意识形态分化密切相关”。(米歇尔:2006:5)从这个意义上,米歇尔实则超越了分析语言和图像关系的结构主义范畴和形式分析的窠臼,他认为这种差异更是言说的自我与被视的他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性也可被形容为讲述与展示之间的距离,是亲眼所见与从他人处得到信息的差距。听到和引用的词语与看见和描画的行动之间的差异;传感渠道、再现的传统和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异。
文字叙事与图像叙事之间的关系,源自语言表达融入了理解范畴。人们对这两种叙事媒介的理解,是模仿、想象、形式和比喻等文学技巧被赋予了鲜明的图像意义。对托尼·莫里森作品从文字图像叙事的对比关系角度来分析,实则是检验奴隶叙事中的描写和记忆的视觉空间特征。
三、《所罗门之歌》的文本图像特征
托尼·莫里森从未放弃在文本中履行的回忆“义务”,她要把记忆带回到已经被忘记的和无法追忆的物质中去。正如她在一篇文章中谈及文本的创作的“文学考古学”的方法。所谓的文学考古学,指的是文学记录了从“形象”到“文本”的记忆,而记忆的过程伴随着“画面”带来的感觉。《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文学考古学”创作理论的一个例证。
《所罗门之歌》的文本图像特征,可以被理解为语言艺术图像化的过程。文本的创作之初,如同要到一个场所去看看留下了什么,用所留之物来重新建立世界的一场“旅行”。依据最初的创作印象,开始形成生产这个形象的时间过程的文本、叙事或论述。莫里森强调,这个形象并不是象征,而是类似于“画面”的事物。
《所罗门之歌》构成的这些“画面”,不仅是语言叙述的非分离系统的构建,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回忆,它包含了一种独立检索机制,仿佛它能够回忆自身。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着重笔墨描写了比拉朵的女性形象。莫里森笔下的比拉朵采用了多重叙事的策略呈现纸上,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都对比拉朵进行了描述。如果用L指代描述比拉朵的language(语言),用O表示文字叙事呈现的object(客体),两者的关系用R来表示:O = R (L)。本文选取文本中对比拉朵描写的几处段落进行分析。比拉朵的出场给人一个穿着奇怪的唱着歌的女人,客体的表现来自文中介绍式的方式:“那唱歌的女人戴的却是一顶用毛线编织的圆顶帽,把额头盖得很低。她没穿冬大衣,而是用一件旧被裹着身体。”(p6)戴德口中的比拉朵则是另一个形象:“听我的话吧。那个女人很坏。她是条蛇,能像蛇那样迷惑你,但是终归她是条蛇。”戴得这里使用的语言,套用O = R(L)公式,读者得到的客体是一个“邪恶的,毒蛇般的女人”。当奶娃自己去拜访姑姑比拉朵,则得到了一个全然一新的客体:“虽然她像人们说的那样穷,但她的眼睛里没有一丝证明她穷的神气。她也不脏;不整洁,是的,但不肮脏。”他人的评论不再可信,奶娃感到“那耳坠、那柑橘和她身上那见棱见角的黑布对他的吸引力很大,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他和她接近的”,“软绵绵”,是他经历的“最快乐的一天”。(p40)可见,文本运用词句的媒介,构成了变形,扭转和差异的R,语言与客体的关系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特征。
《所罗门之歌》的文本图像叙事特征,也从文本的空间意识体现出来。“语言媒介的透明性”按照穆雷·克里格的理解,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看起来一成不变的透明性正“变成空间艺术媒介的物质的坚实性”。指涉的视觉客体与语言再现不存在冲突,空间物质的坚实性实际上就是描写的生动形象,语法和文字风格具备了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等叙事方式的描述能力,从而使文本具有了空间性。(米歇尔:2006:145)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里也采用了弱化线性时间的方式突出文本的空间性。小说的开篇布置了史密斯自杀,露丝生产和比拉朵的歌唱。同时文本刻意赋予场所类的客体以深刻寓意,强化了文本的空间性。奶娃的母亲露丝有明显的恋子情节,哺乳的时刻给了她难得的愉悦,“她从中得到的快感一部分在于她享受这种快感的那个房间。阳光由紧靠窗户的一株常青树形成的湿漉漉的绿色叶丛滤过,那只是曾被医生叫做书房的一间小屋。……她坐在这间房里把她的儿子抱在怀里,凝视着他那紧闭的眼帘,聆听着他的吮吸声”。(p14-15)。正如杰拉德·热奈特阐述叙事的异质性时指出:“情节在时间内的展开预期非正规的孪生兄弟描写模式之间的前沿”(热奈特:1982:127-143),始终伴随着浓厚的视觉艺术特征,也就是空间化的情节和客体的表现。(米歇尔:2006:178)莫里森笔下的记忆,把视觉和空间秩序放在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所罗门之歌》成功塑造的几个黑人形象彼拉多、戴得、奶娃等,无不依托空间的强大力量,利用视觉、听觉和回忆的词汇,抹掉时间,直接进入感觉的现实。
四、结语
《所罗门之歌》的艺术魅力之一在于一定程度上跨越了语言与图像之间的鸿沟。在构建语言与客体的关系上,莫里森在文本中突出了语言表意的非分离性特征,强烈的空间意识凸显了小说的文本图像特征。莫里森小说叙事的声音不断暗示她要像传统小说那样,以生动的细节“让我们看到”那些事件,(米歇尔:2006:190)为生存在白人文化阴影下的非裔文化的自我表述寻求更有效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中对传统语言叙事功能的创新性努力,意在减少阅读认知的局限和文化立场的偏颇,减小种族他性的阻力,成为“语言再现”和“视觉再现”的完美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