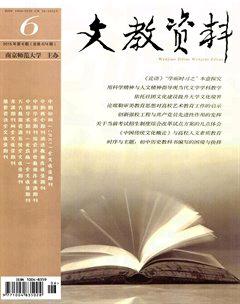清代小说《歧路灯》隐语初探
郭慧
摘 要: 隐语是汉民族语言中古已有之的一种社会语言文化现象,其历史悠久,使用群体广泛,在社会语言学研究和民俗语言学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清代文人李绿园创作的长篇世情小说《歧路灯》中便保存大量涉及清代社会市井生活方方面面的隐语,对其进行探索与挖掘不仅可为近代汉语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资源,更可使我们对清代民俗生活和民俗语言有更深入的认识,体味隐语这种特殊语言现象隐藏着的秘密与魅力。
关键词: 《歧路灯》 隐语 赌博 嫖娼 性爱
《歧路灯》是由清乾隆年间河南文人李绿园创作的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发展到成熟与顶峰时期的优秀作品,曾得到冯友兰、郭绍虞与朱自清等前辈学者的推崇与赞赏。朱自清先生就曾在文章上对《歧路灯》以很高评价,认为它“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歧路灯》并没能像同时期的其他作品那样得到广泛传播,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许多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可这并不能掩盖其价值,其校注者栾星先生就曾说过《歧路灯》“是一部描写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普通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作为写实主义的上乘之作,该小说在语言上也真实记录了当时人们交流的方言俚语,是近代汉语研究和民俗语言学研究难能可贵的语料资源,其中包含的隐语也十分丰富,值得一探。
隐语,作为特别的语言文化现象,其存在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关于隐语的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认知角度提出过观点。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就在《文心雕龙》中设“谐隐”篇,并提出“隐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在其看来,隐语就是通过较为诡谲和让人难以直接联想到的比喻来暗指某事物的。我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先生在《普通语言学》一书中这样概说隐语:“隐语是指改了样子的秘密语言,是为着从事某一种行业的人或某种团体的共同利益而服务的。”我们对于隐语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区分隐语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要看其语言表达上是否具有隐蔽性;二要看其使用主体是否是分团体存在的。《歧路灯》这部长篇世情小说,人物涉及十分广泛,并且多描写了一批门斗衙役、游棍赌徒、堂客暗娼、师婆道姑和屡考不中的酸腐秀才等众多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他们个性鲜明,语言表达生动活泼,饱含生活赋予的智慧与幽默,并且其集团的分化也比较清晰,再加上其中有些行为本身具有不正当性甚至是违法的,或有些行为受传统文化影响是需要避讳的,如赌博、嫖娼和男女性爱等,所以隐语的使用也十分频繁。下面我们就对小说中这三类隐语进行归纳梳理。
一、有关赌博的隐语
《歧路灯》讲述的主线故事即是读书人家子弟谭绍闻被匪人诱入赌场,在混账场中差点将家业败光的故事。作者为历陈赌博对青年人的危害,而不惜笔墨对赌博这种恶习进行了多次描写,其中也涉及了不少赌徒相互交流时所运用的隐语。
1.虿盆。在第十六回,谭绍闻和表哥拜访膏粱子弟盛希侨时,第一次接触到了掷色子这种赌博形式,因书气未退,心中还有所顾忌,结尾有诗云:“赌场原是陷人坑,谁肯虿盆自戕生?总为罗刹推挽猛,学泅先赴滚油铛。”其中的虿盆便隐指色盆这种赌具。虿,是类似于蝎子的一种毒性很强的虫子,这里便是将色盆比成了装了毒虫的器皿,其危害与可怕不言而喻。这是一个用比喻式构词法构成的隐语。
2.巧言令。在第小说中盛希侨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也罢。夏贤弟,掏出你的‘巧言令来。”这句话若在一个不会赌博的人听来是万不知其所云的,但深谙赌博之道的夏逢若马上“撩起衣服,解开顺袋,取出六颗色子,放在碗里”。读到这里,我们方知“巧言令”是赌博场中隐指色子的隐语。为何要用此来隐指呢?原来其出自《论语·学而篇》中的“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后便是“色”字,赌徒们便藏头去尾改造孔圣人的话来隐指自己的赌具。这是一个经典的藏字式隐语。
3.东坡肉。出老千是赌博场中的常见现象,那些出自富庶之家且刚入赌场的赌徒们也常常会被大坑一笔,“东坡肉”便是赌场中作弊者借以隐指那些他们可以大啖一口,大宰一笔的对象。如小说中,一场赌博将要开始之前,张绳祖在决定对谁下手时说道:“那姓管的一派骄气,正是一块不腥气、不塞牙的‘东坡肉。”为比喻式隐语。
4.剥皮厅。“这巴家酒馆,是圝赌博的剥皮厅,窦丛已知之有素。”这里的剥皮厅便隐指赌场,是比喻式隐语。
5.八阵图。书中有诗云:“父打子兮妻骂夫,赌场见惯浑如无。有人开缺有人补,仍旧摆开八阵图。”八卦阵相传为诸葛亮所发明的一种军事阵法,这里用来隐指赌博的场面,既显示了赌场如战场的激烈场景,更巧妙地用隐语隐指了赌博这一不法行为,是借代式隐语。
6.毒药丸。在一次赌博中,虎镇邦与府堂革退门役发生口角,门役拿起他们的赌具作为证据,准备告到官府。“这一句骂得姚荣变羞为怒,伸手将六个毒药丸捞在手中,说道:‘你也不是官赌!起身就走。”这里将毒药丸隐指色子,是据其危害进行的比喻式隐语。
7.打钻、抓彩。谭绍闻因赌博而家势日渐衰微,这时夏逢若便给他出了个开赌场的馊主意,并用其利来诱惑谭绍闻。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夏逢若道:“依!依!依!不惟依,而且无乎不依。只叫老伯母打上几遭钻,兴相公抓过几遭彩,后边还怕前边散了场儿哩。”谭绍闻道:“怎的叫打钻、抓彩呢?”夏逢若道:“赌到半夜时,老伯母煮上几十个熟鸡蛋,或是鸡子炒出三四盘子,或是面条、莲粉送出几瓯子来,那有不送回三两串钱的理,这个叫做打钻。兴相公白日出来,谁赢了谁不说送二百果子钱,谁不说送相公二百钱买笔墨?这个叫做抓彩。”
打钻、抓彩便是开赌场人的隐语。打钻隐指通过向赌徒提供一些服务获得收益;抓彩隐指从赌徒那里获得一些基本的人情收益,为综合式构词法构成的隐语。
二、有关嫖娼狎尼等不正当行为的隐语
在封建时代,娼妓行业虽大量存在,但烟花巷柳地并非正经人家子弟应去之处,寻花问柳事自然并非光明正大可讲之事。《歧路灯》对这种坏子弟性情的不正当行为多次涉及,其中所涉隐语也颇具特色。
1.在小说第十六回中便在人物对话中有一个内嵌式隐语:
希侨道:“针线很好,可惜缎子不好。明日请到我家,与我绣几幅枕头面儿待客,可叫去么?我也不敢空劳。”范姑子道:“叫他再领府上奶奶们些教儿,怎的不叫去。”
谭绍闻与表哥和盛希侨在地藏庵里结拜时遇到范姑子的小徒慧照,盛希侨看到这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尼姑长得眉清目秀,便心生非礼之情,于是对范姑子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在不懂此道的外人看来没有丝毫其他意味,以至于在后面第十六回谭绍闻和表哥去拜访盛希侨,盛提议掷色子玩时喊道:“那一家可算上谁?有了!后边叫慧照来,算上一家。”王、谭二人还大吃一惊。王隆吉不禁问到慧照师傅如何肯让她来这里,盛希侨却笑道:“你不在行,他师傅岂有不叫来之理。”这便一语道破其上次与范姑子的对话中是有隐语存在的。我们仔细品味,方能看出其上边对话中的破绽。慢说盛希侨这种方伯门第的家户不少专门做针线的用人,就是真喜欢慧照的针线手艺也大可以直接定下购买,没有必要非要接到家中。三人结拜时在慧照做针线活的阁子上看到的物件有顺带儿,钥匙袋儿,荷包等,并没有枕头面儿,那么盛希侨为什么不让慧照去做她擅长的其他针线,偏偏选择了这种床上用品呢?且又给这种物品的使用定位为“待客”。我们连在一起便可得出盛希侨话里的实际含义,即通过巧妙地内嵌式隐语隐指让慧照“床上待客”,并且说出“我也不敢空劳”指自己会用金钱来补偿,以此来诱惑范姑子答应。所以故事后边盛公子与晴霞(妓女)和慧照(尼姑)一起媟褻也就不足为怪了。
2.瘦马/瘦马院。古来就有用“入马”或“骑马”隐指男女之间发生性关系的隐语。这里的“瘦马”是指被贩卖给他人做姬妾的贫苦人家女子。在封建时代女性地位低下,常常在较小的年纪就被任意贩卖,人贩子会教其掌握乐器和梳妆打扮,以取悦男性。“瘦”隐指其家庭贫苦身材瘦弱,“马”隐指其身份是为权贵提供性服务的,因而这个综合式构词法构成的隐语称呼是极含污蔑性的。
3.窠子。在第七十二回,店小二游说谭绍闻找私娼时说道:“相公休说这等寻后悔的话……听说我这掌柜哩新在莘县扒出来这一个有名的窠子,就叫那边当槽的来请。”窠,本指动物的巢穴,这里用来指私娼,是借代式隐语。
4.粉头。隐指妓女,娼妓离不开涂脂抹粉取悦客人,故借其装扮品来隐指,是借代式隐语。
5.客。在《歧路灯》中堂客特指娼妓。由于旅店人杂,店小二在拉拢嫖客的怕他人听见,便用了藏字式的隐语,去堂称客。如:傍晚时,店小二笑道:“爷请客罢?”少年道:“我这里没朋友,请什么客?”店小二道:“请堂客。”
6.送梳笼匣子。隐指给娼妓的报酬。如书中店小二向住客青年索要银子时说道:“状元红一百壶,我们该替你赔银子打酒么?单说送梳笼匣子,我们怕惊动客长,就替你赏了两吊大钱。”梳笼匣子是娼妓梳妆打扮接待客人时常常随身携带的物品,匣子既可存放装扮所用的梳子、胭脂等,又可将客人给的钱赏塞入其中。故借报酬所存放之处隐指娼妓所得的酬劳,属于借代式隐语。
三、男女性爱之隐
受中国传统性文化意识的影响,任何对性行为和性生殖的直白语言表达都是我们所需要避讳的禁忌语。我们不仅在正统的经典文献里很难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就连小说家在涉及此类现象时也多用隐晦的隐语方式来表达,正如曲彦斌教授在其《中国民间隐语行话》中所说“性文化是贯穿人类社会文化始终的一种基本文化现象”我们对其的“诸般忌讳与回避,其本身反而说明它是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歧路灯》中也有较多此类隐语。
1.游章台、赴巫山。章台本是西汉时期长安城的一个街名,因妓院多云集于此,故后世便用章台代指妓院等红灯区;巫山本出自宋玉《高唐赋》,赋中讲了楚王梦中与巫山之神女交欢之情,后世便用巫山、云雨、高唐等隐指男女私会。游章台、赴巫山便是隐指男女交欢的用典式隐语。
2.做楚襄王。第二十四回中谭绍闻初入赌场,心思还多在迷恋娼妓上,说其“夜间上灯时,仍蹈前辙。绍闻到黄昏,又是想做楚襄王的”。此处是用宋玉的《神女赋》中楚襄王苦苦追求神女的典故来隐指男子追求男欢女爱的隐语,为用典式隐语。
3.桑中之约。桑中之约原出自《诗·鄘风》中的《桑中》,诗中有“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是一首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旧日被认为是揭露贵族公室男女淫乱的讽刺诗,后人便借“桑中之约”隐指男女幽会并发生性关系,是一个用典式构词法构成的隐语。
4.二仙传道。夏逢若与妓女珍珠串发生私情,被貂皮鼠等调笑为“二仙传道”,实是隐指男女交媾,是比喻式隐语。
5.探花人。夏逢若开设赌场聚集了一帮匪类帮闲,谁知貂皮鼠却将自己的妻子暗占,书中有诗云:“从来赌与盗为邻,奸盗相随更有因;只恐夜深人睡去,入门俱是探花人。”此处的探花人便是对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的隐称,为比喻式隐语。
6.入幕之宾。原出自《晋书·郗超传》,原指关系亲密的人或参与机密的人,在《歧路灯》中指的是与夏逢若妻子发生不正当关系的貂皮鼠,即隐指与主人家夫人发生奸情的男子,为用典式隐语。
7.株林从夏南。谭绍闻与姜氏在夏逢若的牵线下私情未了,书中有诗为证曰:“婉昵私情直类憨,后门延伫寄心谈;娶妻未协齐姜愿,却是株林从夏南。”“株林从夏南”原出自《诗·陈风·株林》,是一首讽刺陈灵公君臣淫乱的诗。据《毛诗序》说:“《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后世便用此隐指男女间的不正当关系。
通过对《歧路灯》中以上三类隐语的归纳与总结,我们不难看出,除了利用语音和文字上的特殊性构成的隐语词汇外,用修辞方式构成的隐语是整个隐语行话中的大家族。隐语如同一位戴着面纱的神秘女子,因其隐蔽性和难以探知性而更具魅力,让探索者深深着迷而欲罢不能。虽然有其独特的个性,但隐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化现象却无处不体现着汉民族的思维习惯和民族文化精神。其表达或生动活泼,为隐蔽让人难以直接从其能指联想到其所指;或含蓄隽永,要想懂必需熟知中华文化典故传说才可以。隐语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和人文观念,《歧路灯》这部清朝时期用方言写作的长篇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当时运用的隐语行话,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参考文献:
[1]李绿园.歧路灯[M].栾星,校注.郑州:中州书画社,1980.
[2]郝志伦.汉语隐语论纲[M].成都:巴蜀书社,2001.
[3]曲彦斌.中国民间隐语行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4]李昌铉.《歧路灯》研究八十年[J].西北师大学报,1999(5).
[5]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