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上海味道
——《繁花》读后
文 李 雷
久违的上海味道——《繁花》读后
文 李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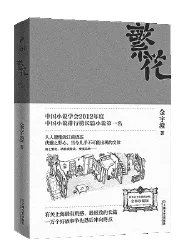
《繁花》书影
一
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信息泛滥的时代,书籍的阅读似乎正在被各色信息的浏览所取代,已经很少有某一部书能够将大众拉回到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之中,而2012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繁花》却令人欣喜地做到了。其以“闪耀的韵致”让万千读者在愈加忙乱而又单调乏味的世俗生活中,能够撇开诸多所谓的重要“事体”,而静坐下来,以喝功夫茶、吃大闸蟹的从容与散漫,沉浸其中,聆听作者来说张三李四,谈家长里短,感受上海市井的生活百态,体味普通人生的悲欢离合。
该小说作者,金宇澄,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除年轻插队时有八年的时间身处东北之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上海。他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写小说,但显然并没有太大的名气,后来不知何故中断了创作道路,而单纯在文学杂志社做编辑,做了20多年的文学编辑之后,再度出手便推出了这样一部几乎囊括了国内诸大知名文学奖项的惊人之作,尤其是2015年又斩获了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茅盾文学奖,可谓风光无限。或许,我们可以说《繁花》是作者二十年磨一剑的厚积薄发之作,但金宇澄似乎更乐于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宁繁勿略,宁低毋高”,以敬畏之心来对待读者,取悦听众。面对这样一部精彩得简直可以摄人心魄的诚心之作,读者没有理由不击节叫好,不拍案叫绝,其也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近三年来中国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之一。
《繁花》的叙事依循着两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从容展开,一条是弥漫着少年旧梦的六七十年代,另一条则是充斥着喧嚣浮华的90年代,新旧两个时空交替出现,又不断转换;彼此勾连,又互相对照。小说的主要人物沪生、阿宝、小毛三人各自的成长经历与复杂的情感纠葛贯穿小说始终,连缀起漫长的40年上海时空中发生的如零金碎玉般俯拾即是的生活点滴与人生故事。这样的结构安排其实并不复杂,我们即使按照时间序列先来阅读奇数章节,再来阅读偶数章节,也无碍于小说情节的整体理解,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小说作者区别于当下的独特写作手法。金宇澄无意于传统的人物塑造,而是着迷于故事的讲述,以至于小说中的男女私情、荤素故事几乎占据了大多半的篇幅,诸如陶陶、汪小姐、梅瑞等游走于诸多情人之间的红男绿女甚至有时遮掩了几位主要人物的光华,沪生、阿宝更多的时候抽身于故事之外而扮演着与读者无异的聆听者或旁观者角色。或许这种小说叙事手法会冲淡主要人物的“戏份”,影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宏大格局的营构,但无形中却可以将笔触不断地放开,延伸,从而聚合更为丰富的生活、人物、历史、记忆与现实,使得作者笔下的上海更加的色彩斑斓,真实迷人,这显然也更为契合多数人关于上海的城市经验与形象认知。小说作者“避重就轻”、收放自如的高明叙事智慧,由此可见一斑。
二
这部小说最为令人称道之处,还是其字里行间所氤氲弥漫着的上海味道,真实,醇厚,绵长,令人回味无穷。这种久违的上海味道,首先来自于小说对民间口语生态中的上海方言的借用与改造。事实上,该小说最初是连载于一个叫“弄堂网”的网络平台,而该网站的最大特色便是由一帮上海人用上海话来写作,所以,金宇澄最初是用上海方言来思维和发声的,只不过后来出于出版和发行单行本的考虑,为了让更多习惯了普通话思维的读者能够看得懂,才对之前的语言形态进行了有意识的改造,或者说创造了一种别开生面的书面沪语形态。单行本小说通篇即是以此种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开展行文叙事,时而文白杂糅,雅俗交错;时而口语铺陈,对话连篇,而且对话以日常短句为主,几乎不分段,也不注重标点符号的使用。此种日常短句,不疾不徐,舒缓而温婉,富有节奏与韵律,带有沪语独有的氛围和韵味,尤其是通篇一千多处“不响”的使用,更是将上海方言无尽的韵味与丰富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繁花》作者金宇澄/金宇澄画的插图是小说的组成部分
其次,这种上海味道还源于作者对上海的石库门、马路、弄堂、商场、电影院、黄浦江、苏州河等地理性标识的深刻记忆与准确记录。当年韩邦庆写作《海上花列传》时,对于那些嫖客们流连忘返的尚仁里、公阳里、会兴里等地的描写可谓不厌其详,读之极容易让人产生如亲临“十里洋场”之感。金宇澄对此进行了很好的借鉴与效法,他花大量的笔墨去描绘小说人物活动的生活空间、所在的地理位置、穿行的每一条马路、乘坐的哪一条公车电车,作者甚至手绘了四张市区地图,配以说明静安区、卢湾区、普陀区和浦西地区等不同的房屋特点、地貌细节和功能属性。这不仅可以带给读者,尤其是上海读者,极为真实的“在地感”和“现场感”,还可以使其沿着这些过去的城市印记找寻那尘封已久的生活记忆。
当然,产生这种上海味道的最关键性因素,要归结于作者借助沪语方言所呈现出的原汁原味的上海市民日常生活,而这便是张爱玲所说的上海的“底子”。在《繁花》中,这个“底子”被金宇澄描绘得地道,自然,且富有层次。上海市民对于吃吃谈谈的迷恋,对于穿衣打扮的讲究,对于生活情调的追求,皆被作者信手拈来,自然道出。不止于此,金宇澄对于上海市民过去的抑或是现代的日常生活状态亦有着准确的把握,小说处处可见作者对这种生活状态的熟稔和敏锐感知,其中最为精彩的莫过于对沪西曹杨工人新村“两万户”家庭每日琐碎世俗生活的流水账式呈现:
“两万户”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木拖板声音,吵相骂,打小囡,骂老公,无线电声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戏,京戏,本滩,咳嗽,量米烧饭炒小菜,整副猪肺套进自来水龙头,嘭嘭嘭拍打。……
类似的这种日常生活场景在小说中还有很多,而正是这些曾经发生在很多上海人身上的日常生活的场景碎片,共同拼贴起了大家关于上海的“形象记忆”与城市画像。
三
《繁花》所散发出的浓郁上海味道,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以及张爱玲、王安忆的众多关于上海的传奇故事与小说作品。惟其如此,《繁花》刚一出版,便被很多文学评论家欣喜地视为是上海城市经验的最准确表达、传统上海叙事的当代接续。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其放置在整个中国小说发展脉络与精神谱系之中来加以审视的话,我们便会发现,该小说所复活的不仅仅是过往的上海城市书写,或许还有被西方现代小说模式中断许久的中国古典话本小说传统。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话本小说在人物描写方面一般以人物的语言和动作为主,疏于人物内心的挖掘与表现,而且人物的塑造更多的时候亦是服务于故事的讲述。金宇澄可谓深得此种小说传统的衣钵,恰如其自己所言,“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当代小说注重心理剖析的写作模式,尝试着回归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通过对各色鲜活人物穿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等表象描述来推进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单靠“说书”、“讲故事”来吸引人,打动读者。而且,金宇澄讲故事的策略亦是一个故事牵引着另一个故事,虽每一章独立成篇,但某些故事的最终结局与谜底往往在其他章节才得以揭晓,与古时“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说书方式颇为相似。小说中小毛与阿宝、沪生中途的决裂,汪小姐莫名的怀孕等情节即采用了此种手法,待到真相大白之时,每每令读者大呼过瘾,产生巨大的阅读快感。
金宇澄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博尔赫斯将小说分为“一千零一夜”与“伊索寓言”两种,表现出消遣与教化的不同趣味,相对而言,他更偏爱前者,因此他在《繁花》的写作时尽量做到不说教,不美化,不补救人物形象,也不提升“有意义”的内涵,而这恰恰也是中国市井话本小说的一贯特色:单纯地讲故事,不进行直接的道德教化,让读者与听众自身在故事中体味对与错、善与恶。基于此种创作态度,金宇澄在讲述故事之时并不避讳人物欲望的书写,如果说在六七十年代的叙事线中,由于物质的极度匮乏、社会的普遍压抑,人物的欲望还处于某种挣扎、渴求与躲躲藏藏的状态;那么到了90年代的叙事线中,作者对于人物欲望的处理则表现得舒展、飞扬甚至有些赤裸裸。我们看到无论是陶陶、汪小姐、梅瑞等人口中男欢女爱的花边故事,还是他们自我沉沦、声色犬马的生活,皆被作者娓娓道来,而这显然要比“文革”时期银凤、5室阿姨源于压抑的偷情来得更为直接和猛烈。当然,作者对于各类感官欲望的书写并非直白如春宫图,而是借助暗示、隐喻等手法做了很多含蓄化、艺术化的处理,所以,尽管小说不乏情爱场景的描绘,但带给读者的并非是低级的感官刺激,更多的则是语言的魔力与文学的魅力。
更为重要的是,金宇澄绝没有停留于一味的欲望书写,其在尽情描绘人生各种“风景”的同时,也时常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人生的种种无奈与不如意,慨叹感官生活的无聊与空虚等,而且小说中大大小小的饭局,亦带有某种隐喻的意味: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小说的各色人物在历经了人世的诸种繁华之后,终究难逃花开花谢、生老病死的悲凉人生结局。且不说世俗男女的悲剧下场,汪小姐身怀怪胎遭遇难产, 小毛病死于养老院,小琴坠楼而亡,李李遁入佛门……即便是被作者灌注了某种理想与诗意的圣洁人物蓓蒂,最终亦被社会革命洪流冲击得如无根浮萍,不知所终,令人无限怜惜。因此,拨开繁花迷雾,人类文学的经典母题——人生如梦一场空,清晰可见,而这恰恰又与大多数中国古典小说文本一贯的情感基调与思想主题相契合。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有评论家将该小说类比于《金瓶梅》《红楼梦》,恐怕并不为过。小说的结尾处,阿宝接到了来自旧情人雪芝的电话,万般回忆涌上心头。这似乎预示着故事远未结束,生活仍在继续,花花世界、滚滚红尘中的人生悲喜剧依然在上演,永不止息。
总之,不可多得的《繁花》注定了要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它既是当下的,又是传统的;既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
自然,这部书也不尽完美,它的叙述还欠紧实,思想性还需提升,境界与《海上花列传》应拉开距离,别让人误认为,中国过了100年,又回到了晚清。
责任编辑/胡仰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