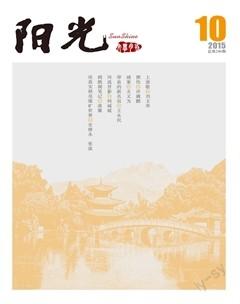带血的匿名信
一
徐欣然深深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咚咚敲了两下门。
“谁啊?”一个穿着吊带裙,头发披散着,十来岁的女孩子半拉开房门问。
“赵队长在吗?我是他队里的工人。”
“妈,找我爸的!”女孩子扭头朝房间里喊道。
“让他进来吧!”房间里一个女人回答道。
徐欣然踌躇着走进房间。一个长得挺富态的女人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看电视,电视里在播放庆祝香港回归的纪录片。
“你们队长开会去了。”女人见徐欣然进来,拽了拽裙角,欠了欠身子招呼说。
“嫂子,我叫徐欣然,来看看队长!”徐欣然满脸堆笑着说,顺手把提着的黑色塑料袋里的两瓶汾酒和一条喜梅香烟放到茶几上。
“来就来吧,拿啥东西啊!”女人笑着把东西往徐欣然手里推。
“嫂子,别,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 徐欣然觉得脸有点儿烫。
“那坐下喝点儿水,小雅,给叔叔倒杯水。”女人对女孩说。
“不用了,队长不在家,我先走了。”徐欣然忙往屋外走,拉开房门一溜烟跑下楼去。
下午四点钟了,太阳还是火辣辣的炙烤着大地。徐欣然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在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根冰糕,咬了两口,凉丝丝的,感觉就像在巷道里卸下肩膀上扛的一根单体柱一样,轻松起来。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成不成就等着吧!即使不成,就像宝根师傅说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给队长送点儿礼总不会吃亏的!”徐欣然想。
新工人来矿下井都要签一份师徒合同,三个月内,师傅负责徒弟的安全、培训等事宜。矿上适当地给师傅发点儿补助。
徐欣然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一年,在西山矿食堂当管理员的舅舅托关系把他在矿上招了工。虽说只是一个合同工,但总比在老家地里刨食强得多。
徐欣然上班的第一天,夜里刚刚下过一场雨,街面湿漉漉的。澡堂里昏暗的灯光下,综一队换好窑衣的矿工吧嗒吧嗒抽着烟,烟雾缭绕,空气里有些发馊的气味。
班长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中年人,长得有点儿像电视里的阿拉伯人。他拿着一张记工表,每念一个人的名字,矿工们哼哼呀呀、有气无力地答应着,大胡子就在记工表上画一个对钩。
“大胡子”念到徐欣然名字时,抬起头,看了他两眼有些赞许地说,后生挺壮实。徐欣然得意地扬了扬胳膊,胳膊上的肌肉隆起,这得益于他在学校里经常打篮球。
井下巷道里黑漆漆的,刮着冷飕飕的阴风。第一次下井,徐欣然心里有点儿发憷,寸步不离地跟着宝根。在巷道里上坡下坡,七弯八拐,差不多走了二里多地才到了掌子面工具箱跟前。徐欣然喘着粗气,一屁股坐在地上。
宝根笑呵呵的递给徐欣然一把铁锹说:“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掌子面的巷道里,徐欣然看到了在矿厂房培训时见过的皮带输送机、溜子等设备,宝根边走边给徐欣然说各种机器。
支架下的工作面,矿灯闪闪烁烁,人声嘈杂。老远就听见有人骂骂咧咧。采煤机前。一个脸上汗渍一道一道的中年人手里握着一个木棍,正冲一个年轻人吼道:“你小子,让你换两把机组刀用了多长时间,都像你这样磨洋工,还出不出煤了!”中年人越说嗓门越高,越说越来气,狠狠踢了年轻人一脚,年轻人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年轻人头也不抬,像霜打了的庄稼。
宝根低声说:“这是‘土匪队长赵东文,那个年轻人是他小舅子。”徐欣然在矿文化广场的宣传栏上看到过赵东文获得省劳动模范时戴着大红花的彩色照片。
“开机割煤!”见出煤班进来了,赵东文吼叫着。
溜子咣当咣当转起来,采煤机张牙舞爪地挥动着两个滚筒咔嚓咔嚓割落了亿万年的煤层,工作面空气顿时浑浊起来,弥漫着呛人的煤尘。采煤机割过煤后,支架工拉架,支架间涌起浮煤。徐欣然跟着宝根清理浮煤。
徐欣然鼻子上戴着防尘口罩,憋气憋得不行,感觉就像乡下蒙着眼睛拉磨的驴,一会儿汗水顺着额头流淌下来。
半班的时候,送饭工送下饭来。轰隆隆的机器声中,矿工们轮流去进风巷吃饭,徐欣然到进风巷时,赵东文咧着大嘴正在吃饭,嘴上油腻腻的。见溜子上的煤呼呼往外拉着,赵东文脸上露出掩不住的喜悦,完全没有了刚才气急败坏的样子。
徐欣然犹豫着走过去,从送饭工手里接过饭盒,揭开盖子,是大米饭。矿工们都是自己准备的勺子,徐欣然没有勺子,旁边看溜子的师傅见状,拿出卡丝钳咔吧一声,从一卷金属网上折断两根铁丝递给徐欣然。徐欣然用衬衣袖口揩拭了几遍,拿起两根铁丝在饭盒里扒拉开来。一边的赵东文吃完饭,用手抹了抹嘴巴,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纸包,仰起脖子把小纸包里的药片塞到嘴里,接过送饭工递过的水,咕嘟咕嘟喝了两口水咽了下去。
一个班下来,徐欣然觉得腰都要折了,身上黏糊糊的,衬衣、衬裤湿淋淋的,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汗臭味儿。澡堂里,宝根从更衣箱里摸出一盒烟,抽出两根来,递给徐欣然一根。宝根点着烟,猛抽了两口,忽然咳起来,一口黑糊糊的痰吐在地上。
两个人抽着烟,跳到澡堂池子里。澡堂水吱吱冒着热气,矿工们边搓澡边聊着,一池子水顿时就像倒进了墨汁一样黑黝黝的,还漂浮着一些煤面。
“师傅,我听说咱们队工资挺高的。”徐欣然问。
“挣得多,苦也大,没有点儿骨头受不了这罪。矿上老百姓有夸咱们的,也有骂咱们是牲口队的。有一次,队里一个叫刘三小的工人到吉祥口买肉,前面围了一圈人,刘三小说我是综一队的,让开让开,前面的人自觉地给他让开了条路,说挣大钱的来了”。
“为啥管队长赵东文叫‘土匪呢?”
“他原来当班长的时候,到了掌子面,有的职工说他看见煤,就像电视里的土匪见了金银财宝一样两眼放光。日子久了,就叫他‘土匪了。他组织生产有一套,班里产量高,都快赶上了两个班的产量了,就是性子有点儿急,因为抢出煤,有一次处理事故,开皮带输送机时绞死了一个人,矿上给了个处分,去年才取消了处分,提拔了队长。”
二
“西山公园发生强奸案了!听说是一个退伍军人干的。”
“傻不傻啊,这年月还强奸啊!花上几十块钱,歌厅里漂亮小姐有的是。”
西山公园是矿上为了职工家属有一个锻炼身体的去处,依山而建的一座公园。
徐欣然靠着支架听宝根和几个矿工聊着。一个月来,徐欣然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阴阳颠倒、上了井吃完饭倒头就睡、下了井握住铁锹就使劲攉煤的生活。井下煤仓满,设备一停止运转,矿工们就凑在一起闲聊。他们的话题基本离不开女人和吃。
宝根说,“大胡子”是饿死鬼转生的。饭店刚推出涮羊肉自助餐时,有次班后,“大胡子”和三个人去矿山路一家饭店涮羊肉。老板见生意来了,笑盈盈迎上来,但吃到最后,老板脸都变成猪肝色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四个人连着要了二十盘羊肉,涮完羊肉,“大胡子”又连着喝了十来个生鸡蛋,然后抹了抹油腻的嘴唇,讪笑着说刚吃了个八九分饱。惊得老板目瞪口呆,逢人就说那是一群狼啊!
“大胡子”脸上挂不住就揭宝根的短说,宝根患了前列腺炎,去医院看病,进了门诊见屋里人多不好意思,说话吞吞吐吐。穿白大褂的大夫问他生殖器疼吗?宝根没有听明白就回答说生气的时候疼,不生气的时候也疼。把大夫笑得差点儿喘不上气来。大夫接着问,睾丸疼吗?宝根说,搞完也疼,不搞完也疼。大家听完哈哈笑起来,徐欣然也笑得合不拢嘴。
有时,徐欣然攉完煤就靠在支架上打盹儿,脑子里胡思乱想,想井上那些花花草草,想矿山路菜市场里人来人往,喧闹的叫卖场景!想着想着就想到了高中时的一个同学赵巧燕。上高中时班里许多男生都喜欢赵巧燕,赵巧燕两只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净净,学习成绩也好,总仰着头走路,高傲得像上午的向日葵。
赵巧燕父亲在西山矿下窑。高一后半学期,她家户口迁到了西山矿,赵巧燕也转学走了。为此,班主任老师接连几天为失去了一个好学生而感叹。
徐欣然也失落了好一阵子。来到西山矿,徐欣然总希望有一天能在矿上遇见赵巧燕,但偌大一个矿没有地址想找一个人很困难。赵巧燕也许去大城市上大学去了,寒暑假回矿上,遇到的概率也几乎为零。徐欣然想。
徐欣然知道想也没有啥意义,但因为有了念想和寄托,井下劳动时精神和身体上也不那么苦楚了。回到宿舍,他有时间就给赵巧燕写那种也许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情诗,写了一首又一首。
三
一天下井前,宝根悄悄对徐欣然说:“一个多月了,你该活动活动了。”
“活动啥啊!”
宝根用大拇指和食指搓捏着数钱的动作,“你给队长送点儿礼啊!”
“送礼干嘛啊?”
“找个技术活,挎上改锥、钳子,干个电工、煤溜工啥的,又体面又威风又不受苦。”
“我才不会送呢,干啥不是干啊,受罪就受罪吧!”
“难道你甘心像我一样握一辈子铁锹把吗?”
那天在井下,徐欣然一直想宝根说的话,但令他想不到是,那天好心办了坏事。
快下班时,掌子面顶板突然来压,矸石哗哗流得支架间满满的,眼看着下一个班就要进来了,还没有拉过支架,拉不过支架就要耽误生产,当班的工作量就要受影响。清完支架间的矸石,徐欣然帮着支架工拉架,在他拉过一支架时,忽然“砰”的一声,电缆槽冒起火花。一瞬间,运转的溜子、采煤机都停了下来。徐欣然吓了一跳。
一会儿,电工跑了进来说,机组顶闸了,估计是电缆线爆了,最后找见原因是徐欣然拉支架把电缆线挤爆了。耽误了半小时生产,电工补好电缆线,采煤机才又轰隆隆转起来。
班后,调度站通知分析事故。调度站会议室里,赵东文瞪着血红的眼睛,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土匪”,几乎是咆哮着,厉声问:“谁耽误了老子的生产?”“大胡子”把经过讲了一遍。徐欣然头也不敢抬,灰溜溜地真想找个地缝钻下去。
“你看咋处理?”赵东文问值班长。
“罚款五百元,写出书面检查,驻矿学习培训班一周。”值班长是个黑胖子,挺着大肚子说。
徐欣然沮丧地走出调度站大门,心里想,五百元大半个月的工资啊!
宝根追上说:“你去队长家送点儿礼,到了月底让队长给值班长求个情看能不能少罚点儿款。”
徐欣然饭也没吃就回宿舍了,躺在床上想彻底完了,赵东文那六亲不认的家伙,以后可有难咽的果子吃了。
舅舅听说了徐欣然的事情,来到宿舍宽慰他说:“这没啥!矿领导去食堂吃饭时,我给你说说。”临走时,舅舅把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到徐欣然床上,让他把袋子里的烟酒给队长送去。
四
也不知道是送礼起到了作用还是舅舅跟矿领导求了情。徐欣然送完礼的第三天,正在矿上培训班学习的他,接到队里电话,通知他回队办公室。
徐欣然忐忑地朝队里办公室走去,办公室的门半开着,赵东文坐在办公桌前和办事员老李说着什么。老李脸色有些难看,白头发这几天好像也见长,老李明年初就要退休了。赵东文见徐欣然进来说:“这段时间老李去外地看看病,你文化高,听你舅舅说还在县市级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就接替老李在办公室先干一段时间。”
说完,赵东文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徐欣然把赵东文的杯子端起,杯子上残留着黄色的污垢,里面飘着几片泛黄的劣质铁观音,徐欣然从暖壶里给他续上水。
“老李,你把工作交接交接,我下井了。”赵东文说完出了办公室。
老李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说:“队长夸你检查写得不错,字写得好。”
“办公室活儿也多,给每一班下工分,给职工办理各类证件……”老李絮絮叨叨给徐欣然介绍日常各项工作。
最后,老李指着桌子上的几瓶药说:“队长有胃病,你别忘了提醒队长上了井吃药啊,生产忙时,队长常常上了井在办公室睡个囫囵觉就又下井了,有时就忘了吃药了。”
“他这病有多长时间了?”
“老毛病了,有时候疼得厉害了,拿胃药当饭吃,抓一把就吃下去了。”
几天后,徐欣然才听说,西山公园发生的强奸案,是老李退伍回来的儿子在山上玩时,见女孩子漂亮动了邪心。老李受不了刺激回老家休养去了。
办事员的工作相当于队里的管家,队里一百多人的大事小情都要操心。徐欣然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边干边学,忙里忙外。赵东文上井,有时吃住在办公室,徐欣然就去矿山路的小饭馆买点儿热饭给他。徐欣然还在办公室给赵东文准备了一箱方便面,这样赵东文半夜上来可以泡方便面吃。
一天下午,井下打上来电话说,“大胡子”受伤了。徐欣然赶到井口时,矿医院的救护车已经在井口等着了,车上两个女护士和一个男医生有说有笑,好像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罐笼上来了,宝根搀扶着大胡子一瘸一拐出来,徐欣然上去帮忙,把“大胡子”平放到担架上。“大胡子”笑着说,没事。到了医院,徐欣然帮着护士把“大胡子”衣服脱光,医生用剪刀把“大胡子”腿上的雨鞋剪断, 拍完片,医生拿着片子端详了半天说:“还好,脚掌上的骨头只是裂开一个缝,输点儿液,在医院养着就行了。”
“你这挂工伤吗?”医生问。
“不用挂,开点药回家养着就行了!”大胡子说。
“该挂工伤挂工伤,万一留下后遗症啥的。”徐欣然说。
“我挂了工伤,就要扣队里的安全奖,弟兄们还不背后骂我啊!工资都代发了,不要给队里找麻烦了,再说也伤得不厉害。”“大胡子”着急地说。
见“大胡子”这样说,徐欣然也不好再说什么。
输完液,洗了澡的宝根也来到医院。徐欣然和宝根打车把“大胡子”送回了家。
“大胡子”家在半山上的一处自建房,用荆棘围成个小院子。徐欣然和宝根搀扶着“大胡子”进了房间,他老婆见“大胡子”被搀扶着进来,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忙问咋回事啊?“脚就是扭了一下,没事,大惊小怪的。”“大胡子”故作轻松地对老婆说。
房间有些昏暗,一个旧沙发、两个大衣柜,一台电视机,房间四周的墙皮有些剥落了,墙顶上糊得满满的报纸。床上躺着一个孩子嘴角歪斜,嘴边流着涎水,啊啊叫着,眼神无助地瞅着屋顶。
徐欣然和宝根两个人从“大胡子”家出来,天已经暗了下来。
“那孩子是咋回事啊?”
“那孩子有点儿傻!”宝根叹了口气说。
徐欣然听了心里酸酸的。
回到队里,赵东文刚上了井,问了问“大胡子”的伤情。赵东文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说:“给大胡子记上井上工,你每天去“大胡子”家担两桶水,大胡子挺不容易的,还拖着一个傻孩子。”
队里给井下受伤的职工不挂工伤的,适当记上一段时间工,算是给点儿补助。有时,队里还要从职工身上截留点儿工资,用作日常的开支,比如上级来检查,吃个饭啥的,花销都从这里面支出。
五
每个月十号是矿上开支的日子,以往每月到了十号下午,不下井的矿工就会陆续到队部开支。
后半年矿上下了文件说,企业效益不好,开始代发工资,工资最多能开五百块钱,超出部分的钱企业先欠着,等企业效益好转了连工资利息一并补发。即使这样,矿上开支也是断断续续的,有时两三个月才开一次支。
每个月十号,矿工们不约而同的来到队部,但经常是满怀希望而来,满怀失望而去。有些矿工有时还骂骂咧咧的,失望之情写满了脑门儿。
中秋节快到了,矿上通知中秋节前开一次支。开支那天,队部办公室门前拥满了人,职工们兴高采烈排队开支。忽然,排队的队伍中乱了起来,一个叫孙东升的工人和一个刚开了支的叫杨三水的工人吵起来。孙东升拽住杨三水的衣角,不让杨三水走,杨三水用力摆脱孙东升的拉扯,两个人面红耳赤,互相骂着。
“欠账还钱天经地义,多长时间了还不还我钱?”
“我有急用,等下次开支还你吧!”
“还下次,上次就说下次,几个下次了?你就是个癞皮狗!”
杨三水个头高,力气大,用力推了一把孙东升,孙东升拽衣角的手松开了,杨三水扭头跑了。
孙东升呜呜哭起来说:“我好心借给他钱,半年了也不还给我,今天好容易开了支,又跑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去他家找他。”旁边有职工愤愤不平地说。
“杨三水的两个儿子上大学,老母亲是个病罐子,每个月买药就花不少钱呢,也难啊!”一个了解杨三水的工人说。
第二天,徐欣然把这件事情跟赵东文讲了。赵东文想了一会儿说:“我找个时间给他们调解一下吧!”
六
一场秋雨一场凉,天气一天天变冷。
一天傍晚,赵东文递给徐欣然一张煤泥票说:“你去选煤厂拉上煤泥,送到职工新区六号家。”
徐欣然找了一个三轮车,在选煤厂装了十五袋煤泥,推着三轮车来到了职工新区,在三层,敲开六号家门。开门的是一个面色憔悴的中年妇女。徐欣然觉得面前这个女人好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
“赵队长让我给你送煤泥来了。”
“放到阳台上吧!”中年妇女冷冷地说。
这时从里屋出来一个穿着工装的女孩,徐欣然一下怔住了,“赵巧燕!”徐欣然脱口而出,透着惊喜。
赵巧燕瘦了,眼睛还有些忧郁。赵巧燕并没有对徐欣然这个老同学表现出多少热情,只是客气地笑了笑,回头对中年妇女说:“妈,这是老家时高中同学。”
“阿姨,你还认识我吗?我去过你们家。”
“有印象,这么高了。”赵巧燕的妈妈嘴角挤出了一丝笑容。
徐欣然一袋袋从三轮车往楼上扛煤泥,十五袋煤泥扛完,额头上已渗出了汗珠。
“冬天生炉子这就不愁了。”徐欣然对赵巧燕说。
赵巧燕打了一盆水让徐欣然洗手。
“巧燕送送小徐。”徐欣然洗完手,赵巧燕的妈妈说。
赵巧燕和徐欣然一同往楼下走去,谁也不说话。
“我请你吃顿饭吧!”徐欣然忽然停下脚步,鼓足勇气看着赵巧燕说。
赵巧燕看着徐欣然心里忽然有些异样,点了点头。
夜色已经暗下来。矿山路一条小巷里,两旁各种小摊一字排开,连绵不绝,热气腾腾的包子摊上白雾缭绕,烧烤摊上一口口小锅咕咕的冒着热气,诱惑着人的味蕾,橘黄的路灯下氤氲的气息在空气中荡漾着,不少背着书包的学生大快朵颐,地上散落着一些白色塑料垃圾。
在一个塑料大棚支起的小饭摊上,两个人坐下来。两个人要了两碗牛肉面,热气腾腾的面上来,上面漂浮着几片牛肉丁,还有点儿辣椒油。
“你在哪儿上班?”徐欣然问。
“我在矿配电室工作。” 赵巧燕说。
“我还以为你上了大学呢?”
“大学……“赵巧燕抬起头,若有所思,眼圈泛红,好久没有说话。
“徐欣然你喝酒吗?”过了一会儿,赵巧燕忽然说。
“能喝点儿!”
两个人要了一小瓶半斤装白酒。赵巧燕给徐欣然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赵巧燕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你少喝点儿。”
“你不要小看我。”
赵巧燕又喝了一口,脸色有些泛红。
徐欣然怕赵巧燕喝多了,赶紧大口大口喝了几杯。
吃完饭,徐欣然送赵巧燕回家。走了一会儿,赵巧燕说:“你知道赵东文为啥每年都给我家送煤泥吗?”
徐欣然摇摇头。
“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一天夜里,赵东文跑到我家说井下的皮带机坏了,让我爸跟着他下井修理,没成想这一去就没有回来,妈妈受不了失去爸爸的痛苦,每日以泪洗面,精神恍惚,为了照顾精神受了刺激的妈妈,我放弃了上大学,我恨他,如果不是他,我家不会这么惨。”赵巧燕哽咽着说完,蹲在地上嘤嘤抽泣起来。
徐欣然一时不知所措,连忙安慰赵巧燕。
哭了一会儿,赵巧燕擦了擦眼泪说:“你喜欢我吗?”
徐欣然说:“哪敢有非分之想啊,那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你就像天上的月亮,我只有仰慕的份儿!”
噗嗤,赵巧燕笑了。
“你笑起来真好看。我暗恋你不是一天两天了,上高中时,有一次上晚自习,忽然停电了,教室里一片漆黑,同学们有些措手不及。慌乱中,我嘴碰到一个女同学脸,有着淡淡的芳香气息,好像电流击中一般,我忍不住轻轻亲了一下。这时候有的同学点着了蜡烛,我看见亲的是你,心里又激动又害怕,但你只是平静地看了我一眼。后来,我一直回忆那个晚上,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晚上。”徐欣然动情地说。
“想不到你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啊!”赵巧燕有些羞涩地说。
那天夜里,徐欣然送赵巧燕到家后,回到宿舍一夜辗转难眠。
第二天,赵巧燕来徐欣然宿舍里找他,他拿出写的诗让赵巧燕看。
赵巧燕看着看着,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落,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赵巧燕忽然搂住徐欣然,徐欣然感到呼吸有点儿急促,听到心怦怦跳。
我给你念一首诗吧!徐欣然说。
凌晨的矿山路上无行人
两只麻雀树梢上窃窃私语
他们幸福的样子让人妒忌
追逐着你的影子
选择来矿山生活
只是为了靠近你一点点
在同一片蓝天下开始新的一天
不知道你在矿山的哪间房里
但,早上你推开窗时
空气里肯定留有你温暖的气息
我驻足贪婪地嗅着每一滴空气
徐欣然念完自己的诗,眼角有些湿润。
“想不到还有你这么痴情的人!”赵巧燕泛着泪花说。
青年人的爱情闸门一旦打开就像泄了闸的洪水,来势汹涌。爱情也许来的太突然,徐欣然措手不及,一连几天他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兴奋之中。
一天,赵巧燕对徐欣然说:“我爸出事,赵东文有很大的责任,我只是想要个说法,但矿上只给了他一个处分。现在,赵东文风光得很,每年派人给我家送点儿煤泥,就想让我和我妈不记恨他,我做不到。”
“你想娶我吗?”
“我做梦都想。”
“那你就帮帮我,给我出口气,我就嫁给你!”赵巧燕咬牙切齿地说。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徐欣然忽然觉得血往上涌。
赵巧燕走后,徐欣然脑子里乱哄哄的。如何给赵巧燕出口气啊?赵东文对自己不错,替赵巧燕出气不是恩将仇报吗?徐欣然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几天后,徐欣然找到赵巧燕说:“我已经写了一封信,准备向局纪委反映赵东文违纪情况。”徐欣然把写好的信递给赵巧燕,信上列举了赵东文的两项“罪名”。第一,记“黑工”,给班长“大胡子”记工两个月;第二,给职工加工分,截留职工工资。
“我这样做也许不地道,毕竟截留职工工资,给“大胡子”记工也是无奈之举,但这样做毕竟是违反了企业规章制度。”徐欣然说。
“这封信我落款没有写名字,纪委一般不会太把匿名信当回事,这样的信要想让纪委重视……”徐欣然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了,看了一眼赵巧燕,忽然一口咬破右手食指,鲜血顺着手指尖悄悄流淌下来,滴落到信纸上。
“你干啥?”赵巧燕一把拉住徐欣然的手。
“这样做,是为了让局纪委重视啊!”徐欣然笑着说,赵巧燕扑到徐欣然怀里泪水簌簌落下来。
七
第二天,徐欣然把信寄给了局纪委。
信寄出去半个月了,没有一点儿动静。徐欣然每天惴惴不安,就在他和赵巧燕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希望时。一天,局纪委下来组织综一队干部职工从德能勤绩廉等几个方面对赵东文进行民主评议。
几天后,关于赵东文被停职、处分的消息就像插了翅膀一样在西山矿传得沸沸扬扬。
赵巧燕高兴地找徐欣然庆祝。徐欣然说:“正式文件还没有下来,赵东文受到处分,我这个临时办事员也干到头了,因为办事员作为经手人肯定有责任的。”
赵巧燕眼里含着泪花说:“我没想到会牵连你,我耽误了你的前程了!”
徐欣然心里一热,搂住赵巧燕说:“为了你,我什么也愿意,你就是我的前程!”
两天后,赵东文被停职处理的文件正式下发了,徐欣然从矿办公室取回文件,赵东文此时却还在井下抢救煤溜事故。
徐欣然坐在办公室看着文件,心里百味杂陈。这时八点班的送饭工满玉推开门说:“我肚子疼得厉害,拉肚子,估计下不成井了,你给找个人送饭吧!”
徐欣然木然地说:“那你去医院看看,我替你送饭。”
徐欣然背着饭包来到掌子面,巷道里职工们忙碌着,有的拖着大链,有的拿着铁锹清溜子里的煤。巷道里低洼的地方还有些积水,赵东文趴在地下,指挥几个职工正在接链条呢!
徐欣然招呼大家吃饭。
“队长你喝点儿水。”徐欣然把怀里揣着的保温杯递给赵东文。赵东文接过水杯,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药,倒了一把放在嘴里,喝了几口水。
赵东文问:“我的停职文件下来了吗?”徐欣然“嗯”了一声。
“这我就放心了,处理完事故就可以回家好好睡一觉了。”
赵东文没有了平日的颐指气使,看着赵东文胡子拉碴、满脸煤尘的脸,徐欣然忽然觉得有点儿心酸。
赵东文停职后,徐欣然作为队里的办事员被纪委叫去谈过几次话,徐欣然一五一十把情况报告了纪委。徐欣然也被停止了工作,回原岗位。
八
生活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宝根和几个职工都替徐欣然惋惜,失去了一个好岗位,也觉得赵东文挺冤枉。
不管别人说什么,徐欣然都是一笑了之,在井下每天拼命干活儿,因为只有沉重的劳动才能使他心里好受一点儿。
一天,区里的李书记通知徐欣然到他的办公室。“是不是匿名信的事啊!”徐欣然胡思乱想着敲开李书记的门。
李书记是研究生毕业分配来矿的,年轻有为。李书记热情招呼徐欣然坐下,递给徐欣然一份文件说:“这是矿上刚下的一个文件,公开招聘秘书,我看你文化水平可以,推荐了你,过几天准备考试。”
“你也抽空去医院看望一下你们队长!赵队长住院了,胃癌晚期。”李书记惋惜地接着说。
徐欣然一时觉得大脑一片空白,他恍恍惚惚走出了李书记的办公室,在路边站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几天后,徐欣然去矿劳资科报名。“我们招聘的范围是在岗管理人员,你是工人身份,不能报名。”劳资科科长油光满面,抽着烟说。
徐欣然沮丧地走出劳资科的大门,忽然想到应该去趟医院。
徐欣然买了些奶粉、水果去了医院。
病房里,赵东文脸色蜡黄躺在病床上,他老婆和女儿小雅愁云满面在病床前陪着。
“听说矿上招聘秘书呢,报名了吗?”赵东文躺在病床上笑着问徐欣然。
“他们要在册管理人员,我是工人身份不能报名。”徐欣然说。
“没关系,别灰心,以后还有机会!”赵东文说。
“队长,我对不起你。”
“傻孩子,是我连累了你才对!”
“那写匿名信的人……”徐欣然犹豫着说。
“我要感谢写那匿名信的人,要不是把我撤职了,我还能安心在医院养病?让我多活了几天,主要是举报我有点儿迟了,再早三个月举报我,我也不至于胃癌发展到晚期啊!”赵东文说完剧烈地咳嗽起来。
徐欣然哽咽着,泪水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几天后,李书记通知徐欣然参加矿招聘。“你们队长真是个好人,都病成那样了,矿领导去看他还不忘把你的情况给矿领导反映,矿上破格让你参加招聘。”李书记说。
天空飘着碎屑般的雪花,冬天来了。
徐欣然参加完考试,自信满满地走出考场,看见赵巧燕在考场门前等他。
赵巧燕说:“我错了。”
“也许,我们都错了。”徐欣然说。
两个人的眼泪悄无声息地滚落下来……
王永民: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现在山西省阳煤集团三矿从事政工工作,曾从事井下采煤工作近二十年,创作了大量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文章,其作品散见于省市报刊,多次在省市报刊征文中获奖。